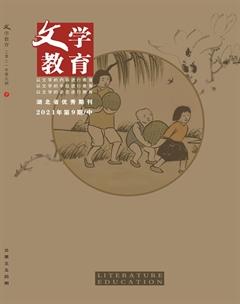周作人文學(xué)觀中的世代觀念及其啟示
張則哲
內(nèi)容摘要: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一書中將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歷程比作一道彎曲的河流,認(rèn)為它的變遷是“言志派”與“載道派”兩種潮流的不斷起伏。這種將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當(dāng)作是非此即彼的帶有世代主義觀念的文學(xué)史觀,同韋勒克在《文學(xué)理論》中提到的世代主義的文學(xué)史觀不謀而合。結(jié)合韋勒克對于世代主義的批評,從文學(xué)理論的角度出發(fā)認(rèn)識這種觀念,對于我們進(jìn)一步探討文學(xué)內(nèi)部的理論問題、文學(xué)批評的標(biāo)準(zhǔn)和認(rèn)識文學(xué)史仍有啟示意義。
關(guān)鍵詞:周作人 世代主義 文學(xué)理論 文學(xué)史
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是二十世紀(jì)三十年代周作人應(yīng)沈兼士之邀到輔仁大學(xué)演講稿,后經(jīng)鄧恭三整理成冊,是周作人一部有關(guān)文學(xué)的論文集。主要分析了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經(jīng)歷,提出了中國文學(xué)就是一條彎曲的河流,其發(fā)展不過是言志派與載道派兩派的不斷起伏。這樣一種文學(xué)發(fā)展的“循環(huán)論”,已經(jīng)涉及到了文學(xué)內(nèi)部的規(guī)律性探討和理論研究,包括文學(xué)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轉(zhuǎn)換,文學(xué)的價值的評價等等。這樣一種帶有世代觀念的文學(xué)史觀,正如韋勒克在《文學(xué)理論》中提到的“文學(xué)史中或多或少具有對立性質(zhì)的一批批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交替轉(zhuǎn)換現(xiàn)象,并且暗示我們這種交替轉(zhuǎn)換現(xiàn)象是沒有離開一般的文學(xué)原則的。”[1]這種現(xiàn)象是有相通之處的。通過對此種現(xiàn)象的分析,同時借鑒韋勒克對于文學(xué)上世代主義的批評,我們可以進(jìn)一步探討研究關(guān)于文學(xué)發(fā)展中的一般規(guī)律,以及文學(xué)批評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
一.周作人的文學(xué)史觀
周作人的《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既然是探討新文學(xué)的源流問題,那么就不能離開他對文學(xué)的本質(zhì)的界定。他說,文學(xué)的本質(zhì)是:“文學(xué)是用美妙的形式,將作者獨(dú)特的思想和感情傳達(dá)出來,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種東西。”[2]而韋勒克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具有“甜美”和“有用”兩個功能:即文學(xué)的快感是從“一種高級活動,無所希求的冥思默想中取得的快感。”[3]同時他也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具有有用性——“嚴(yán)肅性和教育意義”。據(jù)韋勒克提出的文學(xué)的兩大功能來看,周作人關(guān)于文學(xué)的觀念顯然是更偏重于文學(xué)帶給人“快感”的功能。同時他注意到了文學(xué)帶給人快感的復(fù)雜性。他說:“實(shí)際說來,愉快和痛苦之間,相去并不是很遠(yuǎn)的。在我們的皮膚作癢的時候,我們用手去搔那癢處,這時候是覺得愉快的,但用力稍過,便常將皮膚抓破便又不免覺得痛苦了。在文學(xué)方面,情形也正相同。”然而在文學(xué)的嚴(yán)肅性和教育意義這方面,周作人卻沒有給予應(yīng)有的重視。
從這一文學(xué)觀念出發(fā),周作人將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界定為“言志派”與“載道派”兩種潮流的起伏。所謂言志派,周作人認(rèn)為即是“人人都得自由講自己愿講的話,各派思想都能自由發(fā)展。”[4]而關(guān)于載道派,周作人認(rèn)為生出載道派的原因“是因為文學(xué)剛從宗教脫出之后,后來的勢力尚有一部分保存在文學(xué)之內(nèi),有些人以為單是言志未免太無聊,于是便主張以文學(xué)為工具,再借這工具將另外的更重要的東西——‘道表現(xiàn)出來。”言志派即是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的非功利性和無目的性,而載道派強(qiáng)調(diào)的是文學(xué)的功利性和目的性。周作人對兩派的區(qū)分除了從這兩派對待文學(xué)功能的態(tài)度的不同之外,還從兩種文學(xué)創(chuàng)作的方式上做了區(qū)分。“言志派的文學(xué),又可以換一名稱,叫做‘即興的文學(xué),載道派的文學(xué),也可以換一名稱叫做‘賦得的文學(xué)。”即認(rèn)為言志派的文學(xué)都是從自己的情感出發(fā)進(jìn)行文學(xué)創(chuàng)作,而載道派的文學(xué)則是受了他人的命題,出于他人而創(chuàng)作的。從這兩方面的特質(zhì)出發(fā),他認(rèn)為這兩派并非是地位相等的兩派,反而是代表了文學(xué)方面的興衰。他認(rèn)為載道派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是不如言志派文學(xué)的,故而他說:“古今來有名的文學(xué)作品,通是即興文學(xué)。”
在此基礎(chǔ)之上,他認(rèn)為“中國的文學(xué)在過去走的并不是一條直路,而是一道彎曲的河流,從甲處流到乙處,又從乙處流到甲處。遇到一次抵抗,其方向即起一次轉(zhuǎn)變。”甲處即他所說的言志派文學(xué),乙處即是他所說的載道派文學(xué),他認(rèn)為中國文學(xué)的發(fā)展無非是這兩種文學(xué)的反復(fù)、循環(huán)。并且他認(rèn)為這兩種文學(xué)的轉(zhuǎn)換是同政治的好壞密切相關(guān)的:“文學(xué)方面的興衰,總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著的。”在社會動蕩的時期,就會產(chǎn)生言志派的文學(xué)類型,而當(dāng)社會穩(wěn)定,思想統(tǒng)一的期間出現(xiàn)的則是載道派的文學(xué)類型。接著,將民國的文學(xué)運(yùn)動同明末的文學(xué)運(yùn)動關(guān)聯(lián)起來。在他看來,民國以來的幾次文學(xué)運(yùn)動,從根源上來講,是對明末文學(xué)潮流的一次復(fù)古,明末的文學(xué)運(yùn)動正是現(xiàn)在發(fā)生的文學(xué)運(yùn)動的來源,清代的載道派文學(xué)之后的民國時期的文學(xué)是屬于言志派文學(xué)。所以他提出:“胡適之的所謂‘八不主義,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謂‘獨(dú)抒性靈,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張的復(fù)活。”的論斷,主張明末的文學(xué)運(yùn)動同民國的文學(xué)運(yùn)動只存在時間上的距離,而不存在本質(zhì)上的差別。他認(rèn)為現(xiàn)在民國的文學(xué)革命運(yùn)動,是對清八股文和桐城派激起的一次反抗,這次反抗也“有相等的力量在內(nèi)”。而反抗的原因在周作人看來是因為清的載道派文學(xué),有著明顯的缺陷以及對文學(xué)性的壓抑。原因之一便是八股文和桐城派在形式上的保守性。八股文從文章的破題、承題、起講都有固定的要求,以及后面的八股,每兩股作為一段,此平彼仄,兩兩相對,限制頗多,并且要求有一定的格調(diào),這種形式上的要求,在周作人看來“消磨很多的時間,卻毫沒價值。”八股文和桐城派對文章內(nèi)容的拘束,也是激起反抗的另一原因。八股文固定了文章的題目自不必多言;而桐城派的文章,在身份定位上,他們不僅把自己定位為文學(xué)家,并且同時兼作了“道學(xué)家”的身份。他們的志愿是“學(xué)行繼程朱之后,文章在韓歐之間”,因而認(rèn)為文即是道,并且二者不可分離,對文學(xué)的內(nèi)容也做了明確的規(guī)定。總之是“作文章的人,處處都有限制,必須得模仿當(dāng)時圣賢說話的意思,又必須遵守形式方面的種種條規(guī)。”[5]所以他認(rèn)為民國的文學(xué)運(yùn)動之所以得以產(chǎn)生歸為兩個方面:明末的文學(xué)運(yùn)動是其來源,清代對桐城派和八股文激起的反抗。
二.文學(xué)的實(shí)際情況
周作人注意到了文學(xué)史上存在的審美標(biāo)準(zhǔn)相互轉(zhuǎn)換的現(xiàn)象,并將在不同審美標(biāo)準(zhǔn)下產(chǎn)生的文學(xué)簡單地劃分為“言志派”與“載道派”這樣看上去是相互對立的兩個文學(xué)流派,并且將民國時期的文學(xué)定義為言志派的文學(xué),而文學(xué)的實(shí)際情況,卻比周作人想象的要復(fù)雜得多。
周作人對文學(xué)從兩個方面界定了文學(xué)的本質(zhì)。首先,文學(xué)是形式+內(nèi)容的結(jié)合體,并且對形式和內(nèi)容做了限定,文學(xué)的形式是美妙的。同時,文學(xué)的內(nèi)容是作者獨(dú)特的思想和感情。周作人是通過形式內(nèi)容這樣二分法來區(qū)分文學(xué)的本質(zhì),這是一種簡單的二分法。這種方法會使我們注意到文學(xué)作品中形式和內(nèi)容這兩個層面。通過對文學(xué)作品的這兩個層面進(jìn)行分析,也會產(chǎn)生一定的效用,對我們理解一部文學(xué)作品有著一定的意義。但是忽略了對作品的整體性考察。韋勒克在《文學(xué)理論》中說:“一部文學(xué)作品,不是一件簡單的東西,而是交織著多層意義和關(guān)系的一個極其復(fù)雜的組合體。”[6]文學(xué)作品并非是形式和內(nèi)容的疊加。它涉及篇章結(jié)構(gòu)、個性表現(xiàn)、對語言媒介的領(lǐng)悟和采用、不求實(shí)用的目的以及虛構(gòu)性、傳播媒介等等各個方面。所以,文學(xué)是一個復(fù)雜的有機(jī)體。故韋勒克提出:“現(xiàn)代的藝術(shù)分析方法要求首先著眼于更加復(fù)雜的一些問題,如藝術(shù)品的存在方式、層次系統(tǒng)等。”[7]
由于這種二分法,周作人依據(jù)不同時期對待文學(xué)態(tài)度的不同將其劃分為言志派文學(xué)和載道派文學(xué)。而文學(xué)的審美性和社會性這兩種屬性實(shí)際上是一個有機(jī)統(tǒng)一的整體。韋勒克對文學(xué)的這兩種屬性的概括更加有代表性:“如果說詩是‘游戲,是直覺的樂趣,我們覺得抹殺了藝術(shù)家運(yùn)思和錘煉的苦心,也無視詩歌的嚴(yán)肅性和重要性;可是,如果說詩是‘勞動或‘技藝,又有侵犯詩的愉悅功能及康德所謂的‘無目的性之嫌。”[8]我們不能把載道派文學(xué)當(dāng)作是傳播圣人之道的工具,完全不帶給人審美上的快感;也不能將言志派文學(xué)單純的看作是作者言志傳情,而忽略作者在情感中的運(yùn)思跟冥想。并非同周作人所說文學(xué)只有感情沒有目的。人是社會性的,作家也是社會的一員,擁有特定的社會地位,他的作品也需要讀者,他的作品也需要受到社會的評價和認(rèn)可;“審美實(shí)踐不是基于一般社會實(shí)踐之上:甚至它們并不是一般社會實(shí)踐的一部分,而是另一類型的社會實(shí)踐,與其他形式的社會實(shí)踐緊密聯(lián)系在一起。”作家的社會性和審美實(shí)踐的社會性表明了文學(xué)的這樣一種立場:即文學(xué)絕不可能脫離社會而存在,文學(xué)中審美價值與其他各種價值并存的。
在文學(xué)史上,這種將某兩種流派,比如浪漫主義與現(xiàn)實(shí)主義,看作是相互對立現(xiàn)象并不少見。這種簡單的二分法,一直受到理論家們的關(guān)注。夏目漱石在《文學(xué)論》中這樣提到:“凡文學(xué)性之內(nèi)容形式均要求(f+F)。F者意味著焦點(diǎn)性印象及觀念,f者意味著與之相符之情緒。果真如此,則上述公式可顯示其印象乃至觀念兩方面,即認(rèn)識要素(F)與情緒(f)之結(jié)合。”[9]文學(xué)史上不同流派之間的差異,只存在這兩種要素結(jié)合程度的不同,而無本質(zhì)上的差異。周作人所舉的魏晉六朝時期的文章講究清峻,力倡通脫,是“言志”而非“載道”了。魏晉文章其中也包含著信奉禮教的部分。“魏晉時代,崇奉禮教的看來似乎很不錯,而實(shí)在是毀壞禮教,不信禮教的。表面上毀壞禮教者,實(shí)則倒是承認(rèn)禮教,太相信禮教。”[10]而載道派文學(xué)時期當(dāng)然也有不少的言志的佳作,兩漢的文賦、唐代的詩文等等,就并非全是載道的產(chǎn)物。言志派與載道派的文學(xué)也并非如周作人所說的那樣分明,因此不能籠統(tǒng)地將某一朝代當(dāng)作是言志派,某一朝代的文學(xué)當(dāng)作載道派。
三.世代主義的超越
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在給我們建立他自己的文學(xué)史發(fā)展模型以及他的文學(xué)循環(huán)發(fā)展觀中,鮮明地展示出了韋勒克所提到的帶有世代主義觀念的結(jié)論:“這種結(jié)論否認(rèn)了那種被當(dāng)作是屬于個人的‘趣味相對性的看法,但是,卻發(fā)現(xiàn)了文學(xué)史中的或多或少具有對立性質(zhì)的一批批審美標(biāo)準(zhǔn)的交替轉(zhuǎn)換現(xiàn)象(就像沃爾弗林所說的文藝復(fù)興和巴洛克兩種對立標(biāo)準(zhǔn)的情況一樣),并且暗示我們這種交替轉(zhuǎn)換現(xiàn)象是沒有離開一般審美原則的。”[11]同時提醒我們:“要超越這種見解是困難的,但卻是能夠做到的。”[12]我們已經(jīng)注意到周作人自身在文學(xué)的本質(zhì)與目的、文學(xué)的兩大要素、文學(xué)史上這種審美標(biāo)準(zhǔn)交替轉(zhuǎn)換現(xiàn)象認(rèn)識中的局限性。這促進(jìn)了我們的進(jìn)一步的思考,如何讓這種超越成為可能?
誠如韋勒克所言:“一方面,我們不需要根據(jù)過去時代的批評家們所鼓吹的論點(diǎn)而把我們對古典作品的欣賞局限起來。我們可以不承認(rèn)過去時代的文學(xué)批評能公正地對待它自己時代的有創(chuàng)造性的作品或真能公正地對待它自己的審美經(jīng)驗。”一時代固然有屬于自己時代的文學(xué)批評的標(biāo)準(zhǔn),但在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時代,現(xiàn)代的技術(shù)、基于新技術(shù)上的平臺、傳播媒介已經(jīng)日新月異的今天,文學(xué)的構(gòu)成更趨復(fù)雜多樣,我們應(yīng)該避免文學(xué)上簡單的二分法。例如將文學(xué)作品從內(nèi)部分為形式和內(nèi)容,僅僅注意文學(xué)作品的表現(xiàn)手法、修辭、格律方面的形式而忽略內(nèi)容上的結(jié)構(gòu)因素,將形式單獨(dú)分離出來,而忽視形式對表現(xiàn)情節(jié)、性格以及主題等的重要意義。又或簡單地將文學(xué)流派分為現(xiàn)實(shí)的和浪漫的,而需要更加重視文學(xué)作品內(nèi)部的各種藝術(shù)因素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技術(shù)的發(fā)展導(dǎo)致文學(xué)內(nèi)部也產(chǎn)生了新的要素。例如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的產(chǎn)生帶來的文學(xué)文本的變動、作家與讀者的互動關(guān)系更加深入,作家與讀者的身份可以發(fā)生相互轉(zhuǎn)換、文學(xué)作品的影視化要素等等。這些變化使得文學(xué)作品的包容性更加寬泛、復(fù)雜性不斷加深,所以我們在判斷一部藝術(shù)作品是否成熟,我們要公正地審視時代給文學(xué)帶來的新的因子。文學(xué)作品與經(jīng)驗之間的關(guān)系也并非是一一對應(yīng)的關(guān)系,我們要結(jié)合自己的審美情感,把作家自己的經(jīng)驗世界同我們自己所感受到的經(jīng)驗世界相比較,尋找自己的審美經(jīng)驗,而無需將自己對一部作品的評價局限在前人對他的評價之上。
另外,我們也可以斷定,通過建立這樣一種廣泛接受新的時代因素的文學(xué)批評的標(biāo)準(zhǔn),可以避免陷入世代主義中的非此即彼的選擇上的困境。我們不必像周作人那樣肯定言志派時期的作品就否定載道派時期的作品,也不必將文學(xué)史劃為類似自然主義、浪漫主義這樣相互對立的時代并以此為依據(jù)率先對作者形成刻板的印象。而應(yīng)像夏目漱石所提到的“不應(yīng)該以基于某個時代、某一個人的特性來區(qū)分作品,而是應(yīng)該以適用于古今東西的,離開作家與時代的,僅在作品上表現(xiàn)出來的特性去區(qū)分作品。”
當(dāng)然,通過《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我們也不必把周作人降為一個否認(rèn)有審美規(guī)范存在的世代主義者,事實(shí)上他也并非主張所謂文學(xué)內(nèi)部存在完全固定的等級。雖然他認(rèn)為清代文學(xué)屬于載道派的文學(xué),但在《源流》的附錄一中,卻給予了八股文這樣一個很高的評價:“它永遠(yuǎn)是中國文學(xué)——不,簡直可以大膽一點(diǎn)說中國文化的結(jié)晶,無論現(xiàn)在有沒有人承認(rèn)這個事實(shí),這總是不可遮掩的明白的事實(shí)。”[13]可見周作人雖然在文學(xué)史觀中帶有世代主義的觀念,但這也是他通過一種對比的方法,將民國的文學(xué)運(yùn)動同以往的文學(xué)運(yùn)動進(jìn)行類比,發(fā)現(xiàn)當(dāng)時存在著的文學(xué)運(yùn)動的一些特點(diǎn),并且告訴我們這種特點(diǎn)是符合中國文學(xué)的一貫的傳統(tǒng)的,是可以通過比較發(fā)現(xiàn)的。這也是周作人《中國新文學(xué)源流》的獨(dú)特貢獻(xiàn)。
注 釋
[1][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247頁.
[2]周作人:《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第2頁.
[3][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18頁.
[4]周作人:《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第18頁.
[5]周作人:《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第33頁.
[6][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15頁.
[7][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15頁.
[8][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17頁.
[9][日]柄谷行人:《日本現(xiàn)代文學(xué)的起源》,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第2頁.
[10]魯迅:《魯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535頁.
[11][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247頁.
[12][美]韋勒克、沃倫:《文學(xué)理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新修訂版,第247頁.
[13]周作人:《中國新文學(xué)的源流》,南京:江蘇文藝出版社,第64頁.
(作者單位:中南民族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