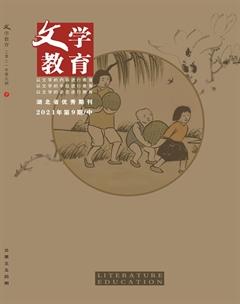登上黃龍寨

高山文學筆會的第一天下午,車從龍坪的南頂草原蜿蜒而下,行駛數里,忽然拐進右側一條剛修不久的土石路。車身如搖曳的小舟,忽左忽右,甚是顛簸。一路烏溜溜柏油路帶來那種舒適感覺,蕩然無存,車輪壓在石土路上發出咯嘣咯嘣的脆響,我們也一陣手慌腳亂。坐在我身邊的郝姐,一手緊抓著前排座椅背靠,另一手緊抱著睡熟的小楊楊,他才七八個月大,還好,小楊楊好像什么事兒都沒有發生一樣,微微閉著雙眼,小臉蛋紅紅的。
車慢如牛,又行里許,勉強停在一山坳處,眾人下車,一陣濃濃的蒿香迎面灌進鼻子,山野氣息驟濃,人也頓感清新。我們的到來,驚起了一片竹林里幾只長尾紅嘴藍鵲,躍上泡桐樹枝,嘰嘰喳喳,不亦樂乎。
我們步行,沿土路從山坳左側拐入山脊右側,突然前面幾人,正圍繞著路邊一種開著紫花植物討論起來,一直鐘愛草木的作家周才彬告訴我們,這種植物叫薊,文聯張太學隨即吟出“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的詩句。隨行的兩美女伊夢和孟娟,蹲下身子,手機對著在微風中輕顫的薊花,尋找最佳的拍攝角度。
峰回路轉,在前面的兩座山坳處,竟然有一個小水坑,水不深,也不大,水甚至有些濁,坑里也漂滿了青苔、樹葉,坑邊上也長滿了雜草。雖然只是毫不起眼的小水坑,我們也還是由衷地驚嘆大自然的神奇,因為,作為“襄陽屋脊”的龍坪,我們一路走來,很少見到山泉,水溝之類的。水,在這里絕對意味著靈氣,黃龍寨選址在此,顯然也是因為這里有水。
水坑對面的樹林里,一條用石條壘砌不久的石階掩映其中,我們拾階而上,漸行漸陡,有時不得不抓緊兩旁小樹攀爬。《今古傳奇》總編輯何大猷一直走在隊伍最前面,行至一半,他坐于石階上小歇。我問,何總編,你經常爬山鍛煉嗎?他倒坦誠,回答道,沒有。見此情景,抱著小楊楊的郝姐和幾位體力不支,無奈放棄了登寨,選擇原地休息。
這時,我不由想起王安石在《游褒禪山記》里面的經典句子:“起夫夷以近,則游者眾;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其大意如此:平坦距離近的地方,前來游覽的人一般都多;危險而又遠的地方,前來游覽的一般都少。但是世上奇妙雄偉、非同尋常的景觀,常常在那險惡、僻遠、人跡罕至的地方,所以,不是有意志的人是不能到達的。有了志氣,也不盲從別人而停止,但體力不足的,也不一定能到達……登黃龍寨也是如此。
石階直至山頂,寨門豁然而立,門墩右側立一尺余高的柏木雕像,僅有面、目、鼻、口,殘漆尚存,盡顯肅然,隨行介紹者告訴我們,寨里以前供奉著楊泗將軍。走在前面周才彬見雕像,雙手合十,滿臉虔誠,連躬三下。雖然不太明白深意,但心里揣摩著,或許是因見廟就進見佛就拜的緣由吧,我也跟隨三拜。
跨過磨得锃光瓦亮的寨門石門檻,寨內的石徑在草叢中若隱若現,沒行幾步,石徑在蕪雜中便是成了殘斷的野徑。我們沿寨墻左側向前,腳下的碎石板,不時發出咯當之聲。左側的半人高的寨墻,均為當地板石壘砌,重量從幾斤到百余斤,如今滄桑斑駁的石寨墻在日曬雨淋、歲月洗禮下,或墻傾石倒、或搖搖欲墜,偶爾,幾根從寨墻石縫里探出頭的嫩草、樹苗向陽而生,迎風而舞。
石路兩邊長滿了各種植物,空氣中彌漫著不同的花香,與樹葉、青草的味道混合在一起的芬芳,讓人神清氣爽。一棵小碗粗的野核桃樹被相互纏繞的藤蔓再次纏繞,翠綠的核桃樹葉下擁簇著七八個圓赳赳的淡綠小腦袋,活像一群圍在井臺上望下瞅的孩子。十余間依山而砌的房子,椽角檁條也早已沒有了蛛絲馬跡,只剩下幾處依然屹立的石墻山尖,和安置拱木的洞孔,倒成了蜘蛛,螞蟻之類擋風遮雨的安樂窩。寨內也早已被那些知名的與不知名的花草、樹木肆意地蔓延開來,你不讓我,我不讓你,幾乎都要拼命地把這里湮沒了,霸占了。
扒開雜草和藤蔓,從一處只能一人可以通過的豁口而下,發現下面又一依山而修的石寨,與上面石寨構成一個整體防御體系。想起孟子在《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中有言:“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而黃龍寨上面是主寨,也謂城,下面是圍在主寨的另一道防線,也稱之為郭。郭面積較大,兩排石房緊挨,近二十余間,中間留一甬道近三尺,也早已草木蔥郁,藤蔓叢生,墻寨高近兩丈多,灰褐斑駁,石縫里長滿青苔、石癬。
順著極不規則的石階而下,見一拱式石門,高近六尺,寬三尺有余,拱門兩側各有圓洞,以固閂寨門,抵御外犯。頭頂兩側分別有七塊長石條構成的拱弧,石條之間也已裂開,可入手指。
出寨門丈來遠,便是懸崖陡坡,樹林密集,雖有一羊腸小道,我們還是選擇了回轉身。此時,才發現寨門之上嵌有一石匾,摳緊寨門石縫攀上,試圖靠近看清碑文,可惜因為年代久遠,石匾上布滿了灰褐色石斑,只能依稀辨得永垂千古四字,在石匾上圓形剔地雕刻,為雙鉤空心字。石匾左部分殘缺,碑刻右側刻有“善首李仕珍造,大清嘉慶六年仲夏立”。出我的意料的是,沒見黃龍寨三個字。后來才得知,黃龍寨因附近有黃龍洞而得名。
我們原路返回,從剛進時的寨門右側而上,進入內寨,即第三層防御核心區域。內寨位于整個山寨制高點,面積不大,只有兩間大石房,房間呈狹長狀,周圍數間房屋環置內寨外側,呈眾星攢月狀。內寨墻殘缺不堪,亂石遍地皆是,曾經堆碼齊整的寨石如今竟也被風雨漸漸涂上一層滄桑。猛然間,穿著五彩繽紛時裝的美女作家,從斷石殘墻殘之后翩然閃出,唇紅齒白,恰如躲貓態,被攝影師傅正國逮個正著,拍下了一連串穿越劇般的艷照。作家們都說,這處古寨廢墟留下了歷史的背影,具有一種難以言狀的荒蕪之美。他們爭先恐后地在這里拍照,與古跡合影,和歷史對話。曉蘇、鄭因、馬南、習福等,都在這斷垣殘壁處留下了蠻荒而時尚的影像。
登上寨頂,我們才發現,整個黃龍寨呈圓型,依山就勢,立于危崖,曾經的望樓、跺口、射擊孔、碉堡,雖都已不復存在,但又依稀可見。靜坐于寨頂,視野空闊,環顧四周,遠眺群山黛綠,眼前全是大山的氣魄,巖、崖、坡、嶺、澗、溝,在夏日余暉下,與黃龍寨融為一體,景色美到極致。在光與影中,山的翠綠與寨的灰褐交織成滿眼的斑駁。俯視腳下,整個黃龍寨,屋頂藤木覆蓋,房間野草叢生,石階布滿青苔,寨墻黯淡斑駁,給人無盡的滄桑感。
龍坪鎮黨委書記張東林一直陪同作家們爬到古寨之巔,沿路給大家充當講解員。他說,鎮上特意保留了黃龍寨這片廢墟,沒有重建,也沒有修繕,更沒有進行現代包裝,目的就在于尊重歷史,讓人們能通過自己的眼睛和想象,去發現歷史的原貌與本相,同時看到社會的變遷與時代的進步。聽了張書記的解說,作家們不由對這位地方領導刮目相看,都說他有思想,有膽識,有遠見,一個個都朝他投去欽佩的目光。
今天,我們登上黃龍寨,雖然看不到昔日的刀光劍影,也聽不見曾經的鼓角轟鳴,但可以遙想到,古人當初在此危險之地壘石建寨,也屬無奈之舉,因為,生逢亂世,匪患連連,他們不得不筑寨抵御。而現在,我們登黃龍寨,走荊山古道,聽鳥語蟲鳴,聞花香草芳,別有一番感觸在心頭。
張道虎,青年作家,現居湖北保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