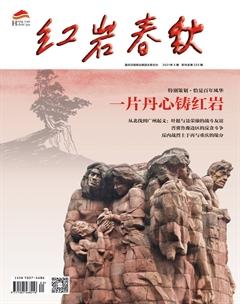紅巖精神與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烈士的關系
劉志平
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英烈以及以他們為代表的川東、川康地下黨人,是否是紅巖精神的實踐主體,學術界認識分歧、社會上認識模糊。
但查閱檔案,我們看到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的英烈中很大部分經歷了抗日戰爭斗爭的洗禮,其本身就是南方局領導下的川東、川康黨組織共產黨人;而1946年及以后入黨的這部分烈士,是在前一批共產黨人的教育和熏陶下成長起來的,是紅巖精神的繼承人。烈士們在獄中的斗爭,正體現了紅巖精神“崇高的思想境界,堅定的理想信念,巨大的人格力量,浩然的革命正氣”和“善處逆境、臨難不茍”的英雄氣概。因此,他們都是紅巖精神的實踐者。
南方局領導所轄省區黨組織共同完成了中央賦予的重大使命
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賦予南方局的使命,包括三個方面:1.代表中共中央直接同國民黨當局進行談判、交涉,維系國共合作;2.由董必武、凱豐、吳玉章組成重慶黨報委員會,出版發行《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作為中共中央在國統區的喉舌和代言人,宣傳黨的方針政策;3.以周恩來為書記的南方局代表中共中央領導南方國統區和部分淪陷區黨的工作。
代表中共中央直接與國民黨當局協商、談判,主要是周恩來、董必武、葉劍英等在南方局領導層面的革命實踐。鞏固和擴大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群眾工作、文化工作、軍事工作、黨的建設等,則是由南方局及其領導下的十省區各級黨組織共同完成的。
在黨的建設方面,1938年南方各省黨的組織恢復和重建以后,根據黨的任務和國共兩黨關系的變化,各省區在南方局領導下貫徹執行六屆六中全會精神,進一步調整、健全和加強省、特委領導機構,繼續發展黨的組織。1939年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后,各省區黨組織貫徹執行“蔭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十六字方針和“三勤”“三化”要求,劃小領導機構、建立平行組織、實行單線聯系,深入社會,擴大群眾基礎。其間,盡管皖南事變、南委事件和桂林七九事件對廣東、廣西、江西黨組織造成了嚴重破壞,但廣大共產黨人仍然英勇奮斗、扎根社會。為保衛黨的組織,謝育才、蘇蔓等省級領導干部,或忍辱負重,堅持斗爭,或寧死不屈,壯烈犧牲。到抗戰勝利,南方十省區除江西以外,省一級組織大都保存下來,南方局所轄省區共產黨員達10余萬人。
在群眾工作方面,根據南方局和各省區地下黨組織工作任務分工,“上層的公開的統戰工作由南方局同志出面做。各省、區主要側重秘密地做中下層統戰工作和群眾工作”。群眾工作是各省區地下黨組織的主要任務。尤其是1939年國共關系逆轉以后,南方各省區黨組織把貫徹執行國統區十六字方針和“三勤”“三化”要求,變成深入社會,團結、影響和組織群眾的過程,開創了黨在國統區群眾工作的新途徑。到1944年,黨在國統區的組織和活動逐漸復蘇,成都、重慶、武漢、西安、長沙、云南、湖南等地,先后成立了“民青”“新青”“新聯”“工盟”等黨的外圍組織。以云南“民青”為例,到云南解放時,僅云南一省,民青盟員就達5000多人。整個解放戰爭時期,各地民青盟員在城市學生運動中發揮了核心骨干作用,留在云南的大批民青盟員還參加了農村武裝斗爭,成為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縱隊和游擊根據地的骨干。
在統戰工作方面,各省區黨組織積極貫徹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配合南方局開展對國民黨左派、中間黨派、地方實力派、進步文化人士、民族資產階級、宗教界人士、少數民族、港澳和海外華僑以及國際人士的統戰工作。例如1941年3月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成立后,為宣傳民盟的政治主張,爭取社會輿論同情與支持,也由于國民黨對中間黨派的打壓,民盟決定在香港創辦機關報。對此,周恩來先后于7月1日和7月24日兩次致電中共中央駐香港負責人廖承志,指示予以支持。廖承志派《華商報》社長范長江經常與梁漱溟聯系,給予包括經費在內的多方面支持。1941年9月18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機關報《光明報》正式出版。10月10日,《光明報》發表啟事,宣告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業已在重慶成立,公布了同盟的綱領和宣言。在對川、滇、粵、桂等地的地方實力派的統戰工作中,相關省區黨組織也積極予以配合和幫助。
在文化工作方面,南方局領導各省區市黨組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知識分子,以重慶、桂林、昆明、香港等城市為抗戰文化中心,“在國民黨統治區建立了一支自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規模最為宏大的文化統一戰線”。黨組織在孤島上海、廣東曲江、港澳和湖南等地開展抗戰進步文化活動,在廣西、成都、昆明開辟和建立文化工作陣地,推動各種民間抗戰進步文化團體成立,并派出黨員進入地方實力派和國民黨主持的文化團體,團結其中進步文化人士共同開展活動。作為黨在國統區的喉舌和代言人,《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除在重慶設立總部外,在廣州、長沙、成都、昆明、桂林等地都設有發行部或分銷處。由我黨主導的《救亡日報》遠銷湘、粵、贛、云、貴、川,乃至香港、南洋一帶。
在軍事工作方面,湘、桂、滇、黔、閩粵贛邊等地抗日武裝是在南方局領導下,由相關省區組建和發展壯大起來的,不僅為抗戰勝利作出貢獻,也為解放戰爭增添了武裝力量。八路軍重慶辦事處、桂林辦事處、貴陽交通站、香港辦事處、韶關辦事處、駐湘通訊處、衡陽辦事處,也分布在所轄區域相關省區。
南方局成立以后,先后發生了1940年鄂西事件、成都搶米事件,1941年皖南事變,1942年南委事件和桂林七九事件。鄂西事件中被捕的何功偉,先后任中共湖北省工委農委委員、中共鄂南特委書記等職,1941年11月17日在湖北恩施犧牲;成都搶米事件中被捕犧牲的羅世文是川康特委書記、車耀先是川康特委軍委委員;南委事件中被捕并犧牲在獄中的張文彬是南委副書記,李大林是粵北省委書記,廖承志為八路軍香港辦事處主任,越獄向南委報警的謝育才是江西省委書記;桂林七九事件中犧牲的蘇蔓是廣西省工委副書記、羅文坤是桂林市委書記兼廣西省工委婦女委員會主任、張海萍是南委駐廣西交通員……他們都是南方局領導下各省區黨組織的負責人和重要領導干部。
1940年冬至1941年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我黨疏散大批愛國民主人士、進步文化人士到香港、新加坡一帶。這些人到香港后,黨中央和南方局即指示香港辦事處,團結在港文化人士,利用香港的特殊環境,開展抗日愛國民主宣傳工作,爭取海外廣大僑胞的支持和同情。同時,南方局派張友漁、范長江、夏衍、胡繩等一批黨內文化骨干前往香港協助廖承志工作。
1941年12月25日,日本占領香港,大肆搜捕抗日人士。日軍進攻港九當天,中央急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等,要多方設法保護相關人士撤離。在廖承志、連貫、劉少文、林萍、張文彬及香港辦事處、南委、廣東黨組織和東江游擊隊的精心組織安排下,800多名民主人士和文化人士,2000多名回國參加抗戰的華僑青年,滯留香港的國民黨官員及其家屬,百余名滯留香港英軍官兵及美、印、荷、比等國僑民脫離虎口。這次行動,營救人數眾多,足跡遍及11個省區,行程萬里以上,各級地方黨組織以及武裝部隊、統戰組織都動員了起來,被譽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文化搶救工程”。除營救行動本身以外,所有的營救經費均由南方局提供。
可見,中央賦予南方局的重大使命是在南方局領導下,由南方十多個省區各級黨組織共同完成。這其中,包括川東、川康黨組織。
解放戰爭時期的川東地下黨組織是南方局時期川東黨組織的繼續和發展
解放戰爭時期的川東、川康地區黨組織,是自抗戰以來中共四川省黨組織恢復重建后的繼續和發展。
以川東地下黨組織為例。1938年1月,中共四川省工委恢復重建。此時,四川省地方黨組織隸屬長江局領導。1938年11月下旬,為貫徹執行黨在國統區的工作方針,長江局決定撤銷四川省工委,在成都、重慶分別成立川西特委(后改為川康特委)、川東特委,羅世文任川康特委書記,廖志高任川東特委書記。
1939年1月南方局成立后,川康特委和川東特委受南方局領導。川東特委兼重慶市委,繼續發展黨員,到1939年10月,有黨員3600多名。1940年1月,南方局決定川東特委不再兼重慶市委,成立由川東特委領導的新一屆重慶市委。
皖南事變發生后,重慶黨組織迅速收縮,市委下屬各區委逐步撤銷。同時,南方局決定川東、川康地區黨組織進一步劃小領導機關的工作區域,從川康特委所轄區域劃出兩塊,分別成立川南特委和川北特委。1942年初,市委領導成員先后全部調離,川東特委改組重慶市委,王璞任書記,彭詠梧、何文逵為委員。1943年9月,廖志高調回南方局,川東特委撤銷,上川東特委和下川東特委成立,直屬南方局領導。
1946年3月,南方局為加強重慶的工作,成立了新一屆重慶市委,王璞任書記,劉國定任副書記,彭詠梧、何文逵、駱安靖為委員。市委的工作重點是,清理和恢復各地失散的組織關系,著手發展新黨員,逐步恢復和建立各級黨組織。4月,公開的中共四川省委成立,吳玉章任書記,領導云貴川康四省工作。重慶市委由四川省委領導。5月,南方局東遷南京改稱南京局。南京局委員、組織部長錢瑛負責領導中共四川省委的工作。
1947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被迫撤回延安,重慶市委與上級的聯系中斷。4月,市委派劉國定赴上海,與錢瑛取得聯系。錢瑛指示由重慶市委書記王璞負責清理川東各地黨組織。5月,中共中央上海分局改為上海局,錢瑛為委員,負責領導云貴川康等省以及北平(南系)的工作。
9月,王璞到上海向錢瑛匯報工作。10月,根據錢瑛指示,中共川東特別區臨時工作委員會(簡稱川東臨委)成立,王璞任書記。同時,重慶市委改組為重慶市工委,領導重慶市區、江北縣、北碚區以及貴州思南部分地區的黨組織。
這一時期,根據上海局放手開展工作的指示,川東地區黨組織得到發展,形成了比較完整的組織系統。許多在抗日戰爭時期失掉關系的黨員與黨組織重新取得聯系,大批在民主運動中涌現出的積極分子加入中國共產黨,黨員人數成倍增加。這是繼大革命時期和抗日戰爭初期之后,川東和重慶地區黨組織的第三次大發展。
1948年4月,重慶市工委機關報《挺進報》暴露,工委主要負責人被捕后叛變,重慶市和川東地區黨組織連續遭到重大破壞,所屬黨組織大部分解體。
從上述中川東地下黨組織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解放戰爭時期,川東地下黨組織不是突然出現的另一個組織,而是南方局時期川東黨組織的繼續和發展。其中,廖志高于1940年任南方局委員,楊述、榮高棠、許立群先后任南方局青委書記或青委成員,林蒙、李莫止、王致中等曾是南方局工作人員。“表一1937年10月至1949年11月市級黨組織領導機構成員名錄”中,重慶市委領導人都是抗戰時期在南方局直接領導下的川東地下黨人(叛徒除外),彭詠梧、王璞在上下川東武裝起義中犧牲,許建業、胡其芬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
由于南方局駐地重慶,川東黨組織直接在南方局領導下工作,所受教育和影響比其他省區市更多。
廖志高在《抗日戰爭時期在南方局直接領導下重建、發展、鞏固川東地下黨的主要情況(1937年12月至1943年9月)》一文中記敘:“四川黨是中央派我們去重新建立的。先后在中央和長江局(很短時間,不到半年)、南方局的領導下,特別是南方局成立以后,在周恩來同志的長期親自領導下,堅決貫徹執行了中央的正確路線、方針、政策,發展和保存了一批革命力量,取得了重大成績……恩來同志和孔原同志對我們幫助很大,所有在四川堅持了我黨地下斗爭的同志,對配合黨擴大解放區的斗爭是做了一定貢獻的。”川東黨組織重建以后,“為了堅決貫徹中央關于四川黨一定要建立成秘密的黨、警惕國民黨突然叛變的指示……我們一邊大量發展黨員,一邊及時地進行教育。”“我們在重慶,對新黨員的教育有個有利條件,就是先是長江局后是南方局駐在地重慶,也辦有訓練班,幫助我們訓練了一些同志。”廖志高回憶,從1939年南方局成立至他調離川東特委,南方局每年都要檢查川東特委的工作,并給予指示。
可見,川東地區黨組織是南方局時期川東黨組織的繼續和發展,川東地下黨的共產黨人也是在南方局直接教育培養下成長起來的。
檔案《犧牲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和息烽監獄的烈士簡歷、名單》分析
根據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所藏檔案《犧牲在重慶白公館渣滓洞和息烽監獄的烈士簡歷、名單》記載:
第一,檔案記載烈士共297名,其中黨員171人,革命志士126人,黨員占總數的57.57%;
第二,171名黨員中,1925年至1945年入黨的有85名,占全部犧牲烈士總數的28.6%;
第三,組織關系屬于南方局的7人,川東、川康黨組織76人,江蘇1人,湖北1人;
第四,1 9 4 6年入黨的有6 1人,占全部犧牲烈士總數20.54%。未標記入黨時間的有25人,占總數的8.42%。
從檔案記載可以看出:85名1925年至1945年入黨的烈士及沒有入黨時間記錄的部分革命英烈都經歷了大革命、土地革命和抗戰時期的革命實踐;他們都隸屬于南方局領導下川東、川康各級黨組織,當中甚至有南方局直接領導的同志,如張露萍電臺小組7人,南方局領導下從事學運和統戰工作的張孟晉;這85名烈士中有部分從事秘密交通工作,據廖志高回憶,林蒙曾為南方局領導同志建立秘密撤退站。
據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中國共產黨四川省組織史資料(1921—1949)》記載,當時南方局與川康、川東特委在干部使用上有交叉。以川東黨組織為例,廖志高1938年12月至1943年3月任川東特委(后為上川東特委)書記;楊述1938年12月至1939年5月任川東特委青委書記;榮高棠1939年9月至1941年1月繼任川東特委青委書記。川東特委領導下的市一級黨組織中,李莫止、羅清、陳野蘋、李亞群、張黎群、王致中等都先后在南方局任職或工作過。
另外,南方局黨史資料征集小組青年組撰寫的《南方局領導下的青年工作(1939.1—1947.2)》中寫道:“南方局青委在重慶地區還直接聯系了一些基層組織,迄止1939年底,沙磁區建立了中大、重大、煉鋼廠、煉油廠等十六個支部,約有黨員一百五十人。北碚特區以復旦大學力量為最強,約有黨員五六十人。與南方局青委有聯系的還有江津白沙的女師學院、重慶女師、樂山武大、宜賓同濟大學、三臺東北大學以及遵義等地的大、中學校。”例如,1949年11月28日犧牲在重慶大坪的王樸,1938年進入復旦大學新聞系學習,曾在南方局青年組張黎群、周力行等領導下工作。在復旦大學期間,王樸積極參加南方局青委領導的《中國學生導報》社的活動,被選為報社財經委員會主任委員,194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文章還寫道:“南方局青委從1939年4月開始,接連辦了幾期短期的黨員干部訓練班。參加學習的都是入黨不久的青年黨員。”
為適應國共關系逆轉的新形勢,南方局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培訓,舉辦了許多培訓班,川東黨組織許多共產黨人接受了培訓。如時任省萬師總支書記的彭詠梧,由川東特委萬縣中心縣委送至南方局黨員培訓班培訓,學習結束后,任川東特委云陽縣委書記,后調重慶市委任第一委員。又如南方局委員、川東特委書記廖志高到萬縣龍駒壩檢查農村建黨工作,為龍駒區委黨員干部培訓班講課。
綜上所述,由于南方局駐地重慶,川東地下黨組織深受南方局教育培養,犧牲在渣滓洞、白公館的革命英烈及其所代表的抗戰以來在南方局領導下的川東、川康地區共產黨人,本身就是南方局領導下革命實踐的親歷者,他們就是紅巖精神的直接實踐者;1946年后入黨的川東地下黨共產黨人深受前輩的教育和影響,是紅巖精神的繼承者和弘揚者,他們同樣是紅巖精神的實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