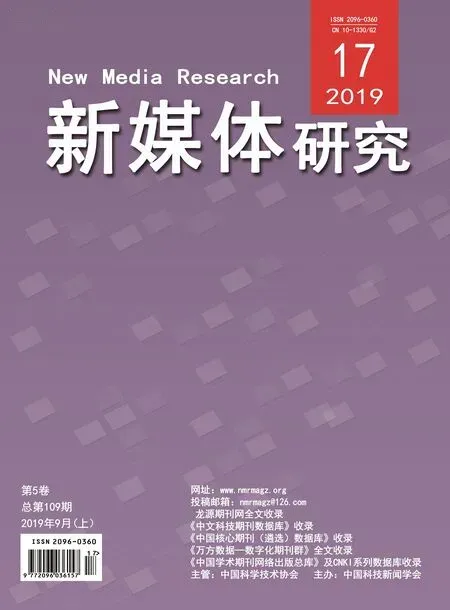海德格爾技術批判視域下的當代思考
李越
摘 要 當代社會是一個由技術所引領的社會,海德格爾將它描述為“形而上學長期遺忘存在過程的最終完成”。文章結合海德格爾的論述,反思我們當今由手機為媒介,由抖音、朋友圈、微博所引領的時代。在“挑戰”這種去蔽模式的支配下,人的生活顯得被動與不知所措,由此產生的焦慮在我們現今顯得更為明顯。不會有一個海德格爾所描述的無中生有的神突然出來拯救我們的世界,能拯救人的,或許只能是自律。
關鍵詞 海德格爾;挑戰;焦慮;自律
中圖分類號 G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2096-0360(2021)17-0093-05
最具當代意義的哲學家,反思現代技術的先行者海德格爾對于現代技術做出過深刻的反思。經過對西方形而上學哲學史的結構和對當今人類生活狀況的洞察,海德格爾得出了他的結論——“哲學-科學-技術-工業-商業體系已經獲得歷史性展開和全球性完成,而人(今天是全人類)已經落入了技術圈套之中”[ 1 ]。
海德格爾看到了技術無所不在的支配性和控制性力量,認為“技術已經成為現代文明最核心的驅動力”[ 1 ],另外,“人類已經從通過技術加工自然進展到通過技術加工人類自身,也即開始加工人類的身體自然了”[ 1 ]。在海德格爾看來,虛無主義危機是整個現代文明作為技術時代的危機。海德格爾屬于未來,也屬于現在,在我們當下這個由手機引領,由抖音、朋友圈、微博所主導的時代下,海德格爾對于現代技術的反思是一條線,牽引著我們思考屬于我們時代的問題。
1 “挑戰”,一種從解蔽到無蔽的占有
海德格爾反對純粹人和世界保持對象化關系的二分,強調天人合一。他對現代技術的反思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對技術的批判,這種反思旨在揭示我們與技術的本質關系。他特別從存在論的意義上來理解技術,認為“現代技術也是一種揭示或去蔽”[ 2 ]。他指出,“支配著現代技術的規則是挑戰。挑戰就是向自然提出蠻橫的要求,要求自然提供本身能被開采和貯藏的能量。挑戰使得農業成了機械化的食品工業。人們設置空氣以讓它交出氮材料,為礦石而設置土地,為鈾之類的材料而設置礦石,為原子能而設置鈾,而原子能則可以為毀滅或利用的目的而被釋放出來”[2]。而“產生”呢?“產生”是一種自然的生發,是“播下種子而把它們交付給自然的生長力”[ 2 ],是一種在人與自然的豐滿本質中遨游的狀態。
“在現代社會里,人通過從事技術而參與作為一種解蔽方式的安置。由此他進入一種無蔽。這種無蔽不是人的單純制品;相反,它占用了人,人只有被它占用才是人。人只有對它敞開,傾聽它的聲音,才能看到已進入它的領域”[ 2 ]。就像我們今天在任何時間任何公共場合都可以看到的現象一樣,幾乎所有人都緊盯著自己的手機,不管有事還是沒事。刷抖音,翻朋友圈,處理事務或者閱讀,無論做什么,每一種手機網絡上的東西都對人們充滿了誘惑,沒有人能置身事外。產生在無聲中滋潤人,中國古代的吸收天地精氣,呼吸日月精華而達到與天地平衡的生活方式即是對“產生”的最好詮釋。而挑戰呢,挑戰總試圖著占領人,在被占領之后,這種占領實際上變成一種支配,成為了一種無意識的領航。“無意識賦予社會事實以共同而明確的特征”[ 3 ],幾乎每個人都沉迷于手機網絡世界,每個人都在這種無意識地被占領中追逐著自己的解蔽。
手機作為媒介,以微博、抖音、朋友圈等為引領的現代技術邏輯或許正是這樣一種邏輯:或許你想的只是回復一條信息或者處理一個一分鐘就能處理好的簡單的問題,然后當你打開手機,你不知不覺地就被它的鎖鏈所牢牢套住了。你把朋友圈刷來刷去,陶醉在抖音的眼花繚亂里。你或許想要的真的只是一涓細流,而你卻發現它就像大湖、大江、大海里的旋渦那樣一直持續不斷地吸引著你。這種渴求不停地牽引著心中那如野狼一般咆哮著的欲望,直到你掏出手機打開屏幕為止。
結合海德格爾所描述的“挑戰”這種去蔽模式去認知現代技術,我們就很容易得到與海德格爾相似的結果并且理解這樣的現象。人其實沒有控制去蔽本身,倒是人自己被技術安置了。在格-設的挑戰下,人一味追逐探索那種在布置中的被解蔽。如果以此為尺度的話,那么在存在的近處的可能性就會被封閉 。那些被布置起來解蔽的東西吸引著人們不斷去推動,而選擇總是有機會成本的,在選擇一項進程時往往需要放棄掉另一項,這樣以來,居住在存在的近處的可能性就被封閉了。坐在一起的家人的互相關心少了,他們各自玩著各自的手機。不知道能否讓遠處的人心心相映,但以手機為主導的現代技術確實給近處的交流設置了屏障。技術縮短了人和人物理上的距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和以往那些可能接觸不到的人的看似更近了,卻實際上與我們身邊的人越來越遠。
技術的統治總是給我們這樣的感受,假如你給它哪怕一點點空間,它就會源源不斷地從那一點出發,并開始一直持續不斷地想要占有你。“我們只能對它敞開”[ 2 ],就算不敞開的當然也敞開了,因為它成了主流的話語體系,我們很多時候好像別無選擇。現實可能是,即使組織一次旨在接受大自然和春風洗禮的春游,手機里的朋友圈、微博、抖音也會消耗我們之間相處或交流的時間,大家都在有意無意、自覺或不自覺地翻著朋友圈,刷著微博,刷著抖音。
反思一下多少人現在每天會花多少時間在記錄別人生活的短視頻世界上,在有著不斷更新信息的微博和朋友圈上。除了別人生活的紛繁復雜,我們自己的生活到底還剩下了些什么呢?在大量地過別人的生活的同時,我們自己的生活在哪里,并且它實際上又有多少呢?在一個廣泛追逐他人生活的時代里,每個人作為一個人的自我意識——那種自我的本質是不是真的就在有意無意間逐漸消亡了呢?就像《娛樂至死》所描述的,“真理被淹沒在了無聊煩煩的世事中”[4]。
2 “挑戰”主導下時代的焦慮
“與格-設伴隨而來的是迷失,它讓人把本質迷失,當然也迷失解蔽自身。”[5]人們在這一過程中一味追逐,越陷越深。那些匆匆流著的時間或許被一刷就是一兩個小時的空耗,而停下來的夜貓子們往往一看時間,就已經到了半夜兩三點。筆者以為,這樣的實踐方式或許也是一種娛樂至死。無聊的人打開并翻看短視頻庫里包羅萬象的世界,淪陷于其中,結果卻是刷得越多,就越空虛和無聊。
為什么會空虛和無聊呢?因為在這個過程中我們只是成為了看客。在接受完一些新鮮信息之后,需要進行消化吸收的頭腦趨于飽和,已經接受不了新的內容。我們開始只是本能地被吸引,大腦停止思考,精力卻持續流失。適量地瀏覽新鮮信息必然是有益的,但問題在于,如果過了這個度,一直離不開手機,甚至是被吸引著為了刷短視頻而刷短視頻,那不是就已經與初衷遠遠背離了嗎?被賦予明確而共同特征的所有人都在躺著坐著刷著屬于自己的狂歡,或許刷得越多,我們就越會失去自己的本質。在這樣的過程中,人們會不會真的成為了那種失去了基本思考能力,就像《娛樂至死》的封面上那些無頭無腦的人呢?“再也不知道想要什么——再也不相信自己能夠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壞的,什么是對的,什么是錯的。”[4]
去蔽方式的改變發生時,問題也隨之發生。當我們去到某個號稱特色鮮明其實全國千篇一律的古鎮之類的旅游景點,買某一集散地集散出來的全國所有景點通用的紀念品時,會不會產生一種虛無感呢?大工業時代用生產出1 000個同質的藝術品的方式生產出僅有模糊分別的城市。在這種同質化的現代世界中,孤獨的人們只能偏向于手機里被設計符合個人喜好的有著差異性的內容,在我們的世界中,手機里的內容也成為了一種符號。“與符號所代表的東西相比,符號本身更真實”[ 3 ],手機成了讓我們感覺更親切的東西,成了比知識,比文化現象,比微信里的聯系人更親切的東西。有時候我們并不需要它,但問題在于,它讓我們感覺更親切,所以我們開始與它寸步不離,不管是有事還是沒事。
伴隨這樣的狂潮而來的,是時代的焦慮。在《娛樂至死》中尼爾·波茲曼認真分析了喬治·奧威爾與奧爾德斯·赫胥黎的觀點對立,解剖了多媒體技術進步對于我們造成的潛移默化的影響。波茲曼傾向于赫胥黎的觀點:“我們再也不用擔心那些剝奪我們信息的人,或許應該擔心的是人們在汪洋如海的信息中日益變得被動和自私。”[4]“另外也同樣重要的是,在我們的時代里,人們或許會漸漸愛上壓迫,崇拜那些讓他們失去思考能力的工業技術。”[4]曾經的理性、邏輯、整體構造性不知不覺中轉變為碎片化、抽離化、膚淺化,公共語言體系也走向泛娛樂化,生活在當代的我們仍然沿著波茲曼所擔心的方向前行。
在技術引領的社會里,人人都好像站在很難變動的生產線上一樣,稍微遇到一點事情總是擔憂恐懼,人海里浮沉總是欲壑難填,結束繁忙的工作后總是又勞又倦,許多人可能做著自己不愿意做的工作,承受著不應該承受的承受卻難以逃離。 摩登時代令人壓抑的高強度的工作狀態總是帶來“人變成機器”的精神挫敗感,或許也因為在越發同質化的時代里我們需要刺激,我們也更需要新鮮事物,于是人們真的開始愛上壓迫,崇拜那些讓他們失去思考能力的技術。更為可怕的是,在我們的時代里,“人們感到痛苦的不是他們用笑聲代替了思考,而是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么笑以及為什么不再思考。”[4]
當代法國哲學的觀點認為,“現代性與后現代研究的出發點是一般等價物和交換這兩個原則。”[ 3 ]在流量成為直接和金錢對接的一般等價物之后,網紅短視頻博主們紛紛將“10萬+”(指短視頻的點擊量達到十萬,就會有伴隨而生的商業價值的現象)當作追求目的, 應用當代實用主義邏輯,各顯神通用渾身解數將我們吸引,于是,我們的注意力也被 “開發、改變、貯藏、分配”了。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問題引起我們的思考:到底是我們在玩手機玩抖音,還是手機及被設計的應用在玩我們,在手機網絡引領的時代里,筆者以為,一個被朋友圈、微博捆綁,被設計的吸引點吸引、淪陷、成為被人收割的韭菜,對著抖音里包羅萬象的信息在無聊中更加無聊,一抬頭卻已深夜兩三點的人或許已經被反轉。
現代性的消解無處不在,在我們的時代里,我們好像離手機所主導的現代技術越近,就離自然越遠。比起以前的人為什么我們更加容易焦慮呢,或許因為我們更少緩沖與“留白”。人需要一個港灣,就像手機電量用完之后也需要充電一樣。人其實還需要一點兒可以用來在墊高的枕頭上反思的閑暇。然而,在當今社會里,抖音、朋友圈、微博好像成為了我們的家園。隨著技術的發展,我們不再需要寫日記了,朋友圈和微博就是最好的生活記錄與感想抒發地;我們好像也不需要看電視和看書了,抖音里的內容包羅無窮而且伴隨著源源不斷的吸引力。我們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在戶外做形形色色的游戲和運動了,因為電子世界里的東西好像更理性、更刺激、也更觸手可及。技術的引領無孔不入,當然也無處不在,那么如果我們被這種無所不在占有得滿滿當當,我們又能拿出什么空閑來反思呢,我們的空與白又在哪里呢?
再讓我們思考一下,手機里的抖音、朋友圈、微博真的能成為我們值得依賴和信賴的港灣嗎?筆者以為,如果一個尋求港灣的人在他以為的港灣里找到的不是滋養和補充,而是在無聊里更加無聊卻難以停止的空耗,那么他其實就已經陷入了被技術統治和吞噬的被動,在這樣的焦慮的過程中更加焦慮。這樣一來,等待他的或許只剩虛無和毀滅,而這種虛無和毀滅并不是突如其來。
3 自律,我們或許唯一能依靠的“神”
1985年在《娛樂至死》中,尼爾·波茲曼曾不無憂慮地談到“人類將毀于我們所熱愛的事物”[4]。而尼爾·波茲曼在解析他那個時代的理性、邏輯、整體構造性逐漸轉變為碎片化、抽離化、膚淺化,書籍引領轉向電視引領,一切公共話語以娛樂的方式出現的社會現實之時,他可能萬萬沒有想到,幾十年后的今天,我們的社會公共話語權特征會更加碎片化到現在這樣一種極致的程度。以手機為媒介,以微博、抖音、朋友圈等為引領,我們的現代生活大踏步走向了新的篇章。
馬克思在對異化勞動四重性的認識時使用了這樣一種描述來表現產業工人對于工作的逃避:“參與勞動的工人們只要肉體的強制或其他強制一停止,他們就會像逃避瘟疫那樣逃避自己的工作。”[ 6 ]如今,我以為用類似的表述方式來描述人們對手機里五花八門的世界追逐再合適不過,揣著手機的當代人只要有了哪怕一點點空閑,他們就會如饑似渴地掏出自己的手機翻看朋友圈,點開微博或者刷起抖音。”
在我們的時代里,經常有人會說一句,現在的人壓力多大啊。誠然,我們這個時代的科學技術可以說比康德的時代進步得多了,但其實,我們在精神方面的所遇到的問題也大得多了。或許今天的我們正跟兩百多年前的康德面對的是同一個問題:如果直面啟蒙主義中科學與自由的沖突,那么啟蒙的缺陷應該由什么來彌補呢?[ 7 ]
我們的時代是信息和行動比例嚴重失調的時代。“在空前便利的電子傳媒時代,我們比任何時候都聰明,也比任何時候都輕飄。”[4]娛樂是人的本能,但很多人在娛樂的無蔽與自我追尋中逐漸失掉了對量和度的把握,像斷線木偶一樣被牽引,在強大的引力面前顯得卑微與不知所措。技術可以輕易地讓人著迷,如果缺乏對待的慎重,我們就很可能被技術反轉,進入一種不是我們在玩手機,而是手機在玩我們的狀態。“控制自然和控制人這兩方面在全部歷史的發展中存在著內在的聯系,控制的真正對象是人”[ 8 ]。而現在,控制人的時代已經氣勢洶洶地來臨了。
“有危險的地方,拯救也在生長”[ 2 ],海德格爾呼喚一個拯救我們的神,“只有一位神能拯救我們。留給我們的唯一可能是,在思想和詩歌中為神之出現或者為在沒落中神之不出現而做準備。”[5]筆者以為則不然,沒有一個神會突然出現來拯救我們。拯救人的是人而不是神,毀滅人的也是人而不是神,或許有人曾在閑暇的靜默里擷取到無聲的神性,但拯救人類的只有人類自己,我們需要自律。在手機主導的時代下,我們很容易陷入浮躁,當我們拿起手機,通往一個五花八門的新世界的大門就被打開了,毫無疑問,我們被拋入了一個他律難以形成的大環境之中。在這樣的背景下,自律就顯得尤為重要了。
一方面,我們需要對技術正確認識,聰明對待。有一個問題在于:如果我不玩手機,不翻朋友圈、微博和刷抖音,那我又能干什么呢?其實,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或許還有很多,或許只是在那種被吸引的狀態下,它們都深深地被遮蔽了。當我們空洞地沉迷在手機世界里,刷了一兩個小時之后,事后的反思就告訴我們,我們其實應該做點兒什么,事實上我們能做的的確也很多。我們并不是像在被欲望牽引時的那樣,以為自己除了面對手機之外,沒有任何事情可為。我以為,離開手機所主導的世界之外,我們仍然應該是一個完整的人。如果技術的統治讓我們覺得在離開它之時我們就少了些什么的話,那我們或許就應該斟酌一下了。
另一方面,我們還需要這樣一種對于主客體關系的反思,而反思的核心就在于喚起我們的主體性。更多地從自我個體性出發,為自己的更好而努力而不是被引導在別人世界的流連中失去自我。擁抱進步的我們不應該反現代性,但明確主客體關系并且認識到這種可怕的無意識的現代性深淵對我們來講或許也很重要——為自己而活,不為迷茫而活。我們需要文化,也需要身邊的人隨時更新的動態和信息。但我們也需要把持“挑戰”對我們的影響,掌控其中的“度”。技術毫無疑問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我們能把握住這個“度”,就能發揮積極作用,避免消極作用。
自律不止是抗拒,好的自律應該是一種駕馭,是疏通導引的大禹治水而不是圍追堵截。合理的實踐方式造就人,不合理的實踐方式毀滅人。在我們的時代里,我們或許應該更多地追求人與自然的豐滿本質。應該把更多的網絡世界主導之外的就像閱讀紙質圖書和戶外運動之類的事物積極引入實踐。更多地去青草正在生長的地方看一看,在落日的余暉里去走一走,別讓抖音、朋友圈和微博像個吸血鬼一樣把你默默吸干,自己卻渾然不知,成為一個對于手機所主導的世界之外的一切事物一點兒都提不起興趣的人。如果對于自然失去了感受力,那我們其實也就是在無意識中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
技術的計算性思維每天都不斷地回擊人類自身,并將其降低為一塊有序的資源,我們終將會失去自己的本質[ 2 ],海德格爾的警告入木三分。讓我們反思一下,在被技術冷酷統治的時代下得意的是誰,被消磨的又是誰呢?那些半夜三更還望著閃著亮光的手機,像孤魂野鬼一樣在網絡世界里不知所措地游蕩的人,他們不是已經被技術碾壓得茍延殘喘了嗎?我們不是不要進步,可是在發展之余我們確實應該意識到這個已經被多次敲響的警鐘,并在此基礎上深刻地反思:我們到底是在進步,還是在選擇毀滅自己?
“有兩種方法可以讓文化精神枯萎,一種是奧威爾式的——文化成為一個監獄,另一種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為一種滑稽戲”[4]而我們現在應該擔心的或許正是后一種。在我們這個由抖音、朋友圈、微博引領,由手機主導的大環境背景之下,當我們從那種持續的,源源不斷地想要占據你的呼喊或深淵外逃離,在人與自然的豐滿本質中多待一會兒時,我們或許才能獲得屬于我們時代的一種解放。
4 結語
海德格爾在《存在與時間》中,將人之存在與“時間”緊密結合起來,在海德格爾那里,本真的“時間”是一種“在-世界-之中”的存在,是與世界的因緣整體相關聯的存在。而當代人在網絡世界中,抖音、朋友圈、微博等把人的時間碎片化、庸俗化。“時間”體現了人的存在方式,人們如何利用時間,也就以何種方式“存在”。農業時代的去蔽方式是“產生”,這種去蔽方式強調我們與自然的和諧相處,天人合一。工業時代的去蔽方式海德格爾則把它稱作“挑戰”,這種方式強調人與自然對立二分,一方張開血盆大口向另一方瘋狂索取。“挑戰”是現代技術的內在邏輯,因此它也是微博、抖音這些引領時代的當代技術的邏輯。這種去蔽模式的掠奪本質不僅掠奪自然,在面向人時也掠奪人,因此它使當代人不斷失去自我,即失去人作為人的本質。由于逐漸失去人的本質,人們在不知所措和迷茫中開始陷入焦慮。
在這種去蔽模式的指引下,“我們的日常生活、我們的心思和身體、我們的社會組織方式,眼下都被技術所掌握了,都被技術化了”[ 1 ]。過分刻意強調工具理性必然導致人文關懷方面的缺失,對手機的沉迷以及對于相關技術的濫用雖然是我們現代的問題,但海德格爾似乎就像一個預言家,他的論述總能指向現代技術引領的每一個至暗時刻。實際上,我們也應該對“如今正在不斷加速的人類生活的全面技術化”[ 9 ]進行反思。從海德格爾對于現代性的思考當中,我們汲取到了或許是我們時代所需要的一些營養。
參考文獻
[1]海德格爾.存在的天命[M].孫周興,譯.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8:199,201.
[2]張汝倫.現代西方哲學十五講[M].北京:中信出版社,2020:312-313.
[3]弗朗索瓦·多斯.從結構到解構:法國20世紀思想主潮[M].季廣茂,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50,36-44.
[4]尼爾·波茲曼.娛樂至死[M].章艷,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5,317,9,8,194,7,185.
[5]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孫周興,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946.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59.
[7]張志偉.西方哲學史[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389-394.
[8]威廉·萊斯.自然的控制[M].岳長齡,李建華,譯.重慶:重慶出版社,2007:189.
[9]海德格爾.鄉間路上的談話[M].孫周興,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