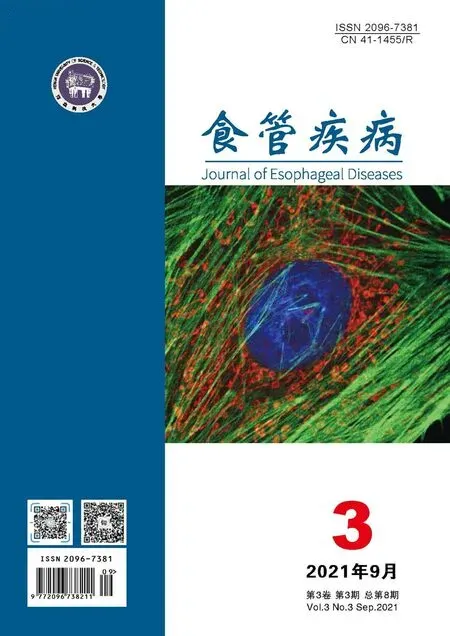基于扎根理論的中青年食管癌患者診斷期心理體驗研究
李變紅,劉鶴陽,喬偉強,李轉珍,趙杰剛
食管癌是最常見的惡性腫瘤之一,發病率位居惡性腫瘤的第八位,死亡率位居第六位[1]。在我國,食管癌的5 a總生存率僅20%左右,成為第四大腫瘤死亡原因[2-3]。近年來,食管癌的發病呈現年輕化趨勢,2014年被診斷為食管癌的185.4萬例男性中,中青年約占24%[4]。中青年食管癌患者處于人生的黃金時期,面臨實現人生理想、撫養子女與贍養父母等重任。一旦診斷為癌癥,不僅患者的健康狀況發生改變,其家庭和事業也受到嚴重影響。尤其在疾病診斷期,生命受到威脅,家庭和社會角色發生轉變,患者的內心必然會產生一系列變化,進而影響疾病的轉歸和生活質量。本研究采用扎根理論方法探討中青年食管癌患者在診斷期的心理體驗,為臨床醫護人員開展針對性的心理干預提供依據。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采用目的抽樣法,選擇2018年12月至2019年5月在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腫瘤外科就診的食管癌患者。納入標準:①首次診斷為食管癌,尚未進行抗腫瘤治療;②年齡為18~59歲;③有基本的文字閱讀和語言交流能力;④知曉病情,同意參與本研究。排除標準:①食管癌復發或轉移;②患有其他惡性腫瘤或嚴重疾病;③既往有精神病史或認知、意識障礙。
樣本量以資料重復出現且在資料分析時不再有新主題呈現為標準,即達到資料飽和。本研究納入的中青年食管癌患者共11例,年齡37~59(52.7±6.2)歲,均已婚。患者的一般資料見表1。

表1 11例中青年食管癌患者的一般資料
1.2 研究方法
1.2.1 資料收集通過查閱文獻及與專家討論初步擬定訪談提綱,邀請3名患者進行預訪談,根據反饋對提綱中個別問題進行適當調整和修改。最終確定提綱如下:①您是如何發現疾病的?②您對食管癌了解多少,是通過什么渠道獲得的?③您覺得患病與哪些因素有關?④當被告知診斷結果時您的感受如何?⑤您現在最擔心的問題是什么?⑥您對未來的治療和生活有哪些顧慮?⑦您覺得患病對家庭有何影響?您看到家庭成員的表現以后,您的內心有什么想法?訪談時機選擇在患者首次入院的1~3 d,在患者知情同意的情況下一對一進行半結構式訪談并錄音,每次訪談時間30~40 min,訪談中記錄患者的語句停頓、肢體動作和特殊情緒表現等,并于訪談結束前澄清一些不明確的問題,以增加資料的準確性。
1.2.2 資料分析本研究根據扎根理論[5-6],對訪談資料進行整理、分析:①開放性編碼:將訪談資料概念化,對收集到的所有文字資料進行編碼,并根據其屬性劃分維度與特征;②軸心編碼:通過因果、時間、情境、類型、結構等關系建立類屬之間的聯系,篩選出與中青年食管癌患者診斷期心理體驗有關的編碼,將其作為一個類屬或“軸心”,構建理論框架雛形;③選擇性編碼:確定核心類屬,既實現理論的盡量精簡,又最大限度保證理論能夠囊括所有類屬。在資料分析過程中,不斷地與原始資料對比,確保形成理論的準確性。
1.2.3 倫理原則本研究獲得河南科技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倫理委員會的批準,訪談前向患者詳細說明本研究的目的和內容并簽署知情同意書。
2 結果
2.1 患者在診斷期間的心理體驗在本研究中,將進行診斷期的訪談時間節點定義為患者首次入院的1~3 d,包括患者在家中或工作場合出現癥狀的時間、在基層醫院或其他醫療場所檢測的時間。經過對訪談資料整理、分析和歸納,將中青年食管癌患者在診斷期的心理體驗提煉為5個主題,3個次主題。
2.1.1 對首發癥狀的臆斷與忽視
食管癌早期癥狀相對隱匿,隨著疾病進展,患者多出現哽噎感或胸骨后疼痛。因為缺乏疾病相關知識,部分患者把身體發出的異常信號判斷為正常或輕癥,延誤就診時機。D:“兩個多月前,我中午去吃炒面,感覺有點兒噎,我想可能是我吃太快了,當時著急上班,也沒在意”。G:“那次吃飯的時候覺得胸口發堵,有點兒疼,因為一直有胃病,就找了點藥吃,沒覺得是大毛病”。J:“我婆婆以前在(世)的時候,她80多歲,就不能吃干飯,咽不下去。我這嚼嚼咽不下去,我心里想著:是老了嗎,怎么也咽不下去了?但是晚上吃飯我又能咽下去了,就沒去檢查”。
2.1.2 對初診結果的震驚與懷疑
本研究的11例受訪者中,有10例表示在告知診斷結果時,自己的第一反應是震驚。C:“我們一起去體檢的,我的身體比他們都棒,他們都沒事,我卻查出個瘤子。我這人一輩子沒做過虧心事,咋能得這個病,想不通(搖頭)”。I:“我拿到報告單的時候,腦袋一下子就蒙了,耳朵嗡嗡響,怎么可能是腫瘤,我才40多歲,我不想死……”。腫瘤患者在診斷前往往沒有充足的心理準備,當事實偏離預期,患者常難以接受,主觀否認患癌的事實。D:“我閨女在××醫院上班,我就在那做了胃鏡,結果出來的時候我想是不是弄錯了,當時檢查的人可多,是不是醫生把別人的單子給我了”。
2.1.3 對疾病的僥幸心理
訪談中,有4例患者表示自己對病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仍抱有僥幸心理。K:“醫生告訴我惡性的可能比較大,但畢竟還沒手術,我還抱點兒希望,說不定做了手術就好了”。此外,有患者認為自己身體基礎較好,只要通過積極治療就能取得較好的效果。D:“我知道這病,我們村里有個老太太就是這病,她就沒怎么看(病)還活了7、8年。現在(醫療)技術先進,我比她年輕,(效果)應該更好些”。H:“大夫說腫瘤也分好多種,有些治療效果還不錯。我這發現早,也沒咋轉移,就聽大夫的好好治,能有個好結果”。
2.1.4 對未來生活的焦慮
2.1.4.1 疾病轉歸的焦慮在診斷期,患者常對治療結果懷有良好期待,對未來寄予希望,但疾病的轉歸又充滿不確定性,使患者深感無力,陷入焦慮之中。E:“我現在特別怕醫生找我老公去辦公室,不知道他們會說什么,是不是我的病又不好了。醫生建議手術,我怕切不干凈白受罪,我也不知道該咋辦……”。I:“我聽說化療有很多并發癥,就是現在(治療)有效果,以后也可能會復發。我都不敢想,這病太嚇人了”。
2.1.4.2 家庭及社會角色缺失的焦慮從疾病診斷開始,中青年食管癌患者的家庭和社會角色就發生了轉變,患者由照顧者變為被照顧者,事業停滯或下滑,這些變化對其內心產生較大沖擊。K:“現在是啥都干不了了,以前總想歇歇,想著哪一天能不上班,這回是徹底歇啦(苦笑)”。本研究發現,在診斷期多數患者還沒完全進入患者角色,有3例患者甚至未將患病信息告知子女或父母,擔心會影響子女或給父母帶來打擊。E:“我兒子今年初三,正是關鍵的時候,我這住院還不知道咋跟孩子說”。I:“我是假裝出差來醫院的,家里就我老公知道,我爸媽就我一個閨女,能瞞多久算多久吧”。
2.1.4.3 經濟壓力增大的焦慮訪談中有5例受訪者主動談及醫療費用問題,并對家庭的經濟狀況表示焦慮。A:“家里條件差,這回住院借了不少錢。孩子們在外面打工,掙個錢不容易,都讓我花了(情緒低落)”。D:“我那孩子都三十了還沒結婚,本來是攢錢給孩子買房的,現在錢花了,不知道啥時候能掙回來,有時候都不想治了”。J:“我入院那天交了兩千,一天就花完了,現在準備手術,大夫說最少交一萬。這才剛開始(治療),也不知道得多少,誰知道下回的錢在哪”。
2.1.5 疾病歸因的反思本研究發現,多數中青年食管癌患者反思疾病原因時,認為負性情緒、不良的生活習慣等因素與疾病關聯較大。E:“我脾氣不好,愛起急,我和孩子他爸開玩笑,說我這病都是他氣出來的”。I:“平常我都是自己,他們都不在家吃,我一個人不怎么做飯,有一頓沒一頓的,這病就弄出來了”。部分患者在回憶患病過程時,將原因歸結為命運安排。B:“之前我和孩子吵架,說你沒有這個媽,我沒有你這個孩子。隔了沒多久就查出來這病,我想是不是我說了這話應驗了”。D:“孩子他爸老是嘆氣,我說你不用嘆氣,活了是我命,死了是我病,這誰能保證,(上)天說了算,過一天算一天,想這有啥用”。
2.2 中青年食管癌患者診斷期心理體驗的理論框架
由于對食管癌的低認知,中青年食管癌患者對首發癥狀表現出臆斷、忽視,同時產生僥幸心理,導致其在被告知初診結果時倍感意外,出現震驚的心理體驗,為降低確診帶來的心理沖擊,患者將懷疑診斷結果做為心理防御手段,緩沖疾病帶來的壓力,但卻間接助長其產生僥幸心理,加重患者對疾病的臆斷與忽視,延誤就診時機。中青年人群往往肩負著一定的社會與家庭責任,受疾病的影響,患者的生活嚴重偏離原來軌跡,對未來倍感焦慮。在反思疾病原因時,有人懊悔以往不良的生活習慣,有人表現為對遺傳因素的無奈,有人歸結為命運的安排,但這些背后更深層次的心理是患者對生命的渴求。基于以上研究,中青年食管癌患者診斷期心理體驗之間的理論框架見圖1。

圖1 中青年食管癌患者診斷期心理體驗的理論框架
3 討論
3.1 加強疾病宣傳,提高公眾認知食管癌是由多種因素引起的惡性腫瘤,與遺傳、環境、生活方式及社會心理等因素有關[7]。為提高食管癌的防治水平,我國已在食管癌高發區開展了針對40~69歲人群的內鏡篩查輔以碘染色和指示性活檢技術,成為現階段最為可行、有效的二級預防措施[8]。本研究中有2例受訪者談及其親屬有患癌經歷,但在出現早期癥狀時,患者并未因此提高警覺性,及時去醫療機構檢查、診斷,以致延誤治療。河南處于食管癌的高發區,加強食管癌相關知識的健康教育具有長遠意義。①我國農村地區醫療基礎相對薄弱,可以通過構建縣—鄉—村三級醫療衛生體系,進行癌癥防治知識的宣傳;②對于城鎮居民,應以社區為單元,通過張貼海報,發放健康手冊,定期開展講座等方式,提高食管癌的知曉度;③針對高危人群,宣傳內鏡對早診早治的重要性,增強其主動體檢的意識,建議政策層面將高危人群的內鏡篩查納入醫療報銷范疇,降低高危人群的經濟負擔。
3.2 重視早期癥狀,正確認知疾病食管癌早期主要表現為進食時胸骨后疼痛或哽噎感,且疼痛部位與病變位置不完全一致。出現首發癥狀時,患者往往將病因臆斷為消化不良、進食過快或胃炎,未給予應有的重視。當被告知診斷結果時,患者心理準備不足,加之“癌癥即是死亡”的傳統認知,患者內心拒絕相信診斷結果,主觀否認患癌的事實。研究表明,由突發事件產生的心理應激不僅損害患者的免疫系統,促進腫瘤的生長,還影響病程與轉歸[9]。作為醫護人員,應引導患者正確認識疾病,減輕對食管癌的恐懼,鼓勵患者傾訴和表達,努力為其營造正向的治療環境,促進患者身心康復。
3.3 評估心理狀態,加強健康教育僥幸心理作為一種防御手段能緩沖應激事件帶來的心理沖擊,發揮積極的作用,也能使患者逃避現實,對治療產生消極的影響。醫護人員應及時評估患者的心理狀態,正確看待患者僥幸的心理體驗,及時把握患者的心理動向并進行有效干預,引導患者理性看待疾病,避免其因僥幸心理延誤或逃避治療。
3.4 疏解負性情緒,完善社會支持Wilson等發現,77.1%的患者認為自己是家庭的負擔[10]。相較于其他人群,年輕的腫瘤患者更容易產生焦慮和抑郁的情緒體驗[11]。一般而言,老年患者有子女贍養或退休后的穩定收入,經濟壓力和家庭、社會賦予的責任不大。而中青年患者脫離工作崗位以后,缺少經濟來源,在家庭、社會方面的支持不足,很難應對撫養子女、贍養父母以及支付高昂的醫療費用等問題,對未來的無力感使其深陷焦慮之中,產生自責、內疚等情緒。研究表明,健全的社會支持系統是癌癥患者克服病痛、戰勝疾病、增強信心的重要心理支柱[12]。有效的心理干預能夠減輕患者的家庭和心理負擔,并改善其經濟壓力,提高生活質量[13-14]。因此,醫護人員應做到:①及時評估患者的心理狀態,給予其有針對性的心理疏導,鼓勵患者選擇更加積極的應對方式,緩解心理壓力,提高生活質量[15-16];②提高患者的自理能力,降低其對家庭照護者的需求,增強患者自身的價值感;③建立良好的社會支持系統,加快重大疾病保障和重大疾病援助體系建設,為患者提供更好的經濟保障。
3.5 提高健康意識,重視靈性護理靈性是腫瘤患者應對疾病的重要資源,能夠幫助患者應對腫瘤診斷及后續治療帶來的身心危機[17]。研究發現,當個體面對壓力時,個體基于對自身壓力的初步理解,通過靈性聯系、靈性應對及其相互作用,重新定義壓力事件的意義,這個創造意義的過程(靈性)會促進個體選擇更加積極的方式應對壓力,進而達到身心健康的狀態[18]。靈性護理是提高腫瘤患者及家屬生活質量的有效方式,能夠促使其感受自身價值,增強承受負性情緒的能力。但在目前的研究中,靈性護理多應用于腫瘤晚期患者,對腫瘤初診患者的護理尚處于探索階段。本研究發現,因受訪者的生活方式、性格特征和宗教信仰等存在的差異,其對疾病的認知和對治療的態度也有所不同。因此,在臨床工作中,醫護人員應根據患者自身的需求,積極引導,幫助其建立正確的人生觀和價值觀,增強治療信心。
本研究尚存在一些不足。首先,納入本研究的患者病理分期較早且發病年齡較低,患者及家屬的治療意愿強烈。因此,本研究未涉及患者及家屬消極或放棄治療的方面,這有待于在以后的研究中進一步拓展。其次,在資料分析階段,本研究不能完全排除主觀因素的影響,但是在提煉主題時,始終秉承嚴謹、客觀的態度,最大限度保證主題的準確性。
本研究基于扎根理論的研究方法,對11例中青年食管癌患者進行訪談,追蹤其在診斷期的心理變化,發現患者存在突出的心理問題和顯著的負性情緒,為醫護人員理解中青年食管癌患者在診療過程中的心理體驗,進一步提供個體化、有針對性的心理干預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