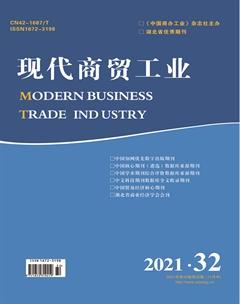民事訴訟中域外電子證據使用問題研究
王曼璐
摘 要:近年來互聯網等技術急劇發展,區塊鏈已開始進入美國法院,跨國間的貿易、投資等越來越便捷,帶來了極大的便利同時也給國家司法實踐帶來了很多挑戰。電子證據在民事訴訟中的地位,效力本身就存在著許多問題,跨境的電子證據取得也受到諸多限制,國內對于域外取得的電子證據缺少相關立法,取證主體、取證方式、證據效力方面都沒有明確而全面的規定,使域外電子證據的適用更加困難。本文結合電子證據的域外取證問題、把分析的重點放在民事訴訟中域外獲得的電子證據在合法性、證明力、真實性以及效力方面的問題,并提出了一些建議。
關鍵詞:電子證據;域外取證;民事訴訟
中圖分類號:D9????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1.32.055
1 電子證據域外取證的淵源
網絡的出現為域外取證提供了全新的視角和途徑。利用電子技術,將傳統的與外取證請求書送達方式演變成將證據通過電子郵件等方式傳送。紙質版的證據變成了數字電文的形式,給各國政府、司法機關以及當事人節省了極大的人力物力交通資源的同時,也增加了新的問題。域外電子取證所得到的數字電文形式的證據,也就是電子證據,是否可以當作證據使用——即電子證據是否具有合法性,它的效力如何,獲取方式有哪些,其增刪查改的基本操作又有著怎樣的法律含義,涉及的法律沖突,都值得研究與探索。
1.1 有關電子證據域外取證的法律
修改前的三大訴訟法將證據分為7大類別,這種分類方法構成了司法實務操作的基礎,我國《刑事訴訟法》和一些相關司法解釋、規范性文件中的一些原則性規定雖然實際的操作可能性不大,但仍然肯定了電子證據的地位及有效性。電子證據作為我們國家承認的證據形式,自然包含在證據的范圍內,雖然電子證據作為證據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因此就否認域外取得的電子證據作為國際民事訴訟中合法證據的可能性。我國于1997年加入了的《關于從國外調取民事或商事證據的公約》,該公約在1970年3月18日簽訂于荷蘭海牙,也叫《海牙取證公約》。公約規定,在民事或商事案件中,每一締約國的司法機關可以根據該國的法律規定,通過請求書的方式,請求另一締約國主管機關調取證據或履行某些其他司法行為。同時公約的第2條也規定了,請求仍然需要通過每一締約國應指定一個中央機關負責接收來自另一締約國司法機關的請求書,并將其轉交給執行請求的主管機關。電子證據作為我們國家承認的證據形式,自然包含在證據的范圍內,雖然電子證據作為證據有其特殊性,但不能因此就否認域外取得的電子證據作為國際民事訴訟中合法證據的可能性。《民事訴訟法》域外取證主要有以下三種途徑:
(1)依照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所規定的途徑進行。
(2)在沒有條約關系的情況下,通過外交途徑進行。
(3)外國駐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使領館可以向該國公民取證。根據《海牙公約》,我國允許外國領事官員在我國境內向其本國國民調查取證,但對于領事官員向駐在國國民及第三國國民取證,我國的法律和條約中均未承認。
1.2 域外電子取證的方式
跨境電子取證的現有規范來看,我國立法非常謹慎、程序和條件也非常嚴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委會指定了司法部為負責接收來自另一締約國司法機關的請求書的部門,接收到請求書后,還應將其轉交給執行請求的主管機關的中央機關。如果中央機關認為請求書不符合公約的規定,應立即通知向其送交請求書的請求國機關,指明對該請求書的異議。執行請求書的司法機關應當使用其本國法規定的方式和程序。但是,該機關應采納請求機關提出的采用特殊方式活著程序的請求,除非其與執行國國內法相沖突,或者依照國內慣例和程序無法進行,或者存在實際困難而不可能執行。在執行請求時,強制措施可以由被請求機關自由裁量適度采用。當然,由于電子證據極容易被獲取和篡改,再加上電子技術和互聯網技術是近幾年才開始發展,并從出現開始就保持著高速發展的態勢,所以我國關于電子證據的法律有所不相適應,以及立法時的嚴謹與嚴厲也是無可厚非的。我國司法實踐中電子數據單邊取證主要有以下幾種方式:
一是公開數據的獲取,在公開的網絡上通過拍照、同步錄音錄像、截取頁面等方式將網頁上的電子數據固定以此充當證據,這類取證方式最為容易便捷、同時合法性也很有保障。
二是通過賬戶和密碼,遠程登錄相應的境外服務器等數據平臺,勘驗提取電子數據。同時要采用全程錄音錄像的方式來保證取證的合法性。
三是由專業人員通過技術偵查手段直接獲取境外服務器內存儲的電子證據。隨后由專門的鑒定機構形成電子數據檢驗報告或電子證據司法鑒定報告作為證據使用。從裁判文書來看,這里的“專業人員”一般是公安機關網安或技術刑偵人員,也可能是專業電子證據鑒定機構的技術人員。但明顯后兩種方式對于在民事訴訟中使用的參考意義不大。對于民事訴訟中域外電子證據的取證方式對其適用時會產生的適用問題還應進一步探究。
1.3 跨境電子取證法律沖突
跨境電子取證的法律沖突需要同時滿足三個前提:(1)證據調取國通過實施“長臂管轄權”獲取證據,但通常此類管轄權僅依據該證據調取國的國內法,而在證據所在國不受認可。(2)證據所在國對證據的使用、流通等有一定限制。(3)前兩項證據調取國與證據所在國的矛盾無法通過二者間的數據流通協議達成共識協調。
2 國際民事訴訟中域外電子證據的適用問題
電子證據雖然是證據的一種,但是由于其易篡改、鑒定難度大、使用門檻高的特點以及很容易侵犯公民個人隱私或國外的數據安全法律法規等問題,使民事訴訟中使用域外取得的電子數據更加不現實,因此對于電子證據的搜查、提取、認證、適用必須更加謹慎。
(1)合法性。2020年4月8日,最高人民檢察院(最高檢)發布第十八批指導性案例(“第十八批案例”),三起案件均為網絡犯罪案例(檢例第67、68、69號)。這是最高檢第二次發布網絡犯罪指導性案例,這些案例主要聚焦在電子取證的合法性以及隨之而來的電子證據是否客觀等問題,這與從前大不相同。表明了我國對于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的問題開始重視并加以規定,電子證據在司法實踐中會應用的更為廣泛。67號案例中電子數據先有境外國家司法機關獲取存儲介質、再通過司法協助或外交的方式將存儲介質移交給我國司法機關,為保證合法性,該指導案例提出“移交過程中應注意審查過程是否連續、手續是否齊全”等指導意見。雖然該案例指向的是從境外起獲的存儲介質中提取電子數據,而不是直接從位于境外的設備中提取數據,但由此可以看出電子數據境外取證合法性問題的重要性以及我國司法機關對電子證據的問題已經開始重視并付諸實踐。國際民事訴訟中,域外取得的電子證據能合理利用,無疑會使司法實踐更加方便迅速.由于各國家對數據安全的法律或規則不盡相同,導致了某些取證方式的合法性發生沖突,或者一國的取證主體另一國不予以承認的情況。對電子證據的獲取的主體和合法方式進行國際的統一約定,或盡快規定電子證據司法協助簡易程序,對于國際的民事訴訟案件判定有極大的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