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理與現代
——《法哲學原理》“倫理總論”釋義
莊振華
(陜西師范大學 哲學與政府管理學院,西安 710119)
提要: 黑格爾倫理學說是對近代早期以來一直困擾學界的“群己權界”問題的一種深刻回答。黑格爾認為,社會活動與人際關系均扎根于生活世界整體(倫理實體),而且后者的概念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更高層面上絕對者的自我實現。這意味著我們既要在實體性根據的意義上看待家庭、市民社會、國家與世界歷史,又不能以這些倫理形態為終極根據,誤將它們(比如國家)當作世界的歸宿。以往對于黑格爾法哲學的研究(從黑格爾同時代人到霍耐特的研究)大都撇開了它的形而上學根據,僅僅就法哲學(或其部分內容)而論斷法哲學。菲韋克重視法的形而上學根據,但在對倫理的邏輯學定位上卻產生了偏差。針對這些研究,有必要將《法哲學原理》放回它與其他著作(尤其是《邏輯學》與《精神現象學》)構成的相對位置中去,通過對關鍵文本的詳細闡釋,既探明倫理的重要性,又勘定其局限性,方能了解其現代意義何在。
“群己權界”是困擾近現代政治哲學與道德哲學的一個難題。表面看來,它似乎僅僅涉及個體與個體、個體與群體的相互關系,而與絕對者和宇宙秩序無關,近代政治哲學的種種爭論,基本都在這個框架下進行。且不論近代早期伴隨著權力政治興起而產生的馬基雅維利學說與“國家理由”學說,單就社會契約論各流派來看,無論假定自然狀態下人人為敵(霍布斯),還是假定那時人人自由平等(洛克),抑或在更思辨的意義上設定理想的“公意”狀態并以此達致每個人的自由(盧梭),這些流派都沒有越出上述兩種關系之外。但在黑格爾看來,不僅這些關系扎根于生活世界整體(倫理實體)①,[1-2],而且它們的概念并不在于其自身,而在于更高層面上絕對者的自我實現。這意味著既要在實體性根據的意義上看待家庭、市民社會、國家與世界歷史,又不能以這些倫理形態為終極根據,誤將它們(比如國家)當作世界的歸宿。
對于黑格爾的《法哲學原理》,以往人們大都關注黑格爾是否是普魯士國家辯護士(黑格爾主義者及同時代人)、社會②與國家的關系(馬克思),或者在近代政治哲學的意義上討論黑格爾關于契約、個人自由、國家政制等問題(英美學界),近些年則比較熱衷于在資本主義框架下研究黑格爾的承認理論(霍耐特、丕平等)。這些研究的共同之處是撇開了黑格爾法哲學的形而上學根據,僅僅就法哲學論法哲學。也有部分德國學者(亨利希、菲韋克)對于去形而上學化的做法有所警惕,正如菲韋克所言,目前“在對《法哲學原理》的研究中占支配地位的大多是認為必須放棄形而上學根據的立場”,然而單就“倫理”篇而言,“在開頭幾段(第142節)這種企圖就必然落空,那里邏輯學的基礎明白無誤地被確定下來了”[3]232。但正如后文將要表明的,菲韋克尊重形而上學背景的意圖雖好,他以《邏輯學》的“概念論”為《法哲學原理》定向的做法卻是一種邏輯錯位,最終還是落入主體性自由的窠臼了。在這個意義上說,他的工作是不徹底的。
重視形而上學根據的做法顯然更合乎黑格爾的本意,而要恢復黑格爾法哲學的本來面貌,“倫理”篇是一個極好的切口,因為該篇以“實體”這一明確的邏輯學定位表明了黑格爾對于倫理的地位的看法不同以往,但“倫理”在整個精神哲學中上通絕對精神的關鍵地位又不容許我們將任何一種倫理形態(包括國家)視作絕對。下文首先以《精神現象學》《邏輯學》《精神哲學》為坐標,確定“倫理”篇的體系位置,間接透顯其思想旨趣,然后從正面對“倫理總論”(第142-157節)部分進行文本釋義,一方面表明倫理具有個體道德、主體際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透顯倫理并非究竟之境,指出倫理層面的局限性,最后在此基礎上簡要討論現代激流中黑格爾倫理學說的潛力。
一、倫理的體系位置
在當今的日常用語中,“倫理”與“道德”幾乎是同義的。然而在現代思想中,黑格爾的“倫理”(Sittlichkeit)概念卻是個新事物③,[4][3]230(Bemerkung)。菲韋克認為,黑格爾并非簡單造出一個新說法,而是將一整個范疇(Kategorie)引入現代實踐哲學,該范疇如今已經成長為一個不可忽視的關鍵概念(Schlüsselbeg-riff)[3]229。從家庭教師時代對實定性(Positivit?t)的逐步接受,到耶拿時代的《哲學批判雜志》系列文章和《倫理體系》,經過《精神現象學》中關于“倫理實體”的論述,直至《法哲學原理》中體系化的“倫理”篇,黑格爾逐步形成一套看似獨特,實則深具傳統色彩的倫理思想。這體現出他在現代語境下承接西方古典傳統的一貫抱負,他絕不愿意僅僅局限在同時代道德哲學的視角下就事論事[5]。
如前所述,以往人們對于黑格爾法哲學的研究,總體來說并不令人滿意。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學者們對倫理的邏輯學根據以及法哲學在整個精神哲學中的地位不予重視,或者進行了錯誤的定位。照此看來,要讀懂“倫理”篇,首先必須從不同方面準確把握該篇在整個體系中的地位。不能僅僅在法哲學的框架下考察“倫理”篇,要將法哲學還原到精神哲學的整體中;鑒于精神哲學是“一門應用邏輯學”[6-7],還要將精神哲學放到與邏輯學的良性互鏡關系中來考察;另外為了充分理解倫理的實體性與絕對性特征,也要將《精神現象學》對“倫理實體”的論述④納入考量。由此我們看出:倫理是作為實體性根據的“現實性”,但還不是《邏輯學》“概念論”意義上的“概念”,因而人們在這個層面上雖然開始承認各倫理形態的基礎性地位,但畢竟無法避免“本質論”意義上的種種反思性設定。因而人們一旦將倫理絕對化,便有封閉化與自我固化的危險。以下我們由遠及近地考察“倫理”篇的體系地位,以期澄清該篇的思想旨趣。
(一)《精神現象學》的“精神”章
在《精神現象學》中,“精神”章處在極為關鍵的位置,因為它達到了此前從未做到的自覺立足于事情本身的境界。黑格爾在該書的前五章描繪了意識的五種形態⑤,而在前四種形態下,意識無論停留在最膚淺的感性印象和事物的單純“存在”(“感性確定性”章),還是在個體內部試圖裁決事物與各屬性或統一性與差別性的爭執(“知覺”章),抑或在類概念與類概念之間建立規律以圖把握事物的內在本質(“知性”章),又或者在尊重他者內在無限性的前提下,在欲望或承認中尋求建立利己的相互關系而不得(“自我意識”章),畢竟都還處在較為抽象或局部的層面,意識還沒有像“理性”這樣達到對“整個世界合乎理性”的信念,可見前五種意識形態由“理性”總其大成。然而理性也有它無法突破的“瓶頸”,它以吞吐洪荒的偉力,經歷了舉凡近代人所能設想的一切理論與實踐領域,卻發現所謂世界的合理性(知識、規律等)原不過是理性在世界上截取的一張合乎它要求的皮(“觀察的理性”),或者說只是它自己認為公正因而強加于人的一些規范(“合理的自我意識通過其自身而實現”)。這樣的合理性不可謂不客觀,但絕不等同于事情本身。于是該章第三節中,理性試圖承認事情本身的力量,最終卻由于其行事方式而陷入與事物本身互為外在個體的窘境。總而言之,在“理性”章中意識發現生活絕不僅僅取決于理性的本事,理性最多只能達到一種自以為客觀的主觀信念。因為理性終究會發覺,有一些高于它之上的因素是它不得不接受的。這便進入了“倫理實體”的形態:事物并不取決于理性對它的描述或推進,“并不是因為我認為某個東西不是自相矛盾,所以它是正當的。毋寧說,正因為它是正當的,所以它是正當的”;不僅如此,人還前所未有地以事物本身為自身的本質了,“由于正當事物(das Rechte)對我來說是一個自在且自為的存在,所以我存在于倫理實體之內。在這種情況下,倫理實體是自我意識的本質,而自我意識則是倫理實體的現實性和實存,是倫理實體的自主體和意志”[8]。這種“還事物本身于事物本身”,而不再以理性勾畫的世界圖景代替世界本身的行事態度,正是“精神”章要描繪的[9]。
但話說回來,在“精神”章中人雖然立足于事情本身,畢竟還是從意識的角度在看問題。“精神”章展示的便是意識在承認精神根本地位的前提下的成長史。具體到“倫理”(希臘倫理世界與羅馬法律狀態)部分而言,這個階段因尚未陷入中世紀教化與近代啟蒙、道德世界觀這些二重化的世界格局之中,相對而言尚屬“個體與整體相統一”的某種較質樸狀態⑥。這種狀態盡管在黑格爾的家庭教師時代與耶拿時代尚未得到系統總結,在后來的精神哲學與法哲學體系中又經歷了相當大的刪削變形,但始終是黑格爾心目中一個“紀念碑”式的典范。從黑格爾歷次法哲學講座中對倫理實體本身的描繪,以及對城邦神與家族神的反復提及,都不難看出古代倫理實體依然是這里的重要參照點。但不可否認的是,所謂“參照”意義也只是相對的,因為古代倫理狀態由于沒有經過中世紀與近代二重化世界觀的“錘煉”,尚屬樸素先民狀態,這意味著它還沒有打開內心化的信仰與道德境界,也沒有我們熟知的近代以來這種主體反思性義務與權利[10],因而嚴格來說不同于法哲學中的倫理。
(二)從《邏輯學》看“倫理”篇的體系定位
如果通過《邏輯學》的構造來間接理解“倫理”篇的體系定位,那么考慮到《精神哲學》是一門應用邏輯學,“倫理”篇大致對應⑦于《邏輯學》的哪個部分呢?《法哲學原理》文本中常見的“理念”“概念”“活生生的善”等字眼,很容易讓人聯想到《邏輯學》的“概念論”,實際上亨利希、菲韋克就是這樣做的。亨利希早年便試圖用概念論中三種推論的模式看待國家內部的各種關系[3]232,而菲韋克則這樣概述自己的想法:“在自由的理念的意義上,倫理事物顯現為目的,顯現為活生生的善,顯現為成了現成世界和意識本性的概念。這里問題便被回溯到《邏輯學》概念論的整個第三部分,被回溯到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被回溯到從推論學說(尤其是各推論構成的體系)經過目的論和生命直至認識的理念與善的理念的統一的那條路。”⑧,[3]231
二人的這種做法看似有很多文本“依據”作為支撐,實則問題很大,最主要的問題是混淆了精神形態的具體運作方式與其體系地位,誤將倫理相對于抽象法、道德而言更深刻的思辨性混同于概念論在《邏輯學》中具有的最根本地位。不可否認,經過《邏輯學》錘煉的思辨思維,已經達到了絕對理念,由此再進入《自然哲學》與《精神哲學》,概念論中“推論”“理念”“概念”這類范疇的確可以運用于上述兩種“應用邏輯學”之中;但這并不意味著運用這些范疇的地方在體系地位上就對應于概念論或概念論第三部分了。否則黑格爾曾說所有的法都是“作為理念的自由”[1]80,照此說來豈非整個法哲學都要置于概念論層面?那么黑格爾為什么又說作為倫理形態之一的市民社會是抽象自由的層面、知性的層面[2]415-416?又比如黑格爾在《邏輯學》中說過一切理性的東西都是一個推論,推論可以充當理性的一般形式[11],這當然也不意味著一切合乎理性的東西在體系地位上只能“回溯”到概念論層面。再比如黑格爾在其法哲學中多次提及的概念與理念關系,其實可以運用于整個精神哲學上,“精神……是自然的真理,……在這個真理中自然消逝了,而精神則表明自己是達到了其自為存在的理念,這個理念的客體和主體都是概念”[12]。
這當然不是說他們喜愛穿鑿附會。促使他們有意忽略《精神哲學》中的絕對精神學說或《法哲學原理》中關于倫理作為“實體”的諸多論述,如此這般方枘圓鑿地將“倫理”篇錨定于概念論之上的,恐怕是他們自己的一套主體主義觀念。由于亨利希的研究成果極多,梳理這些成果的工作非本文所能容納,這里我們且以相對較晚近的菲韋克作品為例。他援引黑格爾的某些文本,將概念論第三部分(“理念”)進一步歸結為一種主體主義式的“概念的自我規定”,并反過來以此融攝整部《邏輯學》,將該書稱為“某種主體性哲學的奠基”[3]231-232,最后又順便擴及黑格爾的實踐哲學,“自我規定和自由(Selbstbestimmung und Freiheit)這些思想在本質上(以各不相同的方式)既塑造了邏輯學的論證路徑,也塑造了實踐哲學的論證路徑”[3]234。不出意外的是,基于這種將倫理定位于概念論的策略和以主體性自由為核心的立場,他還努力將宗教、藝術和哲學“沉降”到國家范疇內⑨,[3]248。菲韋克這種做法實際上等于以本質論消解了概念論,一定會賦予倫理形態某種不適當的絕對性地位,對于黑格爾法哲學而言是極不公正的。
筆者以為,倫理在整個《精神哲學》中的地位與《邏輯學》中的“現實性”相應,這一點有三個主要的依據:(1)僅就“倫理總論”而言,黑格爾反復以“實體”“現實”界定倫理、善⑩,以強調個體主體并不自外于實體,而是以實體為自身生活的根基,這恰恰是《邏輯學》的“現實性”范疇的題中應有之義。(2)在《邏輯學》中,“現實性”對于意識而言具有不容否定的絕對者地位,但那畢竟與概念論層面就絕對者本身而言的絕對者不可同日而語,而法哲學中關于倫理地位的論說也與此相似。表明這一點的一個明確的證據是,黑格爾在1818—1819年為先前的《哲學科學全書綱要》所寫的講座筆記中說倫理整體不是想象中的整體,而是古代家神和民族神意義上的“現實的神”(wirklicher Gott)。(3)與此相關,文中屢次提到希臘倫理世界及《安提戈涅》,這證明黑格爾依然以古代相對和諧的倫理實體狀態為典范。黑格爾在邏輯意義上向來以“實體”界定古希臘世界,在整體上并未以概念論視之。
(三)《精神哲學》中的“倫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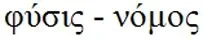
二、從“倫理總論”看倫理的重要性與局限性
作為“倫理”篇的導論,“倫理總論”與前兩篇(“抽象法”和“道德”)進行對照,主要論述的是倫理作為個人生活以及抽象法、道德之根據的實體性地位,以及由此對個人義務(及德性)與權利的關系帶來的影響。對于“倫理總論”部分的整體布局,半個多世紀以來長期深研黑格爾實踐哲學的荷蘭哲學家佩佩爾扎克有極為精當的分析[10]169-170,現按照他對各段落的分劃進行一個文本釋義。
(一)倫理概念(第142—143節)
法的所有形式(抽象法、道德、倫理)都屬于人力所能及的層面,是人站在有限者的立場上與他人人格、自己內心以及作為倫理實體的事情本身打交道的方式,因而在本質上都受制于《邏輯學》本質論揭示出的二元架構。在這個前提下,從具體運作方式(而不是體系地位)來看,在所有這些形式中,倫理又是最具思辨性的。這意味著客觀上對于讀者而言,自由理念的兩個環節(意志概念與作為其定在的特殊意志)不再像抽象法層面的各種法現象那樣直接過渡,也不再像道德層面那樣陷入內心自律與外部勢力之間的對立,而是有意識地、內在地相互蘊含并互為條件。但當事雙方的視角又有所不同:倫理生活的當事人明確意識到共同體是自身存在的根據、動力和目的;而共同體的存在又僅僅體現為每一個具體當事人的行動,此外無他,因而具體當事人并非它的他者,而是它本身的成全者。但又必須留意到,盡管倫理已是法的最具思辨性的形式,它畢竟還沒有達到概念論的層面,因此個人與共同體之間既互為條件,又可能發生矛盾。因此,黑格爾在1822—1823年的法哲學講座中才說:“因此實體的各環節就是意志的概念與其自內反思,但倫理的這些環節中的每一個已經是總體了,而且雙方已經是知識了,因而既是對它們的區別的知識,也是對它們的統一的知識。因此倫理就是意志的理念。”[15]
(二)倫理的客觀方面(第144—145節)
倫理從客觀方面來看就是一些超出了主觀意謂(Meinen)之上而自在自為存在的規律(Gesetzte)與機構(Einrichtungen),或者說是一些倫理勢力(sittliche M?chte)。黑格爾在144節“補充”中說安提戈涅宣稱倫理規律是一些無人知其從何而來的永恒東西[1]294,這表明倫理勢力對于個人而言是無法逾越的崇高之物,個人植根于它們之中,如同子女對于生養他們的父母或故鄉一般。
倫理勢力與個人的關系遠比抽象法和道德層面深刻:個人并不像受到抽象法管制那般與倫理勢力貌合神離,心生怨念卻無如之何,也并非僅僅在內心懷揣其萬分珍惜與崇敬的道德規律,實際上卻使得后者淪為抽象的異己之物,而是如同偶性從屬于實體、肢體從屬于整個有機身體一般,既服從倫理勢力,又僅僅在這勢力中才獲得自身的自由。這樣的自由并非個人的任性,而是依循倫理勢力中的必然性規定而來的。而通過倫理的必然性規定之所以能達致個人自由,根本原因在于倫理本身就是理念的規定的體系,是意志的合理性事物(das Vernünftige des Willens)[13]291[2]397。換句話說,倫理勢力不是外在的權力,而是使意志得以收束自身的內在形式與方向。它們規定了意志能理解的執行路徑,需要意志堅韌不拔地努力克服任性才得以持存。這便類似于我們中國人所謂的“持家之道”“治國之道”等,它們僅僅對于個人的利己私欲而言才是強制性的,而對于具有更深廣、更宏闊眼光的人而言,恰恰能在比個人私利更高的層面達成他們的自由。
(三)倫理的主觀方面(第146—155節)
1.倫理的主觀方面分為義務(德性)與權利兩個環節(第146—147節)
倫理實體與個人的自我意識內在融合在一起,而且除了這種自我意識之外別無其他存在方式,通過這種自我意識才達到對其自身的知識。所以從主觀角度來看,一方面倫理實體有其獨立且高于個人的存在,其堅固程度甚至超過了自然事物,因為自然事物僅限于外在的、個別的形態,而倫理實體的制約作用則深入人內心,令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另一方面倫理的種種規律和力量并非個體的外物,反而是個體的本質和依歸,因為主體只有在它們內部才有其特殊存在,才產生自身感(Selbstgefühl)。上述兩個方面中的前一方面指向義務,后一方面指向權利。
2.義務(德性)(第148-151節)
在倫理層面,義務(Pflicht)是個體在倫理實體那里感受到的約束力。與此相應,倫理的義務論是“倫理必然性圓圈的系統展開”,一種內在而連貫的義務論不是別的,只能是“國家內部因自由理念而成為必然的諸關系的展開”[1]297。因而作為個體之本質與依歸的種種倫理形式固然以“必然性”的形象制約著個體,而且這般的必然性并非零星、個別地出現,而是環環相扣、自成一體,但個體在其中感覺到的并非外來強力的威勢(抽象法義務),亦非符合遙遠目標的抽象的“應當”(道德義務),而是足以拔升自身的崇高使命(倫理義務)。
黑格爾還進一步闡發了這種能使人獲得解放(Befreiung)的義務的性質。只有對于單純遵從主觀好惡(“任意”)的“自然意志”而言,倫理義務才是一種強制和約束;但真正說來個體通過義務得到的乃是解放,因為義務令人擺脫自然沖動和抽象道德反思的牽絆。這種解放并不是順從主觀好惡,而是擺脫主觀好惡本身的局限,是沿著各種倫理形式拾級而上的“實體性自由”(substantiellen Freiheit)[1]297-298。在黑格爾心中,只有這種實體性自由才真正合乎“人的概念”。同樣的意思換一句話說就是,只有依照倫理規律生活的人才得其所哉[15]499。或者說,義務不是對自由的限制,而是對肯定性自由(affirmativen Freiheit)的贏獲[1]298。
正是在通過自覺實現倫理規律而獲得自由的意義上,才出現了適當考察德性(Tugend)與正直(Rechtschaffenheit)的時機。在抽象法層面,個體行動的標準唯有與其他個體保持外在的法律關系,因而只有合法與非法之別,談不上什么深度;到了道德層面,個體行動倒是具有了內心反思的深度,但內外兩分的格局注定了該行動與事情本身的隔離,因而該行動只有抽象的善良與邪惡之別;只有到了倫理層面,個體行動才既體現主體反思的自覺性,又具有客觀實體性,這便是我們通常說到“德性”與“正直”時不言而喻的內涵。在黑格爾看來,倫理體現在自然性格上便是德性,而德性就個體對義務的適應而言便是正直。就德性學說不僅僅是抽象的義務論,還包括性格與自然中的許多特殊因素而言,它是一部自然史。在堪稱“倫理世界”的古代,人們更喜歡談論德性,比如亞里士多德就因為倫理事物包含許多特殊因素,在個體身上總有多少之別,便探討作為中間狀態的德性;而現代人表面上不太談論德性,這并不意味著現代沒有德性了,而僅僅反映出德性一方面更受制于主體內心的道德反思,另一方面倫理在現代不那么體現為英雄式的個體形象,而采取了更具公共性的形式,成了公共領域中的職分。
倫理凝結為個體的現實生活與行事方式,便是倫常(Sitte)。正如大自然形成規律,自由的精神也產生倫常。因此倫常是人的第二自然,而教育便是引導人走向第二自然的過程。第二自然使得自然意志與主觀意志的對立消失,使精神不再受制于主觀念頭,也使理性的思維獲得自由,由此倫常成為人的定在,是一種貫穿性的靈魂、意義和現實,是展現為一個世界的活生生的現成精神。在倫常問題上,黑格爾提到“過”與“不及”的兩種做法,認為那兩種做法都不合適:一是中國人過于重視倫常,使得倫理事物成了外在規律;二是道德還算不上精神,因為它還沉陷在主體與事物本身的對立之中。
3.過渡節(第152節)
在個體克制了私意,向倫理的普遍東西提升自身的前提下,他的主體性不僅值得保留,甚至還成了倫理實體的絕對形式與實存現實(die existierende Wirklichkeit),由此倫理實體性便達致其正當狀態與效用。換句話說,主體性構成了自由概念的實存基礎。主體性在這個意義上持存的必要性,便是倫理“權利”。
4.權利(第153-154節)
黑格爾并不抽象孤立地看待權利,他強調主體無論對于其自由的追求,還是對于其特殊性的堅持,都只能在倫理實體中達成。主體之所以確信自己是自由的,而不陷入主觀空想,那是因為他處在客觀的倫理實體中,能在其中推進客觀的事務。由此這種確定性(Gewissheit)才能成為真理(Wahrheit),才能實現其內在普遍性(innere Allgemeinheit)。黑格爾還舉了一正一反兩個例子來強化這個意思:一個畢達哥拉斯派成員回答一位父親關于如何培養兒子有德性時說,讓他成為一個有良法的城邦的公民;而盧梭在《愛彌兒》中描繪的封閉隔離式教育則是黑格爾不敢茍同的,因為那違背了教育使個體權利與精神世界之整體相貫通的本質規定。
個體對其特殊性的權利也只有在倫理實體中才得到維持,因為特殊性不是別的,正是倫理實體的顯現。人或許會以為自己的特殊要求是他個人獨享的某種私利,殊不知要是沒有倫理實體,這種特殊要求既無法存在,也沒有意義。
5.義務與權利的統一(第155節)
那么在倫理層面,個人事務從其自覺向普遍東西提升的角度來看便是義務,從其維持自身特殊存在的角度來看便是權利,這兩個方面在根本上是一體的。我的義務就是我的權利,因為我通過義務助其成全的倫理實體只存在于千百萬個“我”的權利之中。這與抽象法和道德層面的情形形成鮮明對比:在抽象法層面,一人有了權利,另一人才有義務,一人與另一人在這個意義上外在地相互依賴;在道德層面,我自己所知、所愿、所選的權利只是“應當”與義務合一罷了。當然,黑格爾是很現實的,他不會抽象地陶醉于權利與義務合一的美好愿景,他也看到了階層與職分的區別導致權利與義務不斷細化的情形。另外,相反的情形他也考慮到了:奴隸這種徹底臣服的非人狀態,當然無所謂權利,也談不上什么義務。
(四)小結(第156節)
倫理實體包含自我意識同其概念的統一。黑格爾在這里還表明,他在倫理中提到的絕對者其實并不是在概念論層面而言的,而是在本質論層面“現實性”范疇的意義上而言的,因為它是希臘家族神、民族神一類的精神實體。
(五)“倫理”篇結構(第157節)
黑格爾對這一結構的勾畫已是眾所周知,此不贅述。其中有兩點值得注意:一是倫理層面的國家并非家庭、市民社會長期發展的歷史結果,它反而是家庭、市民社會的前提與根據;二是藝術、文學、科學雖然需要在國家內才能繁盛[2]412,但只是將后者作為生長環境,而并非以國家為根據,因而它們并非像菲韋克暗示的那樣那樣沉降為國家層面的公民自由。
結 語
在黑格爾去世之后,世界上各種“主義”的爭執不曾稍減。人們對他的法哲學的一個典型看法是,它太過理想了,以至顯得抽象甚至空洞。從左翼的角度來看,黑格爾沒有基于社會現實看問題,反而不適當地以越來越抽象的觀念之物(國家、上帝等)充當社會的根據,根本不符合與資本主義斗爭的需要;從當代市民社會的角度來看,人的自由以及個體與個體、個體與國家、個體與自然之間的關系才是核心問題,在黑格爾那里一切更高的東西都應該服從于對這些問題的考量。學者們即便強調倫理實體作為抽象法、道德之根據的地位,仍然會以沉降的方式消解絕對精神及其思辨性思維。
誠如佩佩爾扎克所言,法哲學原理展開的法的理念相對于世界上任何現成的法系而言都是一種理想,黑格爾雖然堅持該理想的現實性,但同時深知他那個時代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與他心目中真正的國家形象相符[10]172。作為實踐的產物,倫理既堅實又脆弱:堅實在于一旦時代趨勢合乎事情本身的秩序,便會很好地實現這種倫理;脆弱在于人們將目光聚焦于人力所能及的層面并追求自身利益時,黑格爾對精神的高級層面的描述并不實用,反而顯得抽象而不近人情。由此人們似乎有資格反問黑格爾:倫理的各種形態何以一定是精神的體現,何以一定是合乎理性的?難道這些形態不是又在兩個方向上瀕于瓦解的危險嗎?——在過于形式化的方向上,倫理可以被描述得合乎宇宙秩序,但那種“不接地氣”的秩序豈非虛懸而自行架空了?在過于質料化的方向上,個體如果過分專注于可見利益的分配,其他一概毋論,就有從倫理實體松脫下來的可能,此時倫理實體其實什么也不是[10]173。伍德基于類似的擔憂提出的辯難也頗具代表性,在《黑格爾的倫理思想》的末章(“現代倫理生活的各種難題”),伍德發現,黑格爾倫理理論的主要目的雖然是展示倫理秩序的合理性(rationality),但與此同時黑格爾也認識到兩個難題,這兩個難題是:窮人陷入的既無權利亦無義務的窘境與該目的相沖突;烏合之眾心態(rabble mentality)對于整個現代倫理,乃至對他的整個客觀精神理論要達到的根本目標,都是一個威脅。雖然黑格爾意欲肯定自己的那些原則,但正如在他的歷史哲學中每個時代原則的反思性自覺都會導致該原則的終結,他的法哲學的界限似乎也由此被揭示出來了[17]。
上述這些現象固然都是現代的核心難題,但筆者以為,黑格爾倫理學說對于現代生活首要的啟發并不在此。認為這種倫理學說最大的毛病是“不切實際”,這終究是以當代人的眼光在要求黑格爾。殊不知在黑格爾看來,恐怕這依然是一孔之見,因為如果片面強調倫理的實體性而忽視其局限性,最終忽視黑格爾整個精神哲學乃至整個哲學體系在貫通于宇宙秩序方面的根本旨趣,恐怕這種實體性最終也確立不起來。原因在于,如果人們不就上述更大的背景討論倫理的實體性,終歸會像對黑格爾法哲學的許多解讀那樣,將絕對精神沉降到倫理中。更糟糕的是,人們不會止步于此,而是進一步以非倫理的態度看待倫理,亦即使得家庭、社會、國家成為人的權力意志的支配對象。若以《邏輯學》的標準來衡量,這便是消解了概念論,落回本質論的封閉狀態。所謂“封閉”,指的是如果人們單純就事論事談論個人與倫理形態、社會與國家、義務與權利的關系,無論他們強調的是這些“對子”的“分”還是“合”,都只是固化人的利益,沒有達到黑格爾超邁于時代之上的遠見。追求“天理”抑或“人欲”、開放的宇宙秩序抑或封閉的人造世界圖景,這恐怕是人類永恒的難題。而在這個問題上,黑格爾倫理學說有著整個近現代哲學中都極為罕見的潛力,尚待抉發。
注 釋:
①《法哲學原理》第151節正文曾將倫理實體界定為“作為一個世界而活生生的和現成的精神”。黑格爾在另一處也說過,倫理是一個世界。
②當然馬克思并未全盤接受黑格爾的框架,他是在他自己鍛造出的全新社會概念的尺度下討論這個問題的。
③這個概念在黑格爾去世后還一直困擾學界,以致學者們在它的譯名上也很犯難,現有的英譯名有“ethical life”(A.Wood)、“customariness”(R.Pippin),日譯名有“公の秩序又は善良の風俗”(公序良俗),中譯名有“倫理”(范揚、張企泰)、“倫理法”(鄧安慶)等。
④鑒于耶拿前期以及更早時期的倫理思想尚未成熟,暫不納入本文考量之內。
⑤或簡稱三種形態,如果將前三種(感性、知覺、知性)統稱為“意識”的話。
⑥這當然只是相對于中世紀與近代而言,細察希臘與羅馬倫理形態內部則并非鐵板一塊。希臘人直接隸屬于具體的倫理勢力,而這些倫理勢力相互之間很可能是對立的;羅馬時代的人服從的是抽象的法權,而皇帝只是相對虛置的。
⑦這當然不意味著《邏輯學》的每一個范疇死板對應于《法哲學原理》中的一種倫理形態,而只是以前者各范疇之間的相互關系為參照大致理解后者的各種倫理形態的相互關系,對兩部著作內部結構的考察應先于對它們之間參照關系的考察。
⑧菲韋克對邏輯學的概述跳躍閃爍,將很多不同層面混同起來,比如“認識理念”(die Idee des Erkennens)在黑格爾那里是涵括了真的理念與善的理念的,而非如菲韋克所說的與善的理念并列;目的論與生命也不在一個層面,菲韋克卻將二者并列;而概念論第三部分雖然是“主觀性與客觀性的統一”(理念),卻不可與菲韋克所謂的“那條路”并提,因為后者其實是整個概念論。
⑨在菲韋克筆下,道德、市民社會、宗教、藝術和科學都被還原為公民的權利:良心自由,寬容,宗教自由,藝術和科學的自由。
⑩第142節正文,第144節正文與補充,第145節正文與補充,第146節正文,第147節正文,第148節正文,第149節正文,第151節正文與補充,第152節正文,第153節正文,第154節正文,第155節箋注,第156節正文與補充,第157節正文與箋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