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
老海
青 澀
那時候,他是“可教子女”,貧下中農的孩子如同避瘟疫一樣躲著他,唯有鄰居家的英子不嫌棄,照樣和他一起玩兒。
他們在一起最常玩兒的游戲是“抓子兒”。“子兒”一共七個,玩兒時將六個子兒先撒開在地上,然后將右手中的一個子兒拋向空中,將地上的子兒按每次一個、二個、三個的順序抓起;每抓一次子兒須把拋向空中的那個子兒接著,三次全抓接住就算成功了。
英子有一副她親手制作的子兒,非常好看。她把瓦碴片子先砸得如大拇指頭肚大小,又在青石上磨得光滑如玉,呈扁圓狀,像極了麥熟時節的青杏兒。玩兒得久了,他們手上的汗液把那子兒浸潤得黑明閃亮,就像收藏家們說的,有了包漿。
看英子靈巧的小手像蝴蝶一樣上下翻飛,真是一種享受。
他抓子兒不行,卻喜歡做些小玩意兒。村上來了木匠給誰家打制結婚家具,他就會跑去癡癡看,不忍離去。父親見他對木工有興趣,就給他置買了鋸斧刨等工具。他用一塊棗木板做了一個精美的小匣子,四角還雕了云鉤圖案。他把那只棗木匣子送給英子裝子兒。那七顆青子兒裝在那只紅亮結實的棗木匣子里,真是珠聯璧合,相得益彰。
一天上午,他和英子結伴兒去剜豬菜,在西河坡上發現了一大片長得蓬勃茂盛的野苜蓿,那是豬們長膘的好青飼料。他們跑過去連割帶拽,很快就把籃子塞滿了。著沉甸甸的籃子上了溝坎,看離晌午還早,他們決定在地堰上一棵濃蔭厚重的樹下休息休息,抓子兒玩兒。
不經意間一抬頭,他看到藏露在枝葉間的許多略顯發白的青杏兒。
“看!”他禁不住喊道,“這杏兒結得多稠啊!”
“我上去摘幾個嘗嘗能不能吃。”英子說。
“這是誰家的?”
“俺家的。”
正疑惑間,英子早已脫了鞋,赤著腳噌噌噌幾下就上去了。英子在樹上猴子一樣靈巧地攀援騰挪,摘了好些杏子裝在口袋里,還挑了個黃點兒的啃了一口。
“好吃嗎?”在樹下的他喉嚨里像要伸出一只手。
“李子哥,接著!”
猝不及防地,樹上就落下了一陣杏雨。
看著他先是挨砸抱頭鼠竄接著又手忙腳亂撿杏兒的狼狽樣,英子在樹上咯咯咯地笑了。
他手上抓著從地上撿起的一大把青杏兒,汗漬麻花地仰臉看著在樹上搞惡作劇的英子。金色的陽光從綠色葉片的縫隙間透過,灑在她好看的瓜子臉上,斑斑駁駁。微風將一綹黑亮的鬢發吹拂到了她紅蘋果樣的臉頰上。
咕咚!仿佛被什么東西擊中了,他一屁股跌坐到了樹下的草地上。
“李子哥,杏兒好吃嗎?”樹上的英子還在揚揚得意。
他慌忙咬了一口手中的青杏兒,啊呀!他的嘴張得老大——酸,酸得直倒牙;酸中還透著澀,酸澀酸澀的。
看著他齜牙咧嘴的樣子,樹上的英子笑得更厲害了。
多年以后,他舌頭上的味蕾日漸麻木,但仍記得那青杏兒的酸澀。雖不香甜,卻最新鮮。那種味道有一個名字,叫青澀。
青澀的味道。
再后來,他上了大學,在城里娶妻生子。英子也嫁給了他的高中同學要武。要武籃球打得好,被那年來公社征兵期間到高中學打籃球的部隊軍官看中帶走了。后來那個軍官官越做越大,要武的官級也跟著往上升到了副團。在全民“下海”經商那年月,軍官讓要武負責后勤調運煤的項目,要武做得風生水起。有了經商經驗和人脈關系后,要武干脆復員轉業,自己成立了公司,不幾年就發了大財,在北京買了房、落了戶。
彈指一揮,三十年嗖的一聲就過去了。
前幾年他到北京去開會,開完會給英子家打了電話。
“李子哥呀?聽不出來了……”
他坐地鐵一號線到蘋果園站下車。電梯剛升到地面,就聽到一聲“李子哥”,他看到英子還是那么苗條,一點兒沒胖,只是臉色顯出歷經滄桑,再不是當年的少女模樣了。
英子把他帶到一輛黑色的轎車前。司機開著車子七拐八繞,走了好遠,最后在一個僻靜的部隊家屬大院停了下來。他隨她上樓,開門。
“孩子呢?”他問。
“上學去了。”
“該上高中了吧?”
“嗯,高一了。你的呢?”
“高三了,明年考大學。”
“他準能考個好大學,你小時候那么聰明,他肯定像你。”
…………
看看快中午了,他說:“要武中午不回來吃飯嗎?”
“哦,他出差了……”英子沒有看他。他覺察到她有點兒閃爍其詞。
“去哪兒了?我還想這次來能見到老同學呢。”
“去新疆、西藏那邊了,得一陣子才能回來。”英子佯裝看了一眼墻上的電子表,岔開話題,“哎呀,看光顧說話,都十二點了,咱們去吃飯吧?院里有餐廳,還有烤鴨。”
“不去食堂吃了吧,你給我做點兒糊涂面,這幾天開會大魚大肉都吃夠了。”
英子笑了:“李子哥到北京也沒忘記咱老家的糊涂面。”
“是呀,在城市多少年,還是覺得家鄉的糊涂面好吃。”
半個小時后,英子把她做好的糊涂面端了上來。他吃了一口,說:“你做的糊涂面真好吃。”
“真的嗎?好吃就多吃點兒。”
其實他知道自己說了謊,他已吃不出當年的味道了。
吃過飯又閑話了一會兒后,他起身告辭,說已買好了臥鋪票,還要回去上班呢。英子見挽留不住,只好唏噓著和司機送他到地鐵站。分手時,她給他一個手帕包著的方盒。
“是什么?”他問。
“上了車再看。”她說。
在地鐵車廂的椅子上剛坐定,他就迫不及待地打開了那方手帕。啊!竟是他當年給她做的那只棗木匣,里面還裝著她砸磨的那副七顆如青杏兒一樣的橢圓形瓦子兒。
地鐵列車在幽暗的隧道里嘩啦啦地向前疾行,裹風挾電。車廂里的人影被隧道墻上的燈光耀得一明一滅,像是夢幻。他轉過身去,用手抹了一把,又抹了一把。
他臉上的“濕蟲子”一直在往下爬。
梅 桃
他六十歲夢到了六歲時的樣子。
那時候,因成分不好,四叔只得委屈入贅到了后山的梅桃溝。那天四叔上街趕集回來經過他們村,說要帶他去梅桃溝玩兒。四叔引誘他說,他們那里有好多好吃的水果,有梅子、桃子,還有大西瓜。前兩樣他們這兒也有,唯有西瓜讓他動了心。他最愛吃大西瓜。
經過母親同意后,他就跟著四叔走。
記憶里,四叔牽著他的手走了好遠,才到了嶺上的瓜田。四叔挑了一個圓滾滾的大西瓜后,才又牽著他的手下坡,回了家——四叔在梅桃溝的家。
梅桃溝名副其實,院子邊有一棵梅子樹、兩棵桃樹。溝底有一條小溪,汩汩流淌。這個風景幽美的梅桃溝其實就四叔這一戶人家。當然戶主不是四叔,而是他老丈人——一個滿臉皺紋的老頭兒。其實老頭兒并不老,也不過四十來歲。
后來才知道,梅桃溝原來沒住人,四叔老丈人一家是從外地逃難到這里的。那時老丈人正年輕,就在這里打了兩孔窯洞住下來,幾年后又蓋了兩間草房。他們兩口兒有三個閨女,沒有兒子,這才把成分高的四叔招贅來當上門女婿。
晚飯吃的什么他不記得了,只記得四叔殺的那個有著美麗黑色條紋的綠西瓜真甜!他吃得狼吞虎咽,紅紅的瓜汁淌了他圓滾滾的一肚皮子。
奇怪的是,四叔老丈人家和他年齡差不多大的二閨女和三閨女卻不怎么吃。她們好奇地看著他,像是看天外來客。她們還把自己的西瓜讓給他吃。
晚上他就睡在那間放了許多農具的草屋里。也許是跑了太遠的路,他一挨著枕頭就睡著了。直到屁股上挨了一巴掌醒來后,他才知天已大亮。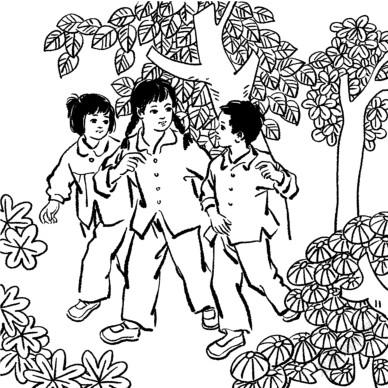
“看看!”四叔提著那條他蓋的薄被,佯裝惱怒。他揉了揉眼,才瞅清上面被他畫上了一幅黑陰陰的“水國地圖”。四叔并沒有多責怪,把被子搭在門外的梅子樹上曬著,就背著糞簍去了瓜園。
他羞愧難當,惴惴不安。
那兩個女孩兒并沒有笑話他,反而像什么也沒發生似的跑過來拉著他的手,和他玩耍。二閨女噌噌地爬到樹上,摘了一大把青梅子給他。他咬了一口,酸得直倒牙,立即就扔掉了。姐妹倆看著他吸溜嘴的樣子,咯咯笑了。
“你叫什么?”
“梅子。”
“你叫什么?”
“桃子。你呢?”
“李子。”
哈!三種水果。
也許是沒有其他玩伴兒的緣故,兩個女孩兒對他好極了。她們帶他跑到山坡上摘時鮮的野果子吃,杏子、五味子、枸杞子、山葡萄……
正中午時,草叢里的綠蚰子在烈日下叫得正歡。他們悄悄靠近,用鞋子一扣一個,捉回關進用高粱稈扎的蚰子籠里,用南瓜花喂它們。它們吃飽了肚子,就日夜叫個不停。二閨女把蚰子籠掛在草屋的房梁上。她說有蚰子叫,晚上睡覺蚊子就不敢咬他了。
果然。
沒有誰任命,也沒有經過選舉,二閨女梅子自然就成了他們仨的首領。梅子比他大一歲,顯得很老練。加之他是客人,在這里兩眼一抹黑,什么也不知道,因而他們到哪里玩兒、怎么玩兒,他都是聽她的。比他小一歲的三閨女桃子,更是應聲蟲、跟屁蛋兒,對她二姐的話言聽計從。
一天中午,太陽正紅。大人們都下地干活兒了,院子里靜悄悄的。他們沒有再去捉蚰子,而是到溝底的小溪邊摸螃蟹。他們玩得太投入,弄濕了衣服,就跑回來把衣服脫了搭在樹上曬。讓他沒有想到的是,不知怎么的,他就被姐妹倆“綁架”進了那間草屋里。他們光著身子,并排躺在溜光的席炕上。姐妹倆一邊一個,把他夾在中間,他們就那樣裸體擠挨著。
梅子說:“閉上眼睛,能飛起來。”
他閉上眼睛,過了一會兒,感到真要飛起來了。
他用力扇動胳膊,果然飛了起來……
他醒了。許久,才意識到自己躺在城市的床上。他怔怔地看著若隱若現的天花板,看著虛空,回味著夢里的事——一點兒不像是做夢。
那是真的,那不是夢。那是藍天白云一樣的記憶,干干凈凈。
到天明的時候,他做出了一個決定,去找找那姐妹倆。應該能找得到,問問老家里的人,問問父親。七歲那年他跟著父親上了鎮街“完小”。四叔一家在兩年后也跟著他老丈人回山西老家去了。他們走時到鎮街坐車,四叔還帶著姐妹倆去了“完小”。在“完小”當老師的父親還給他們端來了“最后的午餐”。
兩年不見,姐妹倆似乎長高了,也更漂亮了,同時卻也陌生了。她們沒再來拉他的手,而是怯生生地看著他,羞紅了臉。臨走時她們一步三回頭戀戀不舍的樣子,至今還清晰地刻印在他的腦屏上。
尤其是梅子,他看到她眼睛里泛出了亮晶晶的東西。
[責任編輯 王彥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