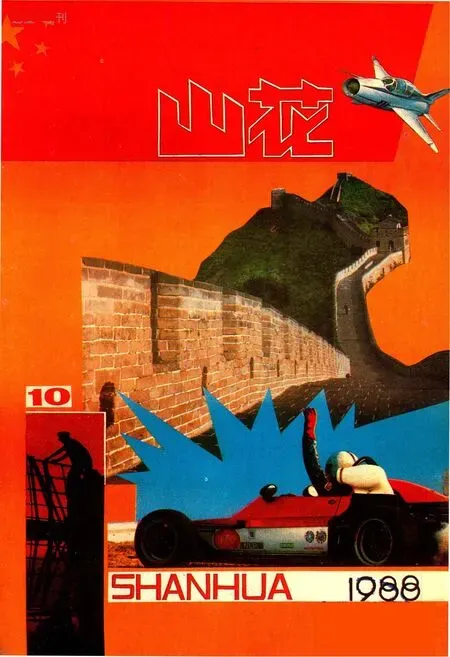奪路
宋離人
我在街角抽完兩支煙,沒打算抽第三支。約莫一刻鐘,王曼麗出來了。我朝她揮手示意,她看見了,一邊往羽絨服里伸胳膊,一邊“多多多”地快步走來。高跟鞋發出的聲音挺悅耳。王曼麗說,等久了吧,老路非逼我喝一大杯,否則不讓走。你看我臉是不是很紅?我借著沿街櫥窗的燈光看了王曼麗一眼,說還好,看不出來。王曼麗吐出一口酒氣,兩只手互插在袖管里,朝我一偏頭說,走吧。我說,去哪?王曼麗說,你什么記性?說好陪我去醫院看我媽,今天輪到我陪,不陪不行。我想起來了。吃飯的時候,王曼麗接了幾通電話,有一個是她嫂子的。掛了電話后,她悄悄跟我說過,差不多了,我先撤,今晚輪我陪我媽。我其實也覺得沒多大意思,老路叫來的幾個人不熟悉。有個叫玲姐的見過幾次,每次吃飯,老路都會喊上她,四十好幾,濃墨重彩的,粘著老長的假睫毛,說話憋著嗓子,也不大愛理人,就和老路耳語說話。我說我也想走。王曼麗說,感覺你有事。我說,沒啥事。王曼麗說,燉羊肉不錯,要不你再吃兩塊。我說,最近牙疼,嚼著費勁。王曼麗說,趕不上你媽的手藝,你媽燒羊肉是一絕。說著看我一眼,對不起,不該提你媽。我說,沒事,我媽不在了,但滋味還在,還有人記得。王曼麗說,是這個意思,你該好好的,讓她在那邊放心。我說, 我吧還行,主要是身體還在恢復中,腦仁里總感覺有淤血似的,不清澈,沒好透,吃啥都不香。王曼麗隔一會說,一會他們要去歌廳,你別去了,都能理解。我說一會我就走。王曼麗說,也行,你在門口等我,我們一起走。王曼麗又說了幾句話,聲音嘈雜,我也沒聽清。這時聽她說是要我陪她去醫院,我也沒反對,反正就我一人,回去也不能怎么樣,誰也不會在乎。
我們一起朝向陽路上的第五醫院走去,不遠,步行也就十分鐘左右。今晚聚餐的地點也是王曼麗選的,可能也考慮了這一步。街上沒什么人,他們都空手縮著腦袋,一些店面張貼著迎新年的酬賓廣告,但也鮮有顧客,離過年還有一個月,最主要是天冷。前幾天的一場雪還沒融化干凈,街面背陰的地方潮濕一片。路上,王曼麗問我沒事吧。我說沒事。她說見我整晚上話也不多,感覺和以前有所不同。我說,其實也不用我說什么,大家說得很好,也插不上嘴。王曼麗說,有沒有發現啥?我說,你說的啥是啥?王曼麗說,老路和陳玲啊,眉來眼去的。我說,他們沒事吧,看著挺近。王曼麗說,可不是一般的近,老路喝水的杯子都是茶垢,幾年沒洗了都,黑里巴唧的,人家端起來就喝,跟自家的一樣,膈應死我了。我說,這有啥,朋友交情深唄。王曼麗伸手拍我一下,去你的,夏天有一次,他們兩人一起吃半個西瓜,記得不,就一個小勺,你一口我一口的,搶著舔呢。我說,我還抽煙呢,一嘴煙味,不是也有人喜歡往上湊?王曼麗又拍我一下,這回下手有些重,我一個踉蹌。邊上沖出一個騎車的,差點撞上,車子拐了幾拐,好歹穩住了。騎車的回頭翻我一白眼,嘟囔了幾句,走了。
三年前,我結束了七年的婚姻。相愛是開始幾年的事,感覺對路,相逢的浪花翻滾,結果生下了兒子,隨后就是乏善可陳的日子的疊加。我媽的重病消耗了我太多的精力和捉襟見肘的生活熱情,加上彼此的性格暗礁裸露出來,都好強,我們開始了爭吵,起先是為了某件細小的事,我們都很隱忍,都知道踩滅哧哧冒煙的導火索,但結果卻是保留了數量可觀的火藥包,這直接導致了更大當量的爆炸。那陣子,我們都覺得委屈,都需要被安慰被理解,都想從對方身上索取點什么,但我們都錯了。她一直尋找著那些幸存的尚能繼續點著的引信。她都保存在自己的內心深處,任何一點煩悶和郁結都會成為那引信再次點燃的可能。那是一段灰色的記憶,壓抑而沉重。我們無話可說,家庭生活成為舞臺上的啞劇,也許可以說是‘冷暴力。我們不愿意再見到對方,只有分別讓彼此輕松和愉快。相愛無從談起,而相處都變得劍拔弩張。在借了一筆巨大的醫療費之后,我媽病情有所緩解。那天,我安頓好我媽,匆匆趕回家。她在路口等我。她事先向單位請了假,我們打了一輛車,去民政局把婚離了。出來的時候,她說,你隨時都可以來家看孩子,房子我先住著,以后都是孩子的。我說,對不起,沒讓你過好日子。她說,也不怨你,我想過了,都是命,其實吧,誰也沒錯,就是根本不該認識,即便認識也只能做朋友,做夫妻大錯特錯。我說,也是,彼此都有自己的路,獨自走得很好,和人并肩就磕絆,摔倒的時候還拖累對方,彼此都走不好。她說,總結得到位,是這個意思。我說,誰也別占道,各人走好就是。
我就跟我媽住,本來我就一直在照顧她。馬尚武工傷走了五年了,活著的時候天天唉聲嘆氣,死了以后倒是和顏悅色地占據著一面墻。我媽很快也覺察出來了。可她也不能說什么,她的病在喉嚨里,那里插著一根喂食的管子。她也想死,可死不成,總有一些藥物維持著。醒來的時候,她就盯著墻上的馬尚武,眼神里都是怨恨,沒有淚,流光了似的,干澀而空洞。
王曼麗是我的高中同學,在我之前離的婚。同學群里離婚的很多,一點也不奇怪。有人建議把群名稱改為‘單身群,當然也就是一個玩笑。我在群里基本不說話,后來嫌煩,直接屏蔽了消息。我就感覺王曼麗很活躍,常在群里組織拼飯會餐啥的。她在稅務局上班,迎來送往,認識的人挺多,三教九流的,挺鬧騰。我后來參加了幾次,主要是拗不過王曼麗。有一次,王曼麗又約我,說陪她去參加一個朋友的生日宴。那天王曼麗化了妝,收拾得挺出彩,粉脂都用上了,連腳趾上都涂了指甲油。朋友叫路正彬,也就是老路。生日宴辦了三桌,全都是混跡于大眾舞廳的‘舞搭子,成雙成對,男的清一色緊身馬甲,脖子上扎著領結,女的一色大紅大綠,裹著各種披肩圍巾,讓人像置身于蝴蝶館。王曼麗逢人便介紹我是他的新男友,走到哪都拽著我的胳膊,演得挺像。席間喝了幾杯酒,主要是老路頻繁敬酒,壽星酒,沾福氣,又祝我抱得美人歸啥的,弄得蠻像那么回事。我也來者不拒,這一陣子,諸事不順,借酒消愁得了。
酒喝多了話多。王曼麗也一樣。王曼麗偷偷跟我說,老路一直在追她,可她沒感覺,老路人品不正,喜歡沾花惹草。最近好像又有了新目標,一個叫陳玲的,不知為啥沒來,老路邊上留著座位,估計是為陳玲留的。飯后還有節目,人民飯店的夜場舞池,老路包下來了,沒準陳玲一會就來。正說著話,老路湊過來說,小馬兄弟,我們初次見面,覺得面熟,親切,來,再整一個。我說,我敬路哥。碰杯喝完,老路嬉笑說,我說王曼麗怎么死活不跟我好呢,原來早就騎上了小駿馬。老路話里有話,一桌人狂笑起來,笑聲五花八門的。王曼麗站起來指著老路說,我來爆料,老路你聽好了,要不是那天你暴露了真面目,我還真就同意你了。大家說,別賣關子了,老路啥面目,檢舉出來。王曼麗看著老路說,那天在運河邊戶外活動,你熱得一頭臭汗,在樹林子歇涼的時候,一根樹杈幫了我大忙。滿桌人支楞著耳朵等待下文。王曼麗說,老路你記得不?你鉆樹林子,一根樹杈把你的假發套子扯掉了,掛在樹枝上像個倒過來的鳥窩,你光著個大禿瓢,像個什么似的,嚇我一跳。滿桌飚起一番狂笑,分貝極高,感覺屋頂的燈都被震得搖晃起來了。老路一張臉紅紫一片,哭笑不得。我后來對王曼麗說,你夠損的,一點情面不講。王曼麗說,總算逮到機會了,哼。飯局要結束的時候,陳玲來了。王曼麗在桌下踢我,說飯后果拼來了。陳玲手里抱著半個西瓜走到老路跟前。陳玲說,給你帶禮物來了。老路忙接過,又殷勤招呼她就座。老路要來一把勺子,遞給陳玲。
散場后,我和王曼麗沒打車。我們打算步行去人民飯店。江邊的夜風涼爽,清風拂面,酒氣也跟著隨風散去大半。路上我問王曼麗,為什么不再找一個?王曼麗說,不想將就,高貴的獨身比渾噩的婚姻強。我說,得了吧,生活其實就是彼此將就。她說,你為什么不將就,要離?我說,我想將就,可她不愿意,要彼此將就才行。她說,狗屁。有一陣,我們沒再說話,都在看江上的燈火。走了一會,王曼麗伸手挽住我,頭也不知不覺地靠上我的胳膊。她比我矮一頭,我盯著路上一高一矮的兩個斜影,心里霎時暗潮涌動。
那天,我們還是去了人民飯店。我和王曼麗摟在一起跳了一晚上的舞,三步四步,快的慢的,全來了一遍,有一陣,王曼麗把臉也貼了上來……十點剛過,王曼麗出去了一小會,我以為她去洗手間補妝啥的,舞池里雖說有冷氣,但效果不佳,總有人進進出出。王曼麗進來后,遞給我一包煙。我說,挺大氣啊,我還有,王曼麗一笑說,犒賞你的。再跳的時候,她才說了出去的目的。她在五樓要了一個房間,不打算回去。我說,你膽子不小啊。她說,你要是覺得為難,也不勉強。我說,也確實累了,折騰著大半夜的,泡個澡正好。王曼麗突然在我臉上親了一口……
王曼麗這人心蠻善良。高中有一年,她坐在我前面,有次我穿著我媽的一件舊襖子,我媽改了改,式樣趨于男式,但一排大紐扣沒換,留著女式的痕跡。那天,一顆紐扣掉了,紐扣挺大,像一枚大棋子,落在了王曼麗的座位下面。王曼麗撿起來,沒還給我。下午上課前,她不知從哪找來一根針。沒線。她從自己的衣服上扯下鎖邊的黑線,硬是幫我把扣子縫好了。這事我一直記得。后來我還寫了作文,夸獎了她的熱心。周末我回家后,讓我媽給換,我媽東拼西湊,總算找齊了五顆……
那晚,我沒和王曼麗在一起。她感覺我不夠主動,或者認為我還在離婚的陰影里,沒完全放開自己。我說,主要是想起你對我的好了,怕害了你,對不起。王曼麗說,啥對得起對不起的,這樣挺好,交往起來沒陰影。我說,主要是我的處境,怕磕絆你。王曼麗說,你想多了。我又說,我媽不見我回去,會睡不著,一準,她還在等我。
王曼麗怔怔地看著我說,你走吧。我一會也走。
醫院對門的花店還開著門。我說,要不我買束花吧,有日子沒見你媽了。王曼麗說,免了吧,大半夜的,估計也認不出你。我說,這幾年,你媽做了幾次手術,都挺過來了,夠堅強的。王曼麗說,最見不得老人受苦,感覺人老了就要開膛剖肚這事特別沒意思。我說,也有從不看病的。王曼麗說,那是人家從不把病當回事,我媽可不行,一點不舒服就鬧,住院吧,得天天要人陪,否則沒好臉色……我想想說,我想到我媽了,一輩子規規矩矩,不多說一句,到頭來還是吃苦受累的命,可憐……王曼麗說,對了,改天我買束花陪你去看她。我想了一下,扯回話題說,真不用買?王曼麗說,留著過年買吧,年三十去我家過,吃餃子。我說,我去算啥,名不正言不順的。王曼麗說,沒把你當外人。王曼麗她媽教過我高中的政治課。我們兩家都是黃泥壩閥門廠的,廠里建有子弟學校,設高中部,起先王曼麗在一班,我在二班,高三時合并在了一起。她媽姓葉,叫什么我忘了,都喊葉老師。葉老師上課總講得頭頭是道,口水飛濺,齊耳短發飛揚起來,仿佛那件灰色舊外套的兩個大口袋也跟著充盈起來。我們都愛上葉老師的課,都喜歡她婉轉頓挫充滿激情的講授,都挺振奮,感覺出了校門就是坦途大道,前程似錦。但是后來,廠子不行了,學校撤銷了,葉老師也光榮退休了。
內科病房在五樓。四人間,兩兩相對,空間還挺大,至少比外科樓的條件要好,是新蓋的。王曼麗她媽住門口頭一張床,床側架著輸液瓶。她媽蓋得嚴實,露一張白皙的老臉,臉上盡是褶子。聽見響聲,她微張著眼睛看著我們。王曼麗說,媽,我來了,嫂子走了吧?我跟過去說,葉老師,我來看您了,還認得出我嗎?她媽盯著我看了一會,滿頭的花白頭發顫了顫,輕聲嘟噥,認識,我學生。王曼麗對我說,我媽不管認不認識,開頭就這一句。她媽說,勞你大駕,還記得來看我,你夠忙的。我說,我有啥忙?閑人一個,多的就是時間。王曼麗說,別跟她說廢話,這回開胸,傷了元氣,人都認不全,見誰都覺得是發了大財的學生。我說,你媽抬舉我了,全身統共不到三十塊錢。王曼麗說,那你還買花。我說,一碼歸一碼。王曼麗說,你找凳子坐會,我去打水,晚了水就涼了。我坐下,四周看了看。剩下三張床上都躺著人,隔簾都拉著,也看不太清,也有陪護的家屬,默不作聲,各自坐著,盯著手機看。醫院這里的環境我熟悉,我媽曾在外科樓住過。我上了一趟廁所,出來的時候,我去陽臺上看了看,窗子都緊閉著,我推開窗,窗子設有限位,兩拳大小的寬度。窗外是醫院的停車場,一片漆黑。對面的外科樓上上下下充盈著燈光,七樓的樓道窗里還有人在抽煙,煙頭明滅著。我記得窗臺上有個摔壞的瓷碗,里面盛滿了煙頭。
我返身坐下。葉老師動了一下,睜開眼。我站起來說,怎么了,哪里不舒服?葉老師眼瞄著輸液瓶。我說,吊完還有一會,您先睡會。葉老師說,針漏水了。我查看起她的手背,沒覺出異樣,滴管也正常。沒漏,好著呢。我說,有我看著,放心吧。葉老師說,剛才護士來扎過,漏了不少,劑量不足了,答應補半瓶。我心說,這老太太,做夢吧。王曼麗去了老大一會才回來,水瓶還是空著。開水器說是壞了,溫度不夠,正修呢。王曼麗說完朝我示意,我跟她出門。王曼麗說,你得多待一會,我要出去一趟,非去不可,一份稅務報表今晚非交不可,我全給忘了,領導剛來電話,對我一通批。我說,沒事,我守著你媽。王曼麗說,就只拔針,完了叫值班護士。我說,我都懂,不用你說。王曼麗說,那是。你等我。我說,行,快去快回。王曼麗說,不用跟我媽說。我說,開水房在哪?王曼麗手一指走廊盡頭說,牌子上寫著,走到頭就能看見。王曼麗走出沒幾步,我突然腦子一熱叫了一聲。王曼麗回頭說,還有啥交代的?我想了一下,又覺得沒必要說,揮揮手,讓她走了。
回房間重新坐下,葉老師閉著眼,眼皮不停顫動,料想也沒睡著。果然沒一會,她抽搐了一下,睜開眼,一眨不眨地看著我。——你是小馬?你怎么來了?——葉老師,您總算記得我了,我是小馬,馬一鳴,您的學生。——我記得你,上課老愛提問,想把我難住,但每次都說不贏我。——我可不記得有這事,您說笑吧?——在哪發財?開了幾家連鎖店?我想起之前王曼麗說她媽一會清醒一會糊涂的話,就順嘴說,暫時還不想擴大業務,閑著,玩半年再看。葉老師說,就差你的那所學校了,校址都選好了,資金遲遲不到位,學生們都在露天上課呢。我接著說,您放心,您給的賬號我都鎖在密碼箱呢。葉老師說,金屋藏嬌,沒準你的錢都養小三了。我說,那不會,我可是正派人,不搞缺德事。葉老師說,給你戴上手銬你就交代了,電視上沒少見。我噗呲一笑,心說這老太也忒能信口開河了,明明糊涂人,滿嘴呼而嗨。葉老師喘一口粗氣,乜我一眼說,你和那女的斷沒斷?鬧得滿城風雨,名聲掃地,多少功名成就化為烏有,一場空,這個教訓要牢記。邊上幾個陪床的紛紛側目,裝作無意地瞟向我。我只好伏身說,建學校的錢我都給您留著呢,沒瞎用,最多半月就打給您,還有啊,奠基儀式那天一定請您,校名還得您親自命名。葉老師說,名兒就叫同福。我說,好聽。葉老師說,我還要上課。我說,那是,那是,葉老師抬起手,我趕緊摁住說,正吊水呢,握手就不必了,老驥伏櫪,向您學習。葉老師放下手臂說,今兒話多了,讓人嫌棄,我口渴,喝水。我這才想起我的職責,吐口氣提著水瓶匆匆出門。走道里晃悠著幾個蹣跚的背影,大都沒了頭發。醫生囑咐過,術后不能直接給水,只能用濕棉簽抹嘴唇。我打來開水,往涼水杯里續了點水,好不容易找來一根棉簽,往葉老師枯澀的嘴唇上抹,她一口咬住,嚇我一跳。葉老師說,吸管。我回過神來,這是內科病房。我端起杯子,插上一根吸管。葉老師側歪著腦袋嘬了幾口,喉嚨深處發出吞咽的聲響,像深井里落下的石塊。她吐出吸管說,你過細了。我擦拭她萎縮的嘴角。她晃晃腦袋,我替她墊好枕頭。她說,一天掛八瓶,連掛七天,罪不好受,但能好起來。我說,你這狀態,不用七天就能下地。她閉上眼不理我,我梳理著她的白發,像安撫一只蒼老的貓。
不知不覺過了一小時,王曼麗發來微信,說快忙完了,正在打印,讓我再等一會,又說順路給我帶羊肉串。我沒回她,看著窗玻璃上的另一間屋子,一個男人如我一樣坐在床邊,悵然若失地和我對望……
……我看見李小妹坐在床沿。我以為她躺久了,想坐起來。我猜想她的腹部一定會很疼,那里七小時之前被劃了一個口子。一截壞死的腸子被取出來。但她一聲不吭自己坐了起來。我說,你老實點躺著,醫生不讓你動。李小妹搖搖頭說,腸子需要蠕動,好得快。我說,你躺著腸子也會蠕動。李小妹說,我渴了。我說,不用你動手,有我。我跟單位說好了,準我半個月假,不扣錢。李小妹說,那也不用天天來,拖家帶口的,多照顧孩子。我說,不用我管,孩子有媽管呢。李小妹說,棉簽在抽屜里,只能蘸水濕濕嘴唇。我扶著李小妹躺下。濕了棉簽涂抹她的嘴唇。李小妹說,給你添累了,大半夜的,外面下雪了吧?我說,看你說的,你是誰?我能不管你嗎?下刀子我也得來。李小妹說,你就是下雪天出生的,生你費我半條命,落地時天快亮了,雞也叫了。過幾天就滿三十了,沒想到給你送了這么大一個禮,要你端屎端尿了。李小妹最初幾天也就是不排便,她本來就有便秘的毛病,也沒當回事。退休以后,她在黃泥壩舊小區附近開墾荒地,每天挖地澆水,面朝黃土,也不跟人交流,只和種子商店的人說話。憋了半個月,腹部腫脹起來,伴隨著絞疼,這才去醫院。診斷是腸梗阻,再不動手術,會危及生命。手術前,才通知我去簽字,我到醫院,看到一臉蠟黃的李小妹,感覺到自己對親情的疏離日久。愧疚梗塞喉頭,我牽著李小妹粗糙的手,哽咽無語……
過了兩天,一個晚上,護士剛拔了針,我扶著李小妹上廁所。她很快出來,我說,放屁了沒有?她看著我,醞釀著什么似的,我說,萬事俱備,只等放屁,有屁,腸子功能就恢復了。她說,好像放了,但我不敢確定是不是,上一次放屁是好久之前的事情了。我說,難得你有樂觀精神,說完,我伸手梳理了一下她額前的白發,感覺像安撫一只蒼老的貓。
讀技校兩年,李小妹只去過學校一次,給我送生活費。她隨基建的車隊去渡口搬運磚塊,回廠的路上讓司機在校門口放她下車。進校門是一道泥坎,正鋪路。那天,才下過雨,泥濘一片。李小妹一身工裝,灰撲撲的,穿的是黑膠鞋,腳底拖帶著一圈黃泥,像踏著兩股黃云,只是這云彩粘黏沉重,讓她不能如飛地行走。生活費三十元,和一些糧票,被層層疊疊地包裹在手巾里,最外一層是塑料袋。李小妹多給了五塊錢,讓我去書店買書,算作生日禮物。小學時,我在黃泥壩的菜場撿到過一元錢,計劃去職工商店買連環畫,中午的時候,還是忍不住拿出來得瑟,李小妹追了我半個廠區,終于被收繳充了‘公。我恨不過,在她手背上留下一個咬痕……這咬痕還在,暌違多年,顏色淡去很多。前年,李小妹吞咽不暢,感覺有異物,鼻腔還會出血,不得不再次住院。她手臂埋著留置針管,每次輸液,我總和這痕跡相逢,朝夕相處,心里無限傷痛。
某天夜里,我帶上工具去了黃泥壩。李小妹在快速路邊種了一片芝麻,路是新修的雙向八車道,路邊的高亮度路燈徹夜不息,照得那塊芝麻地如同白晝,開花的芝麻誤以為是白天的陽光,遲遲不肯凋謝。別處的芝麻花謝結莢,暗懷珠胎,此處的芝麻花影灼灼,爭奇奪艷。李小妹為此很苦惱,對明晃晃的路燈心懷怨恨……
床上的葉老師動彈了一下。她微張著眼睛見我還在,問現在幾點?我說,您睡了沒大一會。她說,你是幾床的家屬?我說,我是王曼麗的同學,就陪您來著。她說,王曼麗隨我,性子急,風風火火,不記仇,刀子嘴豆腐心。我說,心好,也熱情,每次吃飯搶著買單。她說,你多擔待著。我看時間差不多了,就摁了傳呼鈕。護士進來,拔針取瓶,讓我按壓針口。葉老師眼珠跟著轉,一會說,不是還有一瓶嗎?護士說,您記錯了奶奶,這是最后一瓶,您可以放心睡覺了。葉老師不錯眼盯著我,我說,您老還有什么吩咐?她說,實在憋不住。我彎腰從床下拿出便盆,估摸著位置塞進被子。她說,你心細,一步到位。我去廁所沖洗便盆,出來后原樣放好,又聽葉老師說,我記得你,調皮鬼王冬瓜,沒讓我少操心。我說,您記性真好,要不是您說起,我都不記得自己是王冬瓜了。葉老師說,你不能恨我,上課你總搗亂,我只能趕你出教室。我說,您記錯了,那是馬一鳴,我上您的課最認真,回回考滿分。葉老師說,馬一鳴昨天來看我,沒給我帶禮物,空手來的,來了還吃我兩根香蕉,看著挺出息的一個人,求我把王曼麗嫁給他,數他最落難,百般不順,一無是處,你可要幫著點,別為富不仁。我說,回頭我就找他,安排他當總經理,配女秘書,形影不離。現在卻前后挨了三刀……
回轉的路上,李小妹不停咳嗽,越咳越兇,嗆出滿臉眼淚鼻涕。我實在看不下去,伸手為她拍背,費了老大的勁才止住,她心有余悸地說,該不是你爸在罵我吧?我說,你想啥呢。她說,感覺你爸一個勁地在數落我,我說不出話,臊得難受,只能咳嗽,你爸說路政的人會上門抓我,又說,我一輩子沒搞過破壞,今晚算頭一件,感覺是罪人。我說,你想多了。李小妹接過我遞過去的礦泉水,喝了一口說,這回好歹有了教訓,下不為例。
葉老師說,我琢磨好了,準備做一件驚天動地的事,你猜是啥?就是不死,百折不屈,再大的手術也扛下來,回回給自己承諾,回回自我振奮,回回成功,隔天能吃飯,三天能下地……這不得氣死好多人?
李小妹說,這回怕是走到頭了,天天惡心,頭發也掉光了,沒個人樣……盡是折磨,生不如死,再多的錢也救不了我,早點解脫,免得拖累小輩,算做件好事。
我心里七七八八,亂得很,嘴里說,睜眼,路在,就得繼續走,哪怕是滾爬,除非路盡,但邊上的人還在走,路有長短,人各有命,在一時,就走一時,前面峰回路轉也難說。
葉老師說,講得在理,會勸人。明天再來時,別忘記到張店巷找老程,告訴他,四號桌少的那張牌,幺雞,一直在我手里,那天我吊幺雞,自摸三回以后過于激動,眼前一黑,差點短路。這牌靈驗,隨我一起上的手術臺,硌得我醒過來了。
李小妹說,這太陽曬了還是覺得冷……也曬不到幾天了,甭勸我,隔壁床換了幾茬人了,就要輪到我了……昨晚的酸菜魚還剩著吧,想喝幾口,嘴淡,馬尚武燒魚是一絕,醋溜紅燒,手法翻新,沒事就愛看菜譜,做事時也在想著,否則不會踏空出事,想吃還得去找他,他也甭想躲我……要不你推我回去,坐不住,骨頭疼,就想躺。
我看著玻璃窗里的人站起來,躬下了身子。我聽見自己的聲音說,媽,你先躺一會,我出去透透氣,抽口煙。
葉老師說 ,你和曼麗能成,看出來了,你藏不住事,但叫媽是早晚的事。
李小妹無力地闔上沉重的眼皮,沒再理我。
我出了病房,穿過走廊,在樓道口點燃香煙,狠吸了兩口。我并沒有停下腳步,而是順著樓梯從五樓一直來到院子的地面上,抬眼看去,星辰寥落,萬物沉寂。
我再次回到病房的時候,王曼麗正在給她媽洗漱。我進門,她瞟我一眼說,以為你走了,去哪了?我說,就在院子里轉會。她說,你先出去,我一會找你。我說,那你忙,要不我先走。她說,有事?我說,沒事,你忙完也該休息了,不累嗎?她說,你在樓道等會,我很快就好。
王曼麗出來的時候,換了一條棉睡褲,紅底,褲腿上爬滿了小熊,有點短,能看見腳踝,挺白。她趿著她媽的布拖鞋,上身裹著羽絨服,臉上卸了粉彩,皮色光滑,沒見有褶子。樓道口,有一排藍色塑料椅,三個座位,背后是扇窗子,被人拉開半邊,窗臺上煙頭一片。王曼麗說,今晚辛苦你,端了尿盆子。我說,沒見羊肉串啊。王曼麗拍我一下,笑著說,哎呀,見你沒回音,估計不想吃,原來一直惦記著。我說,也不是,順嘴一說,逗你。王曼麗說,改天請你吃頓好的,比今晚的檔次高點,去墨跡山烤全羊怎么樣?我說,羊知道自己被剝皮下鍋,會怎么想?王曼麗說,烤全羊不剝皮吧,皮最好吃。我說,殘忍。王曼麗說,就你心好,那你想吃啥?我說,酸菜魚就行。王曼麗說,行,我做給你吃得了。頓了頓又說,我媽老夸你,說你心細,會照顧人,比我強。我說,那不是我,是王冬瓜干的。王曼麗噗呲一笑說,真以為我媽糊涂了?才不是呢,這是策略,懂不?我說,懶得琢磨。王曼麗說,哎,我媽做了一個夢,醒來就找你,沒見你人。我說,估計是學校建成了,想去剪彩。我把來龍去脈跟王曼麗說了一遍,王曼麗咯咯笑不停,最后收住笑說,不是建學校的事,是夢見上課那會你和她頂嘴,把她給氣的。我說,你媽醒著睡著都說我和她頂嘴,我當年哪有這膽量?
你說我媽藏著掖著,家里好菜好飯,不懂得和鄰居分享。憑啥啊?自個過自個的,不都這樣?再說你怎么知道我家每天吃啥。我說,你媽真會做夢,做什么不好。王曼麗說,知道你后來說啥。我說,說啥?王曼麗說,我媽說,你懷疑她說一套做一套,為富不仁,關起門來吃獨食,可把她氣壞了。我說,做夢也信?王曼麗說,改天趁她清醒了,你得跟她道個歉。我說,夢里的事,至于嘛。王曼麗白我一眼說,德性。你在院子里轉悠啥,我在窗口瞅了一圈,沒見有人。
我一直倚著墻看著窗外,聽王曼麗這么說,在窗臺上摁滅煙頭,收回了目光。
我去了外科樓,七樓,有人一直在過道口抽煙,這人我有印象,身高和我差不多,也瘦,眉頭緊皺,兩眼間刻著‘川字。他有病人要照顧,不該抽個沒完沒了,一定有為難的事,或許我能開導一下,腳下總有一條屬于自己的路……
王曼麗說,你還是多勸勸自己吧。
我順著樓梯到七樓,有點氣喘。那人不見了,窗臺一個豁邊的瓷碗,堆滿了煙頭,有半截還在冒煙。七樓我挺熟悉,病入膏肓的癌癥患者全住這層。那天,李小妹精神出奇的好,能半躺著坐一小會,大腦袋也豎得挺直,白天用了兩支杜冷丁,興致也高了起來。李小妹說,今天感覺好點,腦仁也透亮,想起一件事,按說今天你過生日,陰歷十二月初七,生下你后,吃了兩個雞蛋。其實我生日一般過陽歷,十天前手機QQ提醒過我。我沒當回事,也沒心情。李小妹說,就是今天,算是趕上了,還想吃半個雞蛋慶祝。我說,行,今天你想啥我做啥。其實也就是在破壁機里絞碎,通過進食管注射到胃里。喂食的時候,我說,等明年你康復了,好好給你煎兩個雞蛋,用洋蔥圈煎,規整。李小妹說,那不用你,媽來,你的生日,媽再給你買件新褂子,羊皮的,一早就穿著上班去。我說,羊皮就算了,改吃一頓燉羊肉,擱上大蘿卜,香氣四溢,滿樓都能聞見,羨慕死鄰居。我媽說,你四表叔不是養羊大戶嗎?牽一頭回來得了,燉一大鍋肉,整樓都來吃,自帶碗筷,吃上三天,羊皮給你做件襖子。我說,白天穿著襖子,擠公交逛商城,膻味十足,顯出一股財大氣粗的豪氣,晚上也不脫,穿著睡。李小妹說,行,你說了算……母子倆一人一句,瞎掰扯窮開心,心里卻萬般難過。那頓晚餐她還真‘吃了不少,沒吐,以往根本不行,聞味就吐。自己都覺得奇怪,感覺老天在幫忙。臨睡前,打了止痛針,沒辦法,還是疼起來。半夜好點,不再哼唧,能忍著睡。但還是醒了一回,睜眼就嘟噥,媽呀,被人活生生地捆住剝皮,動彈不得,渾身刀口,我兒,羊皮襖子咱不穿了。說完,吧唧嘴,閉眼又昏沉下去。我困得不行,又不敢睡,就去樓道口抽煙,我媽靠藥,我靠煙。
一連抽了三支,大約二十分鐘。抽第三支的時候,我還有點猶豫,但還是抽了。院子里突然傳來噗通一聲悶響,像水瓶落地,沒準是樓上掉東西下去了。我看了一眼窗臺上的瓷碗,這么想著。回房間,床上沒見李小妹,廁所亮著燈,李小妹終日臥床不起吃喝拉撒都在床上,哪有氣力獨自上廁所?我心下奇怪,推開廁所門,里面沒人。樓下院子里吵吵嚷嚷,接著一個聲音在半空炸響:是誰家的老人?跳下來了!我這才發現限寬的窗子是開著的,窗下一把方凳,窗臺上一雙布拖鞋整齊地放著,我探出半個腦袋看,圍攏過來的人們正在眼皮底下……
我說,李小妹存心要了結自己,之前,她有過自殺的念頭,為此我寸步不離,小刀小勺筷子甚至牙簽啥的都被我藏好了……不讓她按自己的意志走,得按規矩走路,花盡可能多的錢,得挨下去,得疼下去,得尊嚴掃地,得活活地看著自己斷氣。
王曼麗說,看出來了,一年了都,你還難受。你媽自個計劃好了,忍著疼,吃飽,最后那樣……其實,也挺好,彼此都解脫,最起碼,還是自己做的決定。
奪路而逃。我說,她把自己的路奪回去了。
王曼麗說,沒事吧你?成天胡思亂想,后悔讓你來醫院了,觸動了你。那天,你急匆匆地從飯店出來,在樓梯上腳下拌蒜,直接摔昏,血直冒。你說你慌啥,又沒人逼你要跟我在一起,我逼你沒?跟誰過不去呢,好好的電梯不坐,我有搶你的路不讓你走嗎?至于嗎?你媽走了一年多了,哪有在家等你?當時我也不點穿,知道你們母子情深,你還一直沒緩過來……可你……
王曼麗說話的時候,我終于點燃了第三支煙,嘴里泛濫著苦味,嗓子也跟著干癢起來,實在忍不住,嗆得好一陣咳嗽,腦仁缺氧似的,心慌不已,喘不過氣,眼前冒出無數彩球,前后飄搖,又一一幻滅……后來總算止住了,直起腰來,臉上淚涕橫流。
我噎著嗓子說,我看見我媽了,一個勁在背后攆我。我埋頭走路,讓脖子上的鈴鐺響個不停,沒搭理我媽。
啥鈴鐺,你沒事吧?王曼麗咋乎乎說。
路上黃塵彌漫,嗆得我不停咳嗽。我聽到我媽在后面喊我,讓我別往南去,南邊就是城郊肉聯廠,進口了屠宰流水線,專門對付黑山羊,今兒試機慶典,一頭活羊趕進去,出來就分解到位了,皮是皮,肉是肉,手是手,腳是腳,連內臟都不帶錯的,全自動機械化,嘩啦啦,分門別類,直接入袋封裝上餐桌。
王曼麗驚叫一聲說,你胡說什么呢?
回過魂了。有點意思。我說,開始我沒想告訴你,巧得很,今天正好十二月初七,我生日,恍惚中我媽給指了方向。
王曼麗說,真后悔讓你來醫院,神神叨叨,胡言亂語了。
我說,這一通咳,失魂落魄似的,好在我媽趕上來硬拽著我的角轉了一個向,才止住。算趕上了正路,路平坦光亮,通往遠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