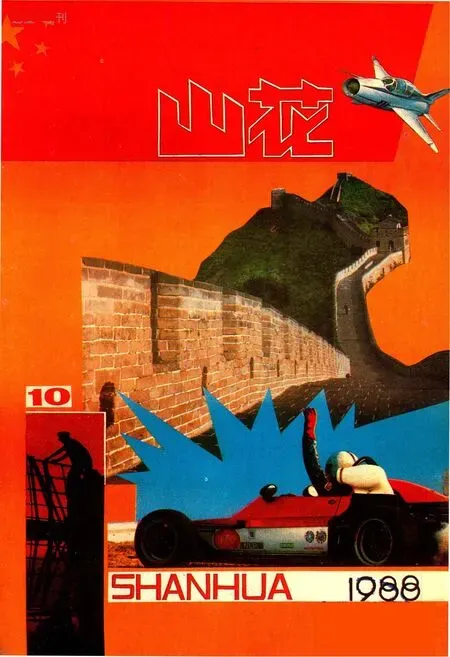家庭教育與時代消息
黃德海
一
1985年,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一本白色封面的小冊子,題名《舊巢痕》,作者署名辛竹。小冊子看起來像回憶錄,奇怪的是,書前“小引”的語氣卻顯得在虛實之間:“我有一個曾經同我形影不離的朋友。他喜歡自言自語似的對我談他的出身和經歷,說話時沉沒在回憶之中幾乎忘了我這個聽話人的存在。這些斷斷續(xù)續(xù)的仿佛獨白的談話,本來不曾引起我的興趣,而且聽得久了更不覺有什么新鮮;卻不料這位朋友竟先我而向世界告別;在懷念故友的心情中,我才漸漸把那些聽熟了的片斷故事和人物聯(lián)綴起來。”
1997年,文匯出版社重版該書,這次變成了評點本,在此前的基礎上加了回目和評說,署名方式也變成了拙庵居士著、八公山人評、無冰室主編。熟悉金克木的人都知道,辛竹是他常用的筆名之一;而他晚年編訂附注的舊體詩集,集名為《拙庵詩拾》;《送廖君奉母東行兼呈相知諸友十首》則自注有云,“‘公山指淮南八公山,故鄉(xiāng)所在”。由此,則拙庵居士、八公山人均為金克木的化名,一人分飾兩角,自作自評,自嘆自笑。加上編輯吳彬假名無冰室主寫“編者的話”,戔戔小冊竟有了小說的感覺。
后來金克木曾自問自答,解釋這本書到底是回憶錄還是小說,更加混淆了作品的文體界限:“小說體的回憶錄,回憶錄式的小說,有什么區(qū)別呢?真事過去了,再說出來,也成為小說了。越說是真的,越是要人以假當真。越說是虛構,越是告訴人其中有真人。”有意思的是,《舊巢痕》的評點里,還提到過寫作的初衷,“寫此書于七十年代末,為給上山下鄉(xiāng)兒女知道前代的事,不為發(fā)表。過了三年才有出版之議,所以不像小說也不足為怪”。不過,無論金克木怎樣混淆文體界限,這書底色的回憶錄特征不會消失。值得琢磨的是,反復在文體上做文章,金克木想傳達的究竟是什么?
1997年底,金克木為新書《莊諧新集》寫序,提到自己晚年寫作的因由:“二十世紀七十年代末期,我發(fā)現自己身心俱憊,確已步入老境,該是對自己而非對別人作檢查、交代、總結的時候了。于是我從呱呱墜地回憶起,一路追查,隨手寫出一些報告。”追查的各種問題,他曾在《比較文化論集》自序中透露過:“我從小學所受教育中得出一些問題:為什么中國這樣一個文明大國卻會受小得多的日本的欺侮呢?……為什么連文字都從中國借去的日本竟然能‘明治維新成功,而堂堂中國的‘戊戌變法卻歸于失敗呢?……我想,一定要知道華盛頓、林肯、拿破侖、俾斯麥、凱撒等人自己怎么講話以及講了些什么?總是想對于像中國和不像中國的國家追根究底,想懂得那里的人是什么樣子,怎么生活,怎么思想的,以和我自己及周圍的中國人對照。總是想追本溯源,看現代外國的所謂文明是怎么來的。”
金克木晚年寫下的各種文字,差不多都可以看成這追查的結果:“我追索兒時的問題,由今而古又由古而今,由東而西又由西而東,過了幾十年;世界和中國都有了很大的變化,前面所說情況已成歷史;問題也不能那樣提了,但不等于解決。……這些文章可以說是我在七十歲時回答十七歲時問題的練習,只是一些小學生的作業(yè)。這些習作也算是我交給我的小學老師和中外古今的,可得見與不可得見的,已見與未見的,各種各樣的,給我發(fā)蒙的老師們的一份卷子。”更重要的是,這個追查過程讓金克木意識到,單靠書本無法完整認識世界,他長大后遇到的形形色色的人,原先“在中國所遇到的各種人也都是我的發(fā)蒙老師,教過我不少知識。這樣我才自己以為有點‘恍然大悟,原來死的書本記錄是要同活的人聯(lián)系起來才能明白的。”
我很懷疑,金克木之所以有意含混《舊巢痕》的文體,就是為了開闊作品的理解空間,讓讀者在注意書本的同時留意人物,從而觀察他身經的時代,綜合考慮一個時期的基本社會風貌和人的各種潛在心理。《舊巢痕》從他出生寫起,因為他“是在中國的新舊文化互相猛烈沖擊中出生的。兒時所受到的家庭、社會和學校教育中充滿了矛盾。在家里一面念‘詩云‘子曰,一面認ABCD”,古今中外的混雜,具體而微地體現在一個小城的孩子身上。
二
明末清初農民大起義,社會動蕩,金克木遠祖自四川流落至安徽壽州鳳臺縣。道光年間,高祖遷至壽州城內。太平天國末期,他的曾祖歿于苗沛霖攻打壽州之役,朝廷明令褒獎,并恩賞其祖父秀才頭銜,其祖父“竟不肯借此進一步應考,也不肯利用這個去走動官府,卻躲在家里不出來,只極力培養(yǎng)他的下一代獨子。他自己四十多歲就死了。他的獨子卻考取了秀才,又補上了稟生,每月有官費,而且有資格給考秀才的童生作保人以取得報酬。他于是成了教私塾的教師,還常常做些詩文,有了點名氣”。盡管不是世代書香門第,但從曾祖到父親這一代,也算得上讀書之家了。
1894年,金克木父親受老師之邀赴軍中,未至而邀者已隨丁汝昌、鄧世昌殉國。其師理喪時,金父因表現仗義,獲得推薦,從而結識軍門,先后謀得幾處“卡子”。“卡子”是“曾國藩和李鴻章在打太平天國和捻軍時,為籌軍餉設了很多‘厘金關卡,在水陸碼頭商旅必經之地設上‘卡子,派一個官吏,帶上差人和扛槍背大刀的兵,攔路抽稅”。從“卡子”上賺了一筆錢,金父“就照當時清朝的公開賣官條例,花錢‘捐班,買到了一個縣官之職”,管轄地是江西萬載。盡管是末代皇帝的末代縣官,仍然不乏文字或口頭逢迎,而即便從這些略顯夸張的話里,也能感受到豐富的時代消息。如興建近代機構,“興警察軍,設習藝所,建城鄉(xiāng)中小學堂及師范傳習所,預籌經費,規(guī)畫久遠”;如開辦學校,“州治設中小學堂五所,八鄉(xiāng)陸續(xù)增建,皆賴公督訓而成”。
金克木出生的1912年,父親五十九歲,生母十九歲。他的生母是江西萬載縣人,生于鐵匠鋪,為丫環(huán)收房。這一年中華民國成立,金父已不再是縣官,且被扣押抄家。轉過年來,金克木還不到一周歲,父親就突然離世了。遠在河南的異母長兄歸來善后,并帶回了包括大嫂在內的數口之家。
其時,依仗自己的聯(lián)絡之才,金克木長兄的事業(yè)正如日中天。一位網羅人才的大公子發(fā)現其長兄“不是尋常之輩,很有點經濟韜略,雜學旁通,是封建傳統(tǒng)中的非凡人物,絕非一個文人或學究。大概不消多日,兩人心照不宣,大老爺棄文就武,由教書而秘書,由文秘書而武秘書”。因父親去世,其長兄只好暫時回家“守制”,卻“毫不猶疑地進行活動”。大嫂是官宦人家出身,見多識廣,回家處理喪事,恰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在兩句話稟明婆母之后,她就一手掌握大權,安排一切”,其精明果敢有類鳳姐。“不消多少天,在一對能干夫婦的全權指揮下,全家連同所有的家私一起上了大船,還掛上某府、某堂的號燈,浩浩蕩蕩由江西回安徽去了。”
回到安徽,大哥繼續(xù)出門闖蕩,大嫂留在老家。金克木身邊的生母、嫡母、大嫂和二哥、三哥,就都成了他最初的啟蒙者。三歲左右,金克木開始學說話,“我探索人生道路的有意識的學習從三歲開始。學說話的老師是從母親到大嫂,學讀書的老師是從大嫂到三哥”。生母最早跟金克木進行語言交流,“當她教我叫她那個寫不出來的符號時,她是教我說話和對她做思想交流”。除了母親,大嫂是教金克木說話的第一位老師,她“說話的特點是干凈,正確,說的句子都像是寫下來的。除了演講、教課、辦外交以外,我很少聽到人在隨便談話時像大嫂那樣說話。她不是‘掉文,是句句清楚,完整”。
這一家人說話,稱得上五花八門。“我的生母是鄱陽湖邊(按江西)人,本來是一口土音土話,改學淮河流域的話。……嫡母說的也不是純粹(按安徽)安慶話,雜七雜八。回到老家后,鄰居,甚至本地鄉(xiāng)下的二嫂和三嫂都有時聽不懂她的話,需要我翻譯。她自己告訴我,她的母親或是祖母或是別的什么人是廣東人,說廣東話,還有什么人也不是本地人,所以她的口音雜。”大嫂是河南人,“講的不是河南土話,是正宗的‘中原音韻吧”。兩個哥哥和其他家庭成員,說的則是安徽壽州話。
這樣復雜的方言系統(tǒng),讓金克木學說話的過程很有獨特性,“我學說話時當然不明白這些語言的區(qū)別,只是耳朵里聽慣了種種不同的音調,一點不覺得稀奇,以為是平常事。一個字可以有不止一種音,一個意思可以有不同說法,我以為是當然。很晚我才知道有所謂‘標準說話,可是我口頭說的話已經無法標準化,我也不想模仿標準了。”金克木后來沒有任何畏難情緒地學各種外語,是否跟他從小習慣各種方言的轉化有關?
學說話與學讀書相關,“讀書也是說話,當大嫂教我第一個字‘人和第一句話‘人之初時,我學習了讀書,也學習了說話”。從此,大嫂開始教讀《三字經》,“她梳頭,讓我看著書,她自己不看,背出兩句,叫我跟著一字字念,念熟以后背給她聽”。如此這般,上午讀書成了金克木的日常功課。“他每天得一枚‘當十銅元,一直到他把整本《三字經》讀完,沒有缺過一次。中間大嫂曾反復抽查,讓他連續(xù)背誦,都難不倒他。不過大嫂并沒有給他講內容,只偶爾講講,例如,‘孔融讓梨,說,‘融四歲能讓梨,你也四歲了,要學禮節(jié)。”過了將近三十年,金克木在印度佛教圣地跟憍賞彌念梵文詩,“開頭他也是讓我看書,他背誦,吟出一句原文,再改成散文句子,再作解說,和中國與印度古書中的注釋一模一樣,說出來的就是散文,吟出來的是詩”,讓他恍然覺得和大嫂當年教他《三字經》的情形相仿。
這或許是印度和中國共同的傳統(tǒng)的講授方式,背誦為主,講解為輔,禮俗也滲透在講解里?這種教學方式,受新潮影響的三哥不以為然,偶爾在回家時實行新式教育法。“在他念了一段書以后,上新學堂的三哥認為這樣死背書不行,買了一盒‘字塊給他。一張張方塊紙,正面是字,背面是畫。有些字他認得,有些字認不得,三哥便抽空教他。他很快念完了一包,三哥又給他買一包來。”這樣新舊方式交替著教了一段時間,四歲多的時候,金克木“念完了《三字經》和一大盒‘字塊,可是不會寫字,不會講”。按傳統(tǒng)教育方式,《三字經》以后,應當是《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詩》,但這時發(fā)生了一件事,致使金克木的傳統(tǒng)發(fā)蒙中斷,其所接受的教育轉向了另外一條軌道。
三
1917年,金克木五周歲,三哥中學畢業(yè)后回到了老家。有一天,大嫂在飯桌上向全家宣布,從今以后,金克木歸三哥教。三哥是新派人物,過去只是偶爾回家,偶爾干涉一下傳統(tǒng)教學,現在要全面接管金克木的教育了。走進三哥屋內,景象果然與大嫂等舊式內室不同,“有一臺小風琴和一對啞鈴。桌上放的書也是洋裝的。有些書是英文的。有一本《查理斯密小代數學》,我認識書面上的字,不知道說的是什么”。每天早晨,三哥兩手各拿一個啞鈴,上上下下,“一、二、三、四”做早操。有時兩手的鈴還撞擊一下,發(fā)出清脆的聲音,所謂“啞鈴不啞,代表新風氣說無聲的語言”。
三哥粗粗算了一下,金克木當時識字差不多有一千了,傳統(tǒng)的“三百千千”,包括講典故逸聞的《龍文鞭影》,都不夠適應新形勢,便決定按新式學堂的方法來教,于是上街買了一套商務印書館的《國文教科書》,“那比用‘人、手、足、刀、尺開頭的一套還要古一些,可能是戊戌變法后商務印書館編的第一套新式教科書,書名題字下是‘海鹽張元濟題。書中文體當然是文言,還很深,進度也快,可是每課不長,還有插圖”。
選定了教材,三哥開始授課。“這書的開頭第一課便是一篇小文章,當然是文言的,不過很容易,和說話差不多。三哥的教法也很特別,先讓我自己看,有哪個字不認識就問他。文章是用圈點斷句的。我差不多字字認識。隨后三哥一句一句教我跟著念。他的讀法和說話一樣。念完了,問我懂得多少。我初看時憑認的字知道一點意思,跟著他用說話口氣一念,又明白了一些,便說了大意。三哥又問了幾個難字難句要我講。講不出或是講得不對,他再講解,糾正。末了是教我自己念,念熟了背給他聽,這一課便結束了。”書中的文言,也讓金克木熟悉了書本的說話方式。
盡管是新式教科書,但金克木對其中的選文并不滿意。或者說,傳統(tǒng)開蒙系統(tǒng)攜帶的禮俗教育,并沒在新教科書中完全消失。在讀這本教科書之前,金克木曾聽嫡母念兒歌:“小老鼠,上燈臺,偷油喝,下不來。叫小妞,抱貓來,嘰里骨碌滾下來。”生母也半說半唱地教他,“打起黃鶯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西”。新式教科書上的兩課也給金克木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一課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另一課卞莊刺虎是講“兩虎相斗,必有一傷”。這些故事給金克木留下的印象太深了,他晚年還常常想起。“小老鼠怕貓,黃鶯兒唱歌挨打,鷸蚌、兩虎相爭,寧可讓別人得利,這些便是我學讀書的‘開口奶。這類故事雖有趣,那教訓卻是沒有實際用處的,也許還是對思想有傷害而不利于處世的。”
新舊交替時期的常見情形是,新或舊的教育還沒怎么展開,舊或新的干擾就先來了,最終是新是舊,要看誰更有權力主張。因為學習速度快,一套《國文教科書》金克木很快就要讀完了。這時候,大哥要從外地回來,三哥趕緊中斷了新式課本的教學,改教《論語》。這書跟《三字經》和新式教科書都不同,“沒有圖還不說,又是線裝木刻印的大本子。本子很長,上下分做兩半。上半都是小字,下半的字有大有小。大字的本文開頭和中間有圓圈,這是標明章節(jié)的。句子不分開,句中插些雙行小字注,讀時要跳著念大字,不連貫。這書看樣子就不討人喜歡,內容更稀奇古怪”。
雖然內容古怪,大字的正文之外還有小字的朱熹注,但金克木念過《三字經》,對孔子和《論語》并不陌生。三哥略略介紹一下,他就明白了,照傳統(tǒng),這是經書,最重要,必須熟讀。過去因為跟應考有關,傳統(tǒng)的教法是連大字帶小字一齊背誦,只許照小字講解大字。三哥的教法跟傳統(tǒng)不一樣,“他說,現在不要應考了,不必念朱夫子的小字注了。至于上面那半截書的什么‘章旨‘節(jié)旨之類批注都可以一概不管。三哥教得很簡單,要求的是識字,能背誦,要能連續(xù)背下去。”背誦恰是金克木的特長,三哥也不要求拖長音吟唱,因此不一會兒就熟讀成誦,當天就把第一篇的三句都背會了。
金克木學《論語》的速度太快了,教的內容很快背熟,字也都認識了,完成后就趴在椅子上看三哥寫字。三哥不便趕他走,就在他“念書的方凳上也擺上一塊有木盒子的小硯臺,一小錠墨,一支筆,一疊紅‘影仿叫弟弟也寫字,免得老早就放學或則總在他旁邊好像監(jiān)考試一樣看他讀書寫字”。三哥要求金克木自己磨墨,拿筆把“影仿”上的紅字一筆一筆描成黑字,“要講筆畫順序,不能亂涂。更重要的是執(zhí)筆要合規(guī)矩,拇指和食指捏在筆兩邊成為‘鳳眼,中指和無名指分放在拇指和食指各一邊,小指靠在無名指后邊,離開筆頭至少一寸,手腕要略略懸起”。
三哥用這辦法把自己從被監(jiān)控的狀態(tài)中解脫了出來,因為這可比念書難多了,金克木“忙習字的時間比念書多,而且每次都是滿手墨污,寫完就要去洗手。單是執(zhí)筆法就練習了不少時候。這樣,他就沒工夫去和三哥搗亂了”。寫的第一篇“影仿”,都是筆畫少的字,“上大人孔乙己化三千七十士爾小生可知禮也”,復雜的“爾”和“禮”用簡筆。即便不熟悉現代文學,也看得出來,這正是魯迅那鼎鼎大名的《孔乙己》同名人物名字的出處。讀到這里的時候,我不禁悚然一驚,仿佛看到孔乙己拖著他的破舊長衫,一步一步從古舊的書本,走進了復雜萬端的現代社會。
四
隨著識字漸多,金克木看三哥的室內情景,也為之一變,“三哥桌上擺的高高一堆線裝書是《古文辭類纂》,只第五個字還不認得,也不知道這是著名的桐城姚鼐編的著名的古文選本。三哥這時也不大讀古文,倒是嘰哩咕嚕常常讀英文書。有幾本英文書上有中國字,那是《華英進階》”。這兩本書,加上前面提到的《查理斯密小代數學》,恰好構成了當時教育系統(tǒng)中的古、今和文、理,也是三哥當時那代人常見的知識結構。
金克木翻過《查理斯密小代數學》,沒讀出什么頭緒,三哥抽空開始教他學英文。“哥哥照他學習時的老方法教。先背《英字切音》,一個輔音加一個元音拼起來,順序發(fā)音好像念日文字母表,不知是不是從日本學來的。再讀本世紀初年的《新世紀英文讀本》。‘一個男孩,一個桃,一個男孩和一個桃。都是單音節(jié)詞,容易背,不過還得記住字母拼法。還要學英國人教印度人的《納氏文法》,也就是‘葛郎瑪。第一冊很薄,第四冊很厚,要求學完前兩冊。這可難了。開頭講的全是詞類,名、形、代、動、狀、連、介、嘆。名稱就難記,還得背定義。名詞定義背了幾天才會,還是拗口。……句子出來,更討厭。‘你是誰要說成‘誰是你。是字也得跟著你變。先說是,你字還沒出來,怎么知道跟誰變?”
照金克木的說法,上小學前,三哥只私下教過他英文字母和幾句英文,甚至說“我剛滿十八歲來北平(北京)打算上大學時還不會英文”。這并不耽誤金克木去北平前,通過讀馬建忠的《馬氏文通》,琢磨出一種獨特的英語學習方式:“馬氏雖是學外國文出身,文言文也寫得不錯,可是越讀越難懂,不知道說的是什么。反倒是引的例子好懂些,有些是我讀過的。于是我倒過來讀,先看例句,懂了再看他的解釋。這樣就容易多了。靈機一動,明白過來。是先有《史記》,后有《文通》,不是司馬遷照《文通》作文章,是馬氏照《史記》作解說。懂了古文看文法,很有意思。不懂古文看文法,照舊不懂。……這樣一開竅,就用在學英文上。不用文法學英文,反用英文學文法。不管講的是什么,不問怎么變化的規(guī)則,只當作英國人講的一句話,照樣會講了再記規(guī)則。說話認識字在先,講道理在后。懂了道理更容易記。學文法先背例句,后背規(guī)則,把規(guī)則也當作一句話先背再講。把外文當作古文念,果然順利多了。接著索性顛倒下去。不從英文記中文,反從中文記英文。”
三哥不知道金克木用了這個方法,只是覺得奇怪,他的學習速度越來越快。“其實我用的是學古文的老辦法,把外國文當作本國文,把本國文當作外國文。成為習慣了,以后我學什么文也用這種顛倒法。不論變化怎么復雜,我只給它列一張表作為參考,然后就背句子。先學會,后解釋。文章在先,文法在后,把文法書也當作文章讀。”這跟當時教育方法相悖的倒行逆施,大概學習效果頗佳,以后金克木便一直如此了。
這樣的效果,讓金克木確認了以受教者為主的學習方法,在以后的教學中經常應用。1932年,有朋友介紹金克木到山東德縣師范教國文。師范課程中必須開教育學和兒童心理學,不料請金克木去的朋友選好課本,教了不久,突然離開學校,金克木只好接下這兩門課。打開教材一看,心理學太淺,太陳舊,教育學又太深,并且都是用文言寫的。應該是想到了自己學英文的方法,金克木便沒有照本宣科,而是把兩本教材“當作‘國文的補充讀物教,著重講語言,大略講一下內容”。這一來,既“講了課本,又講了課本以外我所知道的有關知識”,順利完成了教學任務。
1939年,經陳世驤介紹,金克木到辰谿桃源女中,教四個不同年級的英語,課本竟然“是四個書店出版的,商務、中華、世界、開明,各有一本,體系各各不同,編法互不一樣,連注音方法都有三種”,真叫人為難。金克木急中生智,又用上了他琢磨出來的學習方法。“學語言不是靠講道理,不能處處都問為什么,這個‘為什么,語言本身是回答不出來的”,因此決定“不以課本為主,而以學生為主,使初一的小孩子覺得有趣而高一的大孩子覺得有意思。她們一愿意學,我就好教了。我能講出道理的就講一點,講不出的就不講,讓課本服從學生。我只教我所會的,不會的就交給學生自己,誰愛琢磨誰去研究,我不要求講道理。我會的要教你也會,還要你學到我不會的。勝過老師的才是好學生”。就這樣,金克木順利度過了難關。
金克木究竟能不能教好,連介紹他的陳世驤都有些擔心:“起初我是不大放心的。有位朋友說,像你學的這樣的英文能教中學嗎?我相信你能教,果然教下來了。”這樣的教學方式看起來出人意料,卻是耐心摸索的經驗之談。雖然金克木自謙為“聽用”“救場”,其實可以從中看到新舊交替之間的時代之際,見出一個人學、教之間的巧妙轉換。
五
1918年,金克木六周歲,大哥臨時從外地回來,順便考察他讀書的進度。考察的結果是,從三字經到四書,都背得非常熟練。大哥由此指導了傳統(tǒng)的以記誦為主的讀書順序,“趁記性好,把《四書》念完就念《五經》,先不必講,背會了再說。長大了,記性一差,再背就來不及了。背‘曰若稽古帝堯,‘乾元亨利貞,就覺得不順嘴了。到十歲再念詩詞歌賦、古文,開講也可以早些。《詩》《書》《易》《禮》《春秋左傳》,只要背,先不講,講也不懂。這些書爛熟在肚子里,一輩子都有用”。
大哥在家中住了一段日子,對金克木的讀書又有囑咐:“你念書還聰明。我們家?guī)状顣荒軘嗔恕畷恪O纫雅f學打好根底。……十歲以前,把《四書》《五經》都背過。十歲以后念點古文、唐詩、《綱鑒》。現在世道變了,沒有舊學不行,單靠舊學也不行。十歲前后,舊學要接著學,還要從頭學新學。……有些書,八股文,試帖詩,不用念了,你也不會懂。有些‘維新書,看不看都可以。有些大部頭的書可以翻翻,不能都懂也算了。有些閑書不能看……小本、小字、石印、有光紙,看了,眼也壞了,心也壞了。記住,不許看。有不少字帖是很難得的,沒事可以看看,但不能照學,先得寫好正楷。……記住,不要忙著去學行、草、篆、隸。”
四書五經打底,練字從楷書開始,這是傳統(tǒng)一步步打基礎的教育。除了這些,大哥還講起雜學:“頭一條是要把書念好,然后才能跟你三哥同大嫂學那些‘雜學。那是不能當飯吃的。可是現在世面上,一點不知道不行。要知道,有的事也要會,只是不準自己做。為了不受人欺負愚弄,將來長大了也許用得著應酬,但不許用去對付人。我們家歷代忠厚傳家,清貧自守,從不害人。”臨行前,大哥還專門給金克木講了《詩經·關雎》,算是來自血親的開蒙儀式:“這是《詩經》,開頭是《周南》,這是第一篇。記得孔夫子說的話吧?‘不學詩,無以言。我親自給你起個頭,以后三哥教。建亭來了,再由他教。我不教你念幾句書,總覺得缺點什么。伯伯(按爸爸)要在世,他一定會親自教你。現在我無論如何得親自教你幾句書。”
大哥離開后一段時間,大嫂讓金克木助她理書,主要是彈詞,《天雨花》《筆生花》《玉釧緣》《再生緣》《玉蜻蜓》《珍珠塔》《雙珠鳳》《庵堂認母》《義妖傳》《綴白裘》等,還有兩本棋譜,《桃花泉弈譜》《弈理指歸圖》,并《六也曲譜》一種。大嫂對金克木說的一番話,幾乎是大哥談到雜學的翻版,不過大哥多諷,大嫂多勸:“念書人不光是要念圣賢書,還要會一點琴棋書畫。這些都要在小時候學。一點不會,將來遭人笑話。正書以外也要知道閑書。這是見世面的書,一點不懂,成了書呆子,長大了,上不得臺面。圣賢書要照著學,這些書不要照著學;學不得,學了就變壞了。不知道又不行。好比世上有好人,有壞人,要學做好人,又要知道壞人。不知道就不會防備。下棋、唱曲子比不得寫字、畫畫、作詩。可是都得會。這些都得在小時候打底子,容易入門。將來應酬場上不會受人欺負。長大了再學,就晚了。”
理出這些書來,大嫂忽然來了興致,或者是來了興致才理出這些書來,要給大家唱書。唱的是《再生緣》,簡單交代了故事情節(jié),就開始唱。“大嫂的唱法很好聽,不知是什么曲調。大體是相仿的雙行七字句對稱調,有三字句夾在中間便三字停頓一下。雖然有點單調,卻并不令人厭倦。到后來小弟弟成了大人,學了詠詩,聽了戲曲,也沒弄清大嫂唱的是什么調子。那既不是舊詩,也不是江南彈詞,又不是河南墜子,更不是河南梆子(豫劇),離昆曲也很遠,卻像是利用了詠舊詩七律的音調,改變?yōu)榍樱部赡苁谴笊┳约旱膭?chuàng)造。聽的人一半是聽故事,一半是聽音樂。”
大嫂的唱書,金克木印象很深,以后會就此反思文化的流轉方式,“中國的讀書人在全人口中從來就為數不多。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也是靠口傳的比靠文字書本的多。唱書說書不是僅對文盲有吸引力,知識分子,不論低級高級,聽書迷,愛聽評彈大鼓的,也不少。”也就是說,這種唱書,是很多不識字人的知識和禮俗訓練,讓很多人雖是文盲卻并非“書盲”。1940年代,金克木在印度聽鄉(xiāng)間人唱他們的史詩,印度的有識之士已經察覺到文盲快要兼“書盲”的危險信號,“假若文盲再加上‘書盲,視聽全斷,沒有了說書人和聽書人,各色史詩都不再傳唱了,只剩下迎神廟會使人不致全盲于傳統(tǒng)了,那會是什么樣子?會不會史詩重演而不自知?以舊為新?”
大嫂開始唱書,金克木就開始跟著看。此后,得到大嫂允許,便把唱的《天雨花》一本本拿去看,“他越看越快,沒過多少時候,大嫂的擺出來的藏書已被他瀏覽了一遍,看書的能力大長進,知識也增加了不少。遇到不認識的字和講不通的句子,也擋不住他,他會用眼睛一路滑過去,根本不是一字一字讀和一句一句想,只是眼睛看。這和讀《四書》《五經》大不相同,不過兩者的內容對他來說都是似懂非懂。”后來,金克木找到家里的各種藏書,也用上面的方法來讀,“他看這些文言、白話、正經的、不正經的,各種各樣的書都是一掃而過,文字語言倒能明白,古文、駢文、詩詞、白話,中國的、外國的,他都不大在意,反正是一眼看過去,心里也不念出字。大意了然,可是里面講的事情和道理卻不大了了,甚至完全不懂,他也不去多想。這一習慣是由于偷偷看書怕被發(fā)現而來的。盡管是正經書,也不許私自動,所以非趕快翻看不行。結果得了個快讀書的毛病,竟改不掉了。”
大概在說了關于雜學的一番話之后不久,大嫂開始教金克木學曲和學棋。這個教育過程沒有詳寫,能夠知道的是,大嫂后來有了別的嗜好,對教金克木“下棋、吹簫的事不熱心了;說是棋讓到四個子,可以了,自己去學棋譜吧。曲子是學不會的,簫吹得難聽極了,‘工尺上四合也分不清,調不準,不用學了”。金克木好像的確沒什么音樂天賦,上小學的時候,彈風琴吹笛子也只是勉強及格。倒是跟大嫂學的圍棋,成了他一生的愛好,因此結交了很多朋友,并寫出了很多值得琢磨的文章。
六
除了上面提到的家庭成員,還有一個人算得上是金克木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就是上面大哥提到的“建亭”。三哥準備去教小學,沒有工夫教金克木了,可大哥吩咐的教學任務還沒有完成,是否讓金克木上小學也還得請示大哥。恰好,這時有個和三哥年紀差不多的本家侄子,也就是建亭,因無事可做,想教個家館。三哥連忙趁機脫身,“便請他來,借給他這個小客廳作學塾,教小弟弟,也就是他的小叔叔。同時找了左鄰右舍的小孩子,還有那位侄子自己收的幾個大小不等的學生,正式開塾”。
金克木入塾讀書時,離五四運動還有一年,私塾仍然是舊日模樣,拜師儀式也顯得頗為莊嚴肅穆。“開學時,客廳里四面擺著各色各樣的桌椅,都是學生從自己家里搬來的。正中間一張條幾,上有香、燭,墻壁上貼著一張紅紙,上寫‘大成至圣先師孔子之神位,左右邊各有兩個小字,是‘顏、曾,‘思、孟。條幾前的方桌旁兩張?zhí)珟熞问抢蠋熥缓痛妥弧!蠋熡H自點起香燭,自己向孔子的紙牌位磕了頭,是一跪四叩。然后,三哥對弟弟努了努嘴,弟弟連忙向上跪下,也是一跪四叩。那位侄子老師站在旁邊,微微彎著腰。小孩子站起身,回頭望一望這位老師,略略躊躇,沒有叫,又跪了下去。老師并沒有拉他,卻自己也跪了下去,不過只是半跪,作個樣子。小孩子心里明白,稍微點了點頭,不等侄子老師真跪下就站起身,老師也就直起身來。三哥緊接著朝上一揖,侄子慌忙曲身向上陪了一揖。這是‘拜托和‘受托之意。孔子和他的四個門徒好像是見證人。”
入塾之時,金克木除了背誦過上面提到的幾種書,還念了《孟子》,讀過《幼學瓊林》,“是四六對句的駢文,專教一些典故,還由此學了一些平仄和對對子的常識”。拜師儀式結束后,侄子老師問讀書到什么地方了,金克木答《周南》《召南》已經讀過,該《國風》了。“老師翻到該念的地方,一句一句念,小孩子一句一句跟著念。念完了,老師說:‘回位去念,念熟了,拿來背。他一句也沒有講解。”接下來,老師一個個問下來,童蒙們讀書進度不一,念到《三字經》《百家姓》《千家詩》《論語》《孟子》的都有。按“三百千千”到四書再到五經的順序,金克木年紀最小,念的書卻最深。
因為背書速度快,侄子老師命習字《九成宮》,然后溫習讀過的書。“整個書房里所有學生都是大聲念各自不同的書,誰也聽不清大家念的是什么;而且各有各的唱法,拖長了音,有高有低,湊成一曲沒有規(guī)則的交響樂。虧得這位年輕老師坐得住。他還攤開一本書看,仿佛屋子里安靜得很,或則他是聾子。這倒也許是一種很奇特的訓練,使得小孩子長大了,在無論怎樣鬧嚷嚷的屋子里,他都仍然能看書寫字。”以后去北平,有段時間跟朱錫侯和幾個朋友住在一起,三個人學小提琴,拉出可怕的聲音,金克木讀法文巴爾扎克小說,對噪音充耳不聞,大概就是小時候打下的底子。
私塾教育沒能持續(xù)多久,轉過年來,金克木就隨三哥去他任教的小學讀書了,讀書面貌有了很大的變化。其實無論大哥大嫂和三哥,還是侄子塾師的教育,主要都落實在書本上。對主張“讀書·讀人·讀物”的金克木來說,書本以外人和物的教育也很關鍵,“不比書本小,也許還更大些”。不過,金克木童年似乎并沒有多少值得提起的人和物的教育,或者他自己提到的少。只三哥的放風箏和種菊花,大哥的抓麻雀,算得上是難得的時光。十幾年后,金克木在大城市的小酒店里吃到醬山雀,“他喝著酒,對面前的酒友講兒時這件事;但酒友不以為異,卻去說捉麻雀的方法;他們不能體會天天念《告子》沒有任何小同伴和游戲的寂寞童年的心情”。
就在這樣的寂寞中,金克木迎來了自己的第一個女朋友,她帶他看到了一個更大的世界。“她的小辮子上還扎著小小的野花。一見面就很熟。她帶我到門外菜園中和麥田里,告訴我什么草,什么蟲,這樣,那樣,全是我第一次聽到的新鮮事。”不過好景不長,一兩年過去,再見這個女朋友的時候,她“仍然梳著辮子,扎著野花,仍然和我一起出門玩,可是我覺得有點別扭,因為她走路一拐一跛,走不快了。原來她裹上了小腳。我在家中見到過的女人全是小腳。我以為女人生來就是那樣的。這時看到她那雙尖尖翹起來只用后跟走路的小腳,才知道那是制造出來的。……我不知為什么從心底泛出一陣說不出的感覺,仿佛是惡心要吐。看到她長得比上次更好看,偏偏有這雙怪腳,走路一歪一扭,變成了丑八怪的樣子,于是我連大人的小腳也厭惡起來了。”對小腳的憎恨,金克木到老都絲毫沒有緩和,這種感情甚至轉移到了高跟鞋上,可見制造出來的這雙怪腳,給金克木留下了多么惡劣的印象。
不只是纏小腳的問題,《舊巢痕》里寫了很多女性,從看到自殺的女人,到母親,二姐,三姐,二嫂,到二哥的兩個女兒做童養(yǎng)媳,甚至大嫂從深明事理到生出牌癮,都顯示出金克木對女性命運的關注。這些關注引出的是關心和反思,金克木晚年反復講,“從整體說,從全社會說,以性別分,女性是受男性壓抑的。這是顯文化,不容否定。同時,從局部說,從一個個人說,男性受女性支配的事并不稀罕。這是隱文化。應當說,文化是男女雙方共同創(chuàng)造的,而女性起的作用決不會比男性小多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說,只有出現了這樣的認識,人類才有了所謂進步的可能。也只有出現了這樣的認識,那些在舊時代完全沒有理由辯護的事,才有了被救贖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