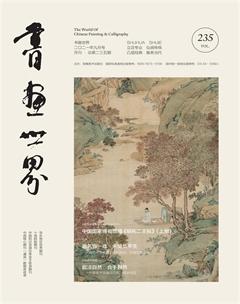俱懷逸興壯思飛順把秋風攬入懷
寒月 翟貴明



詩書畫印,作為中國美學重要的特征,多少年來為中國文人所青睞,成為重要的精神圖譜,彰顯出中國文人獨特的氣質、品位和意趣。詩書畫印的結合,需要多方面的藝術修養,這種全才式的學養只有極少數人才能擁有。當下多數畫作之印,未必出自本人之手,畫中題詩的也不多,大多只為作品起個名稱,對畫作起到延伸和解釋的作用。
從這個角度講,王岳青先生算得上詩書畫印完美結合的成功者。他是書法家、篆刻家,書法篆刻之余喜歡畫大寫意花鳥畫,同時具有極高的文學修養,詩書畫印是他閑暇的樂趣:感懷世事,寫首小詩,畫幅小畫,刻枚印章,率性而作,自得其樂。
俱懷逸興 秋風入懷
王岳青先生和書法的結緣,始于1984年。那年他28歲,是山西省陽泉市礦務局〔后更名為陽泉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一名普通的煤礦工人。有一天,聽說陽泉市文化宮有個書法培訓班,他趕緊報名參加。因為兒時喜歡,有一定功底,他進步飛快,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學生專欄總把他的作品放在第一個。
經過努力,1989年他的書法作品在山西省“企業文化之光”書法大賽中獲一等獎,這是首次在省里獲獎。此后,他一路高歌,作品不僅在山西省第二屆中青年書法篆刻展、第七屆書法篆刻展中獲獎,在山西省第八屆書法篆刻展中獲提名獎,還頻頻入選全國各種書法篆刻展。成績突出的王岳青,2009年被中國書法家協會評為“書法進萬家”活動先進個人,2011年獲得首屆“全國煤炭行業德藝雙馨文藝工作者”稱號。
1994年,他以斐然的成績,順理成章地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礦山出了書法家,是件了不起的大事。他的名氣越傳越遠,不久調入礦工會,后升職為礦工會俱樂部主任,2000年又以當時全市絕對的實力當選為陽泉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從參加培訓班到加入中國書法家協會,王岳青先生僅僅用了十年。
處處留心 玉汝于成
每個人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王岳青能在山西省書法界成為領軍人物,在于他處處留心。
1956年農歷八月二十八,王岳青出生于山西省榆次區北湖村,從小喜歡寫字畫畫。那時家里條件差,他常常從舊墻上摳白灰在地面、門板和墻壁上寫畫。上學后,他的圖畫每次都能得到老師的表揚和很高的分數,寫的仿影,老師給的紅圈圈最多。年紀大一些,他見生產隊的大人在農家后墻寫標語,就站在旁邊琢磨。善于學習和觀察的他,十幾歲就會寫美術字。他在榆次鳴謙中學就讀時,老師發現他的字漂亮,每期學校墻報都讓他出。
父親是個有遠見的人,看他愛學習,小學一年級就給他訂了《中國少年報》,這在20世紀60年代的中國北方農村是罕見的。這份報紙也的確擴大了他的視野,培養了他的閱讀興趣和習慣。20歲那年,他因招工來到陽泉礦務局。先是做一線回采工,由于表現良好,被選拔到礦上“721大學”學習。學習期間,他想起父親訂的《中國少年報》,自費訂了《中國青年報》。他有個工友叫孟生花,是當時太原市書法家王留鰲的大女婿,見他喜歡書法,送他一本小字帖,是后人修改過的《鄭文公碑》。他從此開始日日臨帖,一只腳踏進書法的大門。
上下求索 終成一體
事業有所成就的人,大都懂得把控時間的重要性。王岳青先生年輕時就為自己定下時間表:以晚飯為界線,晚飯前除工作就是篆刻,因為光線充足;晚飯后是臨帖時間。臨帖累了,就隨手畫畫花鳥,權當休息,或者直接躺床上看書,直到晚上12點。幾十年來,這個時間表主宰著他的作息,篆刻,臨帖,讀書,偶爾畫畫,像一日三餐成了生活的必需。尤其是篆刻、臨帖、讀書,一天不做,心里就空得慌。
生活不很富裕,但從小養成的閱讀習慣,已經融入他的生命。他訂閱《書法報》《書法》等報刊,購買大量書籍,文化修養與日俱增,對書法篆刻的認識也從感性上升到理性。同時,他經常和同道好友結伴去全國各地看書法展覽,見識不斷增長,眼界日漸開闊。
他最看重臨帖,認為“學書法不臨帖上不了道”。他先是臨“歐體”,臨了好長時間,發現結字太緊,越寫越死,受了束縛,改臨魏碑《張猛龍碑》《張玄墓志》《楊大眼造像記》等。魏碑棱角分明、拙樸險峻、渾穆奇逸的筆意使他的結字骨力大增,猶如刀劈斧削,入木三分。可是時間一久,他又覺得從法度上看,楷書怎么也繞不過唐楷,又返回來臨“顏體”。他臨《麻姑仙壇記》的時間最長,也寫了一段時間《顏勤禮碑》《多寶塔碑》,學到了顏真卿雄強、大氣、厚重的風格。后來,他又學習褚遂良《陰符經》《房梁公碑》的靈秀、開放和自然,還深入臨摹王羲之、王獻之、米芾、蘇東坡、楊凝式等人的碑帖,潛心鉆研,抓其特點,漸次遞進,見好帖就臨習、研究。同時,他特別在意才華的呈現。他說:“功力不夠,體現不出古意;才華不夠,體現不出自己。”對于行草書,他一直追求個性書寫。快退休的時候,他忽然想到楷書也必須寫出自己的個性,便將目光瞄準鄧石如,認為鄧的字既有歐陽詢的嚴謹工整,又不失顏真卿的厚重大氣,是歐、顏字體完美結合的典范。
盡管書壇公認王岳青先生的楷書寫得相當好,但他從不把楷書作品參展。他認為楷書是基本功的體現,就像練武的人壓腿和站樁,不值得示人,只有行草書才能抒發情感,凸顯格調,才能看出一個人的人生閱歷、文化底蘊和對世界的認知。
王岳青先生的行草書是以章草筆法寫今草,用章草橫勢寫今草縱勢,內含“二王”帖學神韻,外融章草體勢,加之書香的滋養,形成了獨特的行草書風,儒雅樸拙,遒勁清逸。章法和結體上延續了“二王”行草書的特點,行間距與字間距明顯,字形大小相近,呈現出感性和理性的巧妙融合。體勢左低右高,筆法遒麗。字字獨立,氣象高古,筆勢跌宕,環轉穩重,骨肉兼具,蘊含著深厚的文化內涵和滿滿的書卷氣息,像散發著寶光的汝瓷,看似平淡,實則透著貴氣。
疏密聚散 方寸神韻
王岳青先生學習篆刻是在1986年,距在文化宮培訓班學書法僅僅兩年。那時候,他的書法在山西省嶄露頭角,正有噴薄之勢,又瞄上篆刻,希望在篆刻上拓一方天地。然而當時的北方,尤其是山西,篆刻文化積淀不夠深厚,懂篆刻的人鳳毛麟角。
他買了孔白云的《篆刻入門》,逐字研讀;學習吳頤人的《青少年篆刻五十講》和沙孟海的《印學史》,從漢官印滿白文開始摹刻;購置《古璽文匯編》《古璽匯編》等工具書,逐字查對。他大量臨摹古人印痕,吸收古璽印章法參差、開合順勢、向背得當、因體成勢、燦然天成的美學特征,并花費大量心血精研歷代印稿,甚至從潘天壽的花鳥畫構圖中尋找古璽印的章法規律,在傳承中加以創新,總結出一套具有明顯個人特征的古璽印構成方法。
他在筆畫的安排和文字的穿插、重疊、疏密、大小、欹正等方面極盡變化,或生動活潑、妙趣橫生,或挺拔勁秀、玲瓏多姿,或疏密聚散、錯落自然,或渾圓含蓄、古雅淳樸,有法度又好像沒法度。他這樣評價自己的篆刻:“余之治印,向不固守某種模式,因字審形,因形判勢,因勢定制,再三推敲。一稿可隔數日,亦可隔數年,一旦寫稿,則乘興捉刀。”
《各行其道》一印,白文,四字二行分布,右邊占了三個字,左邊只有一個“道”字。“各”字上下錯開,“口”字偏左,為“行”“其”留下一個空白,使右邊的三個字氣息通暢,不至于擁擠。“行”字分成兩部分,“其”夾在中間,“道”字獨占左邊,既突出了“道”的重要,又使整個印章章法疏密有致,平穩協調,讓人玩味無窮。起筆粗,收筆尖而細,金氣重而力道足。
《敢于胡來》,方形朱文印,四字三行排列:“敢”和“于”從右往左,各占一行,“胡”“來”分上下布置在左邊一行。“胡”字的“古”和“月”呈細長狀,占據左邊一條,既強調了“敢”和“來”的激情與沖動,又弱化了“胡”的意義。有些事情是要“敢”去做的,但“胡來”的事不能沾邊。邊款的說明最有趣:“王鐸在其《文丹》中嘗言‘敢于胡來四字。”“敢于胡來”是別人說的,而王岳青先生自己還是“不敢胡來”。此印文風趣俏皮又飽含深意,韻味深刻又空靈協調。
王岳青先生對篆刻相當癡迷,時不時刻枚印章來表述心事。他的朱文印《滿眼荒唐事, 一顆憐憫心》, 借助曹雪芹的“ 滿紙荒唐言, 一把辛酸淚” 句式, 傾訴所思所想。時至立夏,他忽然興發:“拓一組小璽印玩玩。”一下刻了八枚小印章、兩個邊款。他還有很多作品是應邀而作,朱文和白文兩枚《萬印樓》章,就是應山東陳介祺博物館收藏展而刻。陳介祺是清代山東專門收藏印章的大家,他把自己的藏印樓叫作“萬印樓”。
對于篆刻藝術,王岳青先生有自己的看法。他說:“印雖小道,亦須善學。善學者首正其體,次審其勢,三發其韻,四完其神,然后操觚,方能收放自如,開合不悖乎理,變化不詭乎道。”
1989年8月,王岳青先生的篆刻作品入選全國首屆現代篆刻藝術大展;1994年11月與1999年初,連續入選全國第三、四屆篆刻藝術展;1998年,獲山西省中青年書法篆刻展最高獎。同時,他在《書法報》《書法導報》《中國書畫報》《書法賞評》等報刊多次發表篆刻作品,還應邀為國家領導人、專家學者及書畫名家治印,篆刻作品被全國多家博物館收藏。即便如此,王岳青先生仍覺得不夠,花甲之年的他對自己提出更高要求:“篆刻與書畫同理,不僅需要學養與功力的積累,更需要智慧。大智慧者能依托古人碑碣創造自我,若吳缶翁之依托《石鼓文》,齊白石之依托《祀三公山碑》。次智慧者依靠深厚古文字學養創造自家面目,若黃牧甫、趙之謙、吳讓之等先賢。愚者若當代吾儕印人只能在章法上極盡變化之能事。若能有別于古人、今人,此生足矣!”能鉆進去又能跳出來,站在更高的角度看篆刻,先生已經達到一種境界了。
閑暇寫意 情懷覓詩
繪畫是王岳青先生閑暇的水墨游戲。他從小喜歡畫畫,長大后專攻書法,不過寫完字洗毛筆時,常常不由自主地用涮筆水在紙上涂些寫意花鳥畫,久而久之,繪畫成為一種習慣,興之所至,還在畫旁題一句話或寫一首詩,然后蓋上自己刻的印章,形成詩書畫印同構的獨特丹青風格。
他不是專業畫家,卻在筆墨上不輸專業畫家。他筆下的花鳥蟲魚墨色豐富,隨類賦彩,姿態怡然,趣味盎然。他熟練運用勾、點、擦、皴、染等多種技巧,恰如其分地控制筆墨的輕重、濃淡、疏密、干濕的變化,間或配以恰當的色彩,以似與不似的抽象手法,通過點、線、面的巧妙構圖,加上自己的理解,完美呈現筆墨的內在精神。
作為書法家,他有意無意地將書法技巧融于畫中。在他的《秋風過耳》中,葡萄顆粒飽滿,葉片肥厚,藤蔓蜿蜒,筆力縱橫,一氣呵成,足見書法功力。《高花白于雪》以雙鉤筆法畫玉蘭花,枝干蒼勁,花瓣豐潤,花苞鮮嫩,盡顯春日繁華。他畫的花不僅僅是花,畫的鳥不僅僅是鳥。他畫牡丹,大多不點蕊,喻示現代社會人心不古;畫八哥,像黃永玉、齊白石等大家,愛在上面題一些詼諧文字以表心情。
感物傷懷、吟詩弄句是王岳青先生生活的重要組成。秋風襲來,他感慨:“銀杏橫窗已半黃,纖云巧送雁幾行。幽人誰恨日漸短,只戀裙羅卻退藏。”臨寫王羲之小園帖,他由王羲之聯想到自己:“超群攬境氣如虹,百丈游絲在掌中。縱態橫行渾不顧,無今無古任心空。”王岳青先生寫詩,講究平仄、對仗、押韻,格律嚴謹,意境幽遠,氣象萬千。
汲古得新 厚積薄發
王岳青先生讀過很多書,除了書法、篆刻、繪畫、文學等書籍,還讀過很多其他專業的書。他畫作上的諸多題款、書法篆刻的諸多內容,仰仗的就是文化積淀與詩文才情。在對藝術的追求中,他不急功近利,不患得患失,不為藝術而藝術,不為展覽而展覽,把寫字、繪畫、治印、賦詩當作日常生活中的陽光、空氣和水,一步一個腳印,在中國文化的傳承與創新上,踏踏實實地走自己的路。
國內著名書法理論家李庶民先生對王岳青先生的書法和篆刻成就這樣評價:“縱觀王岳青書、印,可窺其在向傳統與現代的多向性變革中,汲古得新,取新用精,適性通變,中節合度,直可當‘筆下無俗情,胸中有古今者。”
決定一棵樹能長多高,不在于枝干有多壯,而在其根能扎多深。詩書畫印皆通的王岳青先生在書壇、印壇甚至詩壇、畫壇處之裕如,作品有言有盡而意無窮的審美效果,就是因為其苦學不輟,根基深厚。然而對他而言,這仍然只是起點,就像當年他剛剛開始學習書法,65歲還堅持每日讀書、臨帖、作畫、治印、寫詩,鐘擺一樣繼續著藝術人生。他以“學古而不背時,趨今而不同弊”的信條維護著詩書畫印,尤其是書法和篆刻的藝術尊嚴,融匯百家,追尋著藝術的更高境界。他的事跡曾被《山西日報》宣傳過,黃河電視臺也為他做過15分鐘的專題報道。在書法和篆刻方面的成就和潛力,讓他成為當今晉東書印界最值得推崇和期待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