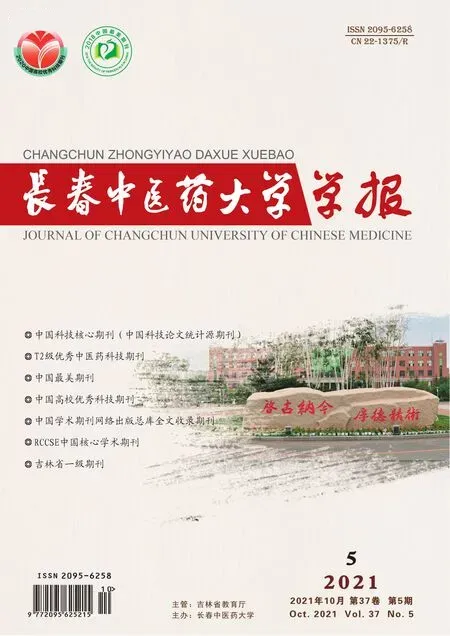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在阿爾茲海默病患者家庭照顧者中的應用效果研究
于雪微,呂 靜,楊 波,李可欣,于 冰
(1.長春中醫藥大學護理學院,長春 130117;2.長春中醫藥大學研究生院,長春 130117)
阿爾茨海默病(Alzheimer’s disease, AD)是一種進行性神經退行性疾病[1],主要表現為記憶力、判斷力、定向力等的整體認知衰退及精神行為異常[2]。在認知衰退的早期階段,大多數AD患者由家庭成員照顧[3]。然而隨著疾病的發展,居家養老的照護模式已無法滿足AD患者的需求,使其照護逐漸由家庭轉向養老機構[4]。研究[5]表明,家庭照顧者將AD患者置于養老機構后不會放棄其照顧者角色,持續的失落感和內疚感導致其悲傷情緒增加,進而對其生存質量產生影響。慢性悲傷管理干預(chronic grief management intervention,CGMI) 作為一種個性化心理干預方法,通過引導式討論使家庭照顧者了解AD相關知識,提高其在溝通和解決沖突方面技能,幫助家庭照顧者緩解家庭成員向機構過渡過程中自身產生的負性情緒,進而提高家庭照顧者的生存質量[6]。因此,本研究將慢性悲傷管理干預用于AD患者家庭照顧者,旨在通過緩解其悲傷情緒,提高生存質量。
1 對象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9年12月-2020年12月入住長春市6所三級養老機構的80名阿爾茲海默病患者家庭照顧者為研究對象,采用隨機數字表法分為觀察組和對照組,各40例。1)患者納入標準:經三級甲等醫院確診且符合WHO國際疾病分類(ICD-10)的診斷標準[7];除AD外,無其他疾病導致的認知功能障礙;入住養老機構的第一年參與本研究。2)患者排除標準:資料信息不全;不符合以上納入標準。3)照顧者納入標準:為AD患者的主要家庭照顧者,且照顧時間最長者;有一定溝通交流能力;自愿參與本研究。4)照顧者納入標準:AD患者主要家庭照顧者為保姆或護工;自身患有AD或合并其他精神疾患。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對AD患者家庭照顧者進行常規健康教育,采取認真傾聽的方式幫助家庭照顧者宣泄心理壓力,包括每月在家庭照顧者探望AD患者時與其進行言語溝通、情緒疏導,或定期與家庭照顧者進行語音通話,了解家庭照顧者目前的情緒狀態,幫助其表達內心想法,舒緩心理壓力。
1.2.2 觀察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進行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具體如下。
1.2.2.1 組建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小組 小組成員包括神經病學專科醫生1名、從事老年護理方向教授1名、護理學研究生3名、臨床心理咨詢師1名。神經病學專科醫生負責篩選符合臨床醫學診斷的AD患者,同時負責完成對家庭照顧者的評估;老年護理教授負責編制慢性悲傷管理干預手冊;護理學研究生和臨床心理咨詢師負責慢性悲傷管理干預的實施,參與并督導整個研究過程。干預前1個月,小組成員均完成15學時的培訓及考核,包括AD相關知識與護理實踐、慢性悲傷管理干預的理論基礎和干預的實施內容等。干預過程安排在連續12周內,會議日期、時間及地點由小組成員同家庭照顧者與養老機構雙方協商后確定,每次會議平均持續60~90 min,每周1次。
1.2.2.2 實施慢性悲傷管理干預 本研究12周小組會議干預內容的制定以Meuser和Marwit構建的癡呆患者照顧者悲傷描述模型為基礎[5]。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分為三個階段:1)知識獲得階段;2)技能掌握階段;3)認識、討論慢性悲傷階段。在首次會議中,小組成員對本研究的目的、意義及過程進行介紹,并強調保密和相互尊重的小組規則。具體干預實施方案見表1。

表1 慢性悲傷管理干預12周小組會議具體實施和內容
1.3 觀察指標
1.3.1 悲傷程度 采用Marwit-Meuser照顧者悲傷量表(the Marwit and Meuser Caregiver Grief Inventory, MM-CGI)評估家庭照顧者的悲傷程度[8]。該量表由高鈺琳等[9]翻譯,包括個人犧牲負擔、內心悲傷和渴望、憂慮和被孤立感 3個維度共18 個條目,采用 Likert 5 級評分,1分表示“非常不同意”,5分表示“非常同意”,得分越高說明悲傷程度越高。該量表Cronbach’s α系數為 0.740,各維度的 Cronbach’s α 系數為 0.835 ~ 0.878,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1.3.2 生存質量得分 采用生命威脅性疾病家庭照顧者生存質量量表(Quality of Life in Life-threatening Illness-Family Carer Questionaire,QOLLTI-F)評估居家或住院患者主要家庭照顧者的生活質量[10]。本研究使用的是中文版QOLLTI—F量表[11],包括7個維度共16個條目,采用 0~4 分計分,分數越高表明主要家庭照顧者生存質量越好,量表及各維度重測信度為0.50~ 0.80。
1.4 資料收集方法
干預前后在學校開具調查介紹信,與各養老機構管理人員溝通,解釋本次研究的內容,闡明研究的目的,取得養老機構管理人員的支持和配合。本研究所有資料均由經統一培訓的3名研究生收集,采用統一的指導語說明問卷的填寫要求,所有調查問卷現場核實、回收,對問卷內容無法理解的調查對象,小組成員逐條進行講解。
1.5 統計學方法
建立Excel數據表,用SPSS 22.0統計學軟件對數據進行分析,計量資料用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用頻數或百分比(n,%)表示,比較采用卡方檢驗。以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2組的一般資料比較
干預結束時,對照組失訪1例(因預留電話后續無法接通),觀察組失訪3例(2例因家庭照顧者需照顧家中幼兒退出;1例因更換養老機構退出),最終完成研究的AD患者家庭照顧者對照組39例,觀察組37例,失訪率為5%(參與率少于50%者視為失訪)。觀察組12周小組會議AD患者家庭照顧者的平均參與次數為(10.81±1.17)次。2組的一般資料比較,見表2。2組家庭照顧者的一般資料比較,見表3。

表2 2組的一般資料比較 例(%)

表3 2組家庭照顧者的一般資料比較 例(%)
2.2 2組干預前后生存質量得分比較
見表4。
表4 2組干預前后生存質量得分比較(±s) 分

表4 2組干預前后生存質量得分比較(±s) 分
注:與對照組比較,# P<0.05
組別 例數 干預前 干預后觀察組 37 42.81±2.38 44.62±2.80#對照組 39 42.31±2.18 43.03±2.17
2.3 2組干預前后悲傷量表總分及各維度得分比較
見表5。
表5 2組干預前后悲傷量表總分及各維度得分比較(±s) 分

表5 2組干預前后悲傷量表總分及各維度得分比較(±s) 分
注:與對照組比較,# P<0.05;與干預前比較,△P<0.05
組別 時間 例數 個人負擔 內心悲傷與渴望 憂慮和被孤立感 總分觀察組 干預前 37 17.68±2.20 19.35±1.96 16.95±2.31 53.97±3.99干預后 16.14±2.32#△ 17.00±2.36#△ 15.59±1.76#△ 48.73±4.29#△對照組 干預前 39 17.97±1.91 19.38±1.94 16.92±2.03 54.07±4.21干預后 17.26±1.87△ 18.33±2.03△ 16.59±2.24△ 52.18±4.15△
3 討論
3.1 慢性悲傷管理干預緩解了家庭照顧者的悲傷情緒
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家庭照顧者干預后悲傷情緒總分及各維度得分均較干預前降低,且明顯低于對照組(P<0.05),說明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可緩解家庭照顧者將AD患者安置養老機構后其自身產生的悲傷情緒。目前我國AD患者大多數采用居家養老的照護模式,居家照顧多由未經過專業培訓的家庭成員提供,包括配偶、成年子女照顧者、親戚[12]。由于AD疾病的特殊性,隨著病情的進展,家庭照顧者已無法滿足AD患者的照護需求,將AD患者安置養老機構成為不可避免的決定。然而將AD患者安置養老機構后家庭照顧者雖緩解了家庭護理帶來的身體疲憊,但內心因不能繼續照顧陪伴父母而產生持續性的內疚感。慢性悲傷管理干預通過向家庭照顧者講解AD疾病發展的進程及各階段病情的變化,增加了家庭照顧者對疾病進展和死亡不可避免性的了解[13],其悲傷情緒有所降低。此外,慢性悲傷管理干預通過引導式討論,鼓勵家庭照顧者分享將AD患者安置養老機構后,面對與家庭成員分離時內心及與家人關系改變方面的感受,幫助家庭照顧者重建信念,改善負性情緒,減輕內疚與失去感;鼓勵家庭照顧者適應無需照顧AD患者的家庭環境,使其積極地投身于新的環境再建積極的人生觀與實現個人價值,以正面的角度與方式來轉移心情,將負性情緒合理化釋放。
3.2 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可提高家庭照顧者的生存質量
本研究結果顯示,干預后觀察組家庭照顧者生存質量得分為(44.62±2.80)分,高于對照組的(43.03±2.17)分,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說明慢性悲傷管理干預可有效改善家庭照顧者的情緒狀態,提高其生存質量。干預前2組家庭照顧者生存質量均較低,究其原因是受傳統孝道觀念的影響,大多數家庭照顧者決定讓家人入住養老機構時內心承受著心理壓力[14],且身體仍處于長期需要照顧AD患者而無暇照顧自己的緊張疲乏狀態[15]。同時家庭照顧者擔心AD患者在養老機構得不到好的照顧,無法滿足家人的各方面需求而對護理人員的照護心存疑慮[16],對各項護理工作提出特殊的要求,進而擾亂了正常護理工作秩序,誘發了矛盾的產生。慢性悲傷管理干預通過鼓勵家庭照顧者相互分享其重新適應無需照顧家庭成員的生活策略,使他們積極投身于生活新的目標和追求之中;使家庭照顧者逐漸正視AD患者的疾病狀況[17],積極地面對生活,更加關注自己與患者的生活質量。此外,慢性悲傷管理干預通過情景再現和小組討論的方式,使家庭照顧者與護理人員置身彼此角度考慮問題,消除彼此矛盾,減輕家庭照顧者緊張疑慮的情緒,促進其與機構護理人員的和諧相處,積極與護理人員進行溝通交流,努力制定自我規劃,豐富日常生活,進而逐漸提高生存質量。
4 小結
慢性悲傷管理干預作為一種個性化心理干預方法,能夠有效減輕AD患者入住養老機構后家庭照顧者的悲傷情緒,增加其對AD相關知識的掌握程度,改善與機構護理人員的人際關系,緩解因無法繼續照顧家人產生的內疚與負罪感,有助于家庭照顧者積極投身于嶄新生活,提高其生存質量。本研究尚有不足之處,僅在實施干預期間對AD患者家庭照顧者的悲傷程度及生存質量進行研究,后續研究可進行隨訪調查,探討該干預措施是否對AD患者家庭照顧者存在持續性幫助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