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岡石窟中維摩詰造像的類型與分期
首都師范大學 | 朱毅
《維摩詰經》又稱《維摩詰所說經》《不可思議解脫經》《凈名經》。該經印度梵本已不存,但自漢末三國時期流布中土以來,成為中土大乘佛教所信仰的主要經典,影響頗深。隨著中國維摩詰信仰的不斷深入,圍繞《維摩詰經》展開的藝術創作活動,也逐漸展開。特別是隨著顧愷之、袁倩等名家的參與,更是讓以《維摩詰經》為中心展開的藝術創作活動,形成了我國中古時期佛教美術的一次創作高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當屬東晉顧愷之與其弟子袁倩的相關創作。據載,顧愷之于瓦棺寺所作維摩詰一改天竺習氣,為士人扮相,“清瀛示病之容,隱幾忘言之狀”[1],一派魏晉名士風骨。這種針對外來題材的本土化風格改造,使這種維摩詰經變相,迅速引起世人的審美共鳴,成為世之典范,使其成為“瓦官三絕”之一。顧愷之后,其弟子袁倩針對《維摩詰經》創作了更為全面的《維摩變相》,被《歷代名畫記》譽為“百有余事,運事高妙,六法備呈,置位無差,若神靈感會,精光指顧,得瞻仰威容”[1],已經具備有后世經變藝術的相關特征。
南朝名士所作《維摩詰經變相》早已佚失,除了相關史籍中的記述,我們無法對其展開實際的認知。與之不同,作為一種重要題材,維摩詰經變相在北朝的諸多石窟中,都有所表現,并留存至今,成為我們窺探中古維摩詰經變相的重要線索。特別是在云岡石窟中,維摩詰經變相,被反復表現,幾乎貫穿云岡石窟的整個開鑿過程,成為云岡石窟的一種重要表現題材。本文著重討論云岡石窟現存維摩詰經變相,通過對其類型研究,結合云岡石窟的整體開鑿歷史,梳理其分期情況,我們發現,云岡石窟中現存維摩詰造像存在一個短暫的獨立發展階段,其在早期造像中表現出強烈的西域文化特征。而后,隨著北魏漢化政策的實施,云岡石窟中維摩詰造像明顯受到南朝影響,在整體風格上表現出日益突出的本土審美因素。其漢化過程,亦可視為南朝佛教文化影響北朝造像風格的一個側影。
一、云岡石窟中現存維摩詰造像概況
經過統計,云岡石窟現存維摩詰經變相35鋪,廣泛分布于1、2、5、6、7、11、13、14、19、24、29、30、31、32、33、35、36、37等18個洞窟當中。其中19窟為云岡石窟一期開鑿洞窟,1、2、5、6、7、11、13、14為云岡石窟二期開鑿洞窟,剩余洞窟為北魏遷洛后開鑿的三期洞窟。其具體分布情況如下表所示:
1窟(圖1),維摩詰與文殊菩薩分列窟門左右兩側內壁(北壁),對稱分布,其中維摩詰居東,文殊居西。維摩詰頭部早年被盜鑿倒賣出國,2017年曾于美國紐約亞洲藝術周公開拍賣。據相關圖冊顯示,維摩詰頭部帶尖頂氈帽,帽下以平紋斜線刻出法線,眉線上調,細目垂視,嘴角上揚,面含笑意,下頜自耳后生出細密短髭,于下巴處聚合成縷。身著對襟交領長袍,袖口緊窄,但左手肘部衣袖寬大下垂,內桌平領內襯,與外衣領口處露出。膝蓋以下風化嚴重,漶漫不清,無法辨認其腳部穿著。右手下垂,撐于座上,左手抬舉,左手殘,無法辨別其手中持物。坐扁平長方形座,座后有一倒三角形背屏。龕頂雕刻一漢式屋頂,屋頂下垂有帷幔。
各窟維摩詰造像的具體位置及表現形式如下:
5窟(圖2、3、4),5窟內存有多幅維摩詰經變相,其維摩詰形象較為多元。5-10、5-11、5-34均為小型維摩詰經變相,維摩詰與文殊分居龕楣兩端,相向而對,表現“文殊問疾”這一主題。其中,5-10中維摩詰跽坐于方形小榻之上,榻下有二足,腰間有一突出之物,為“隱幾”。維摩詰無冠,梳高發髻,面容豐滿,眉眼微閉,形似菩薩。左手扶膝,右手抬舉,手中持有一三角形小扇,當為麈尾。由于造像體量較小,衣紋較為簡略,無法識別其里層衣著樣式,外披著寬袍大袖大衣,衣領出沿兩肩下垂。上覆一平頂,下垂帷幔。5-11中維摩詰交腳箕坐于一平榻之上,平榻之上,墊有軟墊。維摩詰無冠,束發,發髻較小,五官較為平面,更為接近漢人面貌特征,無髭。維摩詰內著交領束腰深衣,下擺呈八字外展式疊放,形同裳懸坐下擺處理方式。外披寬袖大衣,自肩部下垂外展。腰部置隱幾,露出一腿置于身體左側。維摩詰左手下垂,扶于隱幾枝上,右手抬起,肘部置于右膝上,右手持橢圓形麈尾。頂上有一平頂,下垂帷幔,平頂與座榻之間有一方柱連接。5-34中維摩詰位于龕楣右側,頭部崩毀,已無法辨識,坐姿、衣著樣式、手部姿態與著物與5-11中維摩詰相近。5-36中維摩詰形態不明。

圖2 云岡石窟第5-10窟維摩詰造像

圖3 云岡石窟第5-34窟中維摩詰造像

圖4 云岡石窟第5-11龕中維摩詰造像
6窟(圖5),此窟維摩詰經變相為云岡石窟現存規模最大的一鋪,被譽為云岡石窟故事龕雕刻中的上乘杰作。與其他窟龕中的維摩詰經變相不同,該鋪造像位于內室南壁明窗與門拱之間一屋形龕內,正中為釋迦牟尼佛,維摩詰位于佛像左側。維摩詰頭戴尖頂帽,面容飽滿,眉眼細小,面含笑意。有髭,胡須自耳后生出,于下頜處聚攏成三角形。身著交領長袍,領口、袖口、下擺等處有藍色鑲邊,腰部束帶。長袍較短,僅及膝。下身穿著緊口長褲,腳著尖頭靴。坐方形矮榻,榻上飾有波浪狀忍冬紋。左手下垂,撫于榻上,右手抬舉,手持一樹葉形麈尾。身體后傾,整體極為放松。

圖5 第6窟內室北壁維摩詰經變相
7窟(圖6),維摩詰與文殊分別處于內室窟門兩側內壁中層,與1、2窟位置近似。其中維摩詰處于東側,置于盝形龕內,龕楣浮雕飛天,下垂帷幔。維摩詰側身椅坐,由于下部風化嚴重,無法辨識其坐具樣式。維摩詰頭戴尖頂帽,面容漶漫,有髭,胡須自耳后生出,于下頜處聚攏成三角形。身著交領窄袖長袍。右手下垂,似撫于坐具上,左手抬舉,握葉形麈尾。

圖6 第7窟內室北壁西側維摩詰像
11窟(圖7),維摩詰與文殊分列上層明窗左右兩側,其中維摩詰位于左側。維摩詰頭戴尖頂帽,面容飽滿,有髭,胡須自耳后生出,于下頜處聚攏成三角形。身著交口翻領短袍,短袍下擺及膝。短袖,袍袖及肘,露出內衣緊窄的袖口。下身著褲,褲管寬松,腳著圓頭形履。坐方形矮榻,左手撫榻,右手抬舉,手持麈尾。坐姿與其它差別較大,右腿下垂,左腿盤放于右腿之上。

圖7 11窟維摩詰造像
13窟(圖8、9、10)現存維摩詰經變相7鋪,分別位于南壁、13-4、13-12、13-15、13-32等龕。位置相同,除13-15龕為單獨表現的維摩詰經變相外,均位于龕楣附近。維摩詰形象表現與5窟維摩詰類似,均為內著深衣,外披寬袍大袖大衣樣式。跽坐,有隱幾,手持麈尾。麈尾形式不同,除13-15龕為上圓下方形外,13-4南小龕、13-4東柱、13-32等龕均為樹葉形麈尾。

圖8、9、10 13窟部分維摩詰造像
14窟(圖11)現存維摩詰經變相一鋪,為單獨表現的維摩詰經變相,維摩詰形象與5窟維摩詰相似,為深衣披袍式維摩詰,箕作,手持上圓小方形麈尾,有隱幾。

圖11 14窟中維摩詰造像
19窟(圖12)現存維摩詰經變相一鋪,位于19-2龕左右外側上層列龕,維摩詰形象與第5窟相似,且下擺均表現為八字外展式裳懸形式。手持上圓下方形麈尾。

圖12 19窟中維摩詰造像
24、29、30、31、33等窟均存有維摩詰經變相一鋪,位置不一而論,維摩詰形象或崩壞,或漶漫,已無法識別。
32窟現存維摩詰經變相5鋪,其中3鋪位于32-15龕(圖13),一鋪位于32-12龕,一鋪位于32-11龕。其形式大多為深衣披袍,隱幾跽坐式,與5窟、13窟、14窟類似。其中需要注意的是32-11龕和32-15龕中的維摩詰形象。32-11龕維摩詰經變相并不是云岡石窟中常見的圓雕形式,而是以淺浮雕形式表現。浮雕風化嚴重,已無法具體辨別維摩詰衣著形式。從現存殘跡,可依稀看出深衣披袍,隱幾跽坐式。與其它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形象不同,32-11中的維摩詰坐于一平頂行帳當中。32-15龕中維摩詰位于龕內右側,衣著形式依然為深衣披袍,但其坐姿與其它不同,為側臥,右腿曲起,左腿平放。

圖13 32-15龕維摩詰造像
35窟現存維摩詰經變相2鋪,分別位于35-1西壁下層列龕左右兩側和35窟南壁窟門上方。其中35-1龕中維摩詰形象與5窟、13窟、14窟類似,為深衣披袍、隱幾跽坐式。35窟南壁窟門上方維摩詰則形象較為特殊(圖14)。該維摩詰在深衣披袍的基礎上將外展衣裾表現為三角魚鰭狀。坐姿與32-15龕相近,為側臥狀,側臥姿態較32-15龕交代的更為明確。

圖14 35窟南門上方維摩詰造像
36窟現存維摩詰經變相一鋪,位于36-3西壁主像左側下層小龕(圖15)。維摩詰形象為深衣披袍、隱幾跽坐式,衣裾下擺呈八字外展重疊狀。

圖15 36-3西壁維摩詰造像
37龕現存維摩詰經變相一鋪,位于南壁西側,造像風華嚴重,造像細節無法識別。
二、云岡石窟中維摩詰造像的類型
通過對各窟現存維摩詰造像展開具體辨識,我們不難發現,維摩詰作為維摩詰經的主要人物,隨著維摩詰經變相的流傳,反復出現于云岡石窟各窟當中,其形象具有明顯的先后變化。具體而言,我們可將其根據衣著形式、面容特征和身體姿態將其分為胡裝維摩詰、漢裝維摩詰兩個大類。由于漢裝維摩詰在造像細節上較為多元,因此又可根據其坐姿被細分為兩個小類。
(一)胡裝椅坐維摩詰
該造像類型以第1、2、6、7、11-16等窟龕維摩詰造像為代表。其造像特征可以概括為以下幾點。
面容特征:造像的面容方圓飽滿,五官距離較近。平額,鼻線隆起較平緩。細眉,眉毛向后挑起。眼窩較淺,眉眼細小,眼睛微閉。有髭,胡須自耳后生出,于下頜處聚攏成三角形。長耳,耳朵緊貼腦側,耳垂圓扁,但未夸張表現為垂肩樣貌,應為強化維摩詰的世俗身份。
衣著形式:頭戴尖頂帽,尖頂帽底部為圓筒狀,下部較寬,向上逐漸收緊,帽子中間刻平直棱線,并延至帽頂,在帽頂處形成尖角。身著交領窄袖短袍,袍子下緣垂直膝蓋。外袍衣袖較短,下緣至肘部,露出內襯窄袖內衣。領口、袖口、下擺、胸部疊合等處作鑲邊處理。下著寬松長褲,長褲覆靴。雙腳趿履,鞋履形制不一,第6窟中維摩詰著尖頭履,11窟維摩詰則著圓頭履。另外,11-16龕中維摩詰衣著較其它略有不同,其上身所著外袍領口表現為翻領樣式。
坐具與身體姿態:該類型維摩詰坐于方凳之上。不同于床、榻等中國傳統坐具,方凳為一種舶來坐具,最早見于古埃及、兩河流域等西方文明當中。東漢末年,隨著東西方文明交流,傳入中土。宋人吳增《能改齋漫錄》論:“床凳之凳,晉已有此器。”[2]與床、榻等中原傳統坐具不同,方凳是為了滿足垂足而坐的椅坐坐姿而展開的設計。因而其更高,坐者可將腿部自然垂放于地。云岡石窟現存維摩詰造像中,以第6窟、11-16龕中保存較為完整,可明顯看到維摩詰椅坐于方凳之上,雙腿自然垂下的身體姿態。(圖18)除此之外,在11-16龕中,維摩詰除表現有坐于方凳,腿部自然下垂外,其右腿盤屈,疊放于左腿膝蓋之上。(圖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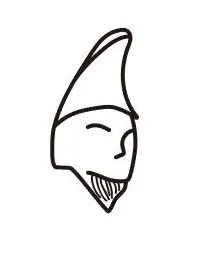
圖16(左) 第7窟維摩詰頭部特寫

圖17(右) 第六窟維摩詰頭部特寫

圖18(左) 第6窟后室南壁維摩詰

圖19(右) 11-16龕維摩詰造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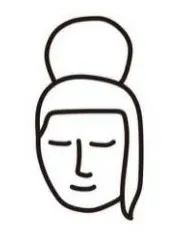
圖20(左) 5-10龕維摩詰頭部特寫

圖21(中) 36-3龕維摩詰頭部特寫

圖22(右) 33-3西壁維摩詰頭部特寫

圖23(左) 5-11龕維摩詰造像

圖24(右) 5-10龕維摩詰造像
(二)漢裝維摩詰
除胡裝椅坐維摩詰外,在云岡石窟中,還流行有另一種維摩詰形象樣式,即漢裝維摩詰。該類型維摩詰廣泛分布于除1、2、6、7、11-16等窟之外窟龕當中。其維摩詰均穿著寬袍大袖之漢服,現將其統一命名為漢裝維摩詰。
與胡裝維摩詰不同,漢裝維摩詰的造像內容更為豐富,可按照其坐具、身體姿態將其進一步細分為漢裝跽坐維摩詰、漢裝箕踞維摩詰兩種類型。
1.漢裝跽坐維摩詰
漢裝跽(箕)坐維摩詰,廣泛分布于5、13、14、32、35、36、39等窟,是云岡石窟中數量最多的一種維摩詰造像形式,其中以5-11龕最具代表。其造像特征表現為如下幾點:
面容特征:面容多呈橢圓形,額骨、顴骨起伏柔和,細眉長眼,眼睛微閉,或直視前方,表現維摩詰與文殊菩薩辯論時的自信灑脫。鼻梁平塌,鼻翼較寬。頜下無髭,面容清秀。(圖20、21、22)
衣著形式:與胡裝維摩詰不同,此類維摩詰身著典型中原士族衣冠,內著深衣,衣服緊窄貼體,呈現出清瘦柔麗的身體審美取向。衣裙較長,下擺一般垂至地面,將整個腿部覆蓋包裹。部分窟龕中,下擺裙裾呈重疊放置狀,衣紋外展,呈八字形打開,與同期其他尊像中的“裳懸坐”類似,繁縟復雜,具有極強的裝飾性。外披寬袍大袖大衣,衣緣敷褡雙肩后,自然下垂。頭頂冠式及發式較為復雜,或頭戴冠巾,其多為漢末形成的平上幘,整體體積較小,置于頭頂之上,或頭戴高籠冠,冠體較大。(圖23)其中5-10龕較為特殊,該龕維摩詰漢服跽作,與矮榻之上,扶有隱幾,手持三角形麈尾。頭部無冠,結高發髻,發髻渾圓,形同肉髻,類同菩薩。(圖24)考慮到第五窟開鑿于北魏遷洛前后,該造像應該為此類型維摩詰造像的早期樣式。
坐具及身體姿態:此類維摩詰造像多呈跽坐或箕坐。跽坐為漢族士族的傳統坐姿,坐時人雙腿屈膝疊放,呈跪姿,臀部坐放于足踵處。跽坐之俗,早于商周時期就已流行,安陽殷墟婦好墓出土跽坐玉人,即為此姿態。李濟先生曾在《跪坐、蹲踞與箕踞——殷墟石刻研究之一》一文中指出:“跪坐是殷人固有的起居習俗,并由此逐步演變成一種供奉祖先、祭祀神祇(跪葬)以及日常生活中待人接客的禮節”,其往往用于正式場合,因而又被稱為“正坐”[3]。這種坐式,也稱為漢族士人的日常坐姿。云岡石窟中5-10龕、13-4南小窟中維摩詰即呈此坐姿,屈膝,臀部枕于小腿和踵部之上。(圖25)

圖25 13-4窟東柱維摩詰造像
2.漢裝箕踞維摩詰
此類維摩詰造像同屬漢裝維摩詰系統,其面容特征、服飾形制均與上述維摩詰形象無異,但其身體姿態與上述維摩詰略有不同,呈踞坐或箕坐狀。
所謂踞坐,《說文解字》曰:踞,蹲也,從足居聲。[4]由此可見,所謂踞坐,即為蹲坐,坐時,人將臀部著地,兩膝自然拱起上聳。這兩種坐姿與跽坐不同,更為舒適,但與禮不合,是輕狂傲慢之姿。魏晉以前,由于服制限制,國人并無褲裝。因此,箕踞于地,難免會走光露點,因而被斥之為無禮,被上層社會所排斥。據《荀子·解蔽篇》記載,孟子曾因妻子踞坐于地而要休妻。魏晉以來,隨著社會動蕩加劇,儒家傳統禮法制度對于社會的鉗制作用逐漸弱化。受玄學影響,越來越多的名士,強調自然、人性,不再遵循傳統禮制,而且蔑視禮制,將其斥之為假。因此,他們自然不會按照傳統禮制來要求自己的坐臥起居,與禮不合的踞坐、箕坐成為名士們的日常主要坐姿。這種特殊的坐姿也稱為當時人們心中名士的視覺形象特征。如南京西善橋六朝墓出土磚鑲壁畫《竹林七賢于榮啟期》中所現人物,即皆為箕、踞之姿,無一正襟危坐。[5]
云岡石窟中此類維摩詰形象較多,是現存數量最多的一種,其廣泛分布于中西部窟龕當中,以5-11、13、14、19、30、31、32、33、35、36、37等窟為代表。其中,呈踞坐狀維摩詰,數量最多,如33-3西壁上層主龕左側維摩詰,維摩詰雙腿盤屈成團,雙膝自然隆起上聳,身體姿態放松。箕坐狀維摩詰數量較少,僅在13、32、33三窟中發現三鋪。其中35窟南壁窟門上方維摩詰造像最為典型。(圖26)該維摩詰坐于矮榻之上,面東而向,臀部著榻,雙腿自然前伸,右腿蜷曲上聳,左腿小腿露于群裾外,足殘損,似為跣足。

圖26 35窟南壁窟門上方維摩詰造像
三、云岡石窟中維摩詰造像的分期
通過類型分析,我們發現,云岡石窟中維摩詰造像主要存在胡裝維摩詰與漢裝維摩詰兩種。其中,漢裝維摩詰又可根據其具體身體姿態,進一步細分為跽坐、踞箕坐兩種。
目前,已知維摩詰造像,主要分布于云岡石窟1、2、5、6、7、11、13、14、19、24、29、30、31、32、33、35、36、37等18個洞窟當中。根據宿白先生的分期理論,這18個洞窟貫穿云岡石窟的整個開鑿過程,其中19窟為一期開鑿,1、2、5、6、7、11、13、14為二期開鑿,24、29、30、31、32、33、35、36、37為三期開鑿。[6]那么,是否現存造像與窟龕開鑿時間一致,能否分別與洞窟分期展開對應。如果無法與洞窟分期對應,云岡石窟維摩詰造像的分期情況又是如何?
(一)云岡石窟一期維摩詰造像
云岡石窟中現存維摩詰造像,開鑿時間最早的洞窟為19窟,位于石窟群西部,毗鄰著名的20窟“露天大佛”,為北魏和平中,高僧曇耀主持開鑿的“曇耀五窟”組成部分。作為云岡石窟第一批開鑿的大型組窟,曇耀五窟是在統一設計下展開施工的,其窟形、題材和造像風格高度近似。洞窟均為穹窿頂、馬蹄形大像窟,佛像面容飽滿,衣紋緊窄,表現出明顯的西域特征。19窟現存維摩詰造像一鋪,位于洞窟北壁2號龕主尊右側靠外列龕上層。該龕從龕形、佛衣形式、天人造型等元素上看,均與云岡石窟一期造像迥異,表現出與龍門石窟②相近的風格特征。由此,我們認為,19窟維摩詰造像的完成時間,并非云岡石窟維摩詰造像中最早者,其應為北魏遷洛后,由民間出資在原有洞窟中補刻完成的小型窟龕。
除19窟外,云岡石窟現存維摩詰造像各窟開鑿年代較早者為7、8窟,據宿白先生考證,7、8窟為《大金西京武周山重修大石窟寺碑》中所謂之“護國寺”,開鑿于孝文帝太和初年(公元471年)。[7]第7窟現存維摩詰造像一鋪,位于內室門洞東側內壁。維摩詰為典型胡裝維摩詰,頭戴尖頂帽,身著交領窄袖袍,面容方圓,有髭,手持扇形麈尾。由于風化嚴重,其下部已無法辨識,但根據遺跡推測,應為椅坐。造像表現出較強的西域因素,符合云岡石窟早期的造像特征。
除7、8窟外,胡裝維摩詰還存在于1、2、6、11等窟當中,這些洞窟多開鑿于云岡二期,為二期代表性洞窟。在這些洞窟中,11窟是云岡石窟現存保存造像銘記最多的洞窟,共有紀年銘刻6處,其具體位置和年份如下:
1.太和十三年銘記(第11窟窟口左上方11-14的東壁)。
2.太和十九年(495)周氏造釋迦、彌勒銘記(第11窟明窗東壁)。
3.太和十九年銘記 (第11窟)。
4.太和二十年(496)銘記(第11窟西壁)。
5.太和二十年銘記 (第11窟西壁)。
6.太和廿年銘記 (第11窟東壁)。[8]
六鋪造像銘記中,以太和十九年銘記時間最早,說明該窟的開鑿時間不晚于此時,其開鑿持續至太和二十年。在充分考慮該窟維摩詰造像的風格特征及其在洞窟中的具體位置后,我們推測該窟維摩詰造像應為該窟早期造像,其具體鑿刻時間在太和十三年前后,即公元489年前后。
在云岡石窟諸鋪胡裝維摩詰造像中,以第6窟中造像最為特別。該窟并未將維摩詰與文殊分置于南壁門洞兩側,而是將其集中安置于南幣門洞上方,以更為整體的畫面布局,表現維摩詰經中的相關內容。因此,相較于其他維摩詰經變相而言,其圖像含義更為復雜,綜合表現了《佛國品》《問疾品》《香積佛品》等多品維摩經義。[9]這種復雜的維摩詰經變相的出現,說明云岡石窟胡裝維摩詰造像的表現已然成熟,因此,其開鑿時間應相對晚于其他胡裝維摩詰。第6窟,又稱佛母塔洞窟,是孝文帝為其祖母文明皇太后馮氏所作之功德窟。因此,其開鑿時間應在文明皇太后去世之后。考慮到文明皇太后去世于太和十四年冬九月,是時平城所在的雁北地區已然入冬,并不適合開窟造像等大規模工程的展開,因此其開鑿時間應延遲至太和十五年,即公元491年。那么,此窟中的維摩詰造像的具體開鑿時間,也應在太和十五年之后,是云岡胡裝維摩詰造像中開鑿時間最晚的一鋪。
(二)云岡石窟二期維摩詰造像
漢裝維摩詰是云岡石窟現存數量最多的維摩詰造像類型,其分布較廣,其中既有一期開鑿的19窟,也有二期開鑿的第5、11、13、14等窟,還有北魏遷洛后開鑿的24、30、32、35、36、37等西部諸窟。因此,其分期情況更為復雜。
云岡石窟中現存漢裝維摩詰造像諸窟中,以19窟開鑿時間最早,但上文已經論述,19窟中維摩詰造像,應為北魏遷洛后補刻,因此其實際雕鑿年代較晚。現存維摩詰諸窟中除19窟外,以第5窟開鑿時間最早。據宿白先生考證,5窟開鑿于太和十年至太和十八年遷洛時(486—494),遷洛后其工程仍未全部完成。[6]第5窟中現存維摩詰經變相四鋪,分別位于5-10、5-11、5-34和5-36等上層小龕。其位置均位于小型佛龕龕楣兩端。維摩詰一改一期造像中的胡風胡貌,搖身變為寬袍大袖、褒衣博帶的漢族士人模樣。其中除5-36龕風化嚴重,維摩詰形象無法辨識外,其他三龕維摩詰保存較好。第5窟,為孝文帝為自己開鑿的功德窟,分為內外兩室,內室不同于云岡石窟二期方形平頂窟形,為橢圓形穹窿頂。主像為三世佛,但佛衣已演化為褒衣博帶式漢化佛衣。這種佛衣樣式的改變與北魏太和十年開始的服制改革關系密切。據《魏書·高祖紀上》:太和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服袞冕”,“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卿服裝”[10],由此開啟了北魏服制的漢化改革。但是,這種類似模仿士大夫日常著裝的佛衣樣式,其實并非北魏首創。四川茂汶出土的齊永明元年(483年)釋玄嵩造像碑中,就已經出現這種漢化佛衣的成熟表現形式。而在開鑿于晉宋之交的南京棲霞山千佛巖一期窟龕中,這種佛衣就已經出現。那么云岡石窟中的漢裝維摩詰是否出現于太和十年服制改革之后呢?
在對第5窟漢裝維摩詰造像的具體位置展開分析后,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維摩詰造像大多位于窟內小龕的龕楣兩側,這些小龕位置混亂,不似在統一規劃下完成。基于此,宿白先生曾在《云岡石窟分期試論》一文中指出,在太和十八年遷都前,第5窟并沒有整體竣工。[6]因此在遷都之后,民間力量參與到該窟的建設當中,導致出現這種無序的開窟現象。因此,云岡石窟中的漢裝維摩詰造像應為太和十八年北魏遷都之后,由民間出資開鑿的。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借口南伐將都城由平城前往洛陽,并全面展開漢化政策。太和十八年十二元下詔禁穿胡服,百官改著漢族朝服。太和十九年六月下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同月下詔“遷洛鮮卑貴族一律落籍洛陽,死后不得還葬平城”;太和十九年八月,于洛陽設國子學、太學、四門小學。太和二十年正月,下詔“改鮮卑復姓為單字漢姓”。[10]相較于太和前期文明皇太后馮氏而言,孝文帝于此時實施的漢化政策更為徹底,也標志著北魏政權開始全面向漢族傳統文化靠攏。受此影響,北魏石窟造像的風格也發生了相應變化,其造像中以南朝佛教造像為代表的本土審美元素更為明顯。
在針對第5窟中維摩詰造像展開分析后,我們不難發現,作為云岡石窟最早出現漢裝維摩詰造像的洞窟,該窟中的維摩詰造像為我們勾勒出了這種新型維摩詰造像在云岡石窟的發展脈絡。第5窟現存維摩詰造像中,以5-10龕造像最為特殊。該龕維摩詰與文殊菩薩分列龕楣兩端,其中維摩詰居于龕右,跽坐與方形矮榻之上。有隱幾,隱幾中間一腿置于兩腿中間。手持三角形鏟狀麈尾。內著衣裝樣式不清,外披大氅,衣袖較短,整體不似后期舒展、飄逸。頭部無冠,高發髻,形同菩薩。這種造像形式,明顯雜糅了云岡本土造像因素與南朝外來因素,較其他漢裝維摩詰相比,更為原始。地處河西地區的炳靈寺石窟169窟中保存有中國目前已知最早的維摩詰造像,據題記顯示,該窟完成于西秦建弘元年(公元420年)。其中維摩詰經變相位于第11龕第三層壁畫中,維摩詰作菩薩裝,擁被病臥狀。左側墨書榜題“維摩詰之像”、“侍者之像”。由此可見,在早期石窟中,即有以菩薩形象表現維摩詰之先例。踞《維摩詰經》,維摩詰為修習在家的大乘佛教居士,是著名的大乘菩薩。因此,將維摩詰表現為菩薩形象,與原始經典并無沖突。但是,這種形象的維摩詰像數量極少,目前已知的僅有炳靈寺169窟一輔。云岡第5窟中的這尊菩薩裝坐榻維摩詰有可能受河西舊俗影響,也有可能是工匠并不熟知漢家衣冠所致。③
與之相比,該窟其他維摩詰造像的漢化形式明顯更為徹底,其形式與南京西善橋出土的劉宋磚鑲墓室壁畫極為接近,表現出強烈的南朝特征。特別是5-11龕,在維摩詰造像中還出現了較為標準的衣裳垂跌的表現形式,而這種衣紋處理方式最早出現于南朝,在開鑿于晉宋之交的南京棲霞山千佛巖一期洞窟中即已經成熟。此外,在四川茂汶境內出土的齊永明元年釋玄嵩造像碑中,也可以看到成熟的裳懸式衣紋處理方法。[11]除了細節表現更為準確,云岡石窟漢裝維摩詰在造像的整體表現上,日益飄展、流暢,整體審美特征與南朝藝術所強調的審美特征愈發貼近。
通過對第5窟維摩詰造像的風格分析,我們可以明顯看到兩種風格樣式之間的前后順序,以及風格之間的演化脈絡。而在晚于5窟的13、14等開鑿于太和十八年前后的窟龕當中,漢裝維摩詰造像不僅本土文化元素更為明顯,而且數量大幅增多,成為云岡石窟所熱衷表現的主要題材。由此,我們可將這批造像歸為云岡二期維摩詰造像,其風格特點為:面呈橢圓形,五官柔和,無髭,面相清秀。漢裝,頭戴漢式冠籠,維摩詰內著深衣,外披大氅,衣袂掩足。手持麈尾,麈尾多為上圓下方式,跽坐于矮榻之上。
(三)云岡石窟三期維摩詰造像
景明年后,隨著北魏政權在漢化政策上的不斷深化,北魏晚期石窟造像的漢化色彩更為強烈,出現了“南式飛天”、裳懸式衣紋處理方法等全新造像元素。而在云岡模式影響下開鑿的龍門石窟,也逐漸擺脫云岡舊有因素的影響,逐漸成熟,形成全新的石窟開鑿模式,并對北魏境內其他石窟造像展開風格影響。而維摩詰造像,作為龍門石窟中的重要表現題材,也不例外,其進一步吸收南朝影響,呈現出更為濃郁的本土審美特征。
作為景明年后龍門石窟的代表性窟龕,賓陽洞始鑿于宣武帝景明元年,但因工程量過大,在北魏一代,僅完成賓陽中洞的整體施工。與云岡石窟相比,賓陽中洞無論是在窟龕形制上,還是在造像的具體風格上,都表現出更為強烈的南朝色彩。該窟北壁門洞兩側,保存有維摩詰與文殊造像各一鋪,其中維摩詰頭戴高籠冠,身著褒衣博帶衣,半躺側臥于飾有壺門的大床之上,身后倚靠在圓形隱囊之上,手持上圓下方形麈尾。床上置有帷幕,側面立柱上懸掛有垂幛環壁。床側立有漢裝侍女兩軀,頭上梳有雙髻。其整體相對于古陽洞中的維摩詰造像而言,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南朝特征。這種全新的維摩詰造像形式,也影響了云岡石窟三期維摩詰造像,使其在二期造像的基礎上,表現出更為明顯的南朝風格。
云岡三期維摩詰造像主要集中于20窟以西的21-45窟。這些洞窟現存維摩詰造像的整體風格特征,表現出了相較二期維摩詰造像更為強烈的漢化因素。在35南壁窟門上方,保留有維摩詰經變相一鋪,其中維摩詰居于右側。該像頭戴高籠冠,面部殘損不清。身著對襟漢裝,左手持棱形麈尾,右手撫于隱幾之上。身體姿態舒展,表現為近似半躺狀的箕坐狀,其左腿前伸,右腿屈膝,左腳露于裙裾之外,足部殘毀。其身體姿態與龍門石窟賓陽中洞中的維摩詰造像極為相似,但不同之處在于賓陽中洞中的維摩詰造像身靠隱囊,而該像仍使用隱幾。其實,從身體姿態上看,這種近乎半躺的身體姿態使用隱囊更為合理,但云岡石窟中仍然使用隱幾,可能是皇室南遷后,平城當地工匠不熟悉新的圖像粉本所致。這也說明遷都后,平城已成為塞北邊陲之地,其文化發展程度明顯落后于新都洛陽。另外,該像最為值得關注的是其對衣紋的處理方式,其衣紋外展,形成尖角凸起。日本學者吉村憐先生將其形象的稱為“魚鰭狀”衣紋。據費泳教授在其《南朝佛教造像研究》一文中,具體歸納了這種衣紋表現形式的發生及傳播脈絡。其認為這種衣紋表現形式最早出現于南朝晉宋年間,在棲霞山一期下024窟正壁主尊右側的脅侍菩薩立像中已有較為成熟的表現。[11]而在北朝,這種衣紋表現形式最早出現于云岡二期造像中,多被用于對立佛、立菩薩及裳懸座的處理上。該像并非立像,且其身份也非佛、菩薩。因此,在維摩詰造像中使用這種衣紋處理方式,足以說明北魏工匠已完全接受這種南朝造像形式,其在吸收南朝影響的同時,還主動融入自身的審美意識,對其加以改造。
另外,32-11龕遺存有一副浮雕狀維摩詰經變相,該像因位于窟門外側,因而風化嚴重,僅殘留有維摩詰一側圖像。其中維摩詰坐于床幔之中,床幔右側刻有漢裝侍女三人。空中刻有飛天兩軀,這些飛天身姿飄逸,軀體自腹部向后彎曲,衣袂飄揚,線條流暢,夸張的天衣與飛天整體構成團花的蓮花形外觀。據吉村憐、費泳等學者研究,這種飛天樣式最早出現于南朝,其本質是對凈土中蓮花化生的形象表現。[12]成都萬佛寺宋元嘉二年(425年)經變石刻中就已經出現這種成熟的飛天樣式。在云岡二期造像中,并未出現這種南朝風格的飛天形象,直至北魏遷都之后,隨著漢化程度的增強,這種南朝風格的飛天形象才大量出現于龍門、鞏縣等石窟造像當中。32-11龕維摩詰經變相,出現此類飛天形象的同時,表現出相較以往維摩詰經變相更為復雜的情節性構圖,都可以視作南朝文化影響下的風格轉變。
由此,我們可以對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造像的分期情況展開歸納。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造像最早出現于二期北魏文成帝后的延興年間,而后一直延續使用至北魏正光三年六鎮起義之前。可被分為三期,其具體分期情況如下表:

表2 云岡石窟維摩詰造像分期
四、結論
作為佛教藝術中國化的重要標志,維摩詰造像為我們勾勒出了早期佛教藝術漢化的基本演變脈絡,成為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研究的重點。遺憾的是,由于歷史原因,目前南朝早期針對維摩詰形象展開的漢化創作,均已不存,我們只能通過文獻記載對其展開想象。因此,散落于北朝境內的維摩詰造像,就成為了解魏晉時期維摩詰造像的關鍵。作為北朝重要的石窟遺存,云岡石窟因其顯著的皇家色彩,成為公元5世紀中國佛教藝術的典范。而散落于石窟中的三十余尊維摩詰造像,無疑是梳理中古時期維摩詰造像風格演變的重要證據,其理應受到學界重視。本文在對云岡石窟中現存維摩詰造像的藝術形式入手,展開類型研究,將其歸納為胡裝維摩詰和漢裝維摩詰兩種主要類型,其中漢裝維摩詰又可因其身體姿態被進一步細分為兩個亞型。在理清維摩詰造像的類型特征后,我們結合相關史料,對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造像的發展脈絡展開梳理,將其分為三個階段:一期造像始于延興元年(471年),沿用至太和十年服制改革前后(486年);二期造像始于太和十八年(494年),沿用至景明前(500年);三期造像始于景明年后(500年),沿用至正光三年六鎮起義前(524年)。
作為北朝重要的石窟造像,云岡石窟的造像風格受到多種文化元素共同影響,已成為學界共識。這種多元的風格特征在維摩詰造像的風格演變上也有突出表現。公元439年,北魏太武帝親征,一舉攻破割據于河西地區的北涼政權。滅涼后,太武帝徙涼州僧眾于平城,從此“沙門佛事皆向東”,魏都平城成為北方新的佛教中心。在短暫的滅法政策后,北魏皇室復歸佛法,并在涼州僧人曇耀的建議下,于京西武州塞開鑿大象五軀。由此可見,云岡石窟的開鑿,完全是在涼州石窟的基礎上展開的,涼州模式對其產生了深刻影響。但是,如果我們對此展開深究,就會發現,作為絲綢之路上的重要關口,涼州也并非這種石窟形式的始作俑者,其開鑿模式源自西域。關于此,宿白先生曾在其《中國石窟寺研究》一書中,為我們具體勾勒了這條風格傳播脈絡,在其看來位于南疆境內的龜茲最先形成開鑿模式,而后龜茲影響涼州,而涼州影響云岡。[13]這一風格傳播模型,為我們解釋了云岡石窟中一期維摩詰造像的風格淵源。其一期造像中的尖頂帽、翻領對襟短袍、收口褲和皮靴等胡服著裝與高足方凳等西域坐具,正是龜茲等西域國家的物質文明,其表現出西域佛教藝術對云岡的風格影響。
而后,隨著北魏漢化政策的不斷深化,以南朝為代表的中華文明成為北魏政權學習和模仿的對象。受此影響,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造像開始于太和十年服制改革后,產生風格變化,出現以南朝維摩詰經變相為藍本創作的漢裝維摩詰。這種造像類型被廣泛出現于開鑿于孝文帝遷都前后的第5窟中,仔細梳理第5窟中的維摩詰造像,我們不難發現其在漢化維摩詰形象的表現過程中存在一個由模糊到清晰的演化過程。太和十八年后,隨著北魏漢化政策的不斷強化,北魏對于漢魏傳統的認知不斷加深,其在漢化維摩詰造像的表現上也日益成熟,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造像也表現出愈發明顯的南朝色彩,出現了諸如外展衣紋、蓮花式飛天等典型南朝造像因素。由此可見,云岡石窟中的維摩詰造像,為我們全面展示了公元5世紀末,北魏佛教造像的風格演變脈絡,它是我們了解當時中國佛教藝術整體發展的重要物質材料。
注釋:
① 關于云岡石窟中現存維摩詰經變相數量,趙昆雨先生在其《云岡石窟:佛教故事雕刻藝術》中統計數量為34鋪。據筆者實地調查發現,于36-3龕主尊西側維摩詰像未被記錄,故其實為35鋪。
② 龍門石窟維摩詰。
③ 據《魏書·高祖本紀上》載:太和十年,正月癸亥朔,帝始袞冕……夏四月辛酉朔,始制五等公服。在此之前,北魏一直固守鮮卑舊俗,其對漢族衣冠禮制并不了解。改制后,北魏鮮卑貴族對漢式衣冠的接受程度較低,直至太和十九年后,仍有北魏貴族拒穿漢族衣冠。另據費泳教授《南朝佛教造像研究》,孝文執政時期,北魏服制漢化并不徹底,《南史》卷六一載:南朝梁武帝天監元年(502年)入北魏褚緭,參加北魏元會看到大臣服飾時作詩曰:“帽上著籠冠,褲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由此可見,當時北魏對漢族衣冠了解極為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