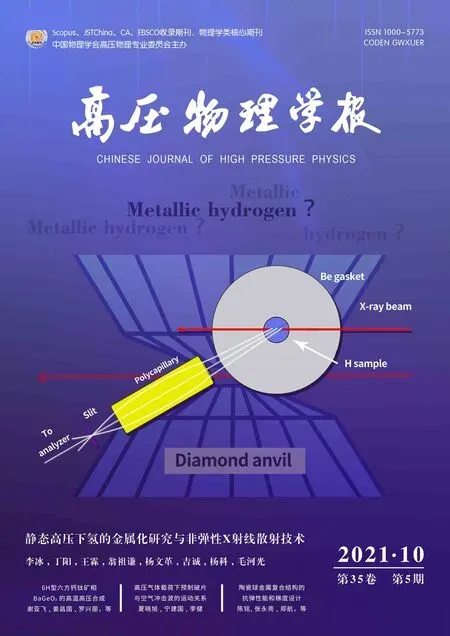層狀千枚巖的斷裂特性
藺海曉,錢立振,程 龍,郭騰飛
(1. 河南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河南 焦作 454003;2. 河南理工大學河南省地下工程與災變防控重點實驗室,河南 焦作 454000;3. 中南大學資源與安全工程學院,湖南 長沙 410083)
層狀巖石是地下工程中一種常見的復雜介質[1-2],受層理結構面的影響,其變形和強度具有明顯的各向異性特征,同時巖層內部還包含大量的構造裂隙。層狀巖體的各向異性特征以及巖層內構造裂隙引起的非連續性極易誘發巷道、隧道及硐室圍巖失穩破裂,為構筑和安全使用地下工程結構帶來了極大的挑戰[3-5]。因此,研究層狀巖石的斷裂力學特性具有重要意義。
目前,非層狀巖石的相關研究已經開展了大量工作,包括巖石的斷裂韌度[6-7]、斷口幾何形貌特征[8]、加載速率對斷裂特性的影響機制[9]、宏觀斷裂與巖樣細觀結構的關聯性[10]、溫度對斷裂特性的影響[11]、巖樣斷裂過程中的聲發射特征[12]、復合型斷裂機理[13]及巖樣斷裂的尺寸效應等[14]。近幾年,層狀巖體的斷裂特性也逐漸引起科研人員的關注。趙平勞[15]、裴建良等[16-17]基于層狀巖石單軸壓縮及常規三軸試驗,研究了層狀巖石抗壓強度、變形特征及微觀斷口形貌。Nasseri 等[18]和Cho 等[19]基于單軸壓縮試驗及常規三軸試驗,分析了不同層理傾角下片巖的強度和變形特性。呂有廠[20]基于半圓盤三點彎曲試驗,探究了加載速率對3 種預制切槽層理頁巖(Crack-arrester 型、Crack-splitter 型和Crackdivider 型)Ⅰ型斷裂韌度的影響規律。趙子江等[21]采用層理直切槽半圓盤試樣和人字形切槽半圓盤頁巖試樣進行三點彎曲試驗,對比分析了兩種試樣測得的Ⅰ型斷裂韌度及斷裂機理。衡帥等[22]基于圓柱形三點彎曲試驗,討論了平行層理及垂直層理張拉載荷作用下層狀巖石的斷裂韌性各向異性特征及裂縫擴展形態。趙小平等[23]分析了層狀大理巖在垂直層理及平行層理三點彎曲作用下的細觀斷裂機理。黎立云等[24]獲得了預制裂隙垂直層理及平行層理在三點彎曲載荷作用下的臨界斷裂曲線。潘睿等[25]的研究表明,層狀頁巖斷裂能各向異性對巖石裂縫擴展偏折路徑有重要影響。目前的研究工作大多集中在層狀巖石的單軸和三軸壓縮的變形及強度特征方面,而針對層理效應的斷裂性能研究也僅涉及3 種類型(Crack-arrester 型、Crack-splitter 型和Crack-divider 型)平行層理和垂直層理方向加載,因此有必要進一步對層狀巖石的斷裂特性開展深入研究。
本研究將層狀千枚巖加工成不同層理傾角的中心直切槽半圓盤試樣,開展三點彎曲試驗,并通過Abaqus 有限元分析軟件建立層狀數值計算模型,研究不同層理傾角、層理強度和層理間距等層理效應在彎拉載荷作用下的斷裂性能。
1 層狀千枚巖三點彎曲試驗
巖樣取自長沙市某工程的層狀千枚巖。單軸壓縮試驗測得其垂直層理方向的彈性模量為27.63 GPa,泊松比0.16;平行層理方向的彈性模量為95.17 GPa,泊松比0.25;層理間距為2~3 mm。將巖樣加工成半徑(R)為50 mm,厚度(B)為20 mm,中心垂直直徑方向預制切縫深度(a)為15 mm,縫寬約為1 mm,層理傾角( θ)分別為0°、15°、30°、45°、60°、75°、90°共7 種半圓盤試樣,如圖1 所示。每種層理傾角制備3 個試樣。圖2 為試樣的幾何尺寸及加載方式,試樣下方簡支跨距2S為80 mm。三點彎曲加載試驗在河南理工大學土木工程學院50 kN 萬能試驗機上進行,加載控制方式為位移控制,位移控制速率為0.02 mm/min。

圖1 不同層理傾角的巖樣Fig. 1 Rock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bedding dip angles

圖2 試樣的幾何尺寸和加載方向Fig. 2 Geometrical dimensions and loading direction of the specimens
2 試驗結果
2.1 斷裂韌度分析
試樣的Ⅰ型斷裂韌度由Kuruppu 等[26]的計算公式確定

式中:KIC為I 型斷裂韌度;pmax為試樣受彎拉載荷作用下的峰值載荷;YⅠ為Ⅰ型無量綱應力強度因子,可通過有限元計算得到。基于本次試驗中巖樣的宏觀力學參數,采用Abaqus 有限元分析軟件建立圖3 所示的應力強度因子計算模型,預制裂隙尖端設置為CPS6 單元,其余部分均為CPS8 單元,施加的單位載荷為1 N。結合式(1)換算無量綱應力強度因子YⅠ,為確保模型計算結果的準確性,將計算結果與文獻[27]數據對比分析,結果顯示誤差較小,見表1。

表1 中心直切槽半圓盤無量綱應力強度因子結果比較[27]Table 1 Comparison of dimensionless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for a half disk with a central straight slotted[27]

圖3 應力強度因子計算模型Fig. 3 Calculation model of stress intensity factor
試驗設定a/R= 0.3、S/R= 0.8 時,中心直切槽半圓盤構型試樣的無量應力強度因子YⅠ=4.783。由式(1)計算得到各層理傾角試樣的斷裂韌度見圖4,擬合結果為

圖4 不同層理傾角試樣的斷裂韌度Fig. 4 Fracture toughness of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beddings dip angles

層狀巖石Ⅰ型斷裂韌度隨層理傾角的變化表現出明顯的各向異性特征:Ⅰ型斷裂韌度隨層理傾角在0°~90°變化過程中,呈現逐漸增大的趨勢。層理傾角為零時,Ⅰ型斷裂韌度值最小;層理傾角為90°時,Ⅰ型斷裂韌度值最大。兩者相差約3.58 倍,與趙子江等[21]測定的層理頁巖Ⅰ型斷裂韌度變化規律類似。但在平行層理方向加載下,千枚巖的斷裂韌度約為頁巖斷裂韌度的1.54 倍;垂直層理方向加載下,千枚巖的斷裂韌度約為頁巖斷裂韌度的3.47 倍。
2.2 層狀千枚巖的載荷-位移曲線分析
圖5 為三點彎曲載荷作用下7 種層理傾角試樣的典型載荷-位移曲線。如圖5 所示,三點彎曲載荷作用下層狀千枚巖的載荷-位移曲線變化大致可分為4 個階段。(1)壓密階段。加載初期,豎向載荷作用下曲線的斜率由小逐漸增大,曲線下凸明顯,且層理傾角在0°~90°變化過程中,即豎向載荷與層理面方向逐漸接近垂直時,該階段愈發明顯。(2)彈性階段。該階段曲線斜率保持不變,應變能逐漸累積,試樣內微裂隙逐漸發育。(3)屈服階段。該階段持續很短,曲線斜率逐漸變緩下凹,微裂隙進一步累積、發展并貫通,材料剛度下降,試樣即將破壞。(4)峰后陡降段。該階段試樣達到峰值載荷后,載荷迅速斷崖式跌落至較小值甚至為零,此時試樣已脆性破壞。當層理傾角在0°~90°范圍內逐漸增大時,試樣破壞時的峰值載荷對應的破壞位移有較大差異。層理傾角為0°時,峰值載荷對應的位移最小,且隨層理傾角的增大,峰值載荷對應的位移有增大的趨勢;當層理傾角為75°時,峰值載荷對應的位移最大,二者相差約2 倍。

圖5 不同層理傾角試樣的載荷-位移曲線Fig. 5 Load-displacement curves of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beddings dip angles
3 層狀千枚巖的斷裂過程分析
3.1 材料本構模型
采用Abaqus 有限元分析軟件,嵌入零厚度黏結單元模型(Cohesive zone model),模擬層狀千枚巖材料的復雜裂紋擴展路徑,通過自編程序將零厚度黏結單元全局嵌入初始網格中。圖6 為所采用的三角形黏結單元模型,其中三角形應力單元之間由嵌入的零厚度黏結單元相連。圖7 為黏結單元的黏結滑移關系,可通過式(3)和式(4)描述。

圖6 黏結單元模型Fig. 6 Model of bonding element

圖7 黏結單元線性牽引分離定律Fig. 7 Linear traction separation law of bonding element

式中:i表示法向(n)或切向(s)方向;τi、δi、ki分別為黏結應力、相對位移和初始剛度; τn、 τs分別為零厚度黏結單元面上的法向黏結應力和剪切方向黏結應力(法向黏結應力可誘發張開位移,切向黏結應力可誘發滑動位移。); δn和 δs分別表示法向相對位移和切向相對位移;kn和ks分別為法向剛度和切向剛度;kiu為斷裂過程中的損傷剛度,D為斷裂過程中的損傷變量,變化范圍0~1。參數的詳細確定方法參考文獻[28]。
3.2 層狀千枚巖數值模型及參數
基于圖6 所示的三角形黏結單元,以30°層理傾角試樣為例,建立中心直切槽半圓盤試樣的數值模型,如圖8 所示。將有限元模型劃分為邊長為2.5 mm 的三角形實體單元,之后在1 322 個三角形實體單元中全局嵌入零厚度黏結單元。將模型中的層理間距統一設為5 mm,模型幾何尺寸與室內試驗試樣的幾何尺寸保持一致。模型的相關計算參數見表2。

圖8 試樣的數值模型Fig. 8 Numerical model of specimens

表2 模型中的單元力學細觀參數Table 2 Microscopic parameters of element mechanics in the model
3.3 模型驗證及斷裂過程分析
表3 為7 種層理傾角半圓盤試樣的室內試驗與數值模擬破壞結果比較,可以看出室內試驗與數值模擬的載荷-位移曲線吻合較好。從7 種不同層理傾角試樣的試驗與模擬破壞結果來看,二者破壞模式基本相同:層理傾角為零時,裂紋自預制裂隙的尖端沿層理面延伸至加載點,發生張拉破壞;層理傾角為15°時,裂紋沿層理面滑移擴展至偏離上部加載點位置,發生剪切破壞;層理傾角為30°時,裂紋先沿層理面滑移擴展,隨后偏離滑移面逐漸切層向加載點靠攏,主要發生剪切破壞;隨著層理傾角繼續增大為45°時,裂紋沿層理面擴展一段距離后,逐漸發生轉向,沿層理呈階梯狀向前延伸破壞,試樣發生拉-剪耦合破壞,且以剪切破壞為主;層理傾角為60°時,試驗和數值模擬試樣的裂紋起初沿層理面滑移延伸小段距離后,在試樣內拉應力的作用下突然轉向加載點穿層張拉破壞,形成張拉裂紋占主導的拉-剪耦合破壞;層理傾角為75°時,在層理的影響下,試驗試樣中的裂紋與層理面成一定夾角穿層擴展,伴有少量剪切裂紋,主要發生張拉破壞,而模擬試樣裂紋沿層理面滑移后,逐步穿層擴展,仍表現為以張拉破壞為主;層理傾角為90°時,裂紋受預制裂隙尖端處層理的影響,先偏向層理面擴展,隨后在試樣拉應力作用下,裂紋向上發生偏轉,逐步偏折穿透層理沿加載軸線向加載點擴展,主要發生張拉破壞。對比7 種層理傾角試樣的試驗與模擬裂紋擴展路徑發現,二者在層理傾角為60°、75°和90°時,裂紋擴展路徑稍有差別,但破壞模式一致,均為張拉破壞為主。

表3 不同層理傾角試樣的試驗與數值模擬結果對比Table 3 Comparison between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simulation results of specimens with different bedding dip angles
圖9 為Dou 等[29]基于矩形梁試件的層理頁巖三點彎曲試驗斷裂破壞結果,對比本研究中的層狀千枚巖斷裂破壞結果可以發現,二者雖均為層理結構巖石,但斷裂破壞模式及裂紋擴展形態卻存在差異。層理傾角為零時,層理頁巖與層狀千枚巖的裂紋擴展形態一致,均呈張拉破壞。層理傾角為30°時,層理頁巖與層狀千枚巖裂紋的擴展形態基本一致,但層理頁巖以張拉破壞為主,而本研究中的層狀千枚巖則以剪切破壞為主。層理傾角為60°和90°時,頁巖與千枚巖的裂紋擴展形態有較大差異,受層理傾角的影響,頁巖裂紋擴展路徑趨于平直狀,而千枚巖裂紋擴展路徑卻呈曲折狀。整體來看,千枚巖的裂紋擴展路徑受層理傾角影響較頁巖更明顯,說明千枚巖的層理強度與巖石基質體強度差異較頁巖更明顯,即千枚巖的層理效應強于頁巖。

圖9 不同層理傾角頁巖的斷裂破壞[29]Fig. 9 Fracture failure of shale with different bedding dip angles[29]
由上述分析可知,除層理傾角為零的試樣外,其余試樣的裂紋擴展路徑并不像勻質試樣自裂尖沿徑向直接貫通至加載點,而是受層理影響發生偏折擴展,使裂紋擴展路徑發生較大差異。層理傾角在0°~90°范圍變化過程中:當層理傾角為零時,發生張拉破壞,即典型的Ⅰ型斷裂;層理傾角增加至15°~45°時,剪切破壞占主導;層理傾角繼續增大至60°~90°時,張拉破壞占主導。由此可見,受層理面的影響,試樣呈現拉伸-剪切-拉伸斷裂的演化趨勢,表明層理面對斷裂破壞模式及裂紋擴展路徑有較大影響。
3.4 相關參數對破壞模式的影響分析
3.4.1 層理強度對破壞模式的影響
表4 為基于上述數值模型開展的不同層理傾角、不同層理強度試樣的數值模擬破壞結果,層理強度參數分別設置為表2 所示層理強度參數的0.5、0.8、1.1 和1.5 倍。從表4 可以看出:層理傾角為零,層理強度由低到高變化時,裂紋均沿層理貫通至加載點產生張拉破壞。層理傾角為15°,層理強度為0.5、0.8 和1.1 倍時,裂紋沿層理發生滑移破壞;層理強度達到1.5 倍時,裂紋先沿層理滑移,后穿透層理偏向加載中心軸線曲折擴展,發生拉-剪耦合破壞。層理傾角為30°,層理強度較低時,裂紋沿層理剪切滑移擴展;層理強度繼續增大至較高時,裂紋開始穿透層理,剪切滑移面向上遷移,裂紋曲折偏向加載點擴展,發生拉-剪耦合破壞。層理傾角為45°,隨著層理強度增大,剪切滑移面不斷向上遷移,呈階梯狀穿層向前擴展,呈現出由剪切破壞為主向張拉破壞為主的演變趨勢。層理傾角為60°時,隨著層理強度的增大,裂紋沿層理面滑移距離不斷減小,且張拉裂紋逐漸平行于加載軸線并向前擴展,逐漸由剪切破壞向張拉破壞演變。層理傾角為75°時,隨著層理強度逐漸增大,剪切滑移面逐漸向上遷移,且呈減小趨勢,試樣逐漸以張拉破壞為主。層理傾角增大到90°,層理強度相對較低時(0.5、0.8 和1.1),受層理影響,裂紋自裂尖發生偏折,逐漸穿層后,沿層理弱面擴展貫通,對裂紋向上擴展貫通呈抑制趨勢;層理強度繼續增大至1.5 時,裂紋擴展路徑受層理影響相對較弱,裂紋基本沿加載軸線穿透層理向上曲折擴展,呈現張拉破壞趨勢。

表4 各層理傾角試樣在不同層理強度下的數值模擬破壞結果Table 4 Numerical failures of each bedding dip angles' specimen under different bedding strength
3.4.2 層理間距對破壞模式的影響
表5 為不同層理傾角、不同層理間距試樣的數值模擬破壞結果,試樣層理間距d分別設置為3、5、8 和12 mm,其他細觀參數見表2。從表5 可以看出,層理傾角為0°和15°時,隨著層理間距增大,裂紋擴展基本無變化;層理傾角為零時,自裂尖沿加載軸線貫通至加載點,發生張拉破壞;層理傾角為15°時,自裂尖沿層理面滑移破壞。層理傾角為30°,層理間距較小(3 mm)時,裂紋逐漸向上穿透層理,滑移面呈階梯狀逐漸向上遷移,形成“拐折”且偏向加載軸線的擴展路徑;隨著層理間距繼續增大(5、8 和12 mm),初始滑移面擴展距離較層理間距為3 mm 時有所增大,裂紋沿層理擴展,“拐折”次數明顯減少,主要發生剪切滑移破壞,且層理間距由5 mm 向3 mm 減小過渡時,試樣有發生以張拉破壞為主的趨勢。層理傾角為45°,層理間距較小(3 和5 mm)時,裂紋沿層理“拐折”擴展次數較多;隨著層理間距繼續增大(8 和12 mm),裂紋“拐折”擴展次數減少且趨勢逐漸減弱,試樣以剪切破壞為主。層理傾角為60°和75°時,隨著層理間距的增大,裂紋沿層理“拐折”次數減少,“拐折”擴展路徑減弱,試樣發生張拉-剪切耦合破壞,且有向張拉破壞演變的趨勢。層理傾角為90°時,隨著層理間距增大,裂紋逐漸穿層,“拐折”擴展趨勢相對減弱,裂紋擴展路徑沿加載軸線逐漸趨于平緩貫通至加載點,試樣主要發生張拉破壞。

表5 各層理傾角試樣在不同層理間距下的數值模擬破壞結果Table 5 Numerical simulation failure results of each bedding dip angles' specimen under different bedding distance
3.4.3 切縫傾角對破壞模式的影響
表6 為各層理傾角試樣在不同切縫傾角下的破壞結果,數值模擬中切縫傾角β依次設置為15°、30°、45°和60°,相關細觀參數見表2。從表6 可以看出,層理傾角為零,切縫傾角較小(0°、30°)時,裂紋沿層理豎直方向擴展貫通;切縫傾角較大(45°、60°)時,裂紋逐漸穿層向加載點處擴展貫通,裂紋擴展形態趨于階梯狀,試樣呈張拉破壞狀態。層理傾角為15°時,隨著切縫傾角的增大,裂紋逐漸穿層,呈階梯狀向上擴展,試樣以剪切破壞為主。層理傾角為30°時,隨著切縫傾角在0°~45°范圍逐漸增大,裂紋逐漸穿透層理,剪切滑移面向上遷移,呈階梯狀偏向加載軸線擴展;切縫傾角增大到60°時,裂紋穿層擴展后,沿層滑移趨勢減弱,階梯狀擴展形態逐漸消去,試樣由剪切破壞為主向張拉破壞為主演變。層理傾角為45°時,隨著切縫傾角增大,裂紋呈階梯狀擴展趨勢減弱,切縫傾角為60°時尤為明顯,試樣由剪切破壞為主向張拉破壞為主演化。層理傾角為60°和75°時,隨著切縫傾角增大,除層理傾角為75°、切縫傾角為零時,裂紋穿層-沿層呈階梯狀“拐折”擴展趨勢明顯外,其余試樣裂紋主要穿層且伴有少量沿層滑移擴展,試樣主要呈張拉破壞。層理傾角為90°,除切縫傾角為零時裂紋穿層后沿層少量滑移外,隨著切縫傾角繼續增大,裂紋穿層后基本不沿層理滑移,試樣主要以張拉破壞為主。

表6 各層理傾角試樣在不同切縫傾角下的數值模擬破壞結果Table 6 Numerical failures of each bedding dip angles' specimen under different cutting seam dip angles
4 結 論
對層狀千枚巖開展了三點彎曲載荷作用下的試驗和數值模擬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層理傾角由0°~90°變化過程中,層狀千枚巖Ⅰ型斷裂韌度值與層理傾角呈二次函數關系。隨著層理傾角增大,層理傾角對斷裂韌度的控制作用增強,表現出良好的增韌作用,層理傾角越大,試樣越難以開裂破壞。
(2)隨著層理傾角在0°~90°變化過程中,層狀千枚巖的變形和強度特征呈明顯各向異性。垂直層理加載時的峰值破壞位移約為平行層理加載時的2 倍,且垂直層理加載時的峰值載荷約為平行層理加載時的2.7 倍。隨著層理傾角增大,峰值載荷和峰值破壞位移有逐漸增大的趨勢。
(3)受層理傾角與不同層理強度、層理間距及切縫傾角的耦合作用,層狀巖石的裂紋擴展形態及破裂模式有較大差異,呈各向異性特征。受層理傾角影響,試樣呈現拉伸-剪切-拉伸的斷裂演化趨勢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