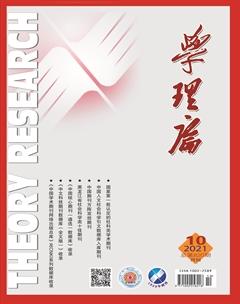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同層次發展目標邏輯關系
摘 要:發展目標是發展主體對于客觀發展事物在某一時期所能達到的狀態或程度所做的展望和要求。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表現出明顯的層次性特征。從邏輯關系來看,新時代不同層次發展目標是在新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邏輯和中國共產黨關于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相結合中確立的,也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邏輯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邏輯相統一中形成的,初級階段是制定新時代發展目標的現實依據,改革開放則是確定新時代發展目標的實踐基礎。
關鍵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邏輯關系
中圖分類號:D6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21)10-0013-03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將“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中的“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調整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意味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實現了新的階段性跨越,同時也表現出新的階段性特征。所謂發展目標,就是發展主體對于客觀發展事物在某一時期所能達到的狀態或程度所做的展望和要求。從理論與實踐、歷史與現實兩個維度深刻認識進入新時代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同層次的發展目標及其邏輯關系,對于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心和共產主義信仰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的層次性特征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共產黨立足新時代這一新的歷史方位,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進行了新的理論建構和頂層設計,在繼承和創新的統一中形成了小康、中國夢、“兩個一百年”、現代化、共產主義等闡釋新時代發展目標的概念和范疇。以發展目標的時間線索和目標指向為依據,可以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分為初級發展目標、宏偉發展目標和最高價值目標三個層次。
1.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初級發展目標。“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是當時生產力條件下中國農耕社會竭力追求的理想生活狀態。歷史上,無論是“貞觀之治”還是“康乾盛世”,都沒有讓絕大多數的中國人民真正過上小康生活,“斯民小康”也不過是有些統治者的美好愿望。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同志對社會主義發展目標進行了科學務實的調整,將“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目標明確為不窮不富的“小康”,由此“小康社會”這一極具中國傳統文化意蘊的概念進入到了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發展目標的話語體系當中。
實現“小康”準確地反映了國家的發展需要和人民的利益訴求,成為各社會階層共同的目標追求和價值共識,并基本按照“小康—總體小康—全面小康”這一邏輯進路和實踐路徑賦予了新的時代內涵。從2002年黨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經過十八年接續奮斗,以消除絕對貧困為標志的小康社會發展目標在2020年全面實現。在21世紀的頭二十年實現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的第一個歷史性發展目標,在中國共產黨的百年奮斗史、新中國七十多年發展史,在改革開放四十多年探索史,以及人類社會減貧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義。
2.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宏偉發展目標。隨著全面小康的建成,現代化強國建設成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今后三十年的發展目標。實現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和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在內涵上是一致的,在時間上是同步的,用兩個十五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實現。
在基本實現現代化的基礎上實現偉大復興具有民族性、人民性和世界性的意義。首先是偉大復興的民族性,民族復興這一發展目標凝聚起了億萬中國人的情感共識、目標共識和價值共識,意味著中國共產黨人追求的“強起來”目標的實現。其次是偉大復興的人民性,馬克思指出,“無產階級的運動是絕大多數人的,為絕大多數人謀利益的獨立的運動。”[1]411偉大復興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美好生活。中國共產黨將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嵌入到實現民族復興的發展目標之中,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社會主要矛盾。最后是偉大復興的世界性,中國夢具有世界意義,實現民族復興這一發展目標對推動全球發展、建設世界和平、維護國際秩序意義深遠。
3.實現共產主義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最高價值目標。實現共產主義是中國共產黨作為無產階級政黨在成立之初就已經確立的歷史使命。1922年黨的二大就提出黨的最高綱領是“建立勞農專政的政治,鏟除私有財產制度,漸次達到一個共產主義的社會。”[2]毛澤東同志指出,社會形態發展規律是“資本主義要轉變到社會主義,社會主義又要轉變到共產主義。”[3]這兩個“轉變”實質上是對馬克思主義關于人類社會發展“兩個必然”規律的繼承和中國化闡釋,劉少奇同志在《論共產黨員的修養》中提出,共產主義社會“當然是人類歷史上最好的、最美麗的、最進步的社會。”[4]這些充分說明中國共產黨人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的大本大源,始終堅守著共產主義這一崇高社會理想和最高價值目標追求。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共產黨在堅持共產主義最高理想的過程中不斷深化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關系的認識,逐漸認識到“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5]。就共產主義社會而言,我們現在處在相當低的社會發展階段。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信念,是共產黨人的政治靈魂”[6]。如何深刻理解和正確處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共同理想和共產主義遠大理想之間的關系,是新時代中國共產黨人要面對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只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最高理想才能從量的積累到質的飛躍,從理想變為現實。共同理想立足當下,最高理想放眼長遠。共同理想是社會主義尚處于初級階段條件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要實現的理想目標,而最高理想必然是超越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才有可能逐步達到的。
二、新時代不同層次發展目標是在新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邏輯和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理論邏輯相結合中確立的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不是主觀臆斷做出的,而是在新中國七十多年歷史演進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理論的守正創新中逐步明確的,具有深刻的歷史根源和理論依據。新中國七十多年的歷史可以分為改革開放前三十年和改革開放后四十多年兩個時期。這兩個歷史時期在具體政策、發展思路等方面都表現出明顯的差異性,但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建設是貫穿并連接兩個歷史時期的主線。新時代不同層次發展目標同樣遵循著這一條歷史主線,并有各個時期中國共產黨關于社會主義建設的創新理論成果內嵌其中,與之交互演進。
1.新中國的成立是一切發展目標確立的歷史前提。新中國成立前,許多先進中國人對未來中國的發展都有過設想。康有為從儒家經典中尋求“托古改制”的理論支撐,提出人類社會要從“據亂世”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主張通過漸進革新變法解決民族危機和現代化轉型;洪仁玕意圖通過向資本主義國家看齊的施政綱領,把江河日下的太平天國再造成“新天、新地、新人、新世界”的“天國”;孫中山謀求通過發展鐵路、港口等實業來尋求國家頹勢的根本改變。近代以來各階級所提出的發展思想不可謂不先進,發展目標不可謂不宏大,但終究未曾實現。究其根源,在于政局動蕩、戰亂頻繁的舊中國不具備中長期發展目標所需要的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在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舊中國無法擺脫守舊勢力和西方侵略勢力的嚴重干擾;在于小農自然經濟為主導的經濟基礎無法實現政治上層建筑和觀念上層建筑的根本革新。
新中國的成立從根本上結束了近代以來中國主權不獨立、國家不統一、社會不穩定的歷史。從1953年開始,中國共產黨借鑒蘇聯經驗開始實施第一個五年計劃,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有計劃地制定經濟發展目標的起點,為改革開放后社會發展目標的確定提供了根本物質保障和經驗借鑒。
2.“四個現代化”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發展目標的初步探索。如何把一個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的舊中國通過自下而上的社會革命建設成為蘇聯式的社會主義強國,是關系到抗戰勝利后中國該何去何從的命運問題。1945年毛澤東同志在黨的七大提出,未來之中國將是“一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國家”[7]。在新政協籌備會上,毛澤東同志提出我們要“建設起一個嶄新的強盛的名副其實的人民共和國。”[8]這是共產黨人對未來中國發展愿景的宏觀展望,為之后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制定“四個現代化”發展目標提供了基本的方向指引。
1955年,毛澤東同志在同日本國會議員交談中提出中國要“由落后的農業國變為工業國”[9],以此來實現中國由幾千年的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逐步轉型。1964年,周恩來同志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提出了以“四個現代化”為主要內容的發展目標,即“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10],1975年,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同志再次重申了“四個現代化”的發展目標,并進一步細化了按照“兩步走”的設想到20世紀末實現“四個現代化”。
新時代發展目標和改革開放前的發展目標在方法論上具有高度的耦合性,在發展目標定位上,改革開放前“四個現代化”的最終目標指向是社會主義強國,新時代要實現的發展目標題中應有之義就是到21世紀中葉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并以此作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重要標志。這表明新時代發展目標和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發展目標兩者之間不是割裂的,而是以實現現代化為連接點緊密聯系的。在實現發展目標的步驟上,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戰略步驟是“兩步設想”,第一步是建立獨立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是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強國。新時代實現第二個百年發展目標的戰略步驟同樣是“分兩步走”,用兩個十五年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無論是實現“四個現代化”,還是實現第二個百年發展目標,都能讓社會主義的中國自信、自強、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給人類貢獻出一條有別于資本主義的全新發展之路。
3.“三步走”戰略為新時代發展目標的確立提供了基本目標框架。“三步走”戰略是由兩個短期目標和一個長遠目標構成的,兩個短期目標以兩個十年為時間期限,以1990年和2000年為時間節點,對改革開放后未來中國七十年發展目標做了總體規劃。1987年黨的十三大正式將鄧小平同志提出的“三步走”戰略上升為黨的奮斗目標和國家發展戰略。1997年黨的十五大站在新舊世紀的交匯點上,將“三步走”戰略的第三步長遠目標進一步細化,形成了從21世紀初到2010年,從2010年到2020年,再從2020年到21世紀中葉“新三步走”的發展目標。
“三步走”戰略之所以能為新時代發展目標的確立提供基本目標框架,原因有三:一是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的政治領導優勢。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能夠保證現代化發展目標不會因為領導集體的更替而停滯,也不會因為領導人意志的改變而改變,更不會像西方政黨那樣為了短期本黨本集團的利益而有損國家長遠利益。二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制度優勢。進入新時代,中國共產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達到了全新的高度,有了成熟穩定的制度,剛性的發展目標就可以具有靈活性和張力。三是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穩定的發展優勢。中國的現代化發展目標是歷史接力棒的傳承,保證了新時代的發展目標可以按照“三步走”確定的目標框架繼續前進。
三、新時代不同層次發展目標是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現實邏輯和改革開放的實踐邏輯相統一中形成的
初級階段的國情和改革開放的實踐既是深刻認識和把握新中國七十多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經濟社會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視角,也是新時代不同層次發展目標得以形成的現實基礎。立足新時代我國仍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通過對內全面深化改革和對外擴大開放,以改革促開放和以開放促改革雙循環共同推進,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目標才具有現實可能性。
1.初級階段是確定新時代發展目標的現實依據。在初級階段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必須在堅定遠大理想的基礎上立足中國國情,構建能夠凝聚起億萬人民共同理想追求的發展目標。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11]10。社會主義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實際決定了在目前的國際力量對比中,我國是日益走近而不是已經站在舞臺中央。我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在較長的一段時期是不會改變的,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黨自改革開放以來始終保持著清醒的認識。1987年8月,鄧小平同志在會見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約蒂時就指出,“社會主義本身是共產主義的初級階段,而我們中國又處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12]。
初級階段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理論立足點,是確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所要遵循的最大實際。在新時代繼續堅持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政治判斷不是抽象的、籠統的,而是有具體的時代內涵和現實表征的。初級階段這一最大國情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具有高度的理論一致性和現實統一性。兩者的理論結合點和理論旨趣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社會主義是社會形態的階段論,是從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統一體的角度闡明我國所處的社會形態以及階段性特征。
2.改革開放是確定新時代發展目標的實踐基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目標是在改革開放的實踐中逐步探索和形成的。從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實踐經驗可以看出,社會發展目標與改革開放的實踐是相輔相成、同頻共振的。20世紀70年代末到80年代以土地制度為核心的農村改革和以國有企業為核心的城市改革雙輪驅動,逐步理順了束縛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注入了強大動力,使得在20世紀80年代末實現溫飽的社會發展目標具有現實可能性。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隨著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的不斷推進,社會發展目標也由溫飽向小康社會邁進。進入新世紀,以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標志,中國對內改革和對外開放進入了新的歷史階段,經濟社會的快速發展讓國家面貌、人民精神狀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改變,中國共產黨把握歷史主動提出21世紀頭20年建設“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13]的發展目標。黨的十八大以來在全面深化改革和更高水平擴大開放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與時俱進確定了分階段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基本實現現代化和建成現代化強國的發展目標。
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實踐總體上仍處于大有可為期,但也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從國際環境來看,西方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仍掌握著全球科技變革的主導權和全球治理與變革的話語權。資本主義社會民主赤字、治理赤字、發展赤字、安全赤字越發嚴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肆虐深刻改變著世界政治經濟版圖和發展格局,后疫情時代充滿著各種不確定、不穩定因素。從國內環境看,發展階段、發展理念和發展格局的變化都要在深化改革中內化和體現,發展與安全、發展與穩定、發展與民生都要在擴大開放中統籌和協調。新時代改革開放的力度、廣度和實現程度對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中國的發展至關重要,是新時代各階段發展目標得以實現的實踐基礎。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上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95.
[3]毛澤東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75.
[4]劉少奇選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122.
[5]鄧小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1254.
[6]習近平關于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6:57.
[7]毛澤東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03,304.
[8]毛澤東年譜(1893~1949)(修訂本)(下卷)[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13:519.
[9]毛澤東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483.
[10]周恩來選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439.
[11]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3卷[M].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
[12]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67.
[13]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259.
(責任編輯:李 慧)
收稿日期:2021-02-05
作者簡介:白耀強,碩士,從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