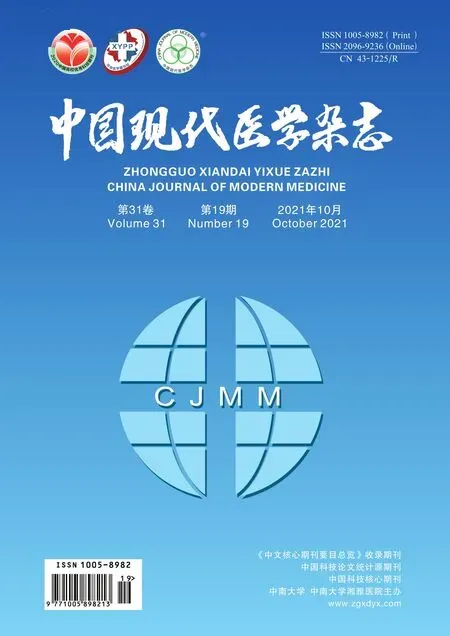基因性兒童癲癇的外科治療*
梁樹立,陳峰,劉婷紅
[國家兒童醫學中心(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兒童醫院)功能神經外科,北京100045]
癲癇病因主要包括結構性、基因性、代謝性、感染性、免疫性和不能確定等方面[1]。隨著全外顯子和全基因組測序等新的基因檢測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兒童癲癇被證實與基因相關[2-3]。目前已有部分單基因相關癲癇可以利用特異性藥物獲得精準治療,如應用大劑量維生素B6治療吡哆醇依賴性癲癇發作有效,而進行生酮飲食可較好控制葡萄糖轉運子1 缺乏。但是大部分基因性兒童癲癇缺乏精準治療方案,仍需抗癲癇藥物治療[3-4]。近年來癲癇外科對基因性兒童癲癇進行了研究和探索,取得長足的進步,但同時也存在許多問題[4]。本文就基因性兒童癲癇的手術適應證、基因異常與癲癇的關系評估及手術方式選擇、切除性手術方式、神經調控手術方式及其他手術方式進行總結和述評。
1 基因性兒童癲癇的手術適應證
兒童癲癇相關的基因異常包括單基因異常、多基因異常、染色體異常等,本文所述的基因異常目前主要是指單基因異常。診斷基因性兒童癲癇需要符合癲癇的診斷標準,同時檢測到異常基因,并確定基因異常與癲癇相關,即異常基因為致病性基因異常、符合遺傳學特征和患者臨床癥狀[3-4]。基因型兒童癲癇的手術適應證主要包括病變相關性癲癇和耐藥性癲癇[5]。
1.1 病變相關性癲癇
病變相關性癲癇主要包括結節性硬化癥(TSC)和腦皮質發育不良。哺乳動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通路基因異常可引起腦部結構性病變。其中性腺細胞來源的基因主要是mTOR、TSC1、TSC2、Gator1基因等,Gator1復合體包括DEPEC5、NPRL2、NPRL3基因,這些基因異常與局灶性皮質發育不良(FCD)和半側巨腦回畸形(HME)相關,占局灶性癲癇的10%,其中以DEPEC5 異常最為常見[7]。性腺細胞來源的TSC1/TSC2基因異常與TSC 相關,其中75%為TSC2基因異常,TSC1基因異常約占13%[8]。大部分腦皮質發育不良僅表現為體細胞嵌合體的基因異常,只能通過病變組織的基因檢測才能確定相關異常基因,常見的基因包括PI3KCA、Akt3、RHEB、mTOR、PTEN、TSC1、TSC2和STRADA等mTOR 通路相關的基因[2,7]。另外一些非mTOR 通路相關的基因異常(ACTB、ARX、DCX、DYNC1H1、KIF5C、LIS1、TUBA1A、TUBA8、TUBB3、TUBG1)也可以導致其他廣泛性腦皮層發育不良,如光滑腦、多微小腦回等。
1.2 耐藥性癲癇
耐藥性癲癇又稱藥物難治性癲癇,是指經過正確選擇且能耐受的兩種或以上(單藥或聯合)抗癲癇藥物正規治療,患者仍未能達到持續無發作[6]。所以,判斷耐藥性基因性兒童癲癇要符合以下幾點:①“正確選擇”,是選擇不加重癲癇且證實對其發作類型有效的抗癲癇藥物,同時劑量達到合理范圍;②“能耐受”,是指無過敏反應、急性白細胞減少或者肝壞死等導致早期停藥的副作用,而服藥較長時間后出現的慢性副作用,無論是否停藥都應當判定為“能耐受”;③“兩種藥物”,是指先后單藥或者聯合應用兩種抗癲癇藥物;④耐藥性癲癇的診斷中沒有限定病程和癲癇發作形式及頻率。
常見的基因性兒童癲癇基因異常的類型及手術方式選擇見圖1。兒童癲癇相關的基因異常本身也可以導致癲癇的耐藥性,如電壓門控性鈉離子通道(SCN1A、SCN2A、SCN8A等)、電壓門控性鉀離子通道(KCNA1、KCNA2、KCNB1等)、ATP 結合盒轉運蛋白(ABCB1、ABCC2等)、線粒體轉運家族成員(SLC2A1、SLC6A1、SLC35A2等)、藥物代謝酶(CYP2C1、CYP2C9、CYP2C19等)、CDKL5、GABA受體等[2]。此外,上述基因異常相關的結構性病變也提示耐藥性癲癇的可能性。

圖1 常見的基因性兒童癲癇基因異常的類型及手術方式選擇
2 基因異常與癲癇的關系評估及手術選擇
術前檢查僅能確定性腺細胞來源的基因異常,而難以發現mTOR 相關的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術前未發現致病性基因異常和明確的致病性基因異常與癲癇的關系評估如下。
2.1 術前未發現致病性基因異常
2.1.1 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MRI 陽性的腦皮質發育不良(如FCD-II 型、HME 等)或者可疑腦皮質發育不良(如FCD-I 型)均可存在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所以術前抽取血液進行基因檢測,結果多提示無明確致病性基因異常[9]。這些患者術前評估時多數不需要考慮基因因素[4]。
2.1.2 現有技術無法診斷的基因異常由于基因檢測技術、檢測方式的限制和一些致病性基因異常未被報道等原因,一些基因性兒童癲癇未被證實有基因異常,這時要全面結合臨床特征和相關腦電圖與影像學等特點進行分析,不能單獨依據未發現基因異常排除手術治療或者限定癲癇治療的方式[3,8]。例如,約12%的TSC 患者不能發現明確的基因異常,但臨床可以確診為TSC,理論上存在TSC 復合體的基因異常,這些患者的癲癇診療與基因檢測陽性的TSC 相關癲癇患者相同[10]。
2.2 明確的致病性基因異常
2.2.1 性腺細胞mTOR 相關基因異常由于二次打擊出現了腦內局灶病變,主要包括TSC 復合體和Gator1復合體相關基因,這些患者的癲癇常與病變相關,可行切除性手術治療。另外,Gator1復合體相關的基因存在外顯率不全可能,一些患者的父輩攜帶相關異常基因,但并不致病,此時并不代表患者攜帶的相同異常基因為非致病性基因(見圖1)。如果與臨床病變及相關癥狀吻合,特別是相關基因異常已經被證實或被預測為致病性異常時,仍應考慮為致病基因[4,7]。
2.2.2 非mTOR 基因的致病性基因異常往往表現為無影像學異常或雙側彌漫性結構異常(光滑腦、雙側對稱性腦裂畸形、雙皮層異常等)的基因性兒童癲癇[11],此類患者不應當推薦切除性手術治療,如果藥物治療效果差,可以考慮神經調控治療[4]。
2.2.3 腦皮質發育不良等局限性病灶可合并病灶無關的單基因性兒童癲癇[12]這種情況下,是否行手術治療要明確癲癇主要與病灶相關,還是與基因異常相關,如果癲癇發作主要與病灶相關,也可以考慮切除性手術治療,但如果主要與基因異常相關,必要時可以考慮進行神經調控手術治療。
3 基因性兒童癲癇的切除性手術
切除性手術是兒童癲癇治療的最常用方法,也是病灶相關性基因性兒童癲癇的重要治療手段[4,13]。
3.1 術前評估
基因性兒童癲癇切除性手術的術前評估與其他病因相關癲癇的切除性手術的評估相類似,需要確定致癇灶的位置與范圍及與功能區的關系。主要包括無創評估和有創評估兩個階段。無創評估主要是癥狀學分析、神經科查體、MRI 檢查、頭皮腦電圖檢查、PET/CT 檢查和神經心理評估6 個方面[10,14]。癥狀學分析重點關注先兆或首發癥狀、癥狀演變和發作后遺留癥狀等。兒童癲癇患者神經科查體多無明顯局灶特征,但如果出現局灶性特征對致癇灶的定位有重要指導價值。MRI 推薦以3.0 T 設備進行3D-T1、3D-T2、3D-T2Flair 掃描,并結合2D-T1和2D-T2Flair 掃描,一般不需要增強掃描。頭皮腦電圖應當包括至少一個完整的清醒-睡眠周期和3 次慣常性癲癇發作期腦電圖,同時包括視頻記錄、心電和肌電檢查。發作間期PET/CT 應當進行常規檢查,掃描前要求素食24 h,禁食12 h,血糖在正常值范圍,與癲癇發作間隔12~24 h。PET/MRI 融合已成為致癇區定位的常規技術,同時,建立了兒童頭顱MRI 模板的中心可利用基于體素的形態學分析指導定位病灶。神經心理評估對于致癇灶的定位有一定的提示作用,對手術預后的預測和判斷手術意義有重要價值,常規至少應包括發育評估、智商、記憶商、生活質量,合并精神異常的應該進行精神科評估。病變可能累及功能區時需行功能MRI 檢查(低齡或低智商患者難以完成任務態功能MRI 檢查)和MRI 彌散張量成像,明確病變與功能區及傳導束的位置關系。有創檢查主要應用于多病灶、病灶范圍廣泛,且腦電圖與癥狀學或病灶位置不一致的患者,目前常用的有創檢查是立體定位腦電圖(Stereoelectroencephalogram,SEEG)。有創檢查前需根據無創檢查結果對致癇區提出2、3 種假設,通常植入5~15 根SEEG 電極來覆蓋這些假設相關的腦區,如果電極數量過少提示SEEG 的必要性不足。如果電極數量過大,說明無創檢查定位信息尚不足,需要完善腦磁圖等檢查或再次進行無創檢查[15]。
3.2 手術方法
切除性手術包括致癇(病)灶切除術、腦葉切除術、多腦葉切除術和大腦半球切除術,大腦半球離斷術、多腦葉離斷術和部分腦葉離斷術的手術目的、病例選擇、術前評估等與切除性手術相似,往往也納入切除性手術。目前對于大腦半球性病變或者多腦葉病變的患者,離斷術相對切除性手術創傷小、出血小、并發癥少、恢復快,所以優先選擇離斷術。腦葉性或亞腦葉的病變切除性手術應用更普遍。致癇(病)灶的全切除(或離斷)是癲癇術后無發作的關鍵影響因素,切除或離斷的范圍應當包括T2Flair 顯示的病變區域,同時參考PET 顯示的明顯低代謝區域及病變與功能區的關系確定病變范圍,當病變不與初級運動區或語言區重疊時,通常應當切除或離斷病變所累及的相應腦回[13]。切除以腦皮質為主,對于白質內異常信號不一定要求全切除,以避免發生不必要的傳導束損害等并發癥。建議應用影像導航、圖像導航或術中神經電生理監測等措施,保障病變的全切除(或離斷)和功能區的保護[14]。
3.3 手術效果
基因性兒童癲癇的手術效果與基因的遺傳方式有一定的關系。源于性腺細胞的基因異常存在全身性改變,同時由于二次打擊而形成了腦內局灶病變,這些患者的癲癇往往是基因異常與結構性病變聯合作用的結果,理論是切除性手術效果可以會低于其他局灶性癲癇。不過,多中心研究顯示TSC 相關癲癇切除性手術后1年的無發作率為71%,4年為60%,10年為50%,其中有顯著結節和致癇結節全切除是術后無發作的獨立影響因素[13]。目前關于Gator1基因異常相關兒童癲癇和其他皮質發育不良相關兒童癲癇的手術治療效果尚無大宗病例對照研究,其預后是否存在差異尚不明確。而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相關的FCD-1 型、FCD-II 型或HME 等病變是否與無體細胞嵌合體相關的病變術后癲癇控制存在差異也尚不明確。隨著基因檢測技術的進步,越來越多的腦皮質發育不良性的組織標本中可能會發現異常的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所以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對兒童病灶性癲癇的手術效果的影響應該不明顯[4]。
4 基因性兒童癲癇的神經調控手術治療
DCX、LIS1、TMTC3等基因異常可以引起光滑腦、雙皮質異常等無法手術切除的病變。另外,離子通道、神經遞質、激酶、蛋白轉錄和修飾等相關基因異常可以引起癲癇發作,但并不引起結構性病變[2,4,11]。這些患者都無法準確定位致癇(病)灶,符合耐藥性癲癇診斷的患者,特別是出現癲癇性腦病表現時,可考慮神經調控手術治療。
4.1 術前評估
神經調控手術的術前評估與切除性手術評估的方法存在一定差異。與切除性手術術前評估需要確定致癇區或致癇病灶及其與功能區的關系不同,神經調控手術術前評估的目標是明確有無神經調控手術的禁忌證、排除局灶性病理灶和局灶性癲癇發作。術前評估一般僅進行無創檢查,而且PET 檢查也非必須檢查項目。其他的檢查與分析方法同切除性手術的術前評估。同時,神經調控手術要更重視神經心理評估,應完成全面的神經心理評估(發育評估、智商、記憶商、生活質量、情緒等評估)。
4.2 手術方法
目前常用的神經調控手術主要包括迷走神經刺激術、腦深部電刺激術、反應式神經刺激術。腦深部電刺激術需將電極植入腦內,而青春期前兒童頭顱的增大會引起靶點移位,費用較高等問題限制了其在兒童癲癇的應用。反應式神經刺激也存在未獲得臨床批準、青春期前兒童有靶點移位風險和需定位致癇區等缺點。迷走神經刺激術是目前基因性兒童癲癇的最主要神經調控手術方法,主要適應于不可治療的基因異常或針對基因異常治療(包括針對病變的切除性手術)失敗后的耐藥性基因性兒童癲癇患者[16]。
4.3 手術預后
目前尚無專門針對基因性兒童癲癇的迷走神經刺激術治療效果結果分析。包括101 項、平均2.5年隨訪的Meta 分析結果[17]顯示,迷走神經刺激術治療兒童癲癇的無發作率為11.6%,有效率為56.4%,而未發現病因與療效有相關性。而另外一項包括了3 321 例患者的Meta 分析結果[18]顯示,迷走神經刺激術有效率為50%,兒童癲癇、全面性癲癇、創傷性癲癇和TSC 相關癲癇的療效優于其他病因。有研究報道[14]52 例TSC 相關癲癇迷走神經刺激術后無發作率為7.7%,有效率為75%;68 例Dravet綜合征迷走神經刺激術后有效率為52.9%[19];此外,這兩項研究中均有部分患者出現明顯的功能改善[14,19]。研究結果顯示,迷走神經刺激術治療基因性兒童癲癇有良好預后。
5 其他手術方式
基于SEEG 電極的熱凝毀損、MRI 引導下的激光熱凝毀損、胼胝體切開等也用于治療基因性兒童癲癇。其中SEEG 熱凝毀損主要針對體積較小(毫米級)的腦深部灰質異位等病變,而激光熱凝毀損主要適用于直徑不超過2 cm 的FCD、TSC、灰質異常位等病變。初步觀察臨床效果良好,但長期療效及其與切除性手術的差異仍需要進一步研究[20]。胼胝體切開術在基因性Lennox-Gastuat 綜合征等應用較多,而在其他基因性兒童癲癇治療中更多被迷走神經刺激術替代。
綜上所述,隨著人類對基因認識的深入和基因檢測技術的進步,基因性兒童癲癇在兒童癲癇中的比例會進一步提升。同時,基因異常不會成為癲癇外科治療的禁忌證,只是癲癇術前評估中一個重要的考慮因素。此外,分子顯像技術的提高可以提高體細胞嵌合體基因異常患者的術前診斷率,更好地指導相關癲癇外科手術的抉擇與實施。切除性手術和迷走神經刺激術是當前基因性兒童癲癇最常用的手術方案。正確評估基因異常與癲癇的關系,合理選擇治療方法,慎重選擇難治性基因性兒童癲癇手術病例,通過癲癇外科手術治療可以取得良好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