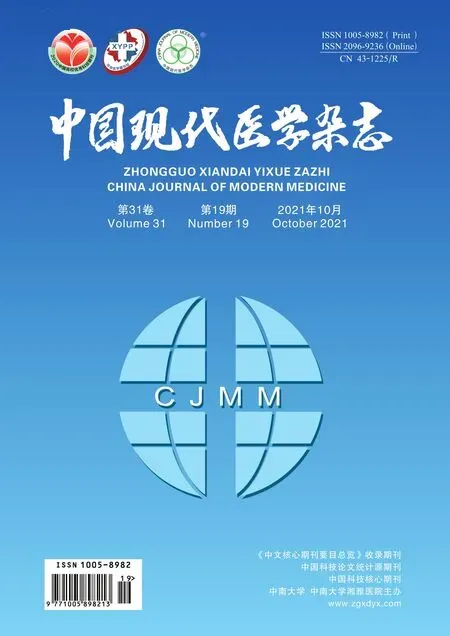血清IL-6聯合淋巴細胞/單核細胞比值對嚴重燒傷患兒膿毒血癥診斷及預后評估的價值*
李鵬程,謝江帆,靳三丁
(1.鄭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 燒傷與整形外科,河南 鄭州450018;2.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 燒傷科,河南 鄭州450004)
燒傷是導致兒童意外傷害的主要致傷因素之一,全球范圍內5 歲及以下兒童燒傷最為常見,尤其是1~3 歲,所占比例高達70%[1]。研究表明,火焰傷、熱液燒傷和接觸性燒傷是引起嚴重燒傷的三大原因,其中熱液燒傷是引起兒童嚴重燒傷的最常見原因,占所有住院燒傷患兒60%~75%,其次是火焰燒傷和接觸性燒傷[2-4]。燒傷不僅損傷局部皮膚屏障,而且可以產生大量細胞因子,引起全身炎癥反應、貧血、白細胞減少、血小板減少及凝血障礙等。皮膚屏障及機體免疫系統的損傷使機體易發生感染和膿毒血癥[5],是目前嚴重燒傷患兒的主要并發癥之一,進一步發展可導致多器官功能障礙綜合征,甚至死亡,是燒傷后引起死亡的首要原因,病死率高達50%~60%。因此尋找有效、可靠的生物標志物,對嚴重燒傷后膿毒血癥的早期識別、診療及提高臨床救治率至關重要[6]。淋巴細胞/單核細胞比值(lymphocyte/ monocyte ratio,LMR)是血細胞中兩種獨立的炎癥標志物的組合,目前LMR 被認為是一種新的全身炎癥標志物,與多數感染性疾病及惡性腫瘤的預后密切相關[7]。此外,燒傷后引起的機體炎癥反應也會激活免疫細胞分泌細胞因子,如白細胞介素-6(Interleukin-6,IL-6)等[8]。研究證明,IL-6 的高表達與感染性疾病的嚴重程度和細胞因子風暴的產生有關,可作為預測疾病轉歸的重要指標[9]。因此,本研究旨在通過回顧性分析嚴重燒傷患兒血液中LMR 及血清IL-6 水平,探討其對嚴重燒傷患兒膿毒血癥的預測及預后意義,以期為臨床救治提供參考。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回顧性分析2015年12月—2020年6月鄭州大學附屬兒童醫院和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收治的78 例嚴重燒傷患兒的臨床資料。膿毒血癥患兒共33 例。其中,男性22 例,女性11 例;年齡1~16 歲,平均(6.0±4.1)歲;非膿毒血癥患兒共45 例。其中,男性23 例,女性22 例;年齡1~13 歲,平均(5.7±4.2)歲。
1.2 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年齡0~16 歲首診燒傷患兒;②入院診斷符合重度及以上燒傷標準,即燒傷總面積TBSA>15%或Ⅲ度燒傷面積>5%;③患兒臨床記錄及病例資料完整;④既往無精神性疾病及其他重大疾病;⑤膿毒血癥的診斷符合中國醫師協會燒傷醫師分會《燒傷感染診治指南》編輯委員會的《燒傷感染的診斷標準與治療指南(2012 版)》[10];⑥入組對象監護人對本研究均知情同意,簽署知情同意書。排除標準:①燒傷合并外傷或嚴重臟器功能障礙甚至衰竭者;②合并其他先天性疾病、免疫系統疾病或有嚴重基礎疾病者;③燒傷患兒中途轉院或放棄治療者。
1.3 分組及研究方法
根據膿毒血癥診斷標準,將患兒分為膿毒血癥組和非膿毒血癥組;根據患兒病情結局分為生存組和死亡組;根據臨界值的高低又將患兒分為低IL-6組和高IL-6 組,以及低LMR 組和高LMR 組。收集患兒的年齡、性別、TBSA、住院時間、是否伴有吸入性損傷、是否行機械通氣及病情轉歸等臨床資料;檢測患兒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的血常規、血清IL-6 等。采用全自動血細胞分析儀檢測血常規,采用酶聯免疫吸附試驗檢測血清IL-6 水平;所有患者從燒傷開始進行60 d 觀察。
1.4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0.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用t檢驗或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計數資料以構成比或率(%)表示,比較用χ2檢驗;相關性分析用Pearson 法;繪制受試者工作特征(ROC)曲線;Kaplan-Meier 法繪制生存曲線。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兒基本資料比較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兒在是否伴有吸入性損傷、是否行機械通氣、是否死亡、TBSA方面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1。

表1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基本資料比較
2.2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者LMR、IL-6水平比較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的LMR 比較,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結果:①不同時間點LMR 有差異(F=102.034,P=0.000);②非膿毒血癥組和膿毒血癥組的LMR 有差異(F=63.367,P=0.000),膿毒血癥組傷后7 d、14 d、21 d 的LMR 較非膿毒血癥組降低;③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的LMR 變化趨勢有差異(F=16.781,P=0.000)(見表2 和圖1)。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的IL-6 水平比較,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結果:①不同時間點血清IL-6水平有差異(F=439.209,P =0.002);②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的IL-6 水平有差異(F=34.337,P =0.011),膿毒血癥組傷后7 d、14 d 的IL-6 水平較非膿毒血癥組升高;③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的IL-6 變化趨勢有差異(F=9.228,P =0.003)(見表3和圖2)。Pearson 相關分析結果顯示,傷后7 d、14 d、21 d LMR 與TBSA 呈負相關(r=-0.441、-0.580 和-0.441,均P=0.000);傷后7 d、14 d、21 d IL-6 水平與TBSA 呈正相關(r=0.417、0.549 和0.293,均P=0.000)。

圖1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LMR變化趨勢圖

圖2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IL-6變化趨勢圖
表2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者不同時間點LMR水平比較 (±s)

表2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者不同時間點LMR水平比較 (±s)
組別非膿毒血癥組膿毒血癥組n 45 33入院時5.55±0.83 5.57±0.82傷后7 d 5.45±0.83 4.72±0.72傷后14 d 5.81±0.88 4.35±0.84傷后21 d 5.35±0.83 4.62±0.72
表3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者不同時間點血清IL-6水平比較 (pg/ml,±s)

表3 非膿毒血癥組與膿毒血癥組患者不同時間點血清IL-6水平比較 (pg/ml,±s)
組別非膿毒血癥組膿毒血癥組n 45 33入院時24.62±6.57 23.49±5.01傷后7 d 71.55±20.30 93.31±27.52傷后14 d 137.33±32.56 168.13±44.03傷后21 d 87.87±21.18 91.21±29.20
2.3 LMR聯合IL-6對嚴重燒傷患兒膿毒血癥發生的預測價值
ROC 曲線分析結果顯示,傷后7 d 單獨檢測IL-6 的ROC 曲線下面積(AUC)為0.717(95% CI:0.597,0.837),敏感性為57.6%(95% CI:0.333,0.788),特異性為62.2%(95% CI:0.511,0.867),臨界值 為89.44 pg/ml(95% CI:85.33,93.50);IL-6 聯 合LMR 檢測的AUC 為0.767(95% CI:0.660,0.874),敏感 性 為93.9%(95% CI:0.818,0.970),特異性為59.3%(95% CI:0.510,0.800),臨界值為0.24(95%CI:0.131,0.353),IL-6 聯合LMR 比單獨IL-6 預測更有效(P<0.05)。見圖3。

圖3 傷后7 d血清IL-6和LMR診斷嚴重燒傷后膿毒血癥的ROC曲線
傷后14 d 單獨IL-6 檢測的AUC 為0.713(95% CI:0.587,0.840),敏感性為63.6%(95% CI:0.364,0.818),特異性為70.2%(95% CI:0.522,0.911), 臨界值為79.96 pg/ml(95% CI:68.551,88.373);IL-6 聯合LMR檢測的AUC 為0.875(95%CI:0.798,0.952),敏感性為93.9%(95% CI:0.697,0.970),特異性為69%(95% CI:0.578,0.911),臨界值為0.34(95% CI:0.221,0.563),IL-6 聯合LMR 比單獨IL-6 預測更有效(P<0.05)。見圖4。

圖4 傷后14 d血清IL-6和LMR診斷嚴重燒傷后膿毒血癥的ROC曲線
2.4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基本資料比較
生存組與死亡組在是否行機械通氣、有無膿毒血癥、TBSA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4。

表4 生存組與死亡組基本資料的比較
2.5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LMR、IL-6水平比較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的LMR 比較,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結果:①不同時間點的LMR 有差異(F=64.520,P=0.005);②生存組與死亡組的LMR 有差異(F=9.797,P=0.000),死亡組在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LMR 較生存組降低;③生存組與死亡組的LMR 變化趨勢有差異(F=31.068,P=0.013)。見表5 和圖5。

圖5 生存組與死亡組LMR變化趨勢圖
表5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不同時間點LMR比較 (±s)

表5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不同時間點LMR比較 (±s)
組別生存組死亡組n 65 13入院時5.65±0.83 5.07±0.62傷后7 d 5.35±0.74 4.10±0.63傷后14 d 5.48±0.94 3.72±0.68傷后21 d 5.25±0.74 4.00±0.63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IL-6 水平比較,采用重復測量設計的方差分析,結果:①不同時間點的IL-6 水平有差異(F=407.063,P=0.000);②生存組與死亡組的IL-6 水平有差異(F=32.975,P=0.001),死亡組在入院時、傷后7 d、傷后14 d、傷后21 d IL-6水平較生存組升高;③生存組與死亡組的IL-6 水平變化趨勢有差異(F=35.960,P=0.000)。見表6和圖6。
表6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不同時間點血清IL-6水平比較 (pg/ml,±s)

表6 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組與死亡組不同時間點血清IL-6水平比較 (pg/ml,±s)
組別生存組死亡組n 65 13入院時23.36±5.73 28.05±5.65傷后7 d 74.65±21.67 111.28±23.81傷后14 d 140.06±34.98 201.88±24.19傷后21 d 85.63±24.61 107.56±16.51

圖6 生存組與死亡組IL-6變化趨勢圖
2.6 LMR及IL-6對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率的影響
通過ROC 曲線確定傷后7 d、傷后14 d LMR 的最佳臨界值分別為4.41 和4.32;IL-6 最佳臨界值分別為89.4 pg/ml 和165.6 pg/ml。Kaplan-Meier 生存分析曲線提示:傷后7 d 低LMR 組和高LMR 組嚴重燒傷患兒住院期間生存率分別為54.0%和94.8%,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4.320,P=0.000);傷后14 d 低LMR 組和高LMR 組生存率分別為25.0%和98.4%,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692,P=0.000)。傷后7 d 低IL-6 組和高IL-6 組嚴重燒傷患兒住院期間的生存率分別為98.0% 和55.6%,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312,P=0.001);傷后14 d 低IL-6 組和高IL-6 組嚴重燒傷患兒住院期間的生存率分別為100.0%和45.8%,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485,P=0.004)。見圖7。

圖7 高低LMR、IL-6組嚴重燒傷患兒的Kaplan-Meier生存曲線
3 討論
燒傷后皮膚屏障受損,病原微生物及有害物質通過受損的創面侵入機體,導致感染,嚴重者會誘發膿毒血癥。膿毒血癥是燒傷患兒的嚴重并發癥之一,也是主要死亡原因之一[6]。燒傷后由于機體的過度炎癥反應導致免疫功能下降,使診斷膿毒血癥的傳統生物學標志物準確性降低[11]。近年來研究表明,降鈣素原是診斷細菌感染及判斷嚴重程度的一個有效指標,但相對單一,且特異性差[12]。因此探索簡單、實用、特異性及敏感性較高的生物學指標用于預測燒傷后膿毒血癥的發生,判斷病情嚴重程度及預后,對成功救治患者至關重要。本研究從免疫炎癥角度出發,探討LMR 及IL-6 與燒傷后膿毒血癥的關系,既可以排除燒傷后機體應激反應的干擾,又可以提高燒傷后膿毒血癥發生及預后預測的準確性。
LMR 是淋巴細胞絕對數與單核細胞絕對數的比值,淋巴細胞體現免疫系統的調控過程,而單核細胞體現機體的非特異性炎癥反應,通過抗原呈遞作用,連接固有免疫與適應性免疫。作為一種新型炎癥標志物,LMR 與許多疾病的發生及預后密切相關[13-14]。低LMR 與結核病及惡性腫瘤的預后有關。LMR 可以預測子宮內膜癌患者的存活率和侵襲性[15]。本研究結果也表明,膿毒血癥組淋巴細胞數量較非膿毒血癥組減少,單核細胞增多,LMR 降低;此外,死亡組的LMR 比生存組低。提示LMR 的降低與膿毒血癥的發生及預后有關。
本研究將嚴重燒傷引起膿毒血癥后淋巴細胞數量減少的原因歸納為以下幾點:①機體的體液免疫和細胞免疫反應均發生顯著改變,出現免疫抑制狀態[16]。燒傷早期CD4、CD8 細胞表面抗原(HLA-DR、IL-IR 及轉鐵素受體)活化及淋巴細胞增殖能力明顯降低,而輔助性T 細胞持續激活,導致T 細胞對正常生理刺激的反應性持續喪失及大量凋亡,機體對病原微生物的易感性增加[17]。②感染引起機體產生大量的前列腺素E2,進而抑制p59fyn激酶活性,使激活蛋白1 和核因子活性降低,從而抑制T 淋巴細胞增殖[18]。③嚴重燒傷引起膿毒血癥激活Caspase-3 和Caspase-9,促進T 淋巴細胞凋亡,引起B 細胞和CD4 T 細胞大量凋亡等[19]。④淋巴細胞的激活需要淋巴細胞受體與MHC-II 分子結合后,輔助協同刺激分子。而在膿毒血癥中CTLA-4 升高,CD86、HLA-DR 表達下降,引起T 淋巴細胞與單核細胞之間的親和力減弱,影響T 淋巴細胞激活[20]。本研究中引起單核細胞數量增加的因素可歸納為:①膿毒血癥引起單核細胞CD64 和CD14 分子表達增加,與機體內毒素及抗體結合增強,促進單核細胞增殖[21]。②膿毒血癥后,骨髓造血干細胞在多集落刺激因子及粒-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作用下,分化為單核祖細胞,從骨髓轉移至血液,分化為單核細胞[22]。這與單核細胞在冠狀動脈鈣化(coronary artery calcification,CAC)中的研究[13]類似,動脈粥樣硬化及輕中度CAC 者血液中炎癥單核細胞數量增加,遷移至動脈損傷部位,體內分泌的黏附分子促進其黏附并浸潤于血管內皮中。
嚴重燒傷后出現以炎癥細胞因子如IL-6、IL-8及TNF-α 等過度產生為特點的全身炎癥反應綜合征,進而導致膿毒血癥[23]。IL-6 是由單核細胞、上皮細胞及淋巴細胞等在外界因素刺激下產生的一種促炎細胞因子,可促進T 細胞、B 細胞增殖,誘導免疫球蛋白及C 反應蛋白生成。動物實驗及臨床研究均表明,嚴重燒傷后機體的IL-6 水平顯著升高[24]。IL-6 水平與膿毒血癥患兒感染的嚴重程度密切相關,是膿毒血癥發生的重要預測因子[25]。本研究回顧性分析嚴重燒傷患兒血清IL-6 水平,比較膿毒血癥組與非膿毒血癥組、生存組與死亡組血清IL-6 水平的差異。結果顯示,血清IL-6 水平出現先升高后下降趨勢,膿毒血癥組IL-6 水平在傷后7 d、14 d 高于非膿毒血癥組;死亡組IL-6 水平高于生存組;且IL-6 與TBSA 呈正相關,提示IL-6 在預測嚴重燒傷后膿毒血癥的發生及預后中具有重要意義。
由于LMR 降低及IL-6 水平升高與嚴重燒傷后膿毒血癥發生有關,進一步探討LMR 聯合IL-6 對傷后膿毒血癥的診斷價值,結果顯示,傷后7 d、14 d LMR 聯合IL-6 的敏感性和特異性比單獨IL-6 預測更有意義。既往研究已經初步顯示IL-6 在其他疾病引起膿毒血癥中的診斷意義,而作為兩種重要的炎癥指標,本研究提示IL-6 聯合LMR 對嚴重燒傷患兒膿毒血癥的預測更具有準確性和特異性。
此外,本研究通過Kaplan-Meier 生存曲線進一步證明傷后7 d、14 d,高水平IL-6 組比低水平IL-6 組生存率低,低LMR 組生存率比高LMR 組低,這提示IL-6 及LMR 對嚴重燒傷患兒生存率的評估具有較好的預測價值。
綜上所述,本文從炎癥指標LMR 及促炎細胞因子IL-6 角度出發,揭示IL-6 聯合LMR 對嚴重燒傷患兒膿毒血癥的發生及預后具有更好的預測價值,動態監測這兩個指標的變化對及時評估患兒病情與預后情況,盡早實施臨床干預、提高救治率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另外本研究屬于回顧性分析研究且樣本例數較少,存在一定局限性,尚需前瞻性臨床研究進一步明確及擴大樣本量,確保研究結果的準確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