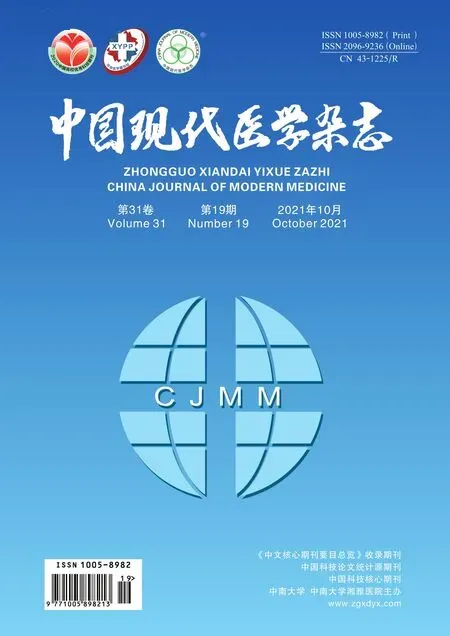益智開竅針刺法結合穴位注射治療腦性癱瘓的療效分析
任敬佩,穆曉紅,郭文杰,焦勇,胡傳宇,徐林
(1.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 骨科,北京100700;2.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潞河醫院神經外科,北京101149)
腦性癱瘓(以下簡稱腦癱)是由于患兒腦部損傷導致其出現肢體功能異常、運動發育延緩,并多伴隨出現語言障礙及智力低下[1]。有研究指出約80%的腦癱患兒伴隨出現語言功能異常,而語言功能障礙的嚴重程度與患兒腦部損傷的嚴重程度及部位相關[2]。語言功能主要受肌肉及神經影響,若患者出現肌張力、姿勢、運動協調、肌力等功能異常則均可能誘發言語質量惡化[3]。語言功能發育遲緩和結構運動障礙性構音障礙是導致腦癱患兒語言障礙的重要因素[4]。近年來,隨著新生兒危重搶救技術和產科技術的發展,臨床有多種方案對腦癱患兒進行干預治療[5]。目前臨床多采用言語訓練等療法進行干預治療,但其療效不佳且起效緩慢[6]。對腦癱患兒采用針灸及穴位注射可有效改善患兒語言功能及智力,但兩者聯合應用的療效及其作用機制尚未完全揭示。本研究探討益智開竅針刺法結合穴位注射對腦癱患兒語言障礙、腦血流灌注、腦葡萄糖代謝的影響,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5年1月—2018年12月北京中醫藥大學東直門醫院收治的100 例腦癱患兒作為研究對象。依照隨機信封法將患兒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50 例。對照組男34 例,女16 例;平均年齡(6.19±0.72)歲;腦癱分型偏癱5 例,雙癱34 例,四肢癱11 例;粗大運動功能分級系統(GMFCS)分級1、2 級29 例,3 級15 例,4、5 級6 例。觀察組男35 例,女15 例;平均年齡(6.21±0.75)歲;腦癱分型偏癱6 例,雙癱32 例,四肢癱12 例;GMFCS分級1、2 級30 例,3 級13 例,4、5 級7 例。兩組一般資料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本研究經醫院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患兒法定監護人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納入和排除標準
納入標準:①患兒均為痙攣型腦癱[7],且存在語言功能障礙;②年齡2~10 歲;③智力測定結果判斷為中度或輕度智力發育遲緩(DQ 分41~75 分);④腦干聽覺誘發電位檢查正常。排除標準:①由于耳聾、聽力障礙、腭裂等因素導致的語言障礙;②孤獨癥量表結果提示患兒為不典型孤獨癥或孤獨癥;③合并癲癇;④存在心肝腎等疾病不適合進行干預;⑤患兒法定監護人主動申請退出本研究。
1.3 方法
對照組患兒采用常規語言療法進行治療,主要包括語言康復訓練和口腔感覺運動刺激療法。語言康復訓練依照患兒自身的語言發育能力及癥狀制訂詳細的訓練方案。語言行為包括基礎性過程、符合形式-指示內容關系、交流態度3 個側面。口腔感覺運動刺激療法主要包括皮膚黏膜按摩、口內及口周肌肉按摩、刺激嘔吐及吞咽反射、立體感知味覺刺激、吞咽/咀嚼/進食訓練、口運動訓練,1 次/d,30 min/次,每周治療5 d,3 個月為1 個治療周期,持續治療1 個周期。
觀察組采用益智開竅針刺法結合穴位注射進行治療。在進行益智開竅針刺法治療時選擇智三針、腦三針、顳三針、四神針、焦式語言一區、語言二區、舌三針、語言三區、合谷、啞門、涌泉作為針灸主穴,若患兒出現脾腎不足加針三里、三陰交、太溪、脾俞、腎俞穴,心腎不足加針心俞、神門、腎俞、三陰交、太溪穴,痰濁壅盛加針陽陵泉、三里、脾俞、豐隆穴,發音不清加針頰車、地倉、承漿穴。針灸時頭針采用平補平瀉法以斜刺方式進針至帽狀腱膜,進行體針干預時以捻轉方式進針,逆時針為補,順時針為泄,給予適當刺激后捻轉退針。在治療過程中若患者較為配合則頭部、體針均留針10 min 左右,對年齡較小或體位不易固定者僅留頭針。啞門直刺0.5 寸點刺后出針。觀察組在針灸隔日進行穴位注射,使用神經節苷脂鈉注射液(濟南齊魯制藥有限公司,批準文號:醫藥準字H20051485)交替對神門、廉泉、百會、通利、語言區一、語言區二、語言區三及啞門進行注射,每個穴位注射0.5 ml,穴位選擇交替使用,以3 個月作為1 個治療周期。
1.4 觀察指標
治療結束后采用尼莫地平法對患者臨床療效進行評估,主要包括痊愈、顯效、有效和無效4 項,有效率=(痊愈+顯效+有效)/總例數。采用格塞爾嬰幼兒發展量表(GDS)[8]對患兒治療前后的語言障礙功能進行評估。在治療前及治療后采用SPECT 對患者進行掃描,記錄患兒腦血流灌注情況,并利用放射性藥物氟標記脫氧葡萄糖成像觀察記錄患兒腦葡萄糖代謝改善情況。
1.5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20.0 統計軟件。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比較采用獨立樣本t檢驗和配對t檢驗;計數資料以百分率表示,比較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患兒療效比較
兩組患兒療效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010,P=0.002),觀察組臨床有效率較對照組高。

表1 兩組患兒療效比較 (n=50)
2.2 兩組患兒GDS評分比較
治療前兩組患兒GD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兩組患兒GDS 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高于對照組;兩組治療前后GDS 評分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治療后均升高。見表2。
表2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GDS評分比較 (n=50,±s)

表2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GDS評分比較 (n=50,±s)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 值P 值治療前49.59±7.29 50.02±8.16 0.279 0.781治療后77.41±9.13 64.58±8.34 8.332 0.000 t 值19.123 8.870 P 值0.000 0.000
2.3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腦血流灌注情況比較
兩組患兒治療前腦血流灌注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兒治療前后腦血流灌注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22.581,P=0.000),對照組患兒治療前后腦血流灌注情況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10.526,P=0.000);治療后,觀察組患兒腦血流灌注情況正常38 例,對照組5 例,兩組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χ2=88.862,P=0.000),觀察組腦血流灌注改善患兒多于對照組。見表3。

表3 兩組患兒治療前后腦血流灌注情況比較[n=50,例(%)]
2.4 兩組患兒葡萄糖代謝水平比較
兩組患兒葡萄糖代謝水平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觀察組患兒額葉、頂葉、顳葉及枕葉部葡萄糖代謝水平高于對照組。見表4。
表4 兩組患兒葡萄糖代謝水平比較 (n=50,±s)

表4 兩組患兒葡萄糖代謝水平比較 (n=50,±s)
組別觀察組對照組t 值P 值額葉0.42±0.05 0.21±0.04 19.600 0.000頂葉0.46±0.03 0.34±0.06 12.649 0.000顳葉0.27±0.04 0.13±0.03 15.748 0.000枕葉0.17±0.02 0.14±0.04 4.743 0.000
3 討論
腦癱患兒語言障礙的臨床療效及預后主要取決于患兒智能障礙情況[9]。有研究顯示,約75%左右的腦癱患兒伴隨不同程度的智力缺陷,其中智力發育輕度遲緩約占30%,中度或重度遲緩約占45%左右[10]。構音障礙及智力發育遲緩均可能導致患兒語言發育遲緩。臨床治療腦癱患兒時,在提高語言功能的同時還需盡可能地提高患兒智力水平,并有效增強其學習能力及理解能力,有助于提高患兒語言功能[11]。有研究指出,腦癱患兒語言進步的同時其理解能力、反應能力、身體素質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且伴隨著語言能力的提高其心智也有一定程度的改善[12]。
傳統中醫學理論認為,腦癱屬于五軟、五遲、五硬范疇,其發病機制與后天失養或胎中感邪,先天稟賦不足,髓海受損,并進一步導致五臟六腑失養,氣血虧虛,心腎蒙蔽且精乏髓竭[13]。因而在對腦癱患兒進行治療時應以調補肝腎、養心益智、醒腦開竅、疏經通絡為主[14]。本研究結果顯示,觀察組采用益智開竅針刺法結合穴位注射后可有效提高患兒GDS 評分。觀察組患兒治療后腦血流灌注情況好于對照組,且觀察組腦葡萄糖代謝水平高于對照組,而腦血流灌注情況是目前評估腦功能的重要指標,葡萄糖是體內腦細胞重要的也是唯一的能量來源,腦葡萄糖代謝情況可直接反應大腦功能。益智開竅針刺法結合穴位注射神經節苷脂鈉時,針刺可有效刺激大腦皮質、改善腦血流量并恢復休眠細胞功能,進而起到治療腦癱的效果。此外,營養腦神經藥物穴位注射,能養心安神、醒腦益智、調整陰陽、疏通經絡,有效促進腦功能代償,改善并提高患兒語言能力。
綜上所述,采用益智開竅針刺法結合穴位注射對腦癱患兒治療后可顯著提高臨床療效,并改善患兒腦血流灌注情況及腦葡萄糖代謝。但本研究臨床樣本數較少,且并未對患者進行長期隨訪追蹤,有待后續深入研究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