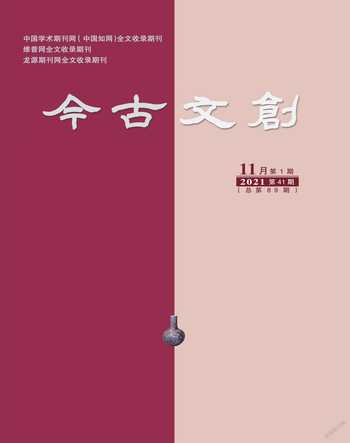許淵沖“ 三化論 ”視域下歌曲《 青花瓷 》英譯評(píng)析
張晴
【摘要】 歌曲《青花瓷》無(wú)論是從音律的角度還是從歌詞的角度看,都堪稱經(jīng)典。歌曲不僅在國(guó)內(nèi)廣為流傳,在國(guó)外也大受歡迎,出現(xiàn)了不少英文版《青花瓷》,其中不乏優(yōu)秀英譯本。從本文從“三化論”的角度,評(píng)析了優(yōu)秀英譯本的譯者是如何通過(guò)等化手段實(shí)現(xiàn)“意境似如初”,通過(guò)深化手段達(dá)到“情深意無(wú)窮”,又通過(guò)淺化手段做到“形美情不減”,以期更好地通過(guò)音樂(lè),讓中國(guó)文化走出國(guó)門。
【關(guān)鍵詞】 《青花瓷》;淺化;深化;等化
【中圖分類號(hào)】H315? ? ? ? ?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 ? ? ? 【文章編號(hào)】2096-8264(2021)41-0118-03
一、引言
《青花瓷》是由方文山作詞、周杰倫作曲并演唱的歌曲,是兩人合作的“中國(guó)風(fēng)”歌曲的巔峰之作,也是“中國(guó)風(fēng)”歌曲的經(jīng)典作品。歌曲在2007年一經(jīng)發(fā)行,就憑借其婉轉(zhuǎn)動(dòng)人的旋律與韻味悠長(zhǎng)的歌詞風(fēng)靡樂(lè)壇,并且經(jīng)久不衰。歌曲不僅獲獎(jiǎng)無(wú)數(shù),是音樂(lè)史上里程碑式作品,其歌詞文化底蘊(yùn)深厚,意境古典含蓄,在文學(xué)史上也占有一席地。《青花瓷》歌詞出現(xiàn)在2008年山東和江蘇兩省的高考試題中就足見其文學(xué)價(jià)值。歌曲不僅在國(guó)內(nèi)大熱,也深受外國(guó)聽眾喜愛。新西蘭歌手羅藝恒和巴西歌手Marcela Mangabeira各自翻唱了英文版《青花瓷》,但他們的版本對(duì)歌詞改動(dòng)較大,失去了中文版歌詞的韻味,不免令人遺憾。原武漢新東方校長(zhǎng)李杜老師的《青花瓷》英譯本,很大程度上還原了中文歌詞的韻味,受到廣泛好評(píng),本文選取了李杜的英譯本,從許淵沖先生的“三化論”角度對(duì)其譯文的巧妙之處進(jìn)行了評(píng)析,并對(duì)其譯文的不足之處提出了修改建議。
二、許淵沖及其三化論
許淵沖是當(dāng)代中國(guó)最有影響的翻譯家與翻譯思想家。許教授的翻譯理論一言以蔽之,即“美化之藝術(shù),創(chuàng)優(yōu)似競(jìng)賽”。他的翻譯觀受到中西哲學(xué)、文藝學(xué)和美學(xué)思想的深刻影響,即展現(xiàn)出與前輩和同時(shí)代學(xué)者一致的一面,也有突出的個(gè)性特征,一分為三的思維方法就是特征之一。一分為三、涵三為一既是一種世界觀, 也是一種方法論。其理論核心概念,如“三美論”(形美、音美、意美)、“三之論”(知之、好之、樂(lè)之)、“三勢(shì)論”(優(yōu)勢(shì)、劣勢(shì)、均勢(shì))等, 無(wú)不是一分為三思維的體現(xiàn)。而與此相應(yīng)的翻譯方法“三化論”(淺化、深化、等化)也是典型的一分為三思維[2]。
“三化論”源于錢鐘書先生的“化境說(shuō)”,錢鐘書認(rèn)為文學(xué)的最高標(biāo)準(zhǔn)是“化”,把作品從一國(guó)文字轉(zhuǎn)變成另一國(guó)文字,既能不因語(yǔ)文習(xí)慣的差異而露出生硬牽強(qiáng)的痕跡,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風(fēng)味,那就算得入于化境[5]。許教授認(rèn)為翻譯可以說(shuō)是“化學(xué)”,是一種語(yǔ)言化為另一種語(yǔ)言的藝術(shù)。這種“化”有限度,只能化成原文內(nèi)容所有、原文形式所無(wú)的譯文,不能化成原文內(nèi)容所無(wú)的東西[4]。
三、《青花瓷》英譯本譯例賞析
(一)淺化避短
淺化,把特殊的東西一般化,包括抽象化、減詞、合譯、化難為易、以音譯形等[3]。淺化是為了規(guī)避目標(biāo)語(yǔ)的劣勢(shì),將原文一些晦澀難懂,富含深層文化意義的詞淺化為淺顯易懂的詞,以著力保留原文的意境,既能消除譯語(yǔ)讀者的理解障礙,又能使他們自然地融入歌詞的意境當(dāng)中。具體請(qǐng)看下面譯例賞析。
例1
原文:“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zhuǎn)淡”
譯文:“Unglazed,from shade to light,unfolds the blue and white”
這句歌詞中,“素胚”顯然不是主語(yǔ),通過(guò)動(dòng)詞“勾勒”可判斷出動(dòng)作主體是人,讀完全文更能肯定此處主語(yǔ)是男主人公“我”。與英語(yǔ)語(yǔ)法不同, 漢語(yǔ)重意合,句子無(wú)主語(yǔ)不影響對(duì)整體句意的把握。但英語(yǔ)重形合,對(duì)句法要求嚴(yán)格,譯者在翻譯時(shí)會(huì)添加主語(yǔ)。但巧妙的是,譯者并沒有直接引入“I”作為主語(yǔ),而是轉(zhuǎn)換思路,用“青花在瓶身徐徐展現(xiàn)”表達(dá)了原句中的“‘我’勾勒青花”的含義,避免了引入新主語(yǔ),卻更突出了筆隨心動(dòng),青花躍然瓶上的畫面感。在處理“青花”這一文化意象時(shí),譯者沒有直譯,而是譯為“the blue and white”,化具體為抽象,變特殊為一般,幫助譯文讀者理解這里的“青花”是藍(lán)白兩色構(gòu)成的圖案,減少讀者跨文化的理解負(fù)擔(dān),并巧妙呼應(yīng)了前面的“濃轉(zhuǎn)淡”。
不過(guò),筆者覺得譯者將“濃轉(zhuǎn)淡”譯為“from shade to light”有不妥之處。譯者用“shade”表“濃”之意,但通過(guò)仔細(xì)查閱詞典后發(fā)現(xiàn),“shade”在該語(yǔ)境下合適的語(yǔ)義有兩個(gè):一是(色彩的)濃淡深淺或色度,本身沒有“濃厚色彩”之意;二是作陰影講,意指濃重的筆墨。前者從意義上就不符,而后者語(yǔ)義合適,但形式上,其為名詞,而對(duì)應(yīng)的“淡”譯為形容詞“l(fā)ight”,明顯無(wú)法并列。中國(guó)畫的墨色分為五色,即焦(concentrated)、濃(thick)、重(heavy)、淡(thin)、清(light),“濃”是“thick”,且符合英文地道表達(dá),所以直接譯為“from thick to light”即可。
(二)等化達(dá)意
等化包括、詞性轉(zhuǎn)換、句型轉(zhuǎn)換、正說(shuō)反說(shuō)、主賓互換、主動(dòng)被動(dòng)互換、同詞異譯、異詞同譯、典故移植等[3]。淺化是避短,等化是半揚(yáng)長(zhǎng)半避短,是為了“通順”,追求意似的等值,取得譯語(yǔ)對(duì)原語(yǔ)的均勢(shì)。具體請(qǐng)看下面譯例賞析。
例2
原文:“素胚勾勒出青花筆鋒濃轉(zhuǎn)淡”
譯文:“Unglazed,from shade to light,unfolds the blue and white”
上文已指出,“素胚”并非主語(yǔ),這個(gè)名詞在句中實(shí)際上是作狀語(yǔ)的,意指“青花”勾勒于“素胚”之上。句中意象“素胚”“青花”“筆鋒”,甚至動(dòng)詞“勾勒”,都是方文山精心挑選的情感載體,寥寥幾詞就奠定了整首詞的意境。而譯者對(duì)“素胚”這一重要意象的處理同樣精彩。
眾所周知,歌詞的翻譯比較特殊,除了要準(zhǔn)確、達(dá)意,還要考慮到很重要的一點(diǎn),那就是譯文歌詞在長(zhǎng)度與節(jié)奏上要貼合原曲。若要按“素胚”在原文中的意義與功能直譯,應(yīng)譯為“on the unglazed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但如此譯文會(huì)過(guò)長(zhǎng),且“blue and white”的重復(fù)既顯冗余,又破壞了歌曲節(jié)奏,而譯者僅用一個(gè)形容詞“unglazed”就巧妙化解了長(zhǎng)度與節(jié)奏問(wèn)題。這個(gè)形容詞的使用,不僅不是錯(cuò)誤,也不突兀。該句是歌詞第一句且“unglazed”位于句首,往前是題目“The blue and porcelain”(青花瓷)。題目已為讀者點(diǎn)出了整首歌曲的核心意象,讀者心中一定有了預(yù)期與聯(lián)想,對(duì)“unglazed”的第一反應(yīng)必是“unglazed porcelain”,再往下自然也能明白青白二色是在其上的勾繪。譯者通過(guò)簡(jiǎn)單的詞性轉(zhuǎn)換這一“等化”手段,用形容詞翻譯了在原句中起狀語(yǔ)作用的名詞,成功傳遞了原文“素胚”這一意象的意義與功能,不僅準(zhǔn)確傳遞了原句的情感和內(nèi)涵,又沒有意境上的丟失,取得了譯語(yǔ)對(duì)原語(yǔ)的均勢(shì),可見譯者對(duì)原文與譯文的把握程度。
(三)深化揚(yáng)長(zhǎng)
深化,即深化原文表層,包括特殊化、具體化、加詞、分譯、以舊譯新、無(wú)中生有等[3]。深化是為了神似,在深度理解原文內(nèi)容,把握原文感情基調(diào)的基礎(chǔ)之下,表達(dá)出原文的言外之意,去傳達(dá)原文深層結(jié)構(gòu)的“意美”,發(fā)揮譯語(yǔ)的優(yōu)勢(shì),爭(zhēng)取取得譯語(yǔ)對(duì)原語(yǔ)的優(yōu)勢(shì)。具體請(qǐng)看下面譯例賞析。
例3
原文:“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
譯文:“The sky is blue enough to expect the rain;for you I am waiting,however in vain”
作者方文山在訪談中曾談到“天青色等煙雨”其實(shí)無(wú)論從意境還是邏輯來(lái)說(shuō)都是錯(cuò)的,天青色并不是青花瓷的顏色,而是汝窯。純正上品的汝窯,只有一種顏色,就是“天青色”,完全沒有任何花哨的紋飾,而且造型簡(jiǎn)單素雅,在他看來(lái)猶如現(xiàn)今極簡(jiǎn)主義大師的作品,雖有一種樸素的內(nèi)涵,與經(jīng)久耐看的質(zhì)感,但總覺得不足以形容詭譎多變,愛恨兼具的愛情[1]。所以在這句中,方文山其實(shí)是嫁接了汝窯的特點(diǎn)在青花瓷身上。這點(diǎn)雖然是邏輯上的硬傷,但考慮到作品的藝術(shù),出于對(duì)整體意境的考慮,也無(wú)可厚非。其實(shí)筆者認(rèn)為,拋開汝窯與青花瓷之爭(zhēng),單就這句詞來(lái)看,邏輯是沒有問(wèn)題的。正如宋徽宗詩(shī)所言“雨過(guò)天青云破處,這般顏色作將來(lái)”,被雨洗刷過(guò)的天空才呈青色,天青等雨也說(shuō)得過(guò)去。并且從整體意境上看,《青花瓷》宛然一出煙雨朦朧的江南水墨山水,“天青”“煙雨”是構(gòu)成這種朦朧含蓄美的重要元素。
但譯者在翻譯這前半句時(shí),未深層理解原文內(nèi)涵,甚至出現(xiàn)錯(cuò)誤,理解為“蔚藍(lán)天空等待煙雨的到來(lái)”,與上文分析到的該句的真正意義截然相反,那么該句的翻譯“The sky is blue enough to expect the rain”自然也是錯(cuò)誤的。筆者認(rèn)為,這前半句可譯為“The azure sky is expecting rain”。首先,筆者運(yùn)用了“深化”的翻譯技巧,將“青色”譯為了“azure”,把原歌詞的表層深化了,傳達(dá)了原歌詞深層的含義:被雨洗刷過(guò)的天空才呈青色,這種色格外清凈明亮,與一般艷陽(yáng)高照的晴天天空的藍(lán)色不同。所以如果用一般的形容詞“blue”來(lái)表達(dá)(比如“青花瓷”的翻譯為“the blue and white porcelain”),就不能傳遞出原歌詞中“天青”與“煙雨”這兩個(gè)由方文山精心挑選的意象之間的關(guān)系,那么整句歌詞意境的構(gòu)造就會(huì)大打折扣。而筆者在深度理解原文的基礎(chǔ)上,選用了“azure”一詞,意指蔚藍(lán)色、碧空,比起“blue”,意義更加具體,含義更加明晰,重點(diǎn)更加突出。在處理該句時(shí)態(tài)時(shí),筆者用了現(xiàn)在進(jìn)行時(shí),而沒用譯者的一般現(xiàn)在時(shí),因?yàn)樵柙~“天青色等煙雨,而我在等你”兩句,前半句寫景,后半句寫情,情境的交融是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經(jīng)典寫作手法,也是這句歌詞的經(jīng)典之處,后半句“我”正在等“你”,前半句必定也是正在等雨,選用正在進(jìn)行時(shí)不僅表意更加準(zhǔn)確,而且通過(guò)前后時(shí)態(tài)的一致完成了譯文中情境的對(duì)比與交融。
后半句“而我在等你”,譯者譯為“for you I am waiting,however in vain”,用了加詞增譯的“深化”翻譯技巧,傳達(dá)了蘊(yùn)藏在原文中的深層次含義。將這句歌詞放到整首歌詞中理解,就會(huì)發(fā)現(xiàn)作者不僅僅只是描寫了男主人公在等女主人公這一事實(shí),更是暗示了故事的結(jié)局。作者在后面寫到“月色被打撈起暈開了結(jié)局”,“月”是“水中月”,被從水中打撈起當(dāng)然是一場(chǎng)空,“暈開了結(jié)局”暗示結(jié)局也是一場(chǎng)空,也說(shuō)明了男主心中朝思暮想的伊人,注定只能留在那個(gè)邂逅的瞬間。譯者理解到了原歌詞的這層含義,在翻譯“而我在等你”時(shí),增譯了“however in vain”,說(shuō)明了“我”等待的結(jié)局,減輕了讀者或聽眾的理解負(fù)擔(dān)。從內(nèi)涵角度來(lái)看,可以說(shuō)譯者將隱含意味闡釋化表達(dá)出來(lái)了,某種程度上來(lái)說(shuō),譯語(yǔ)取得了對(duì)原語(yǔ)的優(yōu)勢(shì)。
四、結(jié)論
具有高度文學(xué)性、藝術(shù)性的歌詞就如同詩(shī)詞一樣,文字簡(jiǎn)潔凝練,意蘊(yùn)悠長(zhǎng)豐富,在翻譯此類作品時(shí),尤其要注重歌詞內(nèi)涵意蘊(yùn)的表現(xiàn)。本文以《青花瓷》廣受認(rèn)可的英譯本為例,從“三化論”的角度來(lái)分析其是如何較為準(zhǔn)確成功地重構(gòu)原作品的意義與情感,從而探索了如何在內(nèi)涵豐富的中國(guó)風(fēng)歌詞翻譯中取得譯語(yǔ)對(duì)原語(yǔ)的均勢(shì),甚至是優(yōu)勢(shì),進(jìn)而詮釋原歌詞中所包含中國(guó)特色的古典意象美和意境美。
音樂(lè)是各民族共通的語(yǔ)言。優(yōu)美達(dá)意的英譯歌詞能讓外國(guó)聽眾在欣賞動(dòng)聽的旋律時(shí), 也能領(lǐng)略歌詞中的文化魅力,從而加深對(duì)中國(guó)文化的了解,甚至產(chǎn)生興趣。這才是真正的中國(guó)文化走出去。
參考文獻(xiàn):
[1]方文山.青花瓷——隱藏在釉色里的文字秘密[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
[2]覃江華,許鈞.許淵沖翻譯理論思維的特征與傾向[J].外語(yǔ)研究,2018,35(05):51-56+67+112.
[3]許淵沖.翻譯的藝術(shù)[M].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6.
[4]許淵沖.如何翻譯詩(shī)詞——《唐宋詞選》英、法譯本代序[J].外國(guó)語(yǔ),1982(4):12-18.
[5]許淵沖.再談中國(guó)學(xué)派的文學(xué)翻譯理論[J].中國(guó)翻譯,2012,33(4):83-90+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