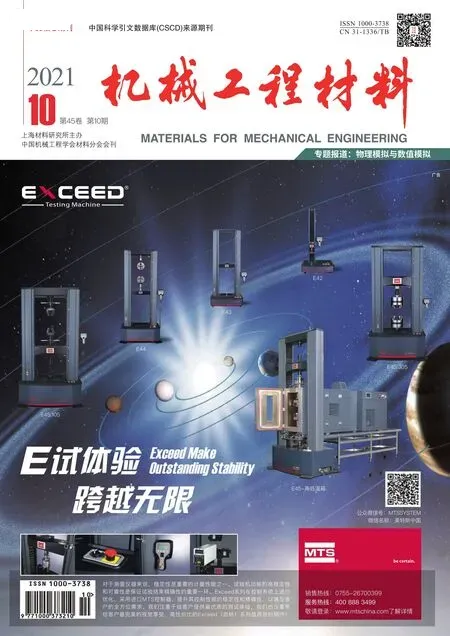超聲表面滾壓加工純鈦梯度材料的力學性能反演與有限元分析
孫銀莎,賈云飛,苑光健,李 曉,張顯程
(華東理工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承壓系統與安全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上海 200237)
0 引 言
在工程部件的服役過程中,疲勞、腐蝕、磨損等失效與其材料表面狀態息息相關;材料表面強度和質量對其可靠性和服役壽命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近年來興起的表面強化技術可以在保持實用性和經濟性的同時顯著延長工程部件的服役壽命。純鈦是一種低密度、高比強度、高耐熱的材料,廣泛應用于航空航天、石油化工等工業領域[1-2]。純鈦在航空領域主要應用在飛機零部件和航空發動機上。航空航天工業的快速發展對純鈦性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純鈦表面硬度低、抗疲勞性能差的劣勢限制了其更廣泛的應用[3-4]。
表面強化技術可以改善金屬材料的表面質量,提升表面硬度,改善抗疲勞性能,對于工業純鈦等材料的廣泛應用有著重要意義。表面強化技術包括激光熔覆、滲氧、滲碳以及表面納米化技術等,其中表面納米化技術能夠在材料表面制備出一定厚度的納米晶層,使納米材料的優勢與傳統工程材料相結合,從而延長材料的使用壽命[5]。超聲表面滾壓加工作為一種新興的超聲輔助表面納米化技術可以同時滿足晶粒細化、加工硬化與表面粗糙度等方面的要求[6-7]。在超聲表面滾壓加工過程中,材料表面因受到工作頭的靜壓力和超聲振動的共同作用而發生彈、塑性變形,產生一定深度的塑性變形層;經過往復加工,材料表面的塑性變形層不斷加深,晶粒尺寸不斷減小,形成典型的表面梯度結構;同時,材料的塑性流動也在材料表面引入了殘余壓應力,殘余壓應力的存在有助于降低疲勞裂紋擴展速率,提高疲勞強度。因此,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可以提高材料的疲勞強度、耐腐蝕性能和耐磨性能[8]。
表面強化技術制備的表面強化層較薄,厚度一般在幾十到幾百微米,其力學性能難以用常規檢測方法獲得。有的研究人員通過將表面強化層剝離下來進行微納拉伸獲得拉伸曲線[9],但該技術成本高,操作難度大,而且難以獲取梯度層不同深度上的應力-應變曲線。如何采用更簡單的方法來獲取梯度強化層不同深度上的應力-應變關系,已成為表面強化層性能研究的關鍵問題之一。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一些研究人員提出了多種納米壓痕反演模型[10]。反演分析方法可以歸納為2種:一種通過對比有限元模擬結果與試驗結果,不斷調整模擬參數以使模擬結果更接近試驗結果,從而獲得材料參數。這種方法誤差比較大,其準確性取決于輸入材料參數是否合理。另一種利用量綱分析,通過一系列量綱函數與有限元模擬結果結合運算,求得材料參數,即利用納米壓痕試驗測試的載荷-壓入深度曲線,結合相關的特征參量量綱分析技術來獲取材料的屈服強度、應變硬化指數等塑性參量。作者采用第二種方法,通過納米壓痕反演分析方法來獲取純鈦梯度強化層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進而得到應力-應變關系,并與有限元模擬結果進行對比,以驗證反演力學常數的準確性。
1 試樣制備與試驗方法
試驗材料為TA2工業純鈦,化學成分[11](質量分數/%)為0.41C,0.17Al,0.11Si,0.26Fe,余Ti。取尺寸為80 mm×80 mm×6 mm的平板試樣進行750 ℃保溫2 h熱處理,再進行超聲表面滾壓加工,進給速度為3 000 mm·min-1,工作頭振幅為16 μm、頻率為20 kHz、靜壓力為470 N,往復加工30遍。
采用線切割法切取包含超聲表面滾壓加工面在內的尺寸為5 mm×8 mm×6 mm的長方體試樣,研磨拋光后,在試樣側面距表面距離分別為30,60,90,140,200,300,500,700 μm處選取納米壓痕測試點,采用Agilent Nano Indenter G200型納米壓痕儀進行納米壓痕試驗。壓頭采用三棱錐形Berkovich金剛石壓頭,棱面與中心線夾角為65.3°,棱邊與中心線夾角為77.05°,最大載荷為100 mN,加載速率和卸載速率均為10 mN·s-1。為了避免相鄰壓痕的應力場交疊而影響測試結果,相鄰壓痕之間的距離均大于10倍壓痕深度。相同測試條件下至少測試3次,取平均值。
取截面金相試樣,采用金相鑲嵌機進行熱鑲,并經打磨拋光處理,使用由體積比為1…2…17的HF、HNO3和H2O組成的溶液腐蝕45 s后,采用蔡司Observer.Alm倒置式光學顯微鏡觀察截面顯微組織。使用JEM-2100型透射電子顯微鏡(TEM)觀察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表面及截面微觀形貌。為了獲得試樣厚度方向的殘余應力大小,采用電解腐蝕法進行剝層處理,電解液為10%高氯酸+90%甲醇溶液(體積分數)。電解腐蝕后將試樣在丙酮溶液中進行超聲清洗,再用酒精沖洗并吹干,采用Proto-iXRD MG40P FS STD型殘余應力測試儀測定殘余應力。重復上述剝層和殘余應力測定工作,即可得到超聲表面滾壓后試樣表面到次表面的殘余應力場。
2 納米壓痕反演方法與有限元模擬方法
2.1 納米壓痕反演模型
彈塑性材料典型的納米壓痕載荷-壓入深度曲線見圖1[12-13]。圖1中:P為載荷;h為壓入深度;C為加載段曲率;Pmax為最大載荷;S為彈性接觸剛度;hr為殘余壓痕深度;Wt為總功;We為彈性功;Wp為塑性功;Pu為卸載載荷;hm為最大壓入深度。根據經典的Oliver-Pharr模型[14],材料的納米壓痕硬度可以表示為

圖1 彈塑性材料典型的納米壓痕載荷-壓入深度曲線Fig.1 Typical nanoindentation load-indentation depth curve forelasto-plastic materials

(1)
式中:H為納米壓痕硬度;A為載荷P下的投影接觸面積。
等效彈性模量的求解公式為

(2)

(3)
式中:E和ν分別為試驗材料的彈性模量和泊松比;Ei和νi分別為壓頭的彈性模量和泊松比;Er為等效彈性模量;β為壓頭非對稱的修正系數,Berkovich壓頭取1.034[15]。
對于大多數應用在工程領域的純金屬與合金材料,可以用冪律關系估計其單軸應力-應變關系[13],該關系表達式為

(4)
σy=Eεy
(5)
ε=εy+εp
(6)
式中:σ為應力;ε為應變;σy為初始屈服應力;εy為初始屈服應變;εp為超過屈服應變之后的塑性應變;n為應變硬化指數。
由式(4)、式(5)、式(6)可知,只要知道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就可以確定材料的塑性性能。在納米壓痕測試中,對某一種特定材料的本構關系的描述服從其特殊的無量綱函數形式。DAO等[13]經過量綱分析及系列研究獲得如下5個函數:

(7)

(8)

(9)

(10)

(11)
式中:σr為代表性應力;εr為代表性應變;pave為硬度;П為無量綱函數。
聯立式(4)以及式(7)~式(11),代入由納米壓痕試驗獲取的各參數,即可得到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將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代入式(4),即可得到單軸應力-應變曲線。
2.2 納米壓痕試驗有限元模擬
對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的表面梯度結構純鈦試樣的納米壓痕試驗進行有限元模擬。為了簡化模型、縮短計算時間,采用二維軸對稱結構進行建模,壓頭作用于結構中心位置處,如圖2所示。采用二維四邊形單元進行網格劃分,節點數為12 940,單元數為12 761,在靠近壓痕處采用加密網格以獲得更精確的結果,其他地方采較疏網格以減少運算量。納米壓痕試驗采用的是Berkovich壓頭,按照接觸面積等效原則,模擬時采用等效錐角為70.3°的剛性錐形壓頭代替。工業純鈦的泊松比為0.32,彈性模量由納米壓痕試驗測得,模擬時使用的不同深度的應力-應變曲線,由前文納米壓痕反演方法獲取材料參數后推導得到。模擬時采用載荷控制,最大壓入載荷為100 mN。

圖2 納米壓痕試驗有限元模型Fig.2 Nanoindentation test finite element model
經不同工藝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表層材料初始屈服應力相同時可能會有不同的應變硬化指數,或者初始屈服應力不同時有相同的應變硬化指數。為此,利用有限元模型進行參數化分析,通過改變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研究了載荷-壓入深度曲線加載段曲率、塑性功與總功之比以及初始剛度的變化規律。
3 結果與討論
3.1 截面顯微組織
由圖3可以看出,與具有均勻晶粒的原始試樣相比,超聲表面滾壓后試樣表面出現明顯的塑性變形層,表面晶粒細化,已無法用光學顯微鏡觀察,其變形形式在微觀結構上呈現為梯度分布。最表層由于直接與加工頭接觸,因此首先發生塑性變形,隨著滾壓加工時間和遍數的增加,其塑性變形量不斷增加。

圖3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前后試樣的截面顯微組織Fig.3 Microstructures on cross section of samples before (a) andafter (b) ultrasonic surface rolling processing
由圖4可以看出:在距表面450 μm處,試樣的晶粒內產生一定量的位錯纏結區,并且位錯分布不均勻;在該位置,超聲表面滾壓加工的影響略小,材料發生一定程度的塑性變形,位錯胞處于形成的初始階段。在距表面300 μm處,試樣組織中出現了由一列列排序規整的位錯墻構成的亞晶結構,并且晶粒尺寸相比于距表面450 μm處明顯減小;亞晶組織是由位錯纏結造成的。與距表面450 μm處相比,距表面300 μm處的材料塑性變形顯著增大。在塑性變形過程中,微區位錯不斷發生湮滅和再生,進而形成位錯墻結構。事實上,位錯胞就是此類位錯墻不斷分割而組成的。位錯胞的胞壁在分割后會繼續滑移和湮滅重組,最終會組成圖4(b)中亞晶結構的初始狀態晶界。因此,在塑性變形顯著增加的前提下,純鈦材料的原始組織通過位錯胞的胞壁不斷湮滅重組,被分割形成大量的亞晶結構。距表面70 μm處的晶粒尺寸相比于距表面300 μm處進一步減小,這是由于越接近表面,超聲表面滾壓加工的影響越大,發生的塑性變形越大,位錯胞的胞壁湮滅和重組現象就越為明顯,晶粒細化程度也更高。試樣表面的晶粒尺寸已經達到納米級(80 nm),且晶粒為等軸晶形態。

圖4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截面不同位置和表面的TEM形貌Fig.4 TEM micrographs at different locations on cross section (a-c) and of surface (d) of samples after ultrasonic surface rolling processing:(a) at 450 μm from surface; (b) at 300 μm from surface and (c) at 70 μm from surface
綜上可知,經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純鈦試樣從表面至次表面發生的塑性變形程度減小,晶粒由納米晶向亞晶轉變。
3.2 殘余應力
在超聲表面滾壓過程中,表層材料發生塑性變形,并且材料表面的塑性變形程度遠大于次表面與基體材料。這種塑性變形量的不同會造成內部結構的約束作用,從而產生內應力。由圖5可以看出,從試樣表面到內部,殘余壓應力先增大,至次表面后逐漸減小,次表面處的殘余壓應力最大,約為326 MPa。雖然超聲表面滾壓后表面材料發生的塑性變形量最大,但由于表面較自由,受到的約束較小,可以釋放一定量的殘余應力,因此最大殘余壓應力未出現在表面,而是出現在次表面處;從次表面到基體,材料受到的超聲表面滾壓作用減小,塑性變形量降低,因此殘余壓應力不斷減小。

圖5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中殘余應力隨距表面距離的變化Fig.5 Variation of residual stress with distance from surface ofsamples after ultrasonic surface rolling processing
3.3 納米壓痕力學性能及反演應力-應變曲線
由圖6可以看出,經相同載荷的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的納米壓痕最大壓入深度隨著距表面距離的增加而增大。這是由于經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表面層(深度30~90 μm)形成了納米晶結構,抵抗變形能力較高,納米壓入深度較淺;隨著距表面距離的增大,試樣的晶粒尺寸增大,抵抗變形能力減弱,納米壓入深度變深。對于純鈦基體材料(距表面700 μm處)來說,由于本身強度較低,抵抗變形能力相對較弱,因此壓入深度比較大。

圖6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納米壓痕載荷-壓入深度曲線Fig.6 Nanoindentation load-indentation depth curv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surface of samples after ultrasonic surface rolling processing
由表1可以看出,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的彈性模量隨距表面距離的變化規律不明顯,距表面90 μm處的彈性模量最大,為121.9 GPa,距表面700 μm處的彈性模量最小,為115.7 GPa,最大值與最小值之間的差距也并不懸殊。彈性模量變化不大說明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對工業純鈦微觀結構造成的損傷較小。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表層的納米壓痕硬度明顯增大,表層最高硬度達到2.625 GPa,與遠離表層的基體材料(硬度2.018 GPa)相比,提高了約30%。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純鈦試樣表層晶粒明顯細化,顯微硬度也得到大幅度提高,符合Hall-Petch理論[16]。此外,根據位錯理論,材料的塑性變形導致大量的位錯運動,引起位錯的切割和增殖,并且伴有微觀結構缺陷,如間隙原子以及層錯等缺陷;這些缺陷會大大阻礙位錯的運動,在宏觀層面上表現為材料產生加工硬化,因此納米硬度增加。

表1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納米壓痕彈性模量與硬度
結合量綱分析和納米壓痕數據得到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純鈦試樣的塑性材料參數,如表2所示。將彈性模量、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代入式(4),即可繪制得到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應力-應變曲線,如圖7所示。由圖7和表2可以看出,隨著距表面距離增加,應變硬化指數逐漸增大,表層應變硬化指數較小,在相同應變下產生的應力更大,均勻變形能力較差。

表2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塑性材料參數

圖7 由反演方法得到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應力-應變曲線Fig.7 Stress-strain curves at different distances from surface ofsamples obtained by inversion method
3.4 反演方法的驗證
將由納米壓痕反演方法得到的應力-應變曲線引入有限元模型,模擬得到納米壓痕載荷-壓入深度曲線,并與試驗獲得的曲線進行對比。由圖8可以看出,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載荷-壓入深度試驗曲線與模擬曲線基本吻合,模擬得到的最大壓入深度與試驗得到的最大壓入深度相比,相對誤差均在8%以內,可見反演方法是可行的。誤差產生的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反演采用的方法是基于量綱分析的,計算步驟繁多,反演得到的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存在一定誤差;二是有限元模擬時輸入的材料參數不夠全面,而且網格數量有限,與實際情況相比存在誤差。

圖8 試樣距表面不同距離處的載荷-壓入深度試驗曲線與有限元模擬曲線的對比Fig.8 Comparison of test curves with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 curves of load vs indentation depth at different distance from surface of samples
3.5 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對載荷-壓入深度曲線的影響
由圖9可以看出,隨著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增大,載荷-壓入深度曲線加載段曲率逐漸增大,塑性功與總功之比逐漸減小,初始剛度變化不明顯。在納米壓痕試驗過程中,隨著工作頭壓入深度的增加,材料先發生彈性變形,隨后發生塑性變形。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越大,說明材料抵抗變形的能力越強,施加同樣載荷的壓入深度越淺,因而加載段曲率越大。在納米壓痕卸載過程中,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越大,殘余應力越大,材料彈性恢復做功更多,因而塑性功與總功之比越小。初始剛度變化不大,因為對于同樣幾何形狀的壓頭,初始剛度與回彈量呈正比關系[17]。

圖9 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對應的納米壓痕載荷-壓入深度曲線參量對比Fig.9 Comparison in nanoindentaion load-indentation depth curve parameters for different initial yield stresses and strain hardening exponents: (a) loading curvature; (b) ratio of plastic work to total work and (c) initial stiffness
4 結 論
(1)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純鈦試樣表面形成了塑性變形層,并形成了從表面到次表面晶粒逐漸增大的梯度結構,最表層晶粒達到了納米尺度;殘余壓應力隨著距表面距離的增加先增大后減小,在次表面處殘余壓應力最大。
(2) 超聲表面滾壓加工后,隨著距表面距離的增加,試樣的納米壓痕硬度逐漸減小,在相同載荷下的最大壓入深度逐漸增大;隨著距表面距離的增加,由反演方法得到的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分別呈現逐漸減小和逐漸增大的變化趨勢。
(3) 將反演方法得到的應力-應變曲線引入有限元模型,模擬得到的納米壓痕載荷-壓入深度曲線與試驗得到的曲線基本吻合,最大壓入深度相對誤差在8%以內,說明反演得到的數據較為準確;隨著初始屈服應力和應變硬化指數的增大,載荷-壓入深度曲線加載段曲率也逐漸增大,塑性功與總功之比逐漸減小,初始剛度變化不明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