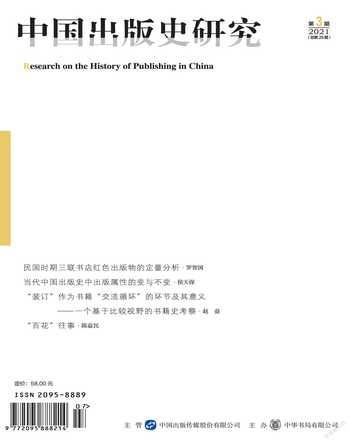“百花”往事
【摘要】成立于1958年的百花文藝出版社以散文為特色,以獨特的圖書裝幀設計令書界矚目,以認真的態度和持久的關切令作者傾心。社長林吶的格局、編輯的進取,使“百花”名滿天下,但因受到“四人幫”打擊,“百花”一度遭到裁撤。出版環境困頓,原“百花”的同人們依然努力著,這為后來“百花”歸來、再創輝煌積蓄了新的能量。本文敘述的是改革開放前百花社經歷的風云歷程。
【關鍵詞】百花文藝出版社 散文 裝幀設計 天津人民出版社
百花文藝出版社,在改革開放前的20年間,近10年崛起,10年多被裁撤。而短短那么些年,“百花”卻確立了自身特色,以散文為號召,以獨特的圖書開本和裝幀設計名世。“百花”社長林吶富于創新,“百花”編輯充滿活力。但開罪于“四人幫”,迭遭打壓。十年沉寂,猶為書界懷念;改革開放,終盼來此后浴火重生。
本文系回憶自“百花”建立至改革開放前,“百花”的那些人、那些事。它們構成了中國出版史上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一、周揚說:“‘百花’厲害啊!”
說起“百花”,出版界都知道,那是指百花文藝出版社。
改革開放前,以出版文學作品為主的出版社不多,主要有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青年出版社、上海文藝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長江文藝出版社和春風文藝出版社等。可見天津的百花社在全國文藝類出版社中,也算是老資格了。
然而,與“人民文學”“中青”“上海文藝”三社比,“百花”又是后來者。它成立于1958年,而另三社都成立于20世紀50年代初。正因為如此,“百花”最初成立時,編輯出去約稿,都是自稱百花社是剛成立的小社,希望人家支持云云。
可是出人意料的是,這個“小社”卻很快在出版界闖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
其一,編輯富于闖勁,廣泛聯絡作者,并對作者充滿溫情。
當時“百花”的編輯敢想敢干,尤其上海、北京作為文化中心,知名作家眾多,“百花”編輯南下北上,常去這些地方組稿,廣泛聯系作家,毫不怵頭。董延梅那時三十歲左右,與另一位年輕編輯第一次出去約稿,就直闖大家郭沫若先生住處,被郭的秘書攔下,恰遇郭沫若先生出來,她們便大膽上前表達來意,以真誠和熱情,居然贏得了郭沫若先生的同意,郭遂將他的《洪波曲》書稿交給了百花社出版。這真讓兩位年輕編輯大喜過望。
年輕編輯如此富于朝氣,令人驚嘆。而“百花”的鋒芒尚不止此,業務骨干們的文化底蘊,更讓百花社得以邁出一個個堅實腳步。據記載,林吶既重視對新編輯的培養,又注重發揮骨干編輯人員的作用。包括徐柏容、任希儒、曾秀蒼、周艾文、李克明、崔興仁、陳玉剛、文秉勛、趙克明、陳景春、汪國風等在內的一批業務骨干,為百花社編輯隊伍的打造,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讓新興的百花社從建社伊始就有了很高的編輯出版水準。
與名家建立了聯系,還要努力維持良好的關系。此后百花社與郭沫若先生就多有往來,“百花文藝出版社”與“天津人民出版社”的社名題詞,就是那個時期請郭先生題寫的。百花社還與其他許多知名作家建立了聯系,如茅盾、孫犁、巴金、老舍、冰心、碧野、王西彥、周而復、梁斌……從而保證了百花社文學類圖書的高水準、高品質。
百花社不僅高度關注知名作家,也注意發現與培養年輕作者。后來大紅大紫的浩然,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還只是一個文學青年,百花社前后約了他好幾部書稿。出版短篇小說集《珍珠》時,浩然回憶:“書稿處理得相當快,不到一個月的時間編輯部就回信告訴我:終審完畢,沒有什么具體修改意見。作者若愿意做些文字潤色工作,可利用畫家插圖作畫的這個空隙時間;愿來天津,出版社可以提供食宿條件。完全是商量的語氣,卻包含著對一個文學新人的關心照顧。”當年為了改稿子,浩然來到天津,住在錦州道6號屬于出版社的那座舊樓的地下室。地下室存放了社里許多書,環境逼仄,卻令浩然難忘。他住了好些日子,不僅改了書稿,還順帶另創作了兩篇新作。浩然說,那是一個“難忘的、愉快的、有成績的暑期”浩然:《不忘“百花”情》,《我與百花(1958—1988)》,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頁。。
為了讓作者滿意,“百花”付出了許多努力。冰心《櫻花贊》出版后,她覺得封面底色不太理想,百花社便在出第二版時換了封面;冰心說還想要一部分精裝書贈送日本友人,出版社也專為她印制了一批。田間的《天山詩抄》、陳大遠的《大風集》等,作者希望同時有一部分線裝本,出版社竟然也慨然應允,為之去做。郭小川的《將軍三部曲》,為了畫好插圖,竟然在社內讓所有美術編輯都來創作,然后進行展示、評選,選擇最滿意的插圖。對于重點書稿,百花社尤其舍得下功夫。梁斌的《播火記》是小說《紅旗譜》的第二部。《紅旗譜》已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反響很大。《播火記》被百花社爭取到后,在出版形式上可謂下足了功夫。50年代后期,國家已規定圖書出版一律橫排,梁斌作為老一代文化人,內心喜歡豎排文字的書。社長林吶就一口答應,專門為此書又印了豎排的版本。而且,該書還出版了平裝、精裝、特精裝等不同層次的版本,使這部書呈現出不同的面貌,適應了不同層次的讀者閱讀、收藏。可見為把書做好,讓作者滿意、讀者滿意,出版社真把暖心的事做到了家。
其二,“百花”的書,精致可人。
百花社從建社之初,就確定了以散文為主的出書方向(此方向一直堅持至今),并且要求內容多樣、形式新穎。據統計,百花社當年的圖書開本,包括普通32開、大32開、長32開、方32開、小32開、新32開,乃至有所謂25開、36開,等等,花樣繁多。僅以1964年為例,出書37種,而特殊開本占了21種之多。開本一多,費紙就多,而百花社更在意作者和讀者的感受,在形式上盡量滿足市場多樣的需求。
不僅開本獨特,封面設計和內文插圖也十分講究。百花社本身的美術編輯設計水平就很高,而出版社并不滿足于此,還時常聘請社外名家幫著設計。張光宇、李駱公、黃胄、華君武、陳半丁、邵宇、黃永玉、米谷、俞沙丁、葉洛、樂小英等,都是美術界名家,他們或為百花社畫過插圖,或設計過封面,或被請至百花社傳授經驗。因此百花社的書除開本獨特外,裝幀設計上也十分搶眼,令人矚目。而梧桐樹引來金鳳凰,當時許多散文名家因之也喜歡將書稿交給“百花”。那時百花社出版的名家名作,包括冰心《櫻花贊》、巴金《傾吐不盡的感情》、碧野《月亮湖》、陳淼《春雨集》、孫犁《白洋淀之曲》、杜宣《五月鵑》、王西彥《唱贊歌的時代》、任大星《野妹子》、陳伯吹《禮花》……內容豐富多彩,又有別致的開本、清新的封面、疏朗的版式、簡潔的插圖,一時風靡那時的出版界,引得各家出版社紛紛模仿,而廣大讀者也熱情追捧。不少讀者對此印象深刻。姜德明在《辛苦了,家鄉人》一文中說:“我同‘百花’真正結緣是在它開始出版小開本散文叢書的時候。我可不小看它那特殊的開本,在那強調‘輿論一律’、連穿衣服都清一色的年代里,這么個‘不倫不類’的開本,不正是在出版界吹起的一曲清豪的‘反調’嗎?”
趙麗宏在《我和“百花”的緣分》一文中,也有類似的回憶:“那時我還是一個中學生,喜歡散文,到書店里總要看看書架上有什么新的散文集出版。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的那套散文集是我最喜歡的。不知是什么道理,那些與眾不同的小開本竟然使我產生了一種奇妙的親切感,仿佛這套散文集就是為我這樣的學生寫的。”
“百花”名編徐柏容主持了一套描寫外國風情的小叢書,包括陳大遠《北歐行詩話》,韓北屏《非洲夜會》,遠千里《古巴速寫》,聞捷、袁鷹《非洲的火炬》……他說要學習20世紀30年代晨光書局的裝幀風格,要摹仿蘇聯愛倫堡《暴風雨》一書的插圖特點。于是那套外國風情叢書設計得非常清雅,封面帶著現代藝術氣息,融合了寫實與抽象兩種格調,加之開本獨特,一時傾倒了無數讀者和出版者。當時出版社年出書量不多,徐柏容便提出那種獨特的開本和設計,只用于那一套書,不讓別的書重復這種風格,使之保持在書界獨特的地位。于是那套書成了別開生面的一股清風,令人久久難忘。
而這種重視開本和裝幀之風,也引起了出版界的震動。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首任社長葉至善說:“因為‘百花’出書慎重,裝幀好,有人講,有了書稿,一是交‘百花’,二是上海,三是北京。”說明當年百花社的書在裝幀設計上是引領風氣之先的,也激發了兄弟出版社在這方面的跟進。巴金當時曾說:“你們‘百花’注意裝幀設計,由你們掀起了(裝幀設計的)競賽。”《“百花”的美術設計是復辟資本主義的重要工具》,“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3期,1968年4月30日。
正因為“百花”在不長的時間內就讓書界矚目,廣泛吸引了讀者和作者,在海內外均產生了影響。百花社建社的前八年,約出版400多種書,就有30多種參加了國際展覽,并有數種還被譯成外文輸出海外。時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的周揚,曾情不自禁地贊嘆:“‘百花’厲害啊!”文化部部長茅盾甚至夸贊:“‘百花’開二十世紀之風!”《搗毀“百花”黑店,砸爛津滬黑網》,“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4期,1968年5月10日。
二、“百花”掌門人的待人之道
百花社的迅速崛起,得益于它有好的掌門人——林吶。林吶既善于獨立思考,又重視博采眾長,百花社在書界迅速脫穎而出,與他的出版理念密切相關。
他是1938年參加八路軍的老革命,曾先后擔任冀中軍區六分區《火焰報》社社長、冀中軍區《前線報》社通訊股長、華北《解放軍報》編委,是位資深的編輯、記者。1949年后曾任中共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1956年以后,擔任天津人民出版社、百花文藝出版社社長。他思想活躍,見識深遠,有膽識、有魄力,在百花社篳路藍縷、剛剛建立之初,就擬訂了百花社未來的長遠發展目標。百花社后來幾十年以散文、短篇小說為主打版塊,實肇基于林吶社長時期。
林吶很注意利用和發揮各方人才的優長,廣結各方實力作家。百花社成立之前,林吶充分調動積極因素,讓大家出謀劃策。資深出版人、當時的編輯部副主任徐柏容,與編輯曾秀蒼專門起草了《關于文藝書籍編輯叢書、擴大組稿工作的初步意見》,其中明確提出四點:1.力爭出版國內一流作家的一流作品;2.出書系統化,邀請著名作家、學者主編幾套叢書;3.挖掘地方文化資源,彰顯地方文化特色;4.裝幀設計要完美,印刷要精致,形成獨特的風格徐柏容:《在“辦一流出版社”的道路上》,《我在百花》,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4頁。。他們的建議被林吶所采納。該“初步意見”中有要從全國“收羅一流作家力作”之語《拔掉“百花”黑據點,砸爛反革命文藝黑網》,“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3期,1968年4月30日。,后來事實上確實“收羅”了許多一流作家和一流作品。而且,當時的做法,一是不只是等作者有了作品后才去“收羅”,而是未雨綢繆,提前“下網”,與作家長期交友;二是不只是瞄準當下活躍的主流作家,也同時去發現尚未成名而有潛力的年輕作家,甚至于舊時代的著名文學“遺老”,亦予關注。
“百花”建社之初,曾在報紙上登載了辦社方針,即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立足地方,面向全國;為讀者服務,為作家服務。像“為作家服務”的提法,在當時就十分特別,而林吶正是照此去做的。在“百花”成立前夕,他就讓徐柏容起草了致國內知名作家報告“百花”成立并請其支持的信函,隨后就分寄給了國內眾多名作家,其中包括田漢、陽翰笙、劉白羽、嚴文井、老舍、巴金、王西彥……信中說,“百花”是稚嫩的幼苗,希望得到各位名家扶持,助其成長。信函得到不少作家響應。而支持是相互的。有些作家當時在別處處境堪憂,“百花”就挺身而出,勇于擔當,為他們出書發聲。
周揚作為主管文學藝術創作的領導,1960年針對現實情況,曾說:“在學術問題、藝術問題上,我們反對武斷,反對壓服,反對粗暴批評,而主張經過充分的討論來明辨是非,逐步達到正確的結論。”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文藝報》1960年第13—14期。然而現實中,尤以上海的姚文元對當時文學的評論最為粗暴。1962年,巴金在上海第二次文代會上發言,批評某些人在文壇上“總是把自己放在居高臨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說服人,單憑一時‘行情’或者個人好惡來論斷,捧起來可以說得天上有地下無,罵起來什么帽子都給人戴上,好像離了捧和罵就寫不成批評文章似的”。不指名地指責了“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處找毛病的人”,即姚文元之流。姚文元為此懷恨在心,隨后不久,即借“拔白旗”之風,搞起了“巴金作品討論”,在數種報刊上對巴金進行圍攻。上海市委常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還說了這樣的狠話:“巴金這樣的人還能夠寫文章嗎?”葉永烈:《“四人幫”興亡》第八章“巴金怒斥‘姚棍子’”節,人民日報出版社2009年版。
然而,林吶卻讓編輯與巴金聯系,表示百花社愿意為他出書。編輯徐柏容在致巴金信中,還因遲遲未見巴金書稿寄到而有“忽忽若有所失焉”之語。當時為出好巴金的《傾吐不盡的感情》一書,林吶囑咐編輯,要保持與巴金的聯系,充分聽取他的意見。1963年9月,該書順利在百花社出版。
還有作家王西彥,是抗戰時期與方紀結識的老友。方紀任天津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局局長時,將他推薦給林吶。“反右”時,王西彥所在單位給百花社來函,稱王西彥“實質上是不戴帽的右派”,當時的上海市委第一書記柯慶施也說過不可以出版王西彥的書《搗毀“百花”黑店,砸爛津滬黑網》,“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4期,1968年5月10日。。而林吶卻讓百花社一連為他出版了若干種書:《唱贊歌的時代》(1958年)、《從播種到收獲》(1960年)、《在漫長的路上》(1963年)。1965年,王西彥被姚文元扣帽子,批判為“資產階級在文藝上的代理人”,“要同黨的革命文藝方針唱對臺戲”,而百花社卻還在計劃出版他的理論雜文集《第一塊基石》。清樣都已排好,終因上海方面施壓,以組織名義通知出版社:不能出版他的書,已出版的書不得重印,正發排的書要終止出版。政治風云趨緊,百花社才抱憾停了下來。王西彥為此一直對百花社的付出心存感激王西彥:《抹不去的記憶》,《我與百花(1958—1988)》,百花文藝出版社1988年版,第15—20頁。。
由此兩例,即可看出林吶社長在政治高壓下仍保持著非凡的擔當,也可以看出百花社所具有的不尋常的斗爭精神。
林吶社長還聽取同樣視野開闊的方紀局長的意見,將目光放得更遠,不局限于當時的熱門作家。
周作人身份特殊,林吶卻主張不因人廢文。早在百花社成立之前,林吶就已經讓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周作人翻譯的《烏克蘭民間故事》《阿拉伯民間故事》《希臘神話故事》等。1959年,他又派編輯與周作人聯系,將他的《草葉集》《紹興兒歌集》等稿子拿回。前者是周氏1949年后發表的散文小品集,交稿后在出版還是不出版問題上,社里幾經周折,爭論很大。1960年6月曾告訴周作人不出版了;1962年6月改書名為《木片集》,又決定出版。審校都已完畢,只待印刷,終因當時的政治高壓,認為作者身份特殊,其作品又盡寫些民風民俗、草木蟲魚之類,與“風起云涌的革命浪潮”毫無關聯,最終該書的出版胎死腹中。周作人在1963年4月10日日記中曾這樣感嘆:“已兩次付排,而終不能出版,亦奇緣也。”轉引自張菊香、張鐵榮編著:《周作人年譜》,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困難重重,一些正常的書在當年無法正常出版,而林吶為此所做出的努力,仍令人敬佩。
還有宮白羽,這位中國現代武俠小說的鼻祖,他在民國年間發表的《十二金錢鏢》,成為中國早期武俠小說的扛鼎力作。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武俠小說因為不合時宜,遭到冷遇。而林吶卻聘請宮白羽為社外特約編輯,不用坐班,每月給予一定的薪酬。他還鼓勵宮白羽繼續給香港報紙寫武俠小說連載。或許,林吶內心有這樣的安排:等政治形勢轉變了,有了適合出版武俠小說的風尚時,或可將宮白羽的新作結集出版。只是這種預想最終消弭在長久動蕩的政治浪潮中。而想想二三十年后武俠小說在大陸又風行起來,則不能不讓人感佩當年林吶內心所具有的深意。
那時擔任“特約編輯”的還有王汶。她熟練掌握俄文、英文、日文,深得葉圣陶、周建人、戈寶權等贊賞。林吶也聘請她為社外特約俄文編輯。她后來翻譯《氣球上的五星期》《罪與罰》《俄國作家童話選》等,可見有相當的語言文學功力。此舉也反映出林吶吸取各方人才為我所用的治社方針。
三、“百花”遭撤銷
天津人民出版社內部原設有兩個編輯部,1958年將其中的第二編輯部組建成百花文藝出版社,而領導班子仍是原來的,行政和出版部門也是原來的,說明這只是一個單位兩塊牌子的狀態。百花社成立后,主要出版文藝類書,由社長林吶負責其業務;天津人民出版社則主要出版社科類書,業務由黨總支書記孫五川負責。
“文革”期間,林吶、孫五川“靠邊站”,正常的出版業務受到沖擊。1967年2月,百花社被撤銷,百花社編輯人員又歸入天津人民社第二編輯部,后又改稱文藝組。
百花社被撤銷的原因,主要是受“四人幫”打壓。“四人幫”污蔑百花社的領導與中央和地方的走資派“沆瀣一氣”,走了一條“修正主義的反動路線”,而且在文學領域構筑了“津滬黑網”。
1968年2月21日,“四人幫”在京接見天津的造反派代表時說:“以周揚為代表的一條文藝黑線,它在全國有相當的一個黑網。”《拔掉“百花”黑據點,砸爛反革命文藝黑網》,“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3期,1968年4月30日。而百花社就被認為是這個黑網中的一個黑據點。“四人幫”之所以對百花社咬牙切齒,重要原因是上海是“四人幫”的老巢,張春橋、姚文元把上海的文學藝術界整得花落滿地,零落塵泥。而偏偏許多在上海遭批判的作家,卻順利地在天津的百花社出版作品,這能不讓張、姚惱怒嗎?姚文元說:“上海有一些最壞的書是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的,而天津有些大毒草是在上海出版的。反正都是一丘之貉。”《徹底砸爛黑出版》,“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2期,1968年4月25日。此言一出,百花社當然在劫難逃了。
百花社被撤銷,社里有編輯私下開玩笑說:要怪當年董延梅,組稿一下就去找郭老,怎么不去找姚文元呢?而戲言話鋒一轉,他們又道是,即使當年真找了姚文元,姚氏那火藥味十足、打棍扣帽的文風,百花社也絕不會給他出集子的。
“四人幫”四面出擊,宣稱從中宣部,到天津市委宣傳部,到天津的出版社,構成了上下一條黑線。應當承認,從出版觀念來說,當時的百花社社長林吶確實與上級各層級宣傳部門領導有共同的志趣。天津市委書記處書記王亢之,市委宣傳部副部長、文化局長方紀,河北省委宣傳部副部長遠千里,與林吶都曾是冀中干部,是抗戰時期的老同事、老戰友,也都做過編輯。還有市委宣傳部副部長白樺,也是抗戰時做過宣傳工作的老干部。他們彼此熟悉,關系密切,尤其是志同道合,因而在出版方向上觀點一致。“百花”社名,就是由白樺提出、經王亢之確定下來的;遠千里則明確劃定了河北人民出版社主要出版通俗讀物,而百花社以出版文藝精品為主的范圍。他們共同為百花社的發展確定了方向。而他們的許多努力,又得到中宣部陸定一、周揚的肯定。他們與當時的中宣部有著相同的文藝思路。按后來批判王亢之的說法,“王亢之長期執行的是舊中宣部陸定一、周揚的文化、文藝修正主義路線”王林1967年2月21日大字報:《萬曉塘、張淮三反黨宗派集團的形成和罪惡活動》,《現代中文學刊》2014年第4期。。百花社主張政治第一、質量第一;主張繼承遺產、洋為中用;主張搞“全民文藝”,百花齊放;主張為讀者服務、為作家服務。這一切均與周揚的主張一致。如周揚說過,“只要政治方向的一致性而不要藝術風格的多樣性,只許一花獨放,不要百花齊放,這是非常有害的”,對于“過去文學藝術中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的優良傳統”,要“批判地繼承和綜合”,“在為工農兵服務、為社會主義事業服務的方向下實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既反對了修正主義,又反對了教條主義;既保證了文學藝術的政治方向的一致性,又保證了文學藝術風格的多樣性;既引導作家、藝術家同工農群眾結合,樹立革命的世界觀,又給與作家、藝術家以充分機會來發揮他們的藝術獨創性”周揚:《我國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道路》,《文藝報》1960年第13—14期。。由此可見,百花社確實執行了中宣部的文藝路線,而這根本就談不上是“文藝黑線”,而應當說是正確的文藝路線,是與“四人幫”宣揚的一套相對立的路線。
1965年11月10日,《文匯報》發表姚文元《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這是“文革”風暴即將到來的序曲,“山雨欲來風滿樓”。最初北京所有報紙均不轉載此文,《北京日報》社社長范瑾甚至質問《文匯報》發表此文背景何在?吳晗當時很緊張,覺得此文大有來頭,而時任北京市市長的彭真則認為不管什么來頭不來頭,只問真理如何!20天后,《人民日報》轉載姚文元文章,彭真還在編者按中說:要就如何“對待歷史人物和歷史劇的問題進行辯論”。作為北京市委一級的領導尚且不知道這篇文章大有來頭,也就不難理解,作為基層出版社的編輯,對姚文元此文的背景就更一無所知了。
“百花”人對于上海姚文元之流在文藝路線問題上亂揮“棍子”、亂飛“帽子”的行徑,非常憤恨。編輯周艾文、曾秀蒼在20世紀60年代初讀到姚文元若干打棍子、扣帽子的文章,就十分反感,認為簡單粗暴,曾秀蒼還想寫文章與之“商榷”。而姚文元評《海瑞罷官》的文章出籠后,更令他們氣憤。于是1966年1月,周艾文署筆名“周雅”,給《文匯報》寄去一封信,反駁姚文元的文章,斥其說為奇談怪論。該信發出前,交社長林吶、副社長張恒看過,得到他們的默許。結果可想而知,信沒有在《文匯報》上登出,他們幾人后來卻為此遭受了批判。從他們身上,可以看到當年百花社編輯內蘊的風骨與情懷。(曾秀蒼還曾大膽寫信,為被打倒的彭德懷鳴冤,其氣節更是令人慨嘆。)
“文革”開始后,在“四人幫”的粗暴干預下,百花社連遭批判,直至被撤銷。當時批判的“罪名”很多,例如關于一花獨放還是百花齊放問題,關于人性、人道問題,關于描寫中間人物問題,關于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問題,關于文藝為誰服務問題,等等。百花社被“四人幫”污為“黑店”,出版的許多好作品被誣為“毒草”。如漢水的長篇小說《勇往直前》,描寫大學生活,極富青春氣息,卻被攻擊為鼓吹修正主義教育路線、鼓吹資產階級人性論;洪汛濤的《望夫石》,1959年曾作為國慶獻禮書,“文革”時卻被誣為充滿低級趣味,宣揚愛情至上和階級調和的“大毒草”;陳伯吹的《禮花》被說成“通過小蟲小鳥、貓狗神仙,宣揚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宣揚和平主義、階級調和,妄圖對少年兒童實行和平演變”;王西彥的《唱贊歌的時代》,被污蔑為“和三面紅旗唱反調”,反黨反社會主義;任大星的《大街上的恐龍》,被歪曲成“誣蔑新中國的誕生是‘恐龍’作怪;大躍進是頭腦發熱,溫度太高了”云云《搗毀“百花”黑店,砸爛津滬黑網》,“文革”小報《出版戰報》第4期,1968年5月10日。。真可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
四、失落的“百花”
“百花”撤銷,編輯人員回歸天津人民出版社,依然做文藝類圖書的出版。但在“文革”前期,出版秩序一片混亂,出版社只是做從中央大出版社租型的書,同時也搞一些報刊上的政治文論摘編,而文藝類作品的出版基本停止。
嚴重的書荒,極大地阻礙了廣大群眾的閱讀需求。到1971年,國家不得不出臺政策,開始清理審查書庫中存留的“文革”前的書籍,挑出沒有政治問題的圖書重新上市,并重印一批市場急需、審查合格的圖書。天津市、區圖書館(組)圖書聯合審查小組于1971年5月編印的《圖書開放試行目錄》第1期164種中國文學作品中,天津人民出版社和百花社的圖書僅列入6種,都屬于庫存書。僅這幾種,還都存在須涂改之處。修改方式有幾種:或撕去,或用筆涂抹,或用白紙條貼蓋,還有貼白紙條后又在上面加上修改之字。如《革命青春的贊歌——記毛主席的好戰士王杰》一書,需要涂去“修養”二字;用紙條貼蓋“《李雙雙》”,并在紙上改寫成“革命電影”(因當時劉少奇《修養》一書、電影《李雙雙》,猶戴著“毒草”的罪名)。可見極“左”路線還在嚴重阻礙著文藝圖書的面世。
1972年以后,本版文藝類圖書的出版才逐漸復蘇,但迎合政治形勢的作品多,可圈可點的高水平文學藝術之作少。那一時期產生較大影響的作品,大致如下(因“百花”社未恢復,當時出書署“天津人民出版社”之名):
浩然已名滿天下,出版社繼續為他出短篇小說集,先后出版了《春歌集》(1973)、《七月槐花香》(1973)、《歡樂的海》(1974)、《百花川》(1976)。其中《百花川》因帶有過多“文革”階級斗爭色彩,“文革”后受到批判。雖然出版社為此受到牽連,但20世紀80年代當浩然的《男婚女嫁》一書要加急出版時,百花社依然出手相助,及時為他出版,令浩然十分感動。
《桐柏英雄》,長篇小說,1972年11月出版,部隊作家創作,描寫解放戰爭時期失散親人重逢的故事,是當時思想性、藝術性較好的作品。責編是文藝組的郭逸塵。該書在“文革”后被北京電影制片廠拍成電影《小花》,1979年上映后,引起強烈反響。日后成為影壇巨星的唐國強、陳沖、劉曉慶,正是在這部劇中作為主演首度亮相的。
《深山明珠》《春滿青藏線》《駝鈴千里》,均為1975年出版的散文小冊子,而書的雅致開本,給那個沉悶的書界帶來了一縷春風。編輯謝大光回憶:1973年以后,“靠邊站”多年的林吶恢復了工作,負責文藝組等部門的業務(還不是領導班子成員),就又惦著找回“文革”前的“百花”圖書特色。那時“無論編輯,還是讀者,都在懷念‘百花’,懷念林吶主持開創的‘百花’風格”。但當時造紙廠已不生產那種小開本的紙,“又不可能為三本書單獨造一批紙。林吶沉得住氣……就是不簽這個字”。最后出版科不得已,就“用普通開本的紙,裁上兩刀,裁成‘小開本’的規格,再上機。用這個法子有個缺陷,浪費紙。‘就這樣吧!’林吶一語定奪”。而后來這三本書在市場上大受歡迎,書界紛傳:“老‘百花’又回來了。”謝大光:《想起林吶》,《我在百花》,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版,第184頁。
《小靳莊詩歌選》,是“文革”后期“四人幫”的幫派作品。它的出版,不是出版社主動迎合“四人幫”,而是由上往下強行壓下來的政治任務。1974年,江青稱贊小靳莊,說“這是我的點”,要宣傳小靳莊的賽詩活動。“四人幫”埋怨天津的出版社對此事冷淡,說如果天津不出版小靳莊詩集,就讓北京的教育出版社去出。因而天津人民出版社不得不派出文藝組的編輯前往小靳莊收集、整理和修改當地的農民詩歌,很快將其出版。首印30萬冊,后來又加印30萬冊。1976年,為“反擊右傾翻案風”,在“四人幫”的督促下,又出版了續集,印10萬冊。但隨著“四人幫”倒臺,《小靳莊詩歌選》及續集從書店下架,大量未銷售的書被銷毀。
大型文學叢刊《今朝》,于1975年5月推出,至1976年5月,出版了4期。后因“文革”結束,沒有繼續出下去。“文革”以來文學創作匱乏,缺少文學雜志,而人民群眾渴望文學閱讀。于是上海出版了大型文學叢刊《朝霞》,為“文革”服務,是政治性的文學刊物。天津受此啟發,創辦《今朝》,思想主旨與《朝霞》相似。不過,拋開其中的政治因素不論,它對于當時文學創作的復蘇,倒是有一定的促進意義。
另外還出版了一些迎合當時政治形勢的長篇小說,如《火焰》是描寫與“走資派”“斗爭”的影射小說,1976年7月出版,“四人幫”垮臺后受到批判;《草原新牧民》,1973年出版,描寫知青扎根邊疆的故事,內蒙古自治區、西藏自治區曾有譯成少數民族文字的愿望;《草原輕騎》,1974年出版,描寫草原的文藝工作者,題材較新穎。
“文革”結束后,各方呼喚“百花”歸來。1979年8月,百花社恢復,林吶重新擔任社長。此后40年來,經幾任社長的努力,經全體“百花”人的共同奮斗,百花社建社初期確定的“辦一流出版社”的方針,得到了全面落實。他們創辦的《散文》《小說月報》《小說家》等期刊,歷經三四十年,依然活躍于文壇;設立了全國性的文學大獎“百花文學獎”,至今已評了十八屆;出版了規模大、影響深的“百花散文書系”,以及一大批有影響的小說,在讀者、作者中有口皆碑;曾被評為全國優秀出版社……
百花社,迎來了它最好的發展時期。
〔作者陳益民,天津人民出版社編審〕
A Look back at the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Chen YiminAbstract:The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founded in 1958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publishing of essays, catches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shing community with unique book binding and design, and wins the trust of writers with a downtoearth attitude and lasting care. Chief Lin Na of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good at big picture thinking, and its editors worked in an enterprising manner. Their efforts made the name of Baihua well known in the country. Unfortunately, the publishing house was once shut down by the “Gang of Four”. The staff of former Baihua still worked hard despite the unfavorable publishing environment, which paved the way for the rebirth of Baihua and its creation of another glory. The paper narrates the development course of the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before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1978.
Keywords: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essays, binding and desig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of Tianj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