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有月光
潘乃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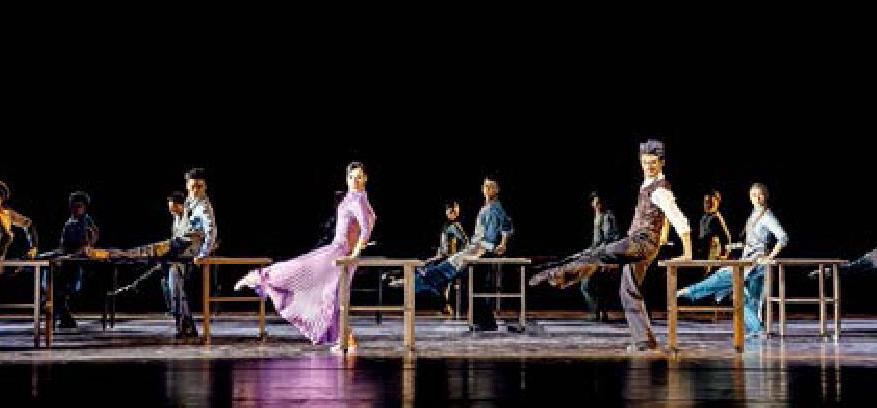
黑龍江人。成都市川劇研究院國家二級編劇,戲劇制作人,中國戲曲學院文學學士、藝術碩士,中國戲劇家協會會員,四川省戲劇家協會理事,四川省文藝評論家協會會員。作品曾獲全國戲劇文化獎大型劇本獎、中國舞蹈“荷花獎”舞劇獎等獎項。
“你是哪里人?聽口音不像成都人。”初次見面的朋友常會因為我講普通話而問我這個問題。
“北方人。“我會如此回答。
“哎呀,還是很不容易,背井離鄉來到成都,不過應該來了很多年吧?吃東西也都習慣了吧?”朋友會追問。
“今年是我來成都的第十五年,吃東西習慣,或者說美食是讓我留在成都的重要動力。”我會繼續答,“而且,月光里的成都格外讓我迷戀。”
在成都的這些年,我幾乎沒有過身處異鄉的落寞感,在我心里,故鄉與異鄉,似乎并不那么遙遠,這大概與當下越來越便利的交通有關,與越來越發達的通訊方式有關,更與故鄉和異鄉共一片月光有關,沒錯,就是月亮散發出的月光。
月亮仿佛有某種魔力,從古至今,生活中和文藝作品中出現的重要意象,總少不了月亮。后人總結古人對月亮情有獨鐘大致離不了幾個原因:古人看到的月亮比現在要大,離得近看得清;月亮更符合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國人認為任何事物都是不斷變化的,盛極必衰,月亮就是不斷變化,陰晴圓缺,每天變化又遵循一定的規律;月亮散發的光芒照在故鄉,也照在他鄉,仿佛月圓那一刻,故鄉、他鄉、月亮會形成一個三角形,彼此鏈接、支撐,構成最穩固的關系,難以撼動,可抵千軍萬馬。
每當月圓,我都會拍下那一刻我所見到的月亮,分享給我的親人、朋友,哪怕拍下來的月亮其明亮、素雅都已大打折扣,仍不影響我這份分享的心。于是在這份感召下,親友也陪著我在不同的地方共賞一輪月。媽媽會說,月光很美,想起了一首老歌《十五的月亮》;朋友會說,哇,這個月亮,簡直絕絕子。也有朋友回復一首古詩詞來,于是張若虛的、李白的、杜甫的、張九齡的、蘇軾的月亮,就都穿過歷史,匯集在手機屏幕上,又從手機出發去到人眼里、心里。
成都的月,總是創造這種讓人為之心醉的機會,而且這種心醉,跨越年齡,比如我的兒子才兩歲多,他也會在看到月亮的時候高喊,媽媽,月亮出來了,快來陽臺看月亮!
在月光的籠罩下,城市也會散發出其獨有的品格與質感。在月光下,當你一路行著,街邊茶館或小店,名字是春風里、春水湖或是七里錦、客至;當你一路行著,眼前時而銀杏時而垂柳,鼻尖時而桂花香時而火鍋香;當你一路行著,心頭忽而是濯錦浣花滄浪一水,時而是草樹云山如錦繡,秦川得及此間無;當你一路行著,貪戀著一路數不盡的草、樹、亭、橋;當你一路行著,抬頭是月光,面前是錦江之水波光粼粼,水中的月亮伴著燈影氤氳著桂花味兒的晚風,沉醉于此情此景此夜此月……我打賭,你一定會愛上這個月夜,愛上這一刻的自己,愛上這一刻的成都。
當我擁有這份美,并把這份感受分享出去,便會感到,異鄉也暖,因有月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