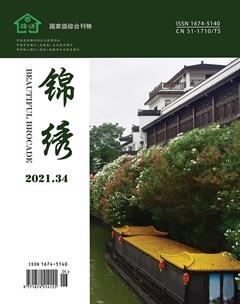我國農村家庭醫生契約化健康服務模式重構研究
摘要:目前我國農村家庭簽約醫生的契約型醫療衛生服務模式在發揮一定積極作用的同時,也存在多種現實問題,主要體現為:一是服務功能目標缺失,未能確立系統提升簽約農民健康素養和水平的功能目標;二是制度形式缺失,存在制度權威性不足、制度規定隨意化等問題;三是制度內容缺失,主要體現為契約參與主體的權責內容及其相互關系模糊性,專門化服務項目不完善等;四是契約實踐效果缺失,服務落地不足等等。形成以上問題的主要根源包括,既有醫療衛生政策目標設計與形式的影響,又有契約形成中相關利益主體相互之間缺乏必要的協商、溝通和博弈互動,以及相關資源支持不足等。針對以上問題,通過服務功能目標、契約形成特質以及制度保障三方面的創新轉變,實現我國農村契約化健康服務模式的重構和優化。
關鍵詞:中國農村家庭;契約化健康服務;家庭醫生;模式重構
一、問題的緣起
以契約化形式為居民提供基本健康服務是當今不少國家采取的重要服務形式,具體體現為相關主體基于契約理念和原則而制定的家庭醫生簽約服務制度規則及其實踐。這種起源于西方國家的服務模式在我國城市試點和推進的基礎上,目前在農村也得以全面展開。從目前實踐看,這種服務模式在改善農村長期存在的醫療衛生服務供給不足中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存在的突出問題是,缺乏對這種服務模式的整體性和本源性問題進行探索。作為特殊契約服務模式,其必然存在特定的理念基礎、功能目標、內容體系、制度設置及運行保障等要素,需要全面加以分析考量,否則就很容易形成片面化和表層化理解。為此本文試圖將理論、政策制度及實證研究有機結合,對這一服務模式進行系統分析,實證方面,在獲得全國性相關數據的同時,在湖北、河南、安徽等多地農村進行了實地調研,并與新的理論建構有機結合,從而有效彌補目前這一重要研究需求的缺失。[1]
二、我國農村家庭契約化健康服務模式反思:缺失及根源
(一)現實問題之反思:四重缺失
1.功能目標缺失
根據該規劃相關調查數據,我國公民整體健康素養還處于較低狀態。規劃 要求我國居民基本健康素養水平從2013 年8.80%的平均較低水平,提高到2020 年的20%。比較而言,農村居民、農村老人以及貧困人群健康素養相對較低,[2]提升任務更加艱巨。據此任務,生活方式干預、中醫養生保健素養、精神衛生、地方病和職業病等領域健康教育工作、心理健康服務等都應成為簽約服務的重要內容。
2.制度形式缺失。為了解決家庭醫生簽約服務
目前還存在大量的地方性制度規則。從以上的制度形式不難看出,我國目前相關制度存在以下多種弊病:正式立法制度較為缺乏, 相關指導意見權威性不足,執行中隨意性較大;臨時性政策法規占據了主導地位,各類指導意見缺少具體細則,執行難度大,影響實際效率;不少規定被包含在相關政策法規中,缺乏精細化規定,不利于實踐操作,而地方操作政策比例過大,很容易形成各地標準不一,造成執行任意性,形成不公平問題。
(二)問題根源之分析
第一,既有的醫療衛生理念及政策設計影響。進入21 世紀以來,我國醫改政策總體上都是在應對“看病難、看病貴”問題的理念下制定和實施的,政策雖然趨于全面系統,但仍缺乏整體、精細的健康服務觀念,而將政策功能設計目標基本局限于基本衛生服務及身體疾病預防和治療。人們之所以對新形式的契約化健康服務知曉度和認可度不高,也與其缺乏自身內容特色有著密切聯系。從制度形式看,在公共服務及社會服務等領域問題治理中,我國長期習慣于依據臨時性政策,過分注重了政策化所具有的靈活性和適應性等優勢,對正式立法制度建設不足,而對法治化的必要性和優勢缺乏足夠認識,實際上體現了一種制度的路徑依賴現象。同時,通常認為,立法需要在政策成熟時才可以進行,而我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仍處于探索中,尚不宜立法,這種觀念直接影響了立法進程。
第二,契約形成特點原因。根據契約的基本特性,契約形成應是相關利益主體在自治基礎上相互協商、反復溝通和相互博弈的過程,以實現共同的利益目標。為保障這一過程特點,英國專門制定了全 民健康服務憲章這一專門性制度。從我國家庭醫生 簽約服務形成看,總體上屬于衛生行政部門或鄉鎮衛生院主導下形成的格式契約,“重簽而輕約”。
三、三重轉變:我國農村契約化健康服務模式重構路徑
(一)功能目標轉變:由衛生醫療服務到實現整體健康
這種轉變由目前通過簽約服務解決農民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缺乏和“看病難、看病貴”的目標思維,轉變為注重提升簽約農民整體健康生活質量的較高層次的功能目標。具體指,將提升簽約農民身體健康水平、心理健康水平、社會健康水平和健康能力水平有機結合,共同納入簽約服務目標體系中,[3]從而獲得整體健康服務效果。這種新目標功能定位,不僅存在現實的客觀需要,而且符合人的健康從受到損害到康復一般規律,因而能夠提升服務效果和節約服務成本,與目前健康中國建設目標、世界衛生組織健康標準及緩和醫療等新服務策略理念具有一致性。
(二)契約形成特質轉變:由行政促成到協商博弈
這種轉變意味著在契約形成過程中,由以往行政主導與促成特質,到契約主體相互之間能夠充分協商、反復溝通、相互博弈和利益嵌入。尤其是注重擴大家庭醫生以及農民作為契約主體參與權利和機會,充分考慮各主體的利益訴求,化解利益沖突,探究和建構各方利益平衡機制,尤其是政府部門及管理機構應作為特殊契約服務主體,保障應有作用的發揮。
參考文獻:
[1]劉峣. 為健康“守護人”撐好“保護傘”[N]. 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07-16:09.
[2]王丹,等. 供需雙方視角下農村地區家庭醫生簽約服務關鍵問題及對策研究[J]. 中國衛生事業管理,2019,36(6): 443-445.
[3]秦江梅,林春梅,張幸,等. 我國全科醫生及鄉村醫生簽約服務進展及初步效果[J]. 中國衛生經濟,2016,35(3): 60-62.
[4]肖蕾,張太慧,張雅莉,等. 分級診療視角下家庭醫生簽約服務“簽而不約”的原因及對策研究[J]. 中國全科醫學, 2018,21(25):3063-3068.
作者簡介:謝婷文(1997—),女,漢族,內蒙古人,碩士生在讀,研究方向:社會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