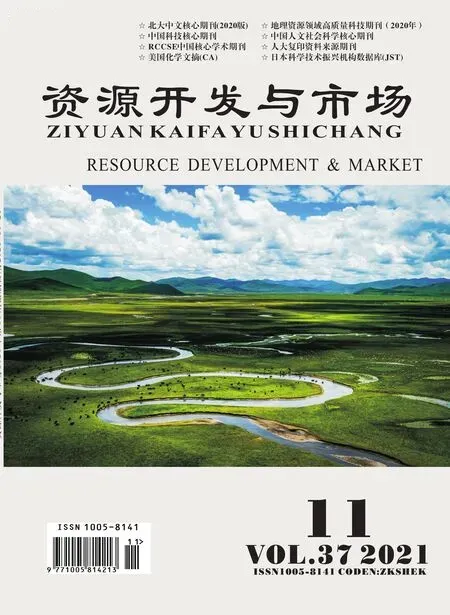中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分析
葉文顯
(陜西國際商貿學院管理學院,陜西咸陽 712046)
伴隨著“十三五”規(guī)劃目標的順利完成,我國社會正式步入“十四五”時期。與此同時,以國內大循環(huán)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huán)相互促進的新發(fā)展格局正逐步形成,我國社會正邁進高質量發(fā)展的新階段,綠色發(fā)展成為新時代的主旋律。城市綠色發(fā)展,尤其是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方式轉型成為生態(tài)文明建設和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進程中的必然戰(zhàn)略選擇。目前,國內不少相關研究關注了國家[1]、區(qū)域[2]、經濟帶[3]、城市群[4]、省域[5]、縣域[6]等層面的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問題,其研究內容主要涉及時空演變[1]、影響因素[2]、效率評價[7]、溢出效應[8]、門檻效應[9]、區(qū)域差異與收斂性[10]等。如,周亮、車磊、周成虎運用SBM-undesirable 模型分析了中國地級以上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的時空演變[1];高贏運用面板回歸模型分析了中國八大經濟區(qū)綠色績效的影響因素[2]。已有文獻大部分采用了DEA 相關模型和面板Tobit模型[11-13],少數(shù)文獻使用了SFA 模型[14]、空間計量模型[15]、分位數(shù)回歸模型[16]、生態(tài)足跡法[17]和門檻回歸模型[18]等。如,孟雪、狄乾斌、季建文運用超效率SBM 模型分析了京津冀城市群的環(huán)境績效水平[13];常新鋒、管鑫運用隨機前沿模型和空間混合模型分析了長三角城市群的生態(tài)效率及其影響因素[15]。此外,一些學者分別關注了城市精明發(fā)展[19]、城市規(guī)模擴張[20]、科技創(chuàng)新[21]、產業(yè)結構調整[22]、地方政府競爭[23]、高鐵運營[24]、環(huán)境規(guī)制[25]、輿論監(jiān)督[26]、城市居民感知[27]、金融集聚[28]等因素與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的關系。如,陳曉紅、周宏浩運用面板VAR 模型分析了生態(tài)效率與城市精明發(fā)展之間的交互響應;賀斌、袁曉玲、房玲運用耦合協(xié)調度模型分析了城市效率與城市規(guī)模擴張之間的協(xié)同發(fā)展效應[20]。
綜上,已有綠色發(fā)展效率的相關文獻在研究內容上多為靜態(tài)效率分析,在研究層面上極少涉及中國省會城市,在研究方法上也較少使用TOPSIS 方法。此外,很多省份實施了“強省會”戰(zhàn)略。“強省會”戰(zhàn)略能否提高區(qū)域綠色發(fā)展效率?這一問題需要通過實證分析進行探究。鑒于此,本文選取包括我國26 個省會城市在內的281 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截面數(shù)據(jù),使用傳統(tǒng)的Super- SBM 模型和ML 指數(shù)測度了26 個省會城市的靜態(tài)效率和動態(tài)效率,使用莫蘭指數(shù)分析綠色發(fā)展效率的空間分布,同時使用TOPSIS方法分析了強省會能力與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的關系,期望本研究能為我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提供理論參考。
1 研究范圍、指標體系與研究方法
1.1 研究范圍
本文選取281 個地級以上城市(含除拉薩之外的26 個省會或首府城市)作為研究對象,不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澳門特別行政區(qū)、臺灣地區(qū)、西藏自治區(qū)、北京市、重慶市、上海市、天津市、三沙市、儋州市、畢節(jié)市、銅仁市、海東市、吐魯番市和哈密市,原因是:香港特別行政區(qū)、澳門特別行政區(qū)和臺灣地區(qū)的行政特殊性,與一般地級城市存在明顯差別;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和重慶市作為直轄市,與一般地級城市也存在明顯差別;西藏自治區(qū)與成立較晚的地級城市(如三沙市、儋州市、畢節(jié)市、銅仁市、海東市、吐魯番市和哈密市)因為缺少相關數(shù)據(jù)而未納入研究范圍。此外,由于青海省只有西寧市1 個樣本城市,部分指標無法計算,故部分表格未將青海省(西寧市)納入分析。
1.2 指標體系與數(shù)據(jù)來源
考慮到指標體系的科學性、綜合性和數(shù)據(jù)的可獲得性,并參考已有研究成果[1,8,9],本文構建了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評價指標體系(表1)。投入要素包括土地、能源、勞動力和資本,具體指標為城市建成區(qū)面積、全社會用電量、勞動從業(yè)總人數(shù)和地方一般預算支出。產出要素包括期望產出和非期望產出。其中,期望產出包括經濟產出和社會福利,經濟產出指標為各城市GDP 和平均GDP 倍數(shù)(各城市GDP 除以該省地級以上城市的平均GDP),社會福利指標為人均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非期望產出指標包括工業(yè)煙(粉)塵排放量、工業(yè)二氧化硫排放量和工業(yè)廢水排放量。研究數(shù)據(jù)為2009 年、2014 年和2019 年281 個城市的截面數(shù)據(jù),數(shù)據(jù)主要來源于2010 年、2015年和2020 年的《中國城市統(tǒng)計年鑒》,少部分來源于26 個省份的統(tǒng)計年鑒和相關城市的統(tǒng)計年鑒,少量空缺值采用插值法補充。

表1 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評價指標體系
1.3 研究方法
非期望產出的Super- SBM 模型與ML 指數(shù):假設有d個個體,每個個體的投入指標、好產出指標和壞產出指標的個數(shù)分別為n、p1和p2,其變量分別為X、Ya和Yb,S 為松弛變量,R 為城市綠色效率值,φ為權重向量,則非期望產出的Super- SBM 模型可表示為:

由于SBM模型測度的是一種靜態(tài)效率,無法反映各地區(qū)綠色發(fā)展效率的跨期變動,鑒于此,本文采用Malmquist- luenberger 指數(shù)測度各地區(qū)的動態(tài)發(fā)展效率。計算公式為:

TOPSIS分析法:TOPSIS法是多目標決策分析方法,常用于多對象的相對優(yōu)劣評價,計算過程為:
原始數(shù)據(jù)的標準化處理。假設原始數(shù)據(jù)為Bij,指標j的最大值與最小值分別為maxBj和minBj,指標個數(shù)為n,采用min—max歸一化的計算公式:

計算所有個體正負理想解的歐式距離。

計算所有個體的相對貼近度。

莫蘭指數(shù):莫蘭指數(shù)是測度數(shù)據(jù)空間相關性的常用方法,包括全局Moran′s I 和局部Moran′s I。假設φ為樣本方差,Wij為空間權重矩陣,則Moran′s I可表示為:

Moran′s I介于-1 到1 之間。當Moran′s I為正數(shù)時,表明空間正相關,即存在低值與低值或者高值與高值的集聚現(xiàn)象;Moran′s I為負數(shù)時,表明空間負相關,即存在低值與高值的集聚現(xiàn)象。
2 結果及分析
2.1 綠色發(fā)展效率的靜態(tài)測度與動態(tài)測度
基于不同省市行政區(qū)劃的測度:構建非期望產出的Super-SBM 模型,運用MaxDEA8.0 軟件計算了我國281 個地級以上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結果顯示,2009 年有55 個城市的發(fā)展效率大于1,約占全部城市的19.57%。281 個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為0.56,其中26 個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為0.77,高于255 個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0.54。2019年有64 個城市的發(fā)展效率大于1,約占全部城市的22.78%。281 個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為0.62,其中26 個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為0.84,高于255個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0.59。由此可知,我國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離生產前沿面還存在較大差距,環(huán)境保護與資源合理利用仍有較大改善空間。整體上,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明顯高于非省會城市。從2019 年281 個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排名來看,以廣州、海口為代表的省會城市,以深圳、青島為代表的非省會特大城市和以舟山、中衛(wèi)為代表的非省會中小城市在綠色經濟發(fā)展方面表現(xiàn)尤為突出,究其原因,可能與這些城市典型的高投入高產出或低投入低污染模式有關。
從26 個省會城市的發(fā)展效率來看(圖1),2009年、2014 年和2019 年分別有11 個、9 個和15 個省會城市處于綠色高效發(fā)展(效率值大于1),分別占全部省會城市的42.31%、34.61%和57.69%,有效城市主要集中在廣州、長沙、福州、海口和西寧,即胡煥庸線以東區(qū)域(除西寧外)。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南高北低”趨勢明顯,這些城市在政策優(yōu)勢與技術優(yōu)勢的雙重推動下,實現(xiàn)了經濟增長與環(huán)境治理的協(xié)調統(tǒng)一。綠色發(fā)展低效方面,2009 年、2014 年和2019 年分別有15 個、17 個和11 個省會城市處于綠色低效發(fā)展(效率值小于1),這些城市主要包括烏魯木齊、貴陽、太原、石家莊、呼和浩特和鄭州,雖然它們聚集了本省的各種要素資源,但是沒有充分發(fā)揮應有的規(guī)模集聚效應。測算26 個省會城市的傳統(tǒng)超效率,結果顯示:2009 年、2014 年和2019 年的平均發(fā)展效率分別為1.02、0.99 和1.13,而考慮環(huán)境污染物后的效率值分別降低了0.25、0.23 和0.29,降幅分別為25%、23%和26%。由此可知,環(huán)境污染導致了省會城市傳統(tǒng)發(fā)展效率的較大損失。

圖1 2009 年、2014 年和2019 年26 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
從2019 年281 個城市的投入產出冗余率計算結果(表2)來看,平均冗余率較高的變量主要有煙(粉)塵排放量58%、二氧化硫排放量55%和廢水排放量43%,三大污染物的冗余率明顯高于各個投入變量的冗余率。因此,我國地級以上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是污染物的過量排放,進一步控制三大污染物的過量排放成為提高我國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抑制“污染天堂”效應的重要途徑。從26個省會城市的測度結果來看,省會城市除了存在嚴重的三大污染物冗余外,還存在明顯的從業(yè)人員過剩,這可能是由于部分省份“強省會”戰(zhàn)略的實施,過多的農村勞動力和小城鎮(zhèn)人口涌入省會城市,造成從業(yè)人員大量過剩。

表2 2019 年26 個省會城市的投入產出冗余率(%)
基于不同地區(qū)和城市規(guī)模的測度:從不同地區(qū)的測度結果來看(表3),我國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呈現(xiàn)明顯的地帶差異性和空間集聚性特征,2009年、2014 年和2019 年四大地區(qū)的省會城市平均發(fā)展效率均明顯優(yōu)于相應非省會城市,且全部城市呈現(xiàn)典型的“東部優(yōu)于西部、中部和東北”和“東部、西部優(yōu)于中部和東北”的格局特征。非省會城市的效率水平同樣表明,東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的平均發(fā)展效率高于中部地區(qū)和東北地區(qū),我國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呈現(xiàn)明顯的“中部塌陷”特征和“新東北現(xiàn)象”。

表3 各維度下省會城市與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
從城市規(guī)模的測度結果來看,省會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明顯優(yōu)于中等城市,且特大城市優(yōu)于大城市,城市規(guī)模與效率水平之間呈現(xiàn)明顯的同向變動關系。非省會城市則發(fā)生了從“小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到“特大城市>小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再到“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的演變,城市規(guī)模與效率水平之間呈現(xiàn)明顯的“U”型關系。原因主要是:省會城市一般具有優(yōu)越的制度、資金、技術和人才優(yōu)勢,在大幅增加投入的同時更易于發(fā)揮規(guī)模效應和虹吸效應,因此省會特大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高于大城市,且大城市高于中等城市。而非省會城市在資金、技術和人才不齊備的背景下,大幅增加要素投入的同時可能無法發(fā)揮規(guī)模效應,由此導致投入產出率下降。在一定的情形下,非省會小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相對較高,而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fā)展,非省會大中城市的資金、技術和人才短板逐漸補齊,大幅增加要素投入后的規(guī)模效應開始顯現(xiàn),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得到明顯提升。
基于ML指數(shù)的動態(tài)測度:構建非期望產出的超效率SBM模型,運用MaxDEA8.0 軟件計算281 個地級以上城市2009—2014 年和2015—2019 年的ML指數(shù)。結果顯示,2009—2014 年,219 個非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得到明顯改善,約占非省會城市總數(shù)的85.9%,技術效率、技術進步分別對63.1%和87.1%的非省會城市的發(fā)展效率有促進作用,技術效率與技術進步的同時改善對52.1%的非省會城市的發(fā)展效率有促進作用。2015—2019 年,9 個非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得到改善,僅占非省會城市總數(shù)的3.5%,技術效率、技術進步分別對52.9%和2.0%的非省會城市的發(fā)展效率有促進作用。
從26 個省會城市的測度結果來看(表4),2009—2014 年,除太原、合肥等8 個省會城市外,其他城市的發(fā)展效率均得到了明顯改善,特別是南京、武漢、廣州等10 個城市的改善尤為明顯(ML指數(shù)大于1.5)。13 個省會城市的技術效率EC 得到改善,23 個省會城市的技術進步TC 得到改善。2015—2019年,僅有南京和哈爾濱的ML 指數(shù)大于1,且都是因為技術效率EC改善所致。15 個城市的技術效率EC大于1,僅有貴陽的技術進步TC大于1。由此可知,與255 個非省會城市的ML 指數(shù)變動趨勢相似,26 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在2009—2014 年的改善速度明顯快于2015—2019 年,且發(fā)生了從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同時并存的“雙因素驅動”到僅存技術效率的“單因素驅動”演變。

表4 26 個省會城市的ML指數(shù)及其分解結果的取值范圍
2.2 綠色發(fā)展效率的空間分析
空間自相關分析:以26 個省會城市所在省份是否相鄰為依據(jù),構建0—1 型地理鄰接矩陣(海南與廣東間的對應元素設為1),分別計算26 個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的全局莫蘭指數(shù)。結果顯示,2014年全局莫蘭指數(shù)為0.067,對應P 值為0.379,未通過顯著性檢驗,而2009 年和2019 年的全局莫蘭指數(shù)分別為0.172 和0.169,對應P 值分別為0.082 和0.085,均通過了10%的顯著性水平,說明2009 年和2019年26 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呈現(xiàn)弱正自相關性,存在“高—高”或者“低—低”的集聚效應。
從局部莫蘭指數(shù)的測度結果看(表5),2009 年太原、南京、福州、南昌、廣州和海口6 個城市的測度值均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福州、廣州、海口和南昌4 個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存在“高—高”集聚效應,太原存在“低—低”集聚效應,南京存在“低—高”集聚效應。2019 年太原、鄭州、海口、石家莊和烏魯木齊5 個城市的測度值通過5%的顯著性檢驗,廣州的測度值通過10%的顯著性檢驗。局部莫蘭指數(shù)值顯示,海口、廣州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存在“高—高”集聚效應,石家莊、鄭州和太原存在“低—低”集聚效應,烏魯木齊存在“低—高”集聚效應。由此可知,廣州和海口所在省份的綠色發(fā)展對周邊省份具有明顯的正向溢出效應,太原所在省份的綠色發(fā)展對周邊省份具有明顯的負向溢出效應,而烏魯木齊的效率水平與相鄰省會蘭州、西寧的效率水平之間存在明顯的空間極化現(xiàn)象。總體來說,2019 年26 個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的空間分布與2009 年較為相似,說明我國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的空間分布具有一定的時空慣性與路徑依賴性。

表5 部分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的局部莫蘭指數(shù)值
城市規(guī)模分布趨勢與綠色發(fā)展效率:運用規(guī)模位次法測度各地區(qū)的城市規(guī)模分布指數(shù),其數(shù)學表達式為:lnRK =a-blnPR。其中,RK為各城市的年末總人口,PR 為各城市的人口排序位次,a、b 分別為常數(shù)項和規(guī)模分布指數(shù)。當b >1 時,表明城市規(guī)模分布較集中;當b =1 時,表明城市規(guī)模分布符合Zipf規(guī)則;當b <1 時,表明城市規(guī)模分布較分散。將各地區(qū)的城市規(guī)模與排序位次進行回歸分析,結果見表6。從表6 可見,4 大地區(qū)的規(guī)模分布指數(shù)b均小于1,說明我國4 大區(qū)域的城市分布均較為分散;各年度4 大地區(qū)的規(guī)模分布指數(shù)b 大小排序為“東北>西部>東部>中部”,說明我國四大地區(qū)城市分布的集中程度為東北最高、中部最低,總體呈現(xiàn)“東北>西部>東部>中部”的格局特征。

表6 四大地區(qū)城市規(guī)模分布的回歸結果
結合表2 與表6 的數(shù)據(jù)可知,東北地區(qū)的城市 布局趨于集中,城市建設趨向單中心發(fā)展,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均呈“先升后降”趨勢;西部地區(qū)的城市布局發(fā)生了“先分散后集中”的演變,但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均得到了提升;中部地區(qū)的城市布局趨于集中,城市建設趨向單中心發(fā)展,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得到了明顯提升,而省會城市則呈“先降后升”趨勢;東部地區(qū)的城市布局趨于分散,城市建設趨向多中心發(fā)展,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的平均發(fā)展效率分別呈現(xiàn)了“先降后升”和“先升后降”趨勢。由此說明,區(qū)域城市布局的單中心、集中化發(fā)展對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影響具有明顯的異質性,即城市布局的單中心、集中化發(fā)展對不同地區(qū)和不同類型的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會產生不同的影響。
2.3 強省會能力與綠色發(fā)展效率的關系
當前,我國很多省份實施了“強省會”戰(zhàn)略,由此進一步研究強省會能力與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的關系。構建除西寧外的25 個城市的強省會能力指數(shù)及其指標體系,包括用各個省會城市的年末總人口和GDP衡量絕對強省會能力。采用各個省會城市的人口首位度(省會城市人口除以第二大城市人口或首位城市人口除以該省會人口)、GDP 首位度(內涵同人口首位度)、平均人口倍數(shù)(省會人口除以該省地級以上城市平均人口)和平均GDP 倍數(shù)(內涵同平均人口倍數(shù))衡量相對強省會能力,用上述6 個指標衡量綜合強省會能力。運用TOPSIS 方法測度上述3 種強省會能力指數(shù),并進行排序,結果見圖2。從圖2 可見,2019 年絕對強省會城市主要有廣州、成都、武漢、南京、杭州;絕對弱省會城市主要有銀川、呼和浩特、海口、蘭州和烏魯木齊;相對強省會城市主要有成都、武漢、西安、哈爾濱和長春;相對弱省會城市主要有貴陽、呼和浩特、福州、石家莊和濟南。綜合能力較強的省會城市主要有成都、武漢、西安、廣州和哈爾濱,綜合能力較弱的省會城市主要有呼和浩特、貴陽、福州、海口和石家莊。分別計算各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排序與絕對能力排序、相對能力排序、綜合能力排序的相關系數(shù),結果分別為0.453(P值=0.023)、0.298(P 值=0.147)、0.446(P值=0.025)。由此可知,絕對強省會能力與省會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變動關系,即絕對發(fā)展能力強的省會城市通常情況下?lián)碛懈叩木G色發(fā)展效率,而絕對發(fā)展能力弱的省會城市通常情況下?lián)碛休^低的綠色發(fā)展效率。綜合強省會能力與省會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也存在明顯的正相關關系,但顯著性不及絕對強省會能力。盡管相對強省會能力與省會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也存在正向變動關系,但變動并不顯著。

圖2 2019 年25 個省會城市的3 種強省會能力指數(shù)排名
3 結論與啟示
3.1 結論
本文選取281 個地級以上城市的截面數(shù)據(jù),使用傳統(tǒng)的Super-SBM模型和TOPSIS 方法等實證分析了2009 年、2014 年、2019 年我國26 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得到以下結論:①我國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呈現(xiàn)明顯的地帶差異性,東部地區(qū)和西部地區(qū)的平均發(fā)展效率明顯高于中部地區(qū)和東北地區(qū)。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南高北低”趨勢明顯,其效率水平與城市規(guī)模之間呈現(xiàn)明顯的同向變動關系,而非省會城市規(guī)模與效率水平之間呈現(xiàn)明顯的“U型”關系。三大污染物的過量排放是中國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損失的主要原因,從業(yè)人員過剩也是一個重要原因。②26 個省會城市綠色發(fā)展效率在2009—2014 年期間的改善速度明顯快于2015—2019年,其促進因素由2009—2014 年的技術進步與技術效率同時并存的“雙因素驅動”轉變?yōu)?015—2019年的技術效率獨存的“單因素驅動”。③我國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呈現(xiàn)弱正自相關性和空間集聚性特征。絕對強省會能力與省會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存在顯著的正向變動關系,而相對強省會能力與省會綠色發(fā)展效率之間并不存在顯著的正向變動關系。④我國4 大區(qū)域的城市分布均較為分散,且分散程度呈現(xiàn)明顯的“東北<西部<東部<中部”的格局特征,區(qū)域城市布局的單中心、集中化發(fā)展對省會城市和非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影響具有明顯的異質性。
3.2 啟示
基于上述結論,得到以下主要啟示:①鑒于省會特大城市的“高投入—高產出—中高污染”模式與非省會小城市的“低投入—低產出—低污染”模式在城市綠色發(fā)展方面表現(xiàn)突出,對于省會或非省會大中城市而言,在既定的中高投入情形下,要想獲得較高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就應努力提高產出水平和降低污染,走“中高投入—中高產出—中低污染”的道路。②對于我國省會城市而言,適當擴大城市規(guī)模,增強絕對強省會能力,有利于提升區(qū)域整體的綠色發(fā)展效率,片面強調GDP首位度或人口首位度并不能顯著提高區(qū)域整體的綠色發(fā)展效率。③我國城市的綠色發(fā)展要重點提升西部省會城市和東北非省會城市的綠色發(fā)展效率,提升過程中不僅要重視降低三大污染物的過量排放,還要注意消除人力資源的大量冗余。④當前許多省份實施了“強省會”戰(zhàn)略,實證結果表明,區(qū)域城市布局的單中心、集中化發(fā)展對區(qū)域整體的綠色發(fā)展效率影響具有明顯的地區(qū)維度與時期維度的異質性。因此,“強省會”戰(zhàn)略的全面實施需要結合具體的省情和城市布局集中化階段進行綜合判斷,不宜搞“一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