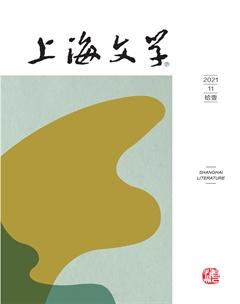有情世界的歌頌者
行超
在整體崇尚現代理性的社會,“情”的意義正在遭遇著消解與危機。個體生活中,我們被教育要時刻保持客觀、理智,切忌“感情用事”;我們更看重那些可以量化的標準與條件,“感情因素”是不穩固的、不值得信賴的。甚至,在本應提供愛與美的烏托邦的文學世界中,思想深度、哲學思辨能力逐漸成為更重要的坐標,“抒情”變得無足輕重,甚至有時竟是膚淺的代名詞。然而,如果文學真的抽空了“情”,它將如何區別于一篇社科論文、一則新聞報道?在那些冰冷的數字與考據之外,它還能提供什么特有的價值?在沒有“情”的文學中,柏拉圖曾贊賞的迷狂般的靈感降臨將不復存在,一切書寫不過是“技藝”的演練。“文學已死”的論調已經是籠罩我們多年的巨大焦慮,也正是在這樣的焦慮下,重新呼喚情感的力量,重提文學的“抒情”更顯得重要而迫切。
20世紀中期,華裔美籍漢學家陳世驤在比較文學的視野中發現,西方文學起源于荷馬史詩、古希臘戲劇,而“中國文學的榮耀并不在史詩;它的光榮在別處,在抒情詩傳統里”(陳世驤《陳世驤文存》,遼寧教育出版社)。這一理論雖然有明顯的盲點與偏頗之處:抒情與史詩不可能全然對立、互斥,在具體的文學作品中,兩者也常有彼此滲透的瞬間。但是,抒情詩作為中國古典文學的最高成就,已是不爭的事實。王國維在點評中國古詩詞時發現,古詩詞中的景物描寫所指向的是主體抒情的需要,所謂“一切景語,皆情語也” (王國維《人間詞話》,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而“敘事的文學,則我國尚在幼稚之時代” (王國維《文學小言》,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十四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從中國古典抒情詩開始,“有情”的傳統對中國文人之影響可謂深入骨髓,從“興、觀、群、怨”到“文以載道”、“感時傷懷”、“托物言志”,及至現當代文學,在“革命壓倒啟蒙”的背景之下,仍有以沈從文、路翎等為代表的書寫,延續著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
沿著這一路徑來考察新時期以后的文學寫作,以及如今的“70后”寫作,我們會發現其中一種隱秘的變化。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在西方現代派文學的影響下,以“50后”、“60后”為創作主體的先鋒文學、新寫實小說等熱潮中,“抒情”遭到了創作者的拒斥。他們或推崇“零度”的寫作姿態,或相信“形式即意義”,他們要反抗的正是此前占據主流的宏大敘事、政治話語,也是中國文學一以貫之的“文以載道”的抒情方式與為文之道。“70后”一代作家,恰恰是在這樣的語境中成長的。1998年,《作家》雜志推出“1970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說專號”,這次亮相被認為是“70后”作家集體“出道”的標志。如今,二十多年過去,商業化、市場化的浮光掠影逐一褪去,“70后”一代真正的文學品質逐漸顯現出來。經歷了時間的淘洗,他們筆下的文學世界也呈現出相對穩定的價值取向、情感結構與美學特點。如今我們看到,“70后”的寫作首先延續了新時期文學對宏大敘事的疏離與解構,以及市場經濟以來“躲避崇高”的審美取向。與此同時,不同于他們的前輩,“70后”的寫作大膽張揚個人情感,個體化的寫作視野、瑣碎的日常細節、幽微的情感深淵,以及消弭了時代背景、道德評判以及意識形態意義的生活本身,始終是最被這代人珍視的部分。在這個意義上,“70后”的寫作,很大地承繼了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但另一方面,在新的時代背景和西方文學思潮的影響下,他們的抒情方式又呈現出諸多變化。
個人與日常的復歸
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文學敘事推崇的是與家國敘事相關聯的“大我”,個體化的“小我”則是被拒絕、被貶斥的。一旦涉及個人情感、夫妻關系、家庭生活,都需要被放置在宏大話語的邏輯之下,方可得到呈現。新時期以來,在“向內轉”等美學觀念的影響下,文學敘事也發生著轉變,人們重新發現了個體情感、日常生活的美學價值與現實意義,而“70后”的寫作正是這一轉變的典型表現。
如同魏微在中篇小說《大老鄭的女人》中寫到的,“似乎在睡夢之中,還能隱隱聽到,我父親在和大老鄭聊些時政方面的事,關于經濟體制改革,政企分開,江蘇的鄉鎮企業,浙江的個體經營……那還了得!——只聽我父親嘆道,時代已發展到什么程度了!我們兩家人,坐在那四方的天底下,關起院門來其實是一個完整的小世界。不管談的是什么,這世界還是那樣的單純,潔凈,古老……使我后來相信,我們其實是生活在一場遙遠的夢里面,而這夢,竟是那樣的美好。”(魏微《大老鄭的女人》,《人民文學》2003.4)如今看來,這段描寫仿佛是對這代人寫作的某種隱喻。對于“70后”作家來說,“時代發展到什么程度”似乎并不是他們最為關注的對象,那只是一個“隱隱”的背景,他們更傾向于構建一個與世隔絕的、“完整的小世界”,這個夢境般的存在“單純,潔凈,美好”,更承載著這代人的審美與價值。
在《現代“抒情傳統”四論》中,王德威曾指出了中國的“抒情”與西方之區別,“誠如學者阿拉克所指出,西方定義下的‘抒情與極端個人主義掛鉤,其實是晚近的、浪漫主義表征的一端而已。而將問題放回中國文學傳統的語境,我們更可理解‘抒情一義來源既廣,而且和史傳的關系相衍相生”(王德威《現代“抒情傳統”四論》,臺灣大學出版中心)。也就是說,西方文學傳統中的抒情,更多與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相關聯,而中國文學中的抒情則通常與社會現實、國家民族話題等息息相關,即便是個人情懷的主觀抒發,也常是作為公共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得以呈現的。上世紀80年代洞開的國門,讓西方文化、藝術思潮急速涌入中國,“70后”作家成長于這一時期,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其寫作初期都深刻地受到西方現代派等的影響。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70后”筆下的抒情與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抒情傳統”呈現出根本的區別,他們的“抒情”并不僅為“言志”或“載道”,更受到西方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的影響,他們對于日常生活、世俗經驗的描摹,對于個體情感的反復咀嚼等,都是基于這一根本立場而產生的。事實上,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文學界對于“70后”寫作“眼界狹窄”、“格局狹小”的批評,也恰恰來源于此。
對于個體生活的日常性的重視,是西方人文主義的基本起點。在中國古典文學中,《詩經·國風》、明清世情小說等,也都是來源于日常生活的生動書寫。日常生活中蘊藏著最漫長、最綿延不息的生命能量,因而,這類寫作得以穿越時空、跨越地域,長久地規約著人類最普遍的情感。“70后”的寫作一方面接續著中國古典文學中的日常書寫,另一方面又與近代中國的“宏大敘事”傳統相區別,顯示出重要的轉折意義。在“70后”筆下,政治、歷史、現實、未來……所有的宏大主題都需要通過個體的人、細碎的生活而進行呈現與傳遞,唯其如此,那些遙遠而宏大的話題方可獲得價值。
張楚的中篇小說《中年婦女戀愛史》(《收獲》2018.2)圍繞女主人公茉莉失敗的戀愛經歷而展開,將故事從1992年講到了2013年。在每章的最末,張楚以“大事記”的形式記錄了這一年真實發生的重要歷史事件,以及關于外太空的零星幻想。這種形式的并立仿佛告訴我們,那些歷史書寫中舉足輕重的“大事”,在個體生命中都不過是一個模糊的背景,而那些看似瑣碎平凡卻真實發生在我們身邊的“小事”,才具有真正崇高的史詩性。也正是因為這樣的立場,張楚以及他所代表的“70后”寫作,他們拋棄了對筆下人物的是非評價、道德判斷,而是深刻感知著每個人的具體處境以及他們各自的悲哀、無奈,對他們來說,萬物皆可含情,萬事皆應被稱頌。
與此同時,同樣是面對“一地雞毛”般的日常生活,“70后”與他們的前輩——新寫實小說作家——也存在根本的不同:新寫實小說的基本訴求是寫出生活的本相與“真實”,他們在寫作中的情感態度是“零度”的,他們的價值觀是“冷也好熱也好活著就好”。而“70后”則試圖在深入描摹生活細節的同時,發現并闡釋其間所蘊含的審美價值、情感力量,換言之,個體的抒情是其描摹日常的旨歸與貫穿始終的訴求。在喬葉的小說《最慢的是活著》中,祖母從小不喜歡“我”,“我”曾因此“記仇”,卻拗不過時光的磨洗、血緣的糾葛,直到走過漫長的生命才終于發現,“我的新貌,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她的陳顏。我必須在她的根里成長,她必須在我的身體里復現,如同我和我的孩子,我的孩子和我孩子的孩子,所有人的孩子和所有人孩子的孩子。活著這件原本最快的事,也因此,變成了最慢。生命將因此而更加簡約,博大,豐美,深邃和慈悲。”(喬葉《最慢的是活著》,《收獲》2008.3)日常生活本身是冗長而瑣碎的,甚至常常包含著惡與恨,就像小說中的“我”與祖母之間長達數十年的情感恩怨、愛恨糾纏一樣,日復一日又滿目瘡痍。但另一方面,這些所有的恩怨與糾纏,恰恰都是來自于“情”,日常生活之所以綿延不斷,除了一成不變的時光的流淌,還有更重要的,就是“情”的生發、起伏、沖突與和解。如同這部小說所展示的,在有情的世界中,日常生活的價值得以被發現、被賦予,個體生命也因此得以延續。在“70后”的寫作中,日常敘事最重要的價值,恰恰也是對其中所蘊含的豐沛的人情與人性的發掘。這種來源于日常的美學與詩意,是“70后”文學書寫的基本底色。
古典美學的傳承與再造
在《天真的詩與感傷的詩》中,席勒曾耐心辨析了兩種寫作方式,由此也延伸出兩種不同的人生觀。在他看來,“天真派”寫作的方式是“模仿現實”,他們的最高成就是“成為自然”;而“感傷派”則注重描繪理想,希圖尋覓已經失去的自然。席勒所說的兩種寫作方式之間的區別,正是古典美學與現代美學的重要分野。在中國,從深信“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的老莊思想,到“以和為美”的禮義規范,“天人合一”、“物我兩忘”式的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始終是中國古典美學的核心追求。同樣是抒情,古典美學傾向于將其對象道德化,一片葉子、一只小鳥、一間陋屋,它們本身并不具有美學意義,通過賦予其道德的力量——它們自然而然、默默生長,它們用最簡單的力量實現了永恒——古典主義者完成了審美與抒情。而現代主義的抒情對象,則常常指向孤獨、生死,以及靈魂與精神等形而上的問題。在這個意義上,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道德,代表了中國古典美學的精神要義。而對于這一傳統道德的表達與書寫,也成為中國文學中抒情的重要表現形式。
在現代化高速發展的當下,中國古典文化中的平和、安靜、詩意,及其背后所蘊含的“真善美”的倫理價值,逐漸成為對抗庸常化、世俗化、碎片化的精神象征,撫慰著生活在浮躁與喧囂中的人們。東君的短篇小說《聽洪素手彈琴》(《江南》2013.2),寫出了古典詩意在現代都市生活中的落寞與困境,小說中的洪素手仿佛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一個是作為打字員的現實世界,另一個是與古琴相伴的精神世界。小說有著明顯的古典氣韻,古琴以及以此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化,既是掙扎在現實泥淖中的“洪素手們”的精神寄托,更傳遞出作者的價值取向與美學追求。以東君為代表的一批“70后”作家,正是這樣在寫作中將古典美學與傳統美德融為一爐,共同構建起作者的抒情世界。
在談及長篇小說《北鳶》的故事為何定格在1947年時,作者葛亮說:“從我的角度來說,這也是一種美感的考慮。因為以我這樣一種小說的筆法,我會覺得在我外公和外婆匯集的一剎那,是他們人生中最美的那一刻。到最后他們經歷了很多苦痛,中間有那么多的相濡以沫,但是時代不美了。”(武靖雅《葛亮:民國最吸引人的地方在于不拘一格的》,界面新聞,2016年10月11日)葛亮偏愛“美”的事物,《北鳶》充分顯示了他的美學,這種“美”首先體現在作家的語言上,小說用一種雅正、沖淡、極富古典意蘊的語言,與中國文學傳統相呼應,在當下文學寫作中顯得殊為獨特珍貴。小說聚焦民國時期的“大歷史”,如他所說,“這就是大時代,總有一方可容納華美而落拓的碎裂。現時的人,總應該感恩,對這包容,對這包容中鏗鏘之后的默然。”(葛亮《北鳶·自序》,人民文學出版社)葛亮無意于敘述那個時代流血的戰爭、政黨的傾軋,他所注目的是其中浮萍般的個體,那些身處時事漩渦卻依然有所堅守的人們。究其根本,前者充滿了暴力與沖突,這些在葛亮看來大抵是“不美”的;后者則飽含著妥協與平衡——而這,恰恰是他所推崇的古典美學的核心。小說書寫了亂世中的人們是如何艱難地傳承著舊時代風骨、大家族禮儀,他們所堅守的傳統文化,尤其是其中的禮義道德,正是最令葛亮傾心之處,他們的溫和、敦厚、謙遜有禮、翩翩風度,都承載并傳遞著作者的審美偏好與追求。
有趣的是,雖然葛亮在小說中反復頌揚傳統美德,但他更推崇與重視的其實是個體及其“私德”,而非與宏大敘事相糾纏的“公德”。在《北鳶》中,“國仇”被一一轉化為“家恨”,所謂的大歷史,只有與個體命運發生糾纏時,才真正得以鐫刻進尋常人的生命。小說中,仁玨投身革命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源于對范逸美的特殊感情;名伶言秋凰的抗日義舉,實則是為了替自己的女兒仁玨復仇。相對于“史詩傳統”下的歷史敘述,以葛亮為代表的“70后”作家更關注其中的個體命運及其情感世界。歷史本身成為作家借以自我抒情的載體與對象,書寫歷史并不僅是為了“抵達某種真實”,更重要的是重新發現其中的每一個個體,進而找到這條浩蕩長河中“我”的位置。《北鳶》的扉頁上寫著,“謹以此書獻給我的祖父葛康俞教授”,在歷史與家族史的視野中,這樣的寫作無疑是一場重要的文字儀式,而對于作家個體來說,這更是對自我身份的探尋與厘清。
在評點《紅樓夢》的美學價值時,王國維曾將“美”分為兩種:“一曰優美,二曰壯美”,前者令“吾心之寧靜”,后者則使“意志為之破裂”(王國維《紅樓夢評論》,見謝維揚、房鑫亮主編《王國維全集·第一卷》,浙江教育出版社)。如果說葛亮的寫作體現了“70后”作家對于“優美”的追求,那么,李修文似乎更鐘情于令人震顫的“壯美”。從《山河袈裟》到《致江東父老》,抒情于李修文而言并不只是修辭方式,更是他的寫作路徑與美學。李修文偏愛那些濃烈的、磅礴的,甚至宏大得讓多數人望而卻步的詞語,比如“人民”。“是的,人民,我一邊寫作,一邊在尋找和贊美這個久違的詞。就是這個詞,讓我重新做人,長出了新的筋骨和關節。”“剎那之間,我便感慨莫名,只得再一次感激寫作,感激寫作必將貫穿我的一生,只因為,眼前的稻浪,還有稻浪里的勞苦,正是我想要在余生里繼續膜拜的兩座神祇:人民與美。”(李修文《山河袈裟·自序》,湖南文藝出版社)在曾經的中國文學作品中,“人民”有時是革命話語中剝離了真實肉身的符號,有時是知識分子眼中被給予厚望的啟蒙者、救贖者,有時又是作為崇高與光明對立面的“底層”“小人物”,他們不斷地被書寫、被代表,卻始終是沉默而尷尬的“他者”。李修文的寫作重新定義了“人民”這個在不同歷史語境中被不斷賦予復雜意義的詞匯,他與盲人一同行夜路(《三過榆林》)、與身患絕癥的姑娘一起“偷青”(《恨月亮》)、為塵肺病人和他生病的女兒摘過蘋果花(《長夜花事》)……經由這些活生生的日子,李修文剝去了那些加諸于“人民”身上的想像,將他們重新還原為樸素而至善的、具有巨大勢能的個體生命——他們更像是《國風》中的勞動者、或是他所鐘愛的杜甫筆下的“天下寒士”,他們困頓而堅韌,籍籍無名卻又生生不息。
這些平凡的生命、困頓的生活為什么值得歌頌?僅僅審美是斷然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他們身上所攜帶的道德與生命的力量——正像是永恒不變的大自然帶給我們的啟示,“我們愛的不是這些東西本身,而是它們所代表的一種思想。我們愛它們身上的那種靜靜地進行創造的生命,它們主動的、默默無聞的工作,它們依自身規律而存在,內在的必然性,永恒的自我統一。它們的現在就是我們的過去;它們現在是什么樣子,我們將來也該重新變成什么樣子”(【德】席勒著《席勒文集VI,理論卷》,張佳鈺、張玉書、孫鳳城譯,人民文學出版社)。于是,在這些平凡的“人民”身上,李修文重新發現了那古老而美好的情感,那曾經被歌頌又被遺忘的“真善美”。進而,作者重新發現了作為“人民”之一的自己,“我曾經以為我不是他們,但實際上,我從來就是他們” (李修文《山河袈裟·自序》,湖南文藝出版社)。為了“配得上”他們,作家改造了自己的語言,改造了此前作為小說家的“虛構”的抒情方式,在與之相匹配的,更接近古典美學的詩詞、民間戲曲等藝術形式中找到共鳴,開始重新寫作,甚至可以說是重新生活。話語方式與情感方式一經打通,所有的磅礴與濃烈也都顯得理所應當。由是,李修文與他筆下的“人民”結成了同盟,構筑起牢靠的情感共同體。也正是因此,他的寫作重新海闊天空。
反抒情時代的抒情
作為一種與古典美學、古典精神高度適應的表達形式,抒情在中國傳統的文學書寫中具有重要的地位,所謂“興觀群怨”,其背后均指向了抒情。然而,隨著小說觀念的變化,尤其是在現代性的視野中,我們開始強調寫作的“零度”、作家的退隱,甚至對一切價值與意義進行著樂此不疲的反諷與消解。抒情的寫作,也在這一觀念的影響下遭到了冷遇。然而,情感及其表達的欲望,如同人性本身一樣,是亙古不變、不容否定的。如同李澤厚所說,中國文化之核心是“情本體”,以家國情、親情、友情、愛情等各種“情”作為人生的最終實在和根本(李澤厚《實用理性與樂感文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那么,我們有必要追問,在如今這樣“反抒情”的時代中,“抒情”是否還有可能?或者說,我們的“情”將歸于何處?
在石一楓的寫作中,我發現了這種可能。中篇小說《世間已無陳金芳》塑造了屬于我們這個時代的“典型人物”,農村女孩陳金芳跟著在部隊食堂打工的姐姐、姐夫來到北京,從被侮辱、被擠兌的外地人,一步步變身為高貴優雅的文化商人陳予倩。然而這一切不過是美麗卻虛幻的泡沫,小說最后,陳金芳涉嫌詐騙,被警察帶走。通過呈現陳金芳的奮斗及其失敗過程,小說折射出現代都市中每個人的欲望、不甘與幻滅,“等我醒過神來,眼前已經空無一人。我的靈魂仿佛出竅,越升越高,透過重重霧靄俯瞰著我出生、長大、常年混跡的城市。這座城里,我看到無數豪杰歸于落寞,也看到無數作女變成怨婦。我看到美夢驚醒,也看到青春老去。人們煥發出來的能量無窮無盡,在半空中盤旋,合奏成周而復始的樂章”(石一楓《世間已無陳金芳》,十月文藝出版社)。小說末尾的這段話,仿佛菲茨杰拉德面對著他筆下死去的蓋茨比,還有他所代表的美夢的破碎。蓋茨比的人生充斥著物質和金錢,這備受批判的現代性的產物看似是情感的反面和終結者,但是,誰又能否認《了不起的蓋茨比》所包含的深刻的浪漫與抒情?在這個意義上,菲茨杰拉德用金錢完成了抒情,也讓現代復歸了古典。同樣地,石一楓試圖讓他筆下的人物通過個體奮斗來對抗、改寫自己的命運,這一對抗的最終落敗,不僅是主人公的人生悲劇,更是每一個個體在面對龐大、堅硬卻又仿佛無物之陣般的現實時的無力與渺小——這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最殘酷的抒情。
在石一楓的另一部小說《心靈外史》中,主人公“大姨媽”曾相信革命,后來又信氣功、信傳銷,最后信了基督,種種信仰非但沒有給她帶來幸福,更最終令她家破人亡。石一楓對這個人物的偏愛,就像是小說中楊麥對大姨媽的依戀一樣,究其根本,這種偏愛與依戀正是源于,在如今這個嘲笑與懲罰所有單純的信仰,在這個人與人之間時時保持警惕的現實世界里,大姨媽看似盲目卻又如此堅定的“相信”。她一次次地受騙,一次次地被生活出賣,卻從來沒有改變過對“信”本身的信仰,“真的假的好像又都并不重要,不能妨礙我讓自己去相信他們” (石一楓《心靈外史》,十月文藝出版社)。大姨媽之死,不僅是一個樸素向善者的人生終結,更是當代生活中理想主義者的悲歌。不管是陳金芳還是大姨媽,盡管她們身上都帶有一定的荒誕感與反諷性,但作者并不是簡單地批判、諷刺這些人物本身,他所批判的是讓他們之所以如此的無形力量,甚至是在他們之外,那些被視為正常與理所當然的人生。
不少人曾指出石一楓的小說與王朔的小說之間的某種聯系,兩位北京作家在語言風格等方面確有相似之處。但是在我看來,兩者的區別卻是本質的:王朔的小說戲謔一切,而石一楓對他筆下的人物卻潛藏著悲憫。面對眼前并不令人滿意的現實以及身處其間的各式小人物,王朔選擇了消解與諷刺,他始終是一個不愿與之為伍的、冷眼旁觀的嘲笑者。但石一楓的反諷背后,始終有一個理想主義的現實與人生作為參考,與王朔的反諷相比,他更懷有一種嚴肅而感傷的情感——這種情感,我們在啟蒙主義、在現實主義與批判現實主義作家筆下常常看到。在這個意義上,正是通過反諷的手法,石一楓重新創造了他的抒情。
如同石一楓的寫作所顯示的,在今天,傳統的抒情面臨著被挑戰、被消解的命運,抒情的方式必須作出改變。如果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古典時代幾乎天生就是抒情的載體,那么,到了充滿未知、震驚以及難以預測的現代,甚至到我們此刻仍未可知的未來,抒情還會存在嗎?
這也是李宏偉在小說《國王與抒情詩》中思考的問題。小說架構于并不遙遠的2050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宇文往戶在頒獎前夕離奇自殺,他的生前好友黎普雷選擇從他的文字和生活痕跡中探索答案。由此,一個致力于建設“意識共同體”的帝國漸次浮現。小說探討了時間、存在、語言等抽象話題,但最讓我感興趣的,是其中對于“抒情詩”的情有獨鐘。在小說中,抒情語言是帝國與國王致力消除的異己,是他們實現同一性夢想之路上的絆腳石,但是,“抒情氣質”卻反過來成為國王死后選擇繼承人時最看重的品質。小說中,國王主張取消文字的抒情性、文學性,讓語言變得干澀、同一,最終局限于功能化,以圖消弭異質性的個體,實現人類無差別的永生。在這里,如果我們運用李宏偉所擅長的辯證就不難得出,在他看來,語言是人類存在的證據,而“抒情”則是個體的人之所以成為自己的根本。
如同所有具有科幻外殼的小說一樣,《國王與抒情詩》無疑是面向未來卻基于當下的寫作。李宏偉此刻面對的是一個抒情話語,或者干脆說文學話語式微的時代,在這樣的語境之下,他坦然接受了文學在未來時空中的命運。然而另一方面,作為一個作家、一個詩人,李宏偉始終懷抱著西西弗斯般的篤定和堅忍,他對文學的意義深信不疑。小說最后,抒情詩人黎普雷接管帝國,以此殘留了扭轉人類命運的最后一線希望。可以說,李宏偉是用寫作實踐著小說中關于抒情的定義:“個人也好,整體人類也罷,意識到結局的存在而不恐懼不退縮,不回避任何的可能性,洞察在那之后的糟糕局面,卻絲毫不減損對在那之前的豐富性嘗試,不管是洞察還是嘗試,都誠懇以待,絕不假想觀眾,肆意表演,更不以僥幸心里,懈怠憊墮。這種對待世界,對待自己的方式,不就是抒情嗎?”(李宏偉《國王與抒情詩》,中信出版社)至此,我們驚訝地發現,在這部書寫未來與未知的科幻作品中,對于古老的“抒情”,作家竟懷有如此古典的、赤誠的熱愛。
近一個世紀前,在現代派崛起之時,瓦爾特·本雅明在法國詩人波德萊爾的筆下發現了一種曖昧的現代性:他們一方面對現代都市的冷漠、惡行進行著鞭撻,另一方面又被其中的新鮮、未知以及由此而來的“驚顫體驗”所吸引——本雅明稱波德萊爾是“發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彼時,資本主義社會正處于蒸蒸日上的上升期,現代性的趨勢更是難以阻擋,不管是波德萊爾還是本雅明,都無法叫停歷史的前行。在這種矛盾中,本雅明選擇了自殺。小說《國王與抒情詩》中,黎普雷一度以為,宇文往戶的死也是類似這樣的抵抗,他以為宇文往戶是因為發現了帝國對自己的掌控,希望以自殺來了結并擺脫國王的控制。但事實上,宇文往戶與國王早已成為同盟,他的死更是為了讓帝國找到更合適的繼承人,在成全國王夢想的同時,讓自己的生命完成最后一次“抒情”。宇文往戶的時代,比本雅明的時代又進了一步;或者說,今天作家所面對的文學處境,比本雅明的時代更狹窄、更逼仄。在今天,詩人之死甚至不再具有隱喻的意義,它不過是時代車輪滾滾而過時無意浮起的一粒灰塵。
但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中,宇文往戶的死才更能喚醒人們對于語言、對于抒情本身的再次關注;也正是在這樣的現實中,“70后”作家對于“抒情”的堅守才顯得尤其可貴。在如今這樣“反抒情”的年代,他們依然懷抱著對“情”的信仰,并以不同的方式延續著人類古老的美好。如果說石一楓的寫作是以反諷的方式完成了一種悲劇的抒情,那么,李宏偉的小說則回歸了“元抒情”,他以堅定而樂觀的態度,重新肯定了抒情的本體性意義。也正是在這樣的寫作中,我們幾乎可以重新相信那個不斷被質疑的、如今想來卻如此令人欣慰的斷言:文學永不消亡,抒情正是拯救現實的力量。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