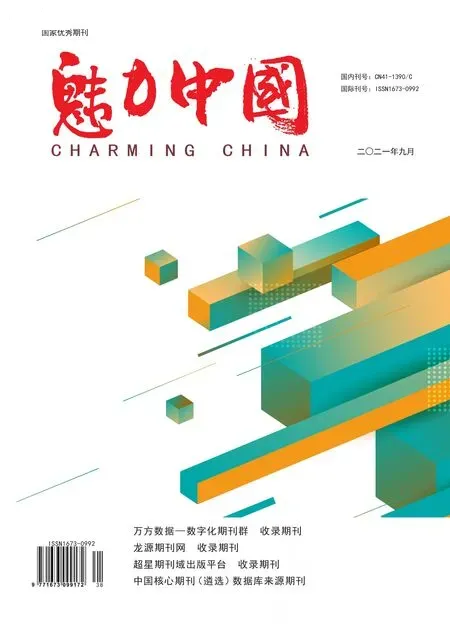陶元慶書籍封面設計互文性研究
邱紫荊 張馥玫
(北京印刷學院,北京 102600)
二十世紀初的中國涌現了一群書籍設計家,創作了許多新文藝書籍藝術作品,從而催生了書籍封面的創作,而陶元慶正身處中西方思潮兼容并蓄的背景下,設計出了富含民族性、不失時代性又兼具其個性藝術語言的書籍封面設計作品。考察陶元慶的現存書籍封面設計作品,通過其設計的封面和對應的書籍文本內容來探討陶元慶封面設計的圖像與文本內容的互文關系,了解陶元慶書籍設計思想,從而為今后的更多相關藝術創作研究提供理論指導和更多可能的發展途徑。
一、互文性理論與書籍封面
“互文性”是文學研究領域的專有詞匯,又被譯作“文本間性”,一般指不同文本之間的相互關系。最早是由法國符號學家茱莉婭·克利斯蒂娃于20 世紀60 年代中期在《如是》(Tel Quel)雜志上發表的兩篇論文中提出這一概念,在汲取了結構主義的優點之上,更注重文本本身的斷裂性和不確定性。進一步而言,互文關系包含了對于特定意識形態即文學傳統的繼承和回憶,以及對于文本作為素材所進行的改變與轉換方式。后來由法國文學評論家羅蘭·巴特提出“任何文本都是互文本”。①
互文性概念的產生反映出了各種文本間的相互轉換關系,即在任何本文當中能或多或少能看到其他文本的影子。在書籍設計當中也有所體現,書籍封面作為文章最重要、最直觀的視覺表征,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文本的大體內容或想要向讀者所傳達的關鍵信息,這種圖像與文本之間的互文性可以更好地突出作者想要傳達給讀者的文章中心思想。書籍封面的互文性即封面設計(包括文字和圖像以及封面三要素的整體設計)中與文章文本內容具有不可割裂、相互滲透的互文關系。
二、陶元慶封面設計的多元化風格
20 世紀上半葉的中國社會正處于思想空前解放、中西方文化交融的多元文化背景之中,伴隨著現代書籍裝幀設計的興起涌現了一批最早的書籍設計家,其中就有陶元慶。陶元慶是我國現代書籍封面設計的拓荒者,開創了新文藝書籍以圖案畫形式作為封面先河,在我國的書籍裝幀史上具有重要意義,陶元慶被譽為書籍封面設計“第一人”。
在當時如此新舊思想更迭的復雜環境下,1924 年陶元慶開始為魯迅的書籍作品進行封面設計。著名裝幀藝術家邱陵評價陶元慶的封面創作:“他在裝幀藝術中的成就是前無古人的,在魯迅先生的引導下是具有創作上、藝術上和設計上的獨創性的。”②陶元慶的設計并不是一味的中國民族傳統風格的傳承,也不是一味學習西方的“拿來主義”風格,而是將傳統性和現代性交融甚好的同時也表達自己的獨到文藝思想,博采眾長,獨具一格,在一眾書籍封面作品中脫穎而出。
將陶元慶的書籍封面設計藝術特色總結為三個方面:
(一)多元化藝術表現手法
陶元慶的書籍封面設計從《苦悶的象征》、《白露》運用的是夸張寫意的手法來表達藝術風格,至《墳》、《朝花夕拾》等封面設計作品中則采用物像抽象化處理的藝術風格,《蝴蝶》在繼承這種寫意筆墨的基礎之上運用線技法,更加追求流線型的表現手法,以及《彷徨》、《唐宋傳奇集》等封面設計作品中還采用了木刻版畫的手法來創作;
(二)兼具民族感與時代感
陶元慶學油畫出身,書籍封面深受其繪畫作品影響,同樣注重中國民族傳統與西方藝術形式的結合運用;
(三)兼具形與色
魯迅評價陶元慶的書籍設計作品:“他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③陶元慶在設計封面之前會先閱讀全書,充分了解書籍的內容立意,從而進行高度提煉和概括、通過形象化的手法來進行封面設計,最終達到封面設計與文本寓意的完美融合,以此達到圖案的準確性即深刻的寓意內涵。
其實陶元慶的書籍封面設計不受限于任何某種風格,他將中西方的藝術巧妙相融,形式和內容具有強烈的現代氣息的同時也不失中國文化的特有民族性格調,正如魯迅所評價的:“和世界的時代潮流合拍的,而由并未梏亡我國的民族性”。④“為了達到內容和設計形式的統一,設計者必須對原著的內涵有深刻的了解,知曉著作者的文化心態及審美主體的審美標準。通過提煉書籍中的精神內涵,用美的形式使書籍達到最佳的藝術表現力。”⑤陶元慶多元化的個人藝術風格創作的書籍封面設計既具有相對獨立性,背后所體現的又正是與文章文本相呼應的互文關系。
三、陶元慶封面設計的互文性
陶元慶現存的相關書籍封面資料并不多,從其與魯迅、許欽文的書信往來和相關書籍等史料記載中可得出:其實《唐宋傳奇集》的封面原本是為《莽原》所作,《一壇酒》是許欽文選用陶元慶的遺作作為封面畫的,《無妻之累》的封面畫也是選用陶元慶的遺作《吹簫人》等。受限于當時的環境影響,這種不論書籍內容選取封面畫并直接套用書籍封面的形式并不少見,反映出了陶元慶的部分書籍封面與文章文本確實是存在一定程度的錯位關系,其所體現出的封面與文本的互文關系并不明顯,所以此文章主要探討的是陶元慶書籍封面與文本的重合關系。⑥
陶元慶一生的書籍封面設計歷程雖短暫卻成就輝煌,從1924 年創作的第一幅封面作品《苦悶的象征》開始直到1929 年逝世,短短四年時間創作書籍封面設計30 余幅,大部分是為魯迅和許欽文的書籍所作。陶元慶與魯迅通過書信形式討論相關書籍裝幀事宜,設計了7幅:《苦悶的象征》、《朝花夕拾》、《彷徨》、《工人綏惠略夫》、《墳》、《出了象牙之塔》和《唐宋傳奇集》。許欽文作為陶元慶的摯友,其著作的裝幀設計幾乎全部都是由陶元慶親自設計,其中包括:《故鄉》、《毛線襪》、《鼻涕阿二》、《幻象的殘象》、《仿佛如此》、《若有其事》、《蝴蝶》和《一壇酒》。陶元慶通過對書籍文本內容的充分理解,以高度形象概括形式來設計封面畫進行闡釋,其設計的封面畫與文本形式、內容、風格等對應性的重合特點使書籍設計整體更加飽滿和完整。⑦
許欽文在《魯迅和陶元慶》一文中提道:“我國印新文藝書籍,以圖案作封面,由魯迅先生譯的《苦悶的象征》開始。”⑧《苦悶的象征》(圖1)是魯迅于1924 年僅用不到20 天翻譯自日本文藝批評家廚川白村的遺作。魯迅與其“異國知音”廚川具有相似的人生哲學,對于批判當時社會上的資本主義、封建制度等落后的思想深感共鳴。陶元慶在這樣一個飽含壓抑的文本中得到啟發,從而設計出充滿夸張寫意風格的封面畫——一個披下長發的半裸女子,腳趾夾著三刺戟,舌頭舔舐著三刺戟的尖頭,雙手別過背后,雙眼緊閉。新穎的團扇形構圖,封面僅用黑紅兩色,傳統古代的殘忍兵器三刺戟與現代化的表達形式相結合,寥寥幾筆線條便勾勒出了該女子的絕望與壓抑,正是文章中人們對資本主義的反抗的具體化體現,通過夸張變形的手法直觀簡潔地表現當時社會的一種復雜壓抑的狀態,表現了所謂的“苦悶的象征”,使封面畫與文本內容呈現出了一種交會互融的對應關系,形象又抽象的封面畫為讀者提供了獨特視野,也隱喻出文章的中心思想,也就是達到書籍中圖文的互文性。⑨
《朝花夕拾》(圖2)和《墳》(圖3)的封面設計從純線條轉而成為幾何因素造型的表現形式,將物像抽象化,利用律動感的線條來表現文本意象。《朝花夕拾》是魯迅1927 年出版的重要散文創作之一,各篇章內容層次分明,描述了一個人從童年、少年到青年的教育成長史,反映中國教育從傳統到現代轉型的一系列變化過程。陶元慶描繪的封面整體色調為暖色,由魯迅題字的字體圓潤,體現出溫暖美好的一種童趣意境,對應文本內容的成長史主題內容。

圖2 《朝花夕拾》封面,陶元慶,設計于1927 年

圖3 《墳》封面,陶元慶,設計于1927 年
《墳》是魯迅1926 年出版的雜文集,運用史筆引據事實來表達了其各種觀點,體現了他不屈不撓于舊勢力抗爭到底的精神。魯迅請求陶元慶為他設計《墳》的封面:“《墳》這是我的雜文集……可否給我制作一個書面?我的意思是只要和‘墳’的意義絕無關系的裝飾就好。”⑩但陶元慶仍堅持自己的創意設計理念,也可看出互文性在書籍封面與文本之間的重要性。陶元慶根據書名“墳”的意象進行設計,描繪了在曠野里兩個三角形的墳墩以及一個棺材頭,整幅畫都利用直線來表現物體,給人以視覺上強烈的荒涼寂靜之意,營造一種壓抑的死亡氛圍,也與雜文中魯迅對當時社會現狀不滿的觀點所反映出來社會一片死寂的現象呼應融合。封面畫與文本內容的完美融合所體現出的統一性是書籍設計中的完整性體現,通過封面圖像來闡釋文本內容,從形式到內容的高度統一,為二者之間的互文性體現。
結語
互文關系之于陶元慶的書籍封面設計是研究陶元慶書籍封面設計相關問題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書籍封面設計作為交叉性研究領域,圖像藝術與文本內容互相交融、互補滲透。陶元慶書籍封面作品以其特有的個人藝術風格成為我國現代裝幀的代表作,其書籍封面圖像具有文章文本的內容與形式,體現出一種互相借鑒、互相依存、相互闡釋的互文關系,在重合互通的同時也具有一定的差異錯位關系。
注釋:
①吳勝男.新文學作品封面的“語-圖”互文研究[D].江蘇師范大學,2014.
②邱陵.邱陵的裝幀藝術:裝幀史論·裝幀設計·寫生作品選[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p107.
③魯迅.《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魯迅全集》第3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
④魯迅.《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我所要說的幾句話》,《魯迅全集》第3 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年版,p573-574.
⑤黃可.陶元慶與新文藝書裝幀[J].讀書,1980,(01),p151-154.
⑥光亞平.草露易晞[D].江西師范大學,2012.
⑦古梅芳.陶元慶的繪畫藝術與裝幀設計研究[D].華南師范大學,2007.
⑧欽文.《魯迅日記》中的我[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79.p84.
⑨劉娟綾.現代書籍封面的興起——論陶元慶對民國書籍封面設計的影響[J].唐山師范學院學報,2019.
⑩《魯迅文集全編》編委會.魯迅文集全編 (全兩冊) [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5.p2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