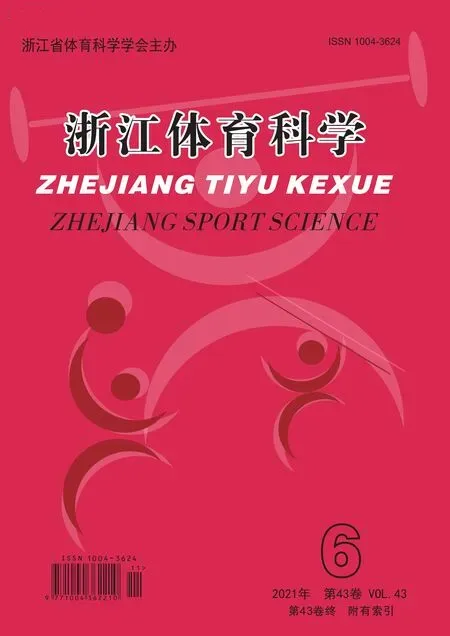體育場館的避災抗疫應急作用探析
應菊英
(浙江經貿職業技術學院,浙江 杭州 310018)
0 前 言
人類社會的發展史就是一部人類與自然災害不懈斗爭的歷史。中國地域遼闊,環境復雜多變,氣候穩定性差,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類型多、頻率高,是世界上自然災害最嚴重的國家之一。據不完全統計,從西漢至今,發生死亡人數過萬的重大自然災害平均不到10年就會遭遇一次,其中以洪災、臺風、瘟疫、旱災、地震、冷害等災害的影響最為嚴重[1]。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70多年來,中華民族經歷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強起來的偉大飛躍,全國各地相繼興建了成千上萬座現代化體育場館。
一些體育場館,在一次次的重大自然災害中,發揮了獨特的避災抗疫應急功能,成為了災疫中托起生命的“諾亞方舟”。如2020年春,武漢新冠肺炎患者數量井噴式增長,大量感染者在發熱門診等待就醫,一部分人等不到床位只能在家自我隔離,最終發展為重癥甚至危重癥,有的還感染了家人。對此,政府及時采取措施,將洪山體育館和武漢體育中心等多家體育場館及會展中心、舊廠房改造為方艙醫院后,增加了上萬張床位,將“人等床”的窘境扭轉為“床等人”的有利形勢,全市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得到極大緩解,患者得到及時救治。再如,在遭遇超強臺風“利奇馬”和汶川特大地震時,浙江和四川災區的體育場館也成為了受災群眾安全的庇護所(表1)。

表1 體育場館在幾起重大自然災害事件中作為應急避災場所的情況概覽[4-10]
在日本和歐美西方國家,體育場館也是避災安置場所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日本在關東大地震和阪神大地震中,體育場館收容的災民數達到二十多萬人[2]。2020年春新冠疫情期間,英國政府將曾承辦2012年倫敦奧運會的Excel國際會展中心、溫布利體育館等改建成方艙醫院,用來收治新冠肺炎患者;巴西科林蒂安足球俱樂部的主場帕卡恩布體育場,也被征用為巴西圣保羅州的方艙醫院[3]。
為了更好地發揮寶貴的體育場館資源的避災除疫應急作用,本文擬分析體育場館的避災應急資源優勢,審視體育場館兼顧避災應急功能設計和管理方面的不足,提出有針對性的對策與建議。
1 體育場館的避災應急資源優勢
作為避災應急場所,體育場館具有覆蓋面廣、容納量大、安全性高、容易改造、通達度好、波及面小等優勢,是得天獨厚的避災應急資源。相比建設專用的避災安置場所,可節省大量的土地空間和建設維護投資。
1.1 覆蓋面廣
據中國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全國共有體育場地169.46萬個,占地面積39.82萬公頃,建筑面積2.59億m2,場地面積19.92億m2。其中,室內體育場地16.91萬個,場地面積0.62億m2;室外體育場地152.55萬個,場地面積19.30億m2[11]。另據報道,截至2018年,中國體育場館數量已達210余萬個。這些體育場館,廣泛覆蓋了全國各地的城市和鄉村,是居民15min至0.5h生活圈內可及性很好的潛在避災資源。如武漢疫情期間改為方艙醫院的洪山體育館、武漢體育中心、武鋼體育中心、武漢全民健身中心、武漢體育館、大花山戶外運動中心、湖北中醫藥大學體育館、武漢市體育運動學校體育館、黃陂一中體育館、石牌嶺高級職業中學體育館、武漢華僑城小學體育館等,分別分布在武漢城的不同片區,為改造方艙醫院就近收治患者提供了便利的設施條件。
1.2 容納量大
一旦災疫爆發,受災群眾為數眾多。基于體育場館的公共活動場所屬性,僅單個場館容納量就少則上千人,多則數萬人,災區所有體育場館的避災人員容納量十分可觀(表1)。如武漢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首批改為方艙醫院的洪山體育館,占地面積4.2公頃,建筑面積2萬m2,可容納觀眾8 000余人,是湖北省及武漢市舉辦各種重大體育賽事、大型文藝演出以及各類展覽展銷等商務活動的主要場所,改造為方艙醫院后,設置了800個床位,于2020年2月5日至3月10日期間累計收治患者1 124人,與其它體育館一起,累計收治患者數量6 000余人,占武漢所有方艙醫院收治患者數量的一半左右。再如綿陽九洲體育館,占地面積2.7公頃,建筑面積2.4萬m2,能容納觀眾6 000人,是綿陽市舉辦一系列大型綜合賽事、演藝、展會和商業慶典等活動的公共場所,2008月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后作為緊急避難所,5月13日至6月29日期間,日均接待災民2萬人次,高峰期日接待量達5.8萬人次[10,12]。
1.3 安全性高
體育場館作為重點防護公共建筑,其選址都經過嚴格的安全性審查,避開地質災害、洪澇災害易發地段。體育建筑多采用鋼結構,塑性形變能力強,抗震性能好,有高度敏感的消防滅火系統,智能化監控系統,而且會定期檢測,對其結構安全性及抗震性能進行評估鑒定,進行維修保養,平時能保證運動員和觀眾的安全,災時能保障避災群眾的安全[12]。
1.4 改造量小
體育館空間開敞,體量較大,分隔方便[13]。如疫情期間可將體育館按需劃分區域,做到工作人員與患者通道分開,確診患者與疑似患者分開,人流、物流分開,清潔物品與污染物品分開等等[14],可避免患者之間交叉感染,防止醫務人員職業暴露,為最終控制疫情發揮積極作用。體育館一般分賽場、觀眾席、運動員用房、競賽管理用房、媒體用房、場館運營用房、技術設備用房和安保用房等多種功能區,空間轉化靈活,如賽事管理用房災時可變身為應急防災指揮中心,體育器材室適合存放救災物資。館內一般備有良好的中央空調、消防、數控、監控、綜合布線、照明、音控等機電設備,供電供水條件相對好,環衛設施基礎較好,內部裝修條件通常良好,地面、墻面基本可以沿用。體育館內廣播電視、電子屏幕、通訊設備一應俱全,受災群眾在滿足基本的生活條件之外可以通過電子屏了解外界新聞、避災抗疫等相關信息,通過各種通信設備與外界保持聯系。如果作為臨時避臺風、地震災害等應急避災點,補充一些飲食起居物資裝備,幾乎即刻可以投入使用。如果改造為方艙醫院,工程量總體也較小,如武漢體育館和體育中心方艙醫院的全部施工任務都僅用了10h。
室外擁有大量開敞空間,如田徑場、風雨操場、集散廣場和大片綠地等,這些開敞空地通常可占到總用地面積50%以上,災時可作為優質的棚宿場地。
1.5 通達度好
體育場館作為人員高度聚集的場所,地理位置好,環境佳,商業服務配套設施齊全。一般位于交通區位條件較好的地方,至少一面或兩面臨接交通干線,且入口處有充足的停車以及回車場地,還可停靠直升機,可滿足涉災人員和車輛的快速抵達以及快速撤離,對外交通便捷,內部聯系順暢,無障礙設施較齊全。
1.6 波及面少
體育場館內通常無大量常住人員,可直接用于避災安置。體育場館一般都建在比較開闊的地方,體育館建筑之外的場地也比較寬敞,與現有公園、綠地、疏散道路等周邊環境互融,離居住區或者學校等人群密集活動區間距相對比較大,對社區民眾的干擾小,同時也降低了潛在的病疫傳染風險。
2 既有體育場館兼顧避災應急功能設計和管理的不足
屬于大空間公共建筑的體育場館,雖然具備上述諸多作為避災除疫應急場所的資源優勢,但多數既有體育場館在設計建造時,純粹以體育功能為目標導向,缺乏對避災應急方面的兼顧,因而,在臨時征用作為避災應急場所時,或多或少地會遇到一些短板問題需要補齊。應秉持平(時)災(時)結合的原則[15,16],更加具有前瞻性和戰略性地重新審視體育場館的設計和管理。
2.1 場館設計問題
汶川大地震和新冠病毒疫情之后,人們才明顯認識到體育場館作為避災除疫應急場所的資源優勢。之前,大多數既有體育場館的規劃設計較少考慮避災除疫方面的需求,沒有為改造成避災場所或方艙醫院預留靈活轉換的接口和空間[17],增添了改造時間、資金和機會成本。
空間布局方面,既有場館主要是滿足運動員、裁判員、教練員比賽訓練及全民健身的需要,缺乏平災多場景空間轉換布局預案,一旦發生災情疫情,還要臨時花時間和精力制定服務于災民或患者的空間改造利用方案[17,18]。
通風系統方面,既有體育場館通風與空調系統大多為正壓系統,可能導致污染區空氣流向清潔區,增加清潔區醫護人員感染風險[18]。
設施接口方面,既有運動場地內電線線路和接口單一,在改建“方艙醫院”時,為了讓每次張床位都能順利通電,需要重新將線路全面進行鋪設;體育建筑運動員和觀眾的人均日用水定額遠低于災民人均日用水量;體育建筑的應急電源裝置一般僅能滿足照明系統用電,難以承載大功率供暖致冷電器的長時間運行;廁所、浴室、垃圾與污水處理設施可擴展性不足[12];看臺和觀眾席座椅大多是固定結構,缺乏靈活可變性。
無障礙設施方面,一些場館尚存在無障礙坡道、廁所、電梯、入口、通道、標識等不夠完善或荒廢、損毀的現象,一旦遇到疫情災情,將會給傷患人員通行帶來不便。
通訊條件方面,既有體育場館,特別是建造年份較早的體育場館,信息化設施基礎一般,智能化水平相對較低,災時庇護或收治的人數多,加上救護、社會公眾、政府各方對數據傳遞和信息交流有著極強的需求,容易造成人多信號差、信號延遲等網絡問題[17]。
2.2 場館管理問題
長期以來,公共體育場館一般是由各級人民政府投資或籌集社會資金興建,供人民群眾進行健身鍛煉的體育運動場所。其主管部門為體育行政管理部門,大中小學體育場館則以學校和教育局管理為主,應急、民政、疾控等減災防災部門,在體育場館的設計、驗收、巡查等環節,參與度較低。
一般情況下,針對體育場館工作人員的防災培訓主要限于樓宇內消防安全能力和反恐、急救方面,較少開展疫情、氣象災害、地質災害等其它場景下的避災應急實操培訓。
體育場館避災抗疫應急預案針對性不夠具體,平時演練不夠,導致疫情、災情早期政府領導、增援隊、醫療隊、志愿者、體育館工作人員責任分工不夠明確[18],需要花時間磨合。
3 對策建議
中國歷來是世界上受自然災害影響最嚴重的國家之一,隨著全球氣候變化,災情、疫情發生更加頻繁。認真總結各地歷年來使用體育場館抗災防疫的經驗,補齊體育場館設計和管理環節的短板,對更有效地發揮其抗災防疫功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3.1 堅持平災結合的設計原則,強化新建改建設施的兼容性和可變性
在滿足體育建筑設計規范的前提下,對新建改建體育場館設施的設計,應充分兼顧抗災防疫需要。
空間布局方面,引入“防災單元”設計理念[16], 與體育構筑設計同時考慮同步進行,制定平災多場景空間轉換布局方案,一旦發生災情疫情,即可快速切換到抗災防疫應急服務模式。如賽場和看臺、輔助用房和設施(觀眾廳、貴賓室、運動員室、辦公室、媒體室、廣播間、檔案室、器材庫等)、練習房等如何快速轉換為抗擊疫情所需的三分區(污染區、半污染區、清潔區)兩通道(醫務人員通道、患者通道)[17,18]。遭遇震災、滑坡、泥石流等地質災害或洪災、雪災等氣象災害時,體育場館在空間布局方面如何高效有序地組織棚宿生活、交通救援、物質集散、醫療衛生等抗災活動[15,16]。
規劃設計階段,還應該預先考慮應急供電車、應急供水車、應急通訊車、應急移動廁所、應急垃圾清運車、應急救災車輛等臨時移動設施的進出路線和停放位置。
設施構件方面,引入模塊化建筑和空間可變設計理念[19],盡可能應用現代自動控制技術,配置組件式可升降平臺、可伸縮看臺、可拆解座椅、可擴展廁所、可開閉門窗、可活動分隔幕簾、可移動排污處理模塊、正負壓可轉換通風系統等,便于根據抗災防疫需要,靈活變換空間布局。
電纜、空調管線、給排水、消防設備等均應設計有應對平時和災時的多套對接接口。
3.2 突出綠色抗災與智慧抗災,營造體育場館低碳高效的避災服務環境
災情期間,避災場所人流量大,供電供水需求量大。而且震災、風災、雪災、洪災等災情,甚至會引起停電停水。大力推廣應用太陽能及地熱能等新能源技術、光導管自然光照明技術、雨水收集利用技術、中水回用技術、建筑節能與新型墻體技術、變頻節能技術、智能光溫控制技術、氣膜綠色建筑技術等綠色環保技術,降低能耗水耗,減少應急供電供水的壓力,打造平時災時都能低碳高效運行的體育場館,對實現綠色抗災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隨著5G和“物聯網+”時代的來臨,體育場館與“物聯網+”的深度融合成為發展趨勢,需要通過硬件升級促進體育場館信息化、智能化,通過軟件創新促進體育場館數據化、互動化[20],提升體育場館的運行效率,增強體驗快感。面向避災需求,還需要構建應急指揮管理系統,應用無線、有線、計算機及衛星等技術和設備,通過集語音、數據、圖像通信于一體的通信網絡,采集和處理場館內外每一個角落、每一個人員信息,實現通信調度、現場指揮、情報信息管理等各類應急指揮功能,還可實現跨區域、跨部門應急協作調度。可開發針對震災、風災、洪災、疫災在不同場景下的移動APP,為避災群眾提供周到的飲食起居、健康監測、醫療護理、親友找尋等全方位的信息服務。
3.3 避免條塊分割各自為政,合力健全平災結合的體育場館管理體制
加強體育、教育、應急、民政、疾控等部門的協同,可由應急管理部門牽頭組織成立防災減災議事委員會之類的機構,合力管好用好包括體育場館在內的避災安置場所。在體育場館的設計、驗收等環節,共同把好質量關。定期檢查設備的防災狀態是否正常、物資儲備是否充足。
居安思危,編制多種場景下的體育場館應急手冊,對體育場館工作人員有針對性地開展遭遇臺風、洪澇、雪災、地震、泥石流、疫情等多場景下的應急處置技能培訓,邀請有經驗的專家傳經送寶,或前往經歷過風災、洪災、震災、疫災等救援的體育場館參觀學習。定期進行避災應急演習,提升各部門工作人員的避災應急處置和協同作戰能力,做到淡定從容、訓練有素地應對各種重大突發災害事件,更好地讓體育場館成為可靠的能在災疫中托起生命的“諾亞方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