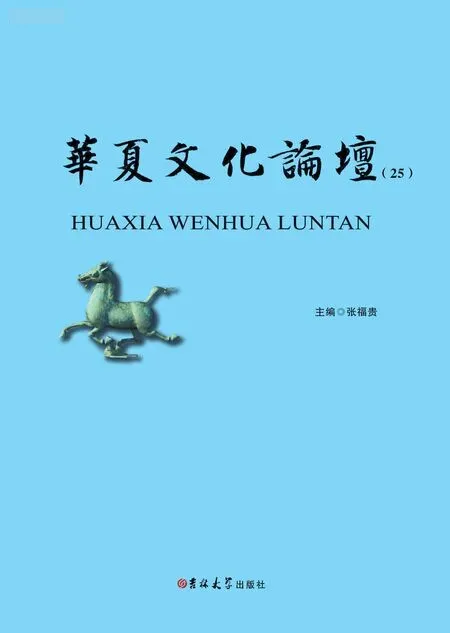論道家對恩德文化的解構
楊春時
道家是春秋戰國時代的主要思想流派之一,也是一種反恩德文化的思潮。道家屬于沒落貴族思想體系,是對春秋戰國時代社會變革的反動。在春秋戰國時代,傳統的貴族社會衰落,等級制度瓦解,禮崩樂壞,地主官僚社會正在崛起,平民文化開始取代貴族文化。面對這種變革,沒落貴族拒絕新興的社會、文化,轉而懷戀國小而民寡的舊時代,甚至把原始社會理想化,同時也以高傲的人格對抗社會的淪落。老子、莊子是這種沒落貴族思想的代表,他們建立了道家哲學體系。老莊思想反對新興的主流文化,以自然無為來對抗權力爭奪。道家主張無為而治,反對禮樂教化;主張人與世界包括人與人之間的“無待”,反對倫理親情,從而解構了儒家的恩德文化。
老子建立了道家哲學,并且在政治文化等領域解構了恩德文化。在哲學本體論方面,他提出了自然本位的思想,從而反撥了儒家的倫理本位思想。儒家以道為最高本體,但儒家的道是倫理性的,天道即人道,道通人性,而人被規定為一種倫理角色,承擔著家族、社會、國家的責任。儒家以“仁”界定人的本質,人性是有情有義的,關涉到他人的,人與人之間以施恩和報恩構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關系和倫理規范,由此形成了恩德文化。而老子的道本體是自然,即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這就是說,道就是萬物自身的規律,是自然而然的天性,而摒棄了人為的文明教化。老子認為,人性不是倫理教化而成的,而是非社會化的自然天性,人是獨立無依、少知寡欲的存在物。天道、圣人都不會施恩于人,人是自生自滅的自然物,他說:“天道無親”(《老子·七十九章》),“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圣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老子·五章》)這就從根本上否定了天恩和人恩。既然如此,人的生存就是為己,而非為人,明白為己者才是明智之人。他說:“貴以身為天下,若可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若可托天下。”(《老子·十三章》)老子理想的生存狀態是回到上古的自然人:“小國寡民,……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老子·八十章》)既然人的本質是自然天性,就無關乎倫理;既然生而為己,也不會發生恩情關系,這就在根本上否定了恩德文化。
老子從道法自然的哲學思想出發,提出了自己的社會思想。春秋戰國時代,各家各派都提出了自己的社會理念,以求結束亂世,重建社會秩序。儒家的社會理念是恢復周禮,實施仁義教化,達到家齊、國治,天下平。在政治領域,主張以仁政施恩于民,實現君德民順,國泰民安。老子反對仁義教化,他認為仁義教化違反自然天性,是一切禍亂之源。他說:“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合,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老子·第十八章》)他指出,德、仁、義、禮等文化系統都是離開了大道的亂源:“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老子·三十八章》)故此。他主張拋棄禮義文化,無為而治。他指出:“道常無為,而無不為。”(《老子·三十七章》)主張統治者要無欲、無為。無欲就是不壓榨百姓;無為,就是不干預民生,讓民眾自然生活。有欲、有為,所以世亂:“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老子·七十五章》)如果無欲、無為,民眾就會過得很好:“故圣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老子·五十七章》)這種無為而治,老子稱為“嗇”,“治人事天,莫若嗇。”(《老子·五十九章》)無欲而嗇的政治,就不是恩德政治,不需要對百姓施行恩惠,更不要施行壓榨,百姓無須報恩,也不受壓迫,自然會活得快樂。
關于社會關系,特別是統治者與百姓的關系,儒家主張德治,君主施恩于百姓,使得百姓感恩、服從君主。這實際是一種權力關系,君主擁有了道德化的權力,使得對百姓的統治合法化。而老子不接受任何恩德,也反對任何權力支配,主張自然而然地生活,他說:“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而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老子·十七章》)這里是說,最理想的君民關系是僅僅知道有君主在(下知有之),其次才是贊譽、畏懼、侮慢,實際上是認為最理想的君民關系不是民眾愛戴或畏懼君主,當然更不是侮慢君主,而是互相無涉,不發生實際關系。儒家追求的君主施恩與民眾、民眾對君主感恩即“親而譽之”的恩德關系,不被老子認可;而百姓淡然處之,“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老子·十七章》),才是老子認可的理想狀態。他認為得道之人是無恩無怨、無親無疏、無貴無賤的,“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老子·五十六章》)這與恩德設計的施恩、報恩互相依存的人際關系是完全不同的。
老子反對政治權力,包括法家主張的暴力統治,也包括儒家主張的施恩者支配受恩者,受恩者依從施恩者的德政,而主張解除人際關系的權力控制,恢復自然的、平等的人際關系。他認為道“萬物持之以生而不辭”“衣養萬物而不為主”,“萬物歸焉而不為主”(《老子·三十四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持,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老子·十章》)把道施行于社會、國家,就是反對強者支配弱者,主張萬物平等,所謂“大制不割”、“孰知其極?其無正。”,圣人的作用只是“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老子·六十四章》)。他反對君主占有天下,“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老子·二十九章》)他主張施而不求報、功成不受,就是反對施恩——報恩的恩德倫理。他指出,圣人“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老子·八十一章》)“功成身退,天之道。”(《老子·九章》)“功成不名有”(《老子·三十四章》)在國與國的關系方面,他反對霸道,也反對王道,而主張大國與小國互相謙讓,特別是大國要謙下:“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這里的意思是大國不過分控制小國,小國也不過分奉承大國,各得其所,而大國尤其要謙下。
在春秋戰國時代,法家主張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儒家主張以施恩獲得權力,成為主宰。老子不主張做強者、支配者,而主張做被動的弱者,提出了貴柔守雌的生存策略。他指出:柔弱是道的應用,“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老子·四十章》)所以做人處事不應逞強好勝,主張知足、不爭:“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老子·四十六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長久。”(《老子·四十四章》)“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為而不爭。”(《老子·八十一章》)“上善若水,水利萬物而不爭,……夫惟不爭,故無尤。”(《老子·八章》)他顛覆了恩德體系中的貴賤、強弱關系,認為“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老子·三十九章》)他認為不應該追求做強者、主宰者,而應該做弱者、被主宰者,也就是不做施恩——報恩關系中的主動者。他說:“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弱勝強,以客勝主,是老子辯證法的應用。他認為明智者應該示弱守雌,弱者最終會勝過強者:“見小曰明,守柔曰強”(《老子·五十二章》)“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為乎?”(《老子·十章》)“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溪:常德不離,復歸于嬰兒。”“復歸于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老子·二十八章》),由于道的辯證法,最終是“柔弱勝剛強”(《老子·三十七章》),這是對恩德秩序的倒置,是對強權的蔑視,對弱者的肯定。同時,他也主張強者要示弱,要謙下,以免遭禍患。例如在在大國與小國的關系上,他就主張“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大者宜為下”。(《老子·六十一章》)這實際上就是要求統治者不要以施恩一方自居,壓迫被統治者,而要向對方讓步。
老子作為道家鼻祖,建立了自然無為的哲學,并且提出了非支配性的社會思想,主張去禮義教化,把人際關系最小化,追求自然的生活,以求明哲保身。莊子繼承了老子的自然無為哲學,而且更為徹底地發展了道家思想。他主張完全的自然化,徹底否定一切文明教化,以實現“逍遙”。
莊子從老子的自然無為的思想出發,提出了比老子的明哲保身更高的生存目標,就是“逍遙”。逍遙是莊子版的自由概念,即“無所待,以游無窮”。他以寓言的方式描述了逍遙游,即超越時空,如鯤鵬萬里,如神人不死。他認為,要實現逍遙,就要無待,即對世界無所希求、無所依賴,從而物化,與世界同一。他認為實現了逍遙游的人就是天性完美的人:“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兌,使日夜無隙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于心者也。是謂才全。”(《莊子·德充符》)莊子認為消除了人與世界的對立,實現天人合一,就達到了逍遙境界:“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謂真人。”(《莊子·大宗師》),他把自由建立在消除主客對立的基礎上,提出了“天與人不相勝也”的思想,雖然帶有消極因素,但作為對主體性的反思,這種思想仍然有其深刻之處。
為了實現逍遙,莊子主張無待,即無所希求、無所依賴,獨立不依。如何達到無待,莊子說:“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莊子·逍遙游》)無己就是去除意志,無功就是不求功利,無名就是不要名分,這樣就也沒有了主體欲求,與世界不發生沖突,也就沒有了社會責任,從而從根本上消除了主客矛盾,落得逍遙自在。這種思想就解構了儒家的恩德文化。儒家恩德文化體現出道德追求,是有己;承擔社會責任,是有功;確定社會身份,是有名。而在逍遙狀態之下,一切道德追求都被超脫,一切社會責任都被廢除,一切名分地位都被摒棄。莊子鄙視世間俗務,特別是摒棄政治功利,拒絕進入統治關系之中,認為這妨礙了自由。他的這段話可說是總括了其無己、無功、無名的思想:“故樂通物,非圣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余、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莊子·大宗師》)
先說“無己”。莊子追求逍遙,企圖擺脫一切社會文化,這首先就要求消解理性自我,即“無己”,這是實現逍遙的內在條件。所謂無己,就是順乎天性自然,放棄主觀意志,做到無知無欲,從而消除了與外界的矛盾。這就區別于儒家通過修身建立理性自我的思想。他提出“心齋”、“坐忘”,使自己虛空無念。從而與外物同一。他虛擬了顏回與孔子的對話:顏回說自己的思想提升了,先是忘了仁義,再是忘了禮樂,最后達到“坐忘”,于是“仲尼蹴然曰:‘何謂坐忘?‘顏回曰:‘墮肢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謂坐忘。’仲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后也。’”(《莊子·大宗師》)坐忘使人無我,達到了與道通,與世界合一的境界。無己還意味著“無情”,這是繼承了老子“圣人不仁”的思想。有情就會發生人際關系,從而發生矛盾。儒家重情,恩德文化就是建立在恩情基礎上的,以恩情關系把自我與他人捆綁起來,從而喪失了自由。而莊子主張對萬事萬物無情,以保持自我的獨立和自由。莊子說:“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莊子·德充符》)因為無情,也就是無所希求、無所依賴,從而獨立于世界,獲得自由。這是對一切社會關系、社會責任的排斥,也是對恩德的排斥。莊子認為人際關系妨礙獨立、束縛自由,主張人際關系疏遠而無爭,從而獲得逍遙。他講述了兩條魚相濡以沫的故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昫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莊子·大宗師》)這則寓言旨在說明,人與人之間的恩惠是不必要的,不如各自逍遙。對于生死窮通,莊子也淡然處之,不動情,認為這都是自然規律,不應有哀樂之情。他講述了“老聃死,秦失吊之,三號而出”的故事,對于弟子的責問,莊子認為吊喪哀哭,“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他接著說,秦失的舉止并無不當,因為“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莊子·養生主》)這種無情的心態,正是為了免除為物所累,陷入社會關系的恩恩怨怨。
再說“無功”。所謂無功,就是順萬物之自然,不求功利,無所作為。儒家倡導有為世界觀,主張“立德、立言、立功”,就是施恩于人、立功于天下,以求得大治。莊子反其道而行之,反對追求社會功利。以無功思想解構了恩德。他服膺老子的無為哲學,認為無為無不為,是道的最高境界。莊子主張“不與物交,惔之至也;無所于逆,粹之至也。”(《莊子·刻意》)“故曰,喪己于物,失性于物者,謂之倒置之民”(《莊子·刻意》)莊子認為道的應用首先是養生,即精神的升華,獲得逍遙,而治理國家的功業是次要的。他說:“道之真以治身,其緒余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莊子·讓王》)這實際上是說,世俗事物都是不得已而為之的,不值得認真。如果一旦求功,就會“攖仁心”,使人失其自然本性。
無功之人,也就無用。莊子主張無用,認為不用之用乃大用,實際上就是取消社會責任,消解社會角色,自然地生活。這是對恩德文化把社會責任即恩義置于首位的反動。他以寓言說明了無用的內涵,如惠子對莊子說,你的言論大而無用,像一棵充滿木瘤而彎曲的大樹。莊子回答說:“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于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莊子·逍遙游》)同樣的道理,莊子在《人間世》中還講述了這樣幾個寓言:神社里面的一棵櫟樹,因無用而得到保存。還有,商丘地方有一棵大樹,也因為無用而得以不被砍伐,因此“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還有,支離破疏因其殘疾而免除服兵役,還得到國家的救濟。這些都是無用的好處。當然這種無用的舉例還是在消極避禍意義上,其積極意義則體現在政治領域的無為而治上。
莊子的無功思想體現在政治上,即無為而治,這是反對儒家的有為而治,當然也就摒棄了施恩于民、報恩于君的恩德政治。他說:“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莫若無為。”他要求不施行禮義教化,“絕圣棄智,而天下大治。”(《莊子·在宥》)莊子講述了黃帝求教于廣成子的故事:黃帝要通過仁政施惠于民,問道于廣成子:“吾聞吾子達于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謂之奈何?”廣成子對黃帝的舉措不以為然,認為他沒有領會道的精華,只得到了道的殘渣,并教導他要修身養性、無為而治,使其拜服。在《庚桑楚》中,莊子借庚桑子之口說:“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于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發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于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吾語女,大盜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歲之后。千歲之后,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莊子·庚桑楚》)在這里,莊子否定了上古圣君堯、舜的治理措施和功績,指出其危害,而且預言其為禍亂之本,流毒千古。莊子總結自己的處世之道:“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游無朕。”(《莊子·應帝王》)
最后說“無名”。無名就是不求名分地位,追求自然的生活。儒家的恩德作為身份倫理,確定了施恩者與報恩者的社會責任,形成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關系。孔子主張正名,就是要恢復周禮規定的社會名分。莊子反對身份倫理,認為社會身份是外在的,功名束縛自然天性,妨礙自由,實際上就是反對擔任任何社會角色和責任,特別是擔任統治者的角色和責任。他提出了“無名”的思想,而注重“實”,所謂實就是自然天性。他在《逍遙游》中虛構了堯欲禪讓天下給許由,被許由拒絕的故事,許由的理由就是不求虛名,而要其實,這個實就是逍遙。他還虛構了一個寓言故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莊子·逍遙游》)這里說堯治理天下很成功,但見到藐姑射之山上的四位得道之人,就悵然若失。忘掉了自己的天子之位。可見做天子并不如做得道逍遙之人。《秋水》篇云:楚王派大夫請莊子出山為官,莊子不允,謂楚大夫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最后答復曰:“往矣!吾將曳尾于涂中。”這里更鮮明地表達了不肯以自由換取名位的思想。在同一篇之中還講述了惠子怕莊子覬覦其相位,莊子以鹓鶵遨游四海,而鴟以為其欲搶其口中腐鼠的故事加以嘲諷,表達了自己對自由追求和對名位的鄙視。
無名也是對依附性的社會關系的否定。在恩德文化中,名分地位規定了依附性的人際關系,即以施恩來支配受恩者,以報恩依附于施恩者:父施恩于子,子依附于父;夫施恩于妻,妻依附于夫;兄施恩于弟,弟依附于兄;君施恩于臣,臣依附于君;官施恩于民,民依附于官。而莊子主張人與人之間無所依附,即使君主圣人也不能居功而支配人,百姓也不因為圣人之功而依附之。(《莊子·在宥》)莊子認為理想的統治者是不居功,既不施恩也不求報恩;民眾也保持獨立無依,無須報恩,雙方都達到了逍遙:“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無測,而游于無有者也。’”(《莊子·應帝王》)這里明顯與儒家主張的恩德政治相反對。
無名還包括對禮義教化的否定。儒家尊崇禮義教化,是謂名教。莊子認為,一切文明教化皆屬于有名,都是自然天性的束縛,所以都要破除。在《應帝王》篇中,莊子講述了倏、忽為混沌開七竅而致其死的故事,表明文明教化扼殺天性。莊子把文明史看作禮教興而大道失的歷史,這與儒家描繪的圣人之治的盛世截然相反:莊子說:“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而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梟淳散樸,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后去性而從于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搏。文滅質,搏溺心,然后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莊子·繕性》)
他否定文明社會的生活,而向往原始自然的生活,認為這才是理想的合乎人性的生活方式: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群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禽獸可系羈而游,鳥鵲之巢可攀援而窺。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圣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尊!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圣人之過也。(《莊子·馬蹄》)
儒家提倡禮儀道德,主張恢復周禮,實即踐行恩德文化。莊子反對恩德,也必然否定遵行禮法,認為禮法是無意義的虛名,不合人的天性,因此可以不顧禮法,率性而行。莊子虛擬了漁父教訓孔子的話:“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貴真,不拘于俗。愚者反此,不能法天而恤于人,不知貴真,祿祿而受變于俗,故不足。”(《莊子·漁父》)莊子還虛擬了一個故事: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為友,子桑戶死,其余二人“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見之問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歸來問孔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眾人之耳目哉?”莊子還虛構了顏回問孔子的話:“顏回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處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乎?回壹怪之。”孔子回答是孟孫氏已經盡了服喪之道,他能夠超越生死,聽任自然的安排而順應變化。(《莊子·大宗師》)這些虛擬的寓言旨在說明,人應該按照自己的自然天性行動,而不受禮法束縛,從而獲得自由。莊子對禮法的反對,就是要破除恩德文化規范,把自我從恩德關系中解脫出來,進入逍遙。
道家思想對儒家思想為主的恩德文化發生了兩種作用,一個是解構作用,一個是互補作用。所謂解構作用,上面已經論說了,主要是自然思想無為對恩德、禮義教化的逃避、反撥。由于這種解構作用,儒家代表的主流文化對道家采取了疏遠甚至批判的態度。自從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后,道家思想就退出了主流文化,被邊緣化。另一方面,道家思想對主流文化也構成了一種補充,緩解了儒家文化的緊張性。由于儒家文化強調禮義教化,使得個體被緊緊地束縛于禮法之中,承受著精神的壓力。而道家文化則以其超脫性,解除了禮法壓抑,而回歸自然。這樣就可能緩解人的精神世界的緊張,獲得某種解脫。當然,這種解脫帶有某種消極性、虛幻性,而不能真正地改變現實。中國士大夫大都在認同儒家思想的同時,也接受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成為他們逃避現實的港灣。正是儒道思想的互補,使得中國人,主要是士大夫的精神世界相對豐富、健康,而減少了實用理性的片面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