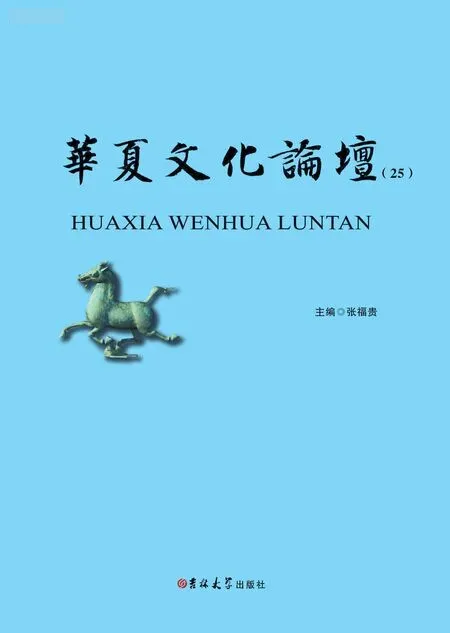復性如何可能?
——從馬一浮會通三教的本體論看工夫論
于曉寧
明清以來,三教會通漸成趨勢,這與陽明學與朱子學的疊相興起與修正、佛教的衰敗與復興,以及中西文化的接觸與碰撞關系重大。馬一浮身處中西方文化劇烈碰撞和國族危亡的現代,既受明清思想史這種趨勢的影響,精研佛道經典,與佛教人士來往密切,同時又飽讀西方學術著作。在艱難困苦的現實人生和命途多舛的國運世事中,在不斷接受中西方文化的劇烈沖擊下,他摒除狹隘的道統觀念,主動選擇和皈依了儒家“六藝”和中國傳統的道學,展示出有得于心的文化上的執著與自信。無疑,馬一浮是一個典型的“接著講”而非閉目塞聽的思想家,他以西方學術思想作為潛在的對話者,以佛道二氏的觀點來解釋發揮儒家義理,從而使呈現出以儒家為主,會通三教也包容西方的風貌。
馬一浮以程朱理學對理氣的闡釋為起點構筑本體論,從理氣不離不雜,講對理和氣的認識過程,最后回歸到理在人身的顯示和認知的問題,自然引出以“復性”為目的的工夫論,就是要靠對欲識的辨識、對法執的蠲除以及對習氣的祛除,使理顯現于人,全氣是理,然后可以復性。
一、理氣的分合
牟宗三等在《為中國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中宣稱:“心性之學,正為中國學術思想之核心,亦是中國思想中之所以有天人合德之說之真正理由所在。”心性之學必以理氣關系為基礎,才能有效理解天人合德的關系。馬一浮的本體論即以此為起點,最終導向工夫論。
馬一浮對于理氣關系的看法,在很大程度上秉承了宋明理學尤其是伊川和朱子的基本觀念。對于他來說,重要的不是新造理論體系,而在于能否在實踐中證成。他認為,理、氣都是普遍永恒的存在,無終無始,無先無后:“理則無終始先后,氣亦本無終始,但可順俗說,以聚散為終始。”(一,P639)作為宇宙構成的要素,理、氣始終是一體的,但從不同的角度相對來說可分為理、氣、三才、道、器、太極、陰陽、八卦諸名。
器者,萬物聚散之目。道者,此理流行之稱。道無定體而器有成形,二名無所不攝。……器即氣也,道即理也。合則曰氣,散則曰器。(萬物散殊,皆名為器。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以氣言也。——原注)寂則曰理,通則曰道,其實一也。立二名而義始備,從而二之則不是。然以道望理,則理隱而道顯;以器望道,則道隱而器顯。(一,P483)
道即言乎理之常在者,器即言乎氣之凝成者也。(一,P38)
道、太極等是理的另一種名稱,器、陰陽、八卦、三才則是氣的別名,理、氣或道、器二名可盡攝天下之教,理、道、氣、器四名,實則是一,只是從隱顯之別上來說可分為兩個名稱,而不能將理、氣截然分為兩個。馬一浮認為,“天下之道統于六藝而已,六藝之教終于《易》而已”(一,P422),道、器這對概念自然也涵攝、會通佛道二教:“自佛氏言之,即是色、心二法也。老氏曰:‘樸散則為器,圣人用之,則為官長。’(亦曰器長,猶《易》言主器。不敢為天下先,故能為器長;即長而不宰之意。——原注)二氏之言亦不出道、器二義。過此以往,竭天下之言有以知其莫能外于此也。如有所不攝,則非大矣。”(一,P483)以儒家義理總攝群教的意圖在這里表現得非常明確、突出。
理、氣的關系,是一種體用的關系,它們不離亦不雜。說其不離,除了上面所討論的,本來是一之外,還在于要于理中見氣、氣中見理。馬一浮用《易傳》中的“形而上”與“形而下”概念來解釋理和氣,并描述它們的這種關系:
有形必有質,有質必有氣,有氣必有理。未見氣,即是理,猶程子所謂“沖漠無朕”。理氣未分,可說是純乎理,然非是無氣,只是未見。故程子曰:“萬象森然已具。”理本是寂然的,及動而后始見氣,故曰“氣之始”。氣何以始?始于動,動而后能見也。動由細而漸粗,從微而至著,故氣由氣而質,由質而形。“形而上”者,即從粗以推至細,從可見以推至不可見者,逐節推上去,即知氣未見時純是理,氣見而理即行乎其中。故曰:“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不是元初有此兩個物事相對出來也。……就其流行之用而言謂之氣,就其所以為流行之體而言謂之理。用顯而體微,言說可分,實際不可分也。“形而下”者是逐節推下去。……這一串都是從上說下來,世界由此安立,萬事由此形成,而皆一理之所寓也。(一,P38-39)
理、氣不可分,有氣必有理,有理必有氣,氣未呈現于前是純乎理,是氣微細之時,并非無氣;氣到質到形的變化,由細變粗,由微而著,理總是行乎氣中,并非無理,它們一體一用,自始至終都是一體的。離開氣,就不能見到理,“太極者,一理至極之名;兩儀者,二氣初分之號。一理不可見,于二氣見之”(一,P425—426)。離開理,氣也不能存在。能否于器中見道,氣中見理,即成圣凡之別。“天人一理,故道器不二。器者,道之所寓也。凡民見器而不見道,故心外有物。圣人見器莫非道也,故道外無事,器之所在,道即在焉。”(一,P484—485)
說其不雜,表現為理、氣雖然不能截然分開,但它們又不是直接同一的,各自具有不同的規定性。主要可歸納為理本純全,氣有偏駁。就氣來說,“氣有偏全、通塞、昏明、清濁之異,人物皆稟是氣以為形質而后有生”(一,P64)。三才都稟氣而生,因此天人是一氣,但人與物、人與人之間所稟之氣是有差異的。理則更復雜一些。馬一浮認為,雖然講“體用一如,顯微無間”,而且理要于氣上見,但氣有偏駁,而理作為體來說,則永遠是純粹至善的。
理、氣既是一體的,又很不同,這種不離不雜的關系有雙重意義:一者,理氣一體,理是氣的理,是氣的本體,對于氣可以有一種根本的決定作用;二者,理氣不是同一的,理雖然可以決定氣,但它不能主動地創造氣,理氣不是一種創生的關系,氣可以不合理,因此會有偏駁。這為善惡的來源及人為善的可能提供了本體論的說明。
二、欲識與法執
理、氣既然是構成宇宙天地的基本要素,人自然也不例外,同樣是理、氣構成的。理、氣在人身上分別對應著的是性和情。他說:
心統性情,性是理之存,情是氣之發。存謂無乎不在,發則見之流行。理行乎氣中,有是氣則有是理。因為氣稟不能無所偏,故有剛柔善惡,先儒謂之氣質之性。圣人之教,使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便是變化氣質,復其本然之善。此本然之善,名為天命之性,純乎理者也。(一,P19)
性是理之存于人,是本然的善,純是理,為人人所同,又名為天命之性。情是氣之發于人,一般來說包含七情,即喜怒哀懼愛惡欲,其質有剛柔善惡,生來就因人而異,又名為氣質之性。性、情如理、氣,也是不離不雜的。
在三才中,人有特殊的位置。物我一體,天地是人的先祖,人為天地之合德,得五行之精華(一,P469)。理無差別,而氣雖有差別,有差別之氣仍是一氣。“理無差別,氣有差別。性是物我所共,命乃萬有不齊,氣質之性亦是命。圣人會萬物為自己者,不唯因其一理,故即此不齊之氣亦是一氣也。”(一,P474)因此,人所稟有的性和情并不是天地之理和氣的一部分,而是全部,人可與天地同其廣大。人由天地變化所生,應以天地為父母,這是儒家、道家和佛教的共識。他批評當時中國所盛行的西方的生物進化學說,這是將人的祖先定為猿猴,人就成為征服自然的產物,失去了道通為一的基礎(一,P242)。
性和情從不同角度在佛道那里由不同的概念名詞來表示。就情來說,“儒家謂情、佛氏謂識,在《樂記》曰‘欲’曰‘知’,《太極圖說》只言‘知’。此‘知’謂徇物之知,故曰‘誘于外’。意存有取,故名為‘欲’。廣則有七(指喜怒哀懼愛惡欲——引者注),約惟好惡,得正則善,失正則惡,故周子分善惡言之。以情識之動不即是惡,唯熾而流蕩無節乃稱為惡”(一,P65)。佛教將人的感官分為眼、耳、鼻、舌、身五根,將外物分為色、聲、香、味、觸五塵外境,五根與五塵外境一一對應。佛教認為,五根與五塵外境之間本來都是無因緣而生,沒有自性的,人的感性自身和外物就像大海中的眾漚一樣,起滅無常。感性對于外物、外境的欣厭取向,其實是一種虛妄,這種取向就是識,其取向形成一種人身執著的心理勢能,就是意根。起于感官的知識都是事物的表象,本來因心而起,是變化流轉而非常恒不變的,若認為其不變,妄加執著,則成幻垢法塵或法執,對于性德在自心顯現成為一種障蔽。
因此,法執與真實的法性是不相應的,要反對法執。馬一浮曾以佛教義理解讀老子《道德經》中第十一章“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認為此章即是顯緣生之法。車能載重行遠,它本身其實無此用,其用有待于人,用乃是緣生之法,沒有自性。就車本身來說,它只有相,而無用,其用不在車,也不在人,所以用是幻。車是有,有其相,但用是無,無即是無自性。身心執取這些法相,成為幻垢,障蔽真實法性。這都是反對對于外物、外境的執著,認為外物、外境沒有自性,執著是對自性的違背。有之以為法,無之以為用,用待于人,非法本具,故法是緣生,無自性。“以緣生故有,有即幻有,非是定常;以無性故空,空乃本無,非是滅取也。”(一,P96)在莊子那里,身也不是人可得而有的,更何況道。這樣,三家共證:
自道家、儒家言之,皆謂氣聚則生,氣散則死。自佛氏言之,則曰緣會則生,緣離則滅。會得此語,則證二空:身非汝有是人空,不得有夫道是法空。在儒家謂之盡己。私人我,諸法不成;安立,然后法身真我始顯,自性功德始彰。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圣人無名。”無己之己無所不己,是為法身,即性也;無功之功任運繁興,是為般若,即道也;無名之名應物而形,是為解脫,即教也。(一,P96)
因此,去矜、去私、去執,是三家之共法,性、道、教皆對此而顯現,亦是三家共法。
但教法自有優劣不同。按照佛教、道家對情識、意根的理解,一方面構成對意識外求在價值意義上的否定,逼人反觀自身,另一方面也容易造成對世界萬物的全面否定。而儒家認為,人的喜怒、好惡作為一事或一物,是人性的自然,因為人不是枯木頑石,其中有合理性,理是其體,視聽言動有可能合于理,也有可能不合理,前者是情之正,后者是情之私。只有后者才構成欲,會害仁悖理。“好惡、愛憎,流蕩所極,則為忿、欲,忿則斗爭,欲斯奪取,害仁悖理,皆由此生。……圣賢非是無怒,怒當于理發而中節,其怒也在物不在己,如明鏡照物,妍媸在彼,故能不遷。”(一,P68)這就是說,氣或情有善有惡,不能一概否定,主要在于能否應理。
欲就是情之過,氣之發用不當,是不仁,因此,仁和欲構成了非此即彼的對反關系,不能同時存在。馬一浮論《尚書》“惟精惟一,允執厥中”的“中”和“精一”的含義時指出:“一理渾然之謂中,一有人欲之雜,即失其所謂中矣。……夫曰精一,即不二不雜,安有所謂參半之說邪?”(二,P1049)并舉《詩經》“天生烝民,有物有則”說明,男女飲食是物,男女有別、飲食有道是則,有物必有則,是天理,若不顧理,則男女飲食失其道,則是欲,因此,理、欲不能并立,這就是孔子所說的:“道二,仁與不仁而已。”
三、祛習與復性
氣質之偏駁,情識之過惡,都是習,它包括善習和惡習兩種。習大致是指由氣質的偏好和行為的取向而形成的一種較為穩定的心理勢能,可能喜歡為善,也可能喜歡作惡,這可能是先天就有的,也可能是后天養成的。惡習自不必說,必須革除,善習也同樣如此。可能有人會認為,善習既然稱“善”,就應當是可取的,甚至可作為人向善的基礎。但在馬一浮,習是心理的一種執著,會污染人心性的虛靜靈明,造成對本體之理的遮蔽,同樣要遣除。因此,他將性與習相對立:“性只是善,無有不善;只是仁,無有不仁。其有不善、不仁者,習也。程子曰:才有一毫私吝心,便與天地不相似。人心本無私吝,本與天地相似,其有私吝者,亦習也。……私是我執,吝是法執,并是虛妄習氣。”私吝是佛教用語,習氣、私吝心是小,性與天地相似,是大。今人都在習氣中生活,從消極面努力,一旦去掉習氣,則自性自然發露;從積極面努力,“義理昭著,私吝自消。故明得一分義理,即消得一分私吝。習氣消盡,全體是性,便是圣賢”。人要磨而不磷、涅而不緇,性不失不壞,隨時從習氣中自拔有為,“須知自性本來清凈無染,即是性善義也”。(二,P875—876)
人的氣質既然有習之偏駁,就須知道何為正,何為偏,須變化氣質以去其偏駁,這就是學的內容和價值。雖物之不齊,人生下來就有智愚賢不肖之分,但無論人氣質美惡皆不可能完美,只是程度差別,因此皆須變化,才可至道。“人雖質美,不能無偏,自知其偏,正好用力。知病便是藥,變則可至于道,故謂質美亦須變化也。”(一,P603)若人知道在變化自己氣質上用力,就識得救取自己。凡是氣質上病痛輕自己又有自知之明的,就容易變化,講學易入;氣質上病痛重又自信甚堅的,就很難救治,雖有良藥,無可奈何。
對于習氣的糾正和遣除在儒釋道三家是共通的。比如老莊講損益,老子曰:“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為。無為而無不為。”馬一浮說這“是為損其習惑至于都盡,則道自顯也”(一,P455)。損的是習氣,益的是道。并解釋“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就是講常人不知習氣當去,反而增益助長它,不知習氣去除之后,道才得增長,內以理為主則外見氣順。
到得習氣遣除,人就可以成為像孔子和顏回那樣的圣賢。他引用伊川《顏子所好何學論》的觀點,認為孔子到“耳順”“從心”時習氣已經消除殆盡,氣質中非理的東西都變化了,不須思勉,心即是理,可以從心所欲,而顏回跟孔子相比,其差別在于顏回還處于“守”的階段,還沒達到“化”的境界,與孔子相差“一息”,假以時日亦為圣,說明圣人可學而至,人人皆應效法顏回。馬一浮解釋:“顏子雖位齊等覺,已與圣臨,猶須思勉。未到顏子地位,不致思,豈能有得;不力行,豈能有中。”(一,P69—70)他認為初學尤其不能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反對陽明后學執性廢修。
馬一浮對于祛習非常重視,將祛習與復性當作同等重要的事,因為這兩者殊途同歸,都可至道。他說:“是故知性習之分而后可以明因革之道。其可得與民變革者,習也。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性也。”(二,P1171)他講學和個人修養中同時關注這兩方面的努力,他自號“蠲叟”,“蠲”義為除去,減免,使清潔。其中蘊含著他對祛習的理解和身體力行。他應蔣介石之邀,到四川辦書院,題其名曰“復性”,這是書院的宗旨。之所以叫復性,也是立于自性,且針對時弊而發。他在《書院之名稱旨趣及簡要辦法》中說:“學術人心之所以紛歧,皆由溺于所習而失之,復其性則同然矣。……教之為道,在復其性而已矣。今所以為教者,皆囿于習而不知有性,故今揭明復性之義,以為宗趣。”(一,P749)復性是學的目標,而祛習則是學的方法途徑。書院之設立,始于立身,終于化民成俗,因此,當此亂世,須蠲除門戶之見,砥礪品性節操,特立獨行,才能外御強敵,不應把心性之學作為空談,而處處以西學為鵠的。
四、性德的認知
對于性和理的關系,馬一浮在本體論上基本繼承了程朱理學“性即理”的看法。性是理的全體,并不是理的一部分。天地人雖事相上有差別,但所稟之理是同。“自佛氏言之,總該萬有,即是一心;自儒者言之,通貫三才,唯是一性。”(一,P243)通貫三才的是一理,也即是一性。他在解釋《論語》最后一章“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時指出,性、命、理三者是一:“性、命一理也,自天所賦言之,則謂之命;自人所受言之,則謂之性。不是性之上更有一個命,亦不是性、命之外別有一個理。……盡心、知性、知天不是分三個階段,一證一切證。”(一,P31—32)唯有這樣,人自我自律的修養才有完整的道德合法性。
性和德是意義極為相近的兩個詞。這兩個詞都表示理之在人,這是它們的相同之處。但也有所差別。一般來說,性表示人所有美德在自身的根源,更多地和“理”相聯系,是對道德本體的總稱。而德則可分別表示性的不同面相,如仁、義、禮、智、信等,更多地和具體的行為表現相聯系。
馬一浮常常將“性”“德”連用,成為“性德”,這個詞可以顯示道德的先天性、完滿性及與日常行為的密不可分,主體詞是“德”。他說:“知德即是知性,由道即是率性,成德即是成性,行道即是由仁為仁。德即是性,故曰性德,亦曰德性。(即性之德,是依主釋;即德是性,是持業釋。——原注)”(一,P220)他曾以“變滅從緣,虛空不爛”來言性德,前半句表用,后半句表體,表明“性德”是兼體用的。他解釋伊川的《顏子所好何學論》中的“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認為這是舉性德:“本謂心之本體,即理也。無妄曰真,本寂曰靜。《樂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理渾然,常恒不變,其體本寂,故曰‘真而靜’。未發謂‘沖漠無朕’,五性即性中所具之五德。德相有五,實唯一性,人人同具,無有增減。”(一,P64—65)性是人心之本體,性即理,無妄而本寂,仁義禮智信是性之五種德相,是人人同具、沒有增減的。性和性德的使用范圍還是略有區別的,性的使用范圍更廣,性德作為人性,特指人的合于理。
在“性德”這個概念下,馬一浮將一些世俗習見的概念做了語義探源式的重新解釋,使這些名詞從有限的、歷史的概念變為有永恒價值的理性道德行為標準。比如,對于“禮”和“義”。“義為禮之質,所存是義,行出來便是禮。又禮與義本是性德,就其斷制言之,則謂之義,就其節文言之,則謂之禮。”(一,P305)禮與義,皆為性德。禮是天理本身所有的條理,這是禮的本質,不能只以制度儀節等為禮。義是天理本身的是非決斷。再如,天、帝都表性德之名。“至高無上曰天,審諦如實曰帝,皆表理之名。圣人與道為一,即與天同德,故曰‘配天’。天、人對言,故曰‘配’耳。實則一性無際曰天,法爾純真曰帝,性外無天,人外無帝。本來具足,是曰天成;一念無為,斯名帝出:皆性德之異稱耳。……天地之塞吾其體,何莫非天也;天地之帥吾其性,何莫非帝也。或言法界,或言道體,皆天帝義也。”(一,P249)天是表示性德之體存在的普遍性和崇高性,帝表示性德之體存在的純真性和統帥性,將天、帝人格化、神秘化的意味徹底消除了。
性德是實體,但不是可把捉的物質性實體,既看不見摸不到,也不是思維所能強探力索的,從這個角度說,它是無。馬一浮在《復性書院講錄》中通過對《禮記·孔子閑居》的解讀詳細闡釋了這個問題。子夏請教君子如何可為民之父母,其實是問君子德性的內涵。孔子答以致五至、行三無。對于“五至”,孔子說以志、詩、禮、樂、哀的迭次生成,其實是表明性德不拘一隅的普遍性。馬一浮也從言行德性來解釋,他對“至”的闡釋可看作是對性德之理概括性的正面描述:
至有三義:一來義,二達義,三極義。湛寂之中,自然而感,如火始然,如泉涌出,莫之能御,此來義也。如水浸潤,竟體皆濡,如光照耀,幽暗畢燭,更無不到處,此達義也。如登山到最高頂,如涉水徹最深底,過此更無去處,此極義也。(一,P276-277)
他描述了理氣如一的一種存在狀態,所謂“神用無方,寂而常感”,非常精妙,也很微妙難識。因為此性此理畢竟是實見實感,是語言所難以盡其底蘊的。孔子的描述是:“是故正明目而視之,不可得而見也;傾耳而聽之,不可得而聞也。”(《禮記·孔子閑居》)表明它不是可見聞的一物。馬一浮認為它也不是一種境界,境界是心或識所變成,“了境唯心,離心無境”。(一,P396)境不是根本性的本體,不可執取,否則成為對性德的遮蔽。因此要“行三無”(無聲之樂、無體之禮、無服之喪)。三無指“心行”而言,不是緣物而起、可見可聞的事相,如樂之聲律,禮之度數,喪服之等級等,因此稱之為“無”。但“無”不是虛無,而是實相。“鐘鼓以為樂,升降以為禮,衰绖以為服者,禮樂之文也;‘三無’者,禮樂之情也。……若專以形名器數說禮樂者,則事相有所限,未足以盡此心之量也。”(一,P280)“禮樂之情”即是性德。
性和理既是人人所具的,也是不能授受給予的,它有賴于每個人在自身發見。在此,“性”這個概念也有特別意義,它特別表示三才所固有稟賦的理,是人本身所具的,不能向外求理。因此它不能完全用“理”這個詞來代替。“離性而言理,則理為幻妄。”(一,P221)離性向外求理,不知理在自身,應反身而求,而向外求,則理成隱背,是舍己求人。“理本寂然,但可冥證。”(一,P425)“理與德默而自證,故屬乾知,成己性也。”(一,P469)但內求默證也會產生像上面所講的,將某種識變的心理意義的境界當作性理、悟道,馬一浮告誡:“此事大須子細,不可鹵莽承當,錯下工夫,翻成執礙。”(一,P524)凡有物可把捉,如一種恍惚的境界者皆非道,這仍是一種知覺、見聞,屬氣,須知止而后能定靜,于氣中見理,理中見氣方可。(一,P524—525)“所謂性者,亦非有渾然一物可以把捉,但隨時體認,不令此心走作向外,則得之矣。”(二,P424)為此,還要進一步了解性與修、理與證的關系,才能避免這種情況產生。“得之”即是悟證,這有賴于人自身努力的修養工夫。
在他那里,“窮理”更少學究氣、書卷氣,主要成為一種日常當下可行的修養工夫。窮理、盡性、至命是一件事:“故格物即是窮理,窮理即是知性,知性就是盡心,盡心就是致知,知天就是至命。程子曰:‘理窮則性盡,性盡則至命。’不是窮理了再去盡性,盡性了再至于命,只是一事,非有三也。……此(按指《中庸》所謂‘盡其性、盡人之性、盡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引者注)是一盡一切盡,其間更無先后。”(一,P113)六藝之道都具于自性之中,因此是古今不變的法則。“性外無道,事外無理。六藝之道,即吾人自性本具之理,亦即倫常日用所當行之事也。亙古亙今,盡未來際,盡虛空界,無須臾而可離,無一事而不遍者也。……吾人性德本自具足,本無纖毫過患,唯在當人自肯體認。”(一,P211)六藝所陳之義理性道是永恒的,也是普遍存在的,而不是暫時的(只存在于特定社會)、有限的(只屬于特定階級),只要人們愿意反身回觀,則性德自足,遠離私欲的過患。他甚至效法禪宗,告訴向他問學的人,不必理會很多佛理,只要自識便可:“釋迦、老子、文殊、普賢、觀音、彌勒只是一群閑漢。……今語公只須識得自己,更不用理會諸佛,此語決不相誑。”(二,P418)而在浙江省政府舉行的一次教師節孔子紀念會演講詞中他表示,心性不是暫時的,而是永恒的;孔子不是歷史的,而是現實的:
凡世間有形之物,可以毀滅,唯有心性,不可毀滅。……蓋今日在會諸君尊崇圣道之一念,即是人心中有一孔子誕生也。欲明孔子之道,須求之自己心性。歷史上之孔子是跡,自性中之孔子是本。(二,P1258)
想求自性中的孔子,就要從判敬肆、辨義利、慎言行等修養工夫入手。
陳來指出,馬一浮的思想特質應屬于“即內在即超越”,“內在的真實體悟已經同時就是知天合天,并不意味著需要經過一個過程再去接通超越”。作為信仰,它“不是知性和理性可以了解的”,其“本體論亦可借助一種知性結構加以表達,但真正的‘證實’則需要工夫的‘自證自悟’。”這里的工夫的自身和本體顯現其實是一個共時的歷程,人的悟證與理的具體內容之間,不是認知主體與知識客體的關系,不是一個二元對立的結構,而是一個由人而天的超越,或者人向自身的回歸。因此,這是不可能求諸他人的,悟就是理顯現于自身,是成己之性;迷就是自身欲的放縱,是鑿己之性。而一性無外,所謂“性外無理”“性外無事”,盡心、知性不但是成己,也是成物。
在這里,要去除人我之別,才是回到真己,人就可以盡己(忠)、推己(恕),這個己不是私己,而是具有普遍性的我。他批評當時的學者受西方學術的影響,把事物從自身推出去,客觀地研究。
今時學者每以某種事物為研究之對象,好言“解決問題”、“探求真理”,未嘗不用思力,然不知為性分內事,是以宇宙人生為外也。自其研究之對象言之,則己亦外也。彼此相消,無主可得,而每矜為創獲,豈非虛妄之中更增虛妄?以是為窮理,只是增長習氣;以是為致知,只是用智自私:非此所謂窮理致知也。(一,P114)
他認為,用這樣的態度窮理致知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只是增添虛妄而已,體現出他對現代學術方法的批判。有張君欲以科學方法研究儒學,馬一浮認為所謂科學方法,是以思量分別之心,勉強雜糅而成體系:“今時科學哲學之方法,大致由于經驗推想、觀察事相而加以分析,雖其淺深廣狹所就各有短長,其同為比量而知則一。……其較勝者,理論組織饒有思致可觀,然力假安排,不由自得,以視中土圣人‘始條理’‘終條理’之事,雖霄壤未足以為喻。”(一,P519)這種科學體系是以揣摩推想而來的,是義襲而取,而圣人之學則必本自身體驗而來。
在馬一浮那里,性和理的表達更主要只是指示一種生命的信仰和學問的至善方向和價值源頭。郭齊勇說:“由于馬一浮‘心統性情’的心性論以‘性德’為中心、根源關鍵,并重視反求諸己,回歸性德,使得人性分內所本具之德性不受習氣之遮蔽扭曲,因此他特別重視會通儒佛二宗特別是宋明理學的修養工夫論,并形成其以‘復性’為方向的本體—工夫論。”馬一浮的“大創舉”為傳統文化的現代轉型提供的新范型對于克服“當代科技商業社會的發展所造成的道德價值失落和人的自我喪失的問題”具有重要作用。
作為融會儒釋道三家的大師,他固守傳統儒學的以實踐的修養為學問的主要途徑和歸宿,這也可以說是對以西學為源頭和法式的現代科學學術的一種批判。因為,將一切事物包括自身客觀化、對象化,是現代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的基本方法,認為不如此,其知識就是想象性的、沒有客觀有效性的幻象。而馬一浮則將此種知識歸為虛妄,歸于增長習氣、自私用智。這里涉及現代思想史上的科學與人生觀之爭。德性與知識、科學主義與反科學主義的問題是現代中西方思想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在此,筆者沒有能力對這兩種方法孰是孰非做評判,但很明顯,馬一浮是一位反科學主義者,用科學思維是難以理解馬一浮的。如果現代和現代性就是科學主義及其知識學術體系的話,那么,馬一浮就是現代性的反對者和批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