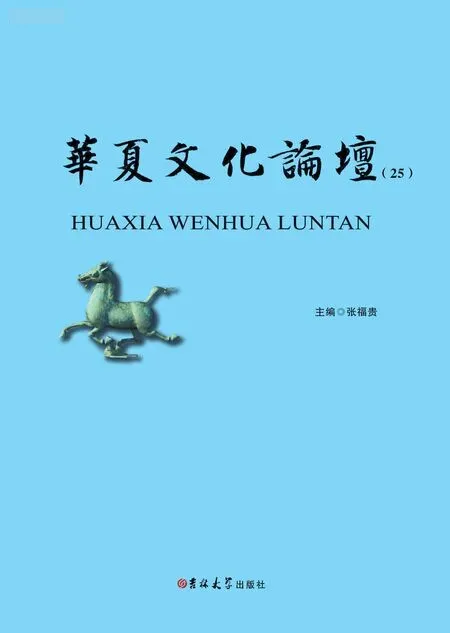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的美育中介
王 姣 張澍軍
藝術作為社會生活的產物,伴隨著人類的發展與進步。可以說社會生活是藝術的唯一源泉,任何一個歷史時期和社會形式下都有其獨特的藝術形式,而藝術之“美”則是美育中必不可少的教育元素。藝術也是藝術家對社會生活的能動的意識化反映。藝術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不是機械、刻板、消極的,而是一種積極的能動的反映,即毛澤東認為的“藝術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所以藝術的“美”是經過意識、思想加工且可以被大眾所接受的。生活元素通過藝術加工,最終形成的藝術之美具備了情感性、典型性、理想性,而其對于美育的價值也隨之升華,使之可以教化人性。因此藝術對于美育的價值是不言而喻的,其不僅僅是人對“美的規律”的掌握,更是對“美的規律”的發現、理解、反映、蘊意,所以源自生活且高于生活的藝術之美可以實現當代美育的目標。
藝術素養來自藝術,成為人固有的審美素養,更成為人對“美”的感知能力,“美”對于人類社會的影響有目共睹,作為“美”的典型代表,“藝術”的發展與影響,對時代、社會是不容忽視的。就如“文藝復興”對于社會發展的影響一樣,客觀且深遠,“復興”的原動力在于藝術家對藝術感知、藝術創作的變革,卻影響了社會發展,可以說是“有點起源”而達到了影響時代的效果。反觀思想意識化的藝術素養,對于社會的價值更加契合個體發展的需求,對于人的思想意識、認知能力、價值觀和人文精神的影響是客觀的,且存在于每個人的意識中,可以說每一個人都具備藝術素養,只是影響的程度存在差異,如藝術家的藝術素養可以幫助他創作更好的作品,普通人則可以更好地欣賞“美”,并具備更高的精神意識。可見藝術素養植根于思想意識,是審美意識的體現,是審美價值觀的體現,對于人的精神世界影響較大。
美育是一種審美實踐活動,離不開“美”的事物。大千世界的“美”,為人提供了生動、豐富無比的“美”的感受,這些鮮明的直覺形象充斥著人的感官,只要發現和體驗就可以無時無刻不感知到周遭的“美”,所以“美”總給人帶來生動愉悅的感受。美育引導人塑造、發現和體驗美的審美意識,此時“美”的感受無須那種耳提面命式的教導和說教,自然而然地就可以影響人的思想意識。美育所形成的教育體系和目標是要人在審美實踐中去直觀的感受和體驗,而不是學習數理化那樣具備抽象思維定式和概念界定,因此美育更加情感化、意識化,所塑造的感知美的能力也更加感性。延伸到美育對藝術素養的培育和形成過程,通過發現“美”的能力提升,幫助人形成良好的性格,即通過藝術陶冶作用來實現“人格”的塑造,藝術素養作為人發現美的基礎,也是人領悟“美”的重要精神意識基礎,在“美”的教化作用下改變人的思想意識,進而塑造美的“人格”,在這個視域下,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塑造是契合的。藝術素養對人格的內化影響效果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人格塑造需求,可以形成良好的互動和促進,思想政治教育可以借助藝術素養的培養和提升來滲透思想教育、人格教化的目標和內容,推動良好人格的形成,美育的教化作用在藝術教育、藝術素養的形成中塑造了“高尚人格”,無疑契合了思想政治教育對“人格”塑造的目標。
藝術素養具備了突出的美育屬性,其培育目標是影響和塑造“高尚的人格”,即通過藝術的潛移默化來感化人、影響人,使之可以提升自身的思想境界和人格水平,這一目標下“美”與“善”可以在美育的中介作用下形成關聯與互動。藝術素養的形成以及提升可以改變人對美的欣賞、理解能力,藝術中所蘊含的“美”可以被發現,并對人的思想意識產生影響,人就會懂得欣賞美、表達美。美育中對“美”的發現可以影響人的“善”念,善念增加、內化也必然引發人思想意識的改變,就可以實現“德”的塑造,并促進“德”的外化。由此可見,美育和道德修養培養對人都有著由內而外的影響效果,二者的契合之處是“人格”的塑造,即人格養成過程中實現內化,并在付諸欣賞、創作、行為規范時轉為外化具體行為。
藝術素養作為藝術欣賞以及發現藝術美的重要能力,也是一種審美活動,這與美育的審美實踐存在必然的邏輯關系。審美實踐活動中必然包括對藝術美的欣賞和體驗。由此可見藝術素養有著審美活動的特征,也應隸屬于美育中的藝術教育,且作為美育中的審美活動意識基礎而存在,是審美實踐的重要的思維過程、學習過程。藝術素養是人對藝術之美進行審視和理解的能力,可以說是發現美的重要手段,因此藝術素養可以推動美育的目標實現,就如馬克思所言的“音樂的耳朵”一樣,藝術素養是發現“美的規律”的重要意識、思想基石,只有具備藝術素養才能理解和發現美,才能被美所感動,進而形成美好的品格和情操。由此可見,藝術素養與美育之間存在從屬和必要關系,美育中包括了藝術教育的內容,藝術教育的目標不僅僅是讓人具備“藝術技藝”,更重要的是賦予人聆聽、觀賞、理解藝術美的耳朵、眼睛、頭腦,由此可見培養藝術素養是藝術教育的重要目標,自然也是美育的重要目標,畢竟只有具備了欣賞美的基本素養、自發意識、理解能力,才能更好地接受“美”所傳遞的“育”的內容和內涵。
藝術素養作為人對藝術形式、作品鑒賞和共鳴感知的基本能力,它具備美育的功能,它的主要目標就是影響人的審美意識、人文素養和道德意識,借助“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的教育方式,以“美育”為中介,將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相契合,把提高人的藝術素養,作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重要途徑之一,激發其對于人精神世界的塑造作用,使之更好地為思想政治教育服務,提升人綜合素質的同時也達到塑造“高尚人格”的目標。思想政治教育從本質上看是對人思想意識的教化,也是一種內化轉變外化的思想引導教育過程。通過各種途徑對人進行意識影響、思想教育,使得人的外化行為發生改變,促進人的行為符合社會發展、人類發展的需求,而人的思想和行為符合社會發展與建設的基本需求時,人自身的全面發展也不斷實現。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必須重視對人格的塑造,不論是使用何種教育方式,所需要達到的目標就是影響人的思想意識,并形成符合社會、自身發展的人格。健康的人格包括:良好的認知能力,可以很好地表達自我、處理人際關系、綜合分析與學習良好的性格,如自尊、自信、積極向上、自制力等;良好的自我意識,積極自我認知、成熟的自我控制、客觀的自我價值感、良好的自控等;良好的價值取向,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誠信意識、和諧意識等。
美育以“中介”的方式,嫁接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使得藝術素養的培養成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的重要途徑。中介的概念屬于辯證法、辯證思維或者辯證認識論范疇,是辯證思維體系下的重要概念。其概念界定也較為多樣,如蘇聯哲學家羅森塔爾·尤金在《簡明哲學詞典》中指出的“被用來認識客觀世界的中介是指思維對感覺材料的概括而言,感覺材料是外部世界作用我們感官而引起的直接結果。抽象的思維是間接的認識,它是以感官材料、生動直觀材料為依據的,沒有這些材料,就不可能有抽象的思維。運用到客觀現實上的中介表明,每一事物都和另一種事物相聯系,有了這種聯系事物才存在。”雖然在這個概念界定中,尤金將感覺材料定性為客觀世界和思維意識之間的“中介”有些片面,但是卻提供了一個對中介的定義思路。我國在《辭海》中定義中介:不同事物或者同一事物內部不同要素之間的間接聯系的哲學概念。在馬克思哲學視域下,中介是事物轉化的中間環節,事物可以是相關聯的也可以是對立的,任何事物、現象都存在必然聯系,此時各個系統之間就存在中介,中介使得系統形成一體,掌握中介可以讓辯證邏輯得以體現。
中介是各種現實事物之間或系統內部的樞紐,任何事物都存在必然的關聯,即使有些事物表面上并沒有任何關系。中介還是事物相互轉化的關鍵環節,沒有中介,事物之間就不會出現轉化,從而不能獲得完善和發展,這也是辯證思想的核心思路。任何事物都會發展和變化,這是客觀存在的規律,而其變化的結果往往與周遭的環境有著直接關系,此時事物之間的中介在發展和變化中也就會起到關鍵的作用。另外,中介不是孤立、簡單的存在,是特定認識領域或者過程,是人理解現象的重要基礎,這就是“中介”的重要意義。黑格爾指出,“如果中介或反映不被理解為絕對的積極環節而被排除于絕對真理之外,那就是對理性的一種誤解。正是這個反映,使真理成為發展出來的結果,而同時卻又將結果與其形成過程之間的對立予以揚棄”。中介作為哲學概念,所體現的客觀意義包括:
首先,中介是人的認識客觀存在的活動中不可缺少的環節,是一種積極認識的重要環節。好比人的認識是通過思辨活動開展,會形成不同的自我中介體系,在常見的政治、社會、藝術、宗教等行為中都存在復雜的中介體系,它們相互交織,相互影響。對某種客觀體系的認識不是簡單的對經驗事實的機械反應,而是通過一系列的實踐活動和中介體系關聯、理解才能獲得客觀的、理性的認知結果。
其次,認識的主體與客體互為中介,形成特定的認識領域和認識過程。認知中,中介體現的是復雜的滲透、融合關系,系統之間互為主客,相互認知和理解的過程中,中介也被認知。在這個過程中主體、客體互為中介的基礎是實踐,其也是二者相互聯系的認識領域、過程的手段。如藝術源于生活卻高于生活,藝術作品是藝術家思維意識激蕩所產生的結果,更是藝術家在對社會、生活、自然的認識領域和認識過程中生活常態的反映,此時生活等外物是客體,藝術家是主體。再如道德修養的主體和客體也可以互為中介,教育者是主體、受教者是客體,他們之間存在思想、方法、內容等中介。可見,諸多認知領域和過程中,其主體、客體之間必然存在中介,只有具備中介的聯系才能讓主體、客體產生互動,才會有必然的“結果”。
最后,主體和客體、主觀與客觀之間存在相互中介過程,中介的作用是揚棄主客體之間的對立,不斷推動認識的發展,進而實現主客體的共同進步。縱觀人類的歷史發展,其中必然存在不斷的認識和改變世界的過程,比如生產實踐與科學認知即為主觀性和客觀性的中介,人在生產實踐中發現客觀規律,進而形成主觀認知改變,進行形成科學知識并應用其改變世界,此時客觀規律與科學知識之間的中介是勞動實踐,這個認識過程使得主觀接受客觀規律,而改變原有的片面的主觀認識。反之,在應用科學改變生產實踐的過程中仍會發現新的客觀規律,此時科學就成為生產實踐與客觀規律的中介,主客體之間發生了轉換。在藝術發展中,一些代表先進階級意識的藝術形式或者符合時代的藝術形式,替代了原有的不適應時代發展的藝術形式或者意識,也是一種主觀與客觀在中介作用下的認知過程。
中介普遍存在于形式和意識之間,即在事物形成的客觀形式中蘊含著某種思想意識作為中介,使其可以被人所關注、理解,最終形成主觀認識。這就是一種客觀照進主觀的認識過程,此時中介的存在是客觀的、必然的。不論是何種事物,只要被意識所認知就必須存在某種思想意識作為中介,就如同哲學、宗教、實踐、藝術這四種掌握世界的重要方式,其中必然蘊含著現實與意識之間的中介轉化。如今天探討的藝術素養作為美育育人目標之一,其在美育過程中幫助人與藝術作品實現意識交流,從“美”中獲得情感和精神慰藉,是感官到意識,再從意識反饋到感官的復雜的“意識過程”。好比觀看一出喜劇,如何獲得精神的愉悅,獲得這樣程度的精神愉悅,乃至獲得“感動”,這些都需要人具備感知、理解能力才能得到體驗。這些體驗恰恰是因為客觀和主觀、客體和主體之間存在“中介”的影響,這些中介是多樣的,也是復雜的,但不論是何種“體驗”“感悟”,都存在中介的影子,這也是不可否認的必然。
縱觀歷史,階級形成和國家產生以來,統治階級對公眾的思想教化實踐活動客觀存在,始終沒有停止。思想教化的目標就是讓公眾形成相對統一的,符合統治階級意志的世界觀、價值觀,從思想意識上實現對公眾的“同化”,使其為統治階級建立的國家服務。雖然“思想政治教育”沒有被明確定義,但是在任何國家體制下都客觀存在。“思想政治教育”的定義是隨著無產階級政黨的誕生和社會主義國家發展而逐步演變而形成的。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主義者同盟的章程中就明確指出“宣傳工作”的重要性;列寧在沿用“宣傳工作”的同時提出了“政治工作”“政治教育工作”兩個概念;斯大林在1934年提出了“思想工作”“政治思想工作”的相關工作內容。我國在黨和國家的建設中沿用上述概念,直至1951年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初步理念和設想。毛澤東在1957年提出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但是具體工作仍沒有統一定論并形成體系。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確定了有關黨員、公眾思想意識教育的相關工作,即“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并以此形成了相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內容和工作重點,思想政治教育的基本范疇包括:個人與社會、思想與行動、教育主體與客體、內化與外化、教育與管理等相關內容和方針。此后思想政治教育以及相關工作成為我國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其概念被界定為:社會或社會群體用一定的思想觀念、政治觀點、道德規范對其成員施加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影響,使他們形成符合一定社會、一定階級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會實踐活動。由此可見思想政治教育對我國而言即為對群眾思想意識引導和改善,在社會發展中縮小精神文明與社會物質文明之間出現的差異,使得人民思想意識與社會發展相適應,推動人的思想品德塑造,使之思想意識和行為符合社會發展的基本訴求,尤其是適應社會主義發展、共產主義建設的目標。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在于,引導和塑造人良好的自我意識。可以通過意識引導理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在追求實現自我價值的同時也不會損害社會、他人的權利。激發人對于自我發展的追求欲望,優化自身的生存狀態,實現自身意識完善。激發人良好的發展能動性,使人具備認識、把握世界的能力和自覺要求。塑造意識造就一種自我發展和自我完善的意識趨向,良好意識外化為良性行為,在轉化中就形成了發展的精神動力與客觀規范的行為轉化,為人設定發展的價值坐標,明確發展中“舍與得”的標準,由此可以幫助人拓展精神世界的發展空間。從其本質上看即為通過各種手段教化人的思想意識,改變人意識中的不良形態,使之形成高尚的意識、人格和行為模式,并使之適應社會主義的發展和建設,達成精神文明建設的目標。
美育突出的是人對美的價值的定位,是通過對美的追求發現美的價值,獲得精神愉悅和人格的完滿,引導人進行價值審視,如遇到金錢、物質所帶來的享受與自身審美價值發生沖突的時候,通過自身對美的價值判斷來進行取舍。美育也可以豐富人的精神體驗,人在欣賞美的過程中獲得滿足和幸福。如英國H.A·梅內爾指出,“關于藝術品的基本美學問題,應視其能否從藝術品中得到滿足,以便它能長久地滿足人的要求,并為人類生活的整個幸福添磚加瓦。所有好的藝術品都能在適當的條件下,使人從欣賞中獲益并得到滿足,這一切都是建立在人類的身心的提高和豐富,并以此獲得長久的幸福的基點上”。美育中藝術美的價值在于可以提供豐富的精神體驗,可以幫助人獲得精神上的美滿和幸福。
思想政治教育要培養的道德修養、意識形態、價值觀等同樣具備精神價值,可以借其人塑造高尚人格。在真善美的視域下,美育與思想政治教育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人對“真善美”的主觀認識和追求是美育與思想政治教育形成的重要紐帶,美育的作用即為以美引善。究其本質,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是對人情感與意識加以引導、教化、修正。思想政治教育所承載的不僅僅是道德、意識的標準,也是一種情感、意識上的認知、判斷以及行為外化。如前文所述,思想政治教育的價值在于培養、形成良好的自我意識、人格乃至良好的德行。客觀看人的意識往往與精神、情感直接關聯,因此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往往不能脫離情感、精神而孤立存在,其塑造的良好行為也不能離開意識形態的支配。此時美育對人的思想意識影響就成為以美引善的源動力,美與善之間的必然關聯使得“以美育德”成為思想政治教育過程中所倚重的手段。
中介作為一個哲學概念,其貫穿的不僅僅是主體與客體之間的聯系,也存在于諸多事物、系統之間。藝術素養是一種精神境界和能力,在美育中有著重要的精神塑造價值,是發現美、欣賞美、塑造美、創造美的重要意識自覺,因此其對于美育而言是培養的目標之一。思想政治教育也是一種對精神、人格的塑造、意識形態的糾正,二者之間都與精神和意識共通。此時藝術素養作為美育的目標,通過美的教育方式和渠道可以對人的精神和意識產生更加直接的影響。如蓋格爾認為,“當我們談到一個藝術作品所具有的精神內容的時候,我們所指的是兩種各不相同的東西:我們首先指的是蘊含于主題之中,蘊含于藝術作品所表現的客觀對象之中的精神內容;其次,我們所指的是藝術家的藝術觀念所具有的精神內容,這種精神內容是通過表現方式被表現出來的”。“美”中自然蘊含著精神境界和思想意識,借助這種精神傳達,美育就可以改變道德意識、人格修養,進而使得精神意識得到升華。美育以精神屬性為紐帶成為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道德修養的中介,所體現的是“以美育德”理論的基礎。美育促進藝術素養提升,可以提高人的審美能力和審美價值,是以美引善的重要途徑,如果人可以發現美、感知美,感知藝術中的精神內涵、意識價值,則更容易形成善良的人格意識,此時其道德修養、意識形態也必將獲得良性提升。美育這個中介,將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相連接,借助藝術素養的提升,改變人的審美價值觀,使得人具備高尚的道德情操和思維意識、行為模式,更可以塑造高尚的人格修為。此時,思想政治教育的目標也同步完成。
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是共通的。首先,藝術素養和思想政治教育塑造意識的目標共通,人類社會的發展是人類運用智慧來發現和改變世界,并使得自身脫離“自然”存在,從而獲得客觀和主觀的生存滿足。單純地將人的生存、活動界定為獲得更多的生存、生活資料,顯然不夠全面,因為在物質生活滿足后,人的精神世界發展和建設被關注,而精神層面的滿足和發展則成為推動人獲得生存滿足后,仍不斷發展自我的重要源動力。人類從動物性存在提升到人性存在,其表象是“物質”的改變,是生活、生存資料的獲取和豐富,其內核是人類精神世界的豐富與發展,良好的意識形態可以幫助人獲得良好的人格修為、人際關系等,形成適應社會和自身發展的良好意識形態。藝術素養是人發展自身所造就的審美意識。人類生活的產生和發展離不開人精神世界的發展,畢竟推動人類進步的科學技術所形成和發展的基礎,是人類獨立的思考與解析,因此精神世界的發展和進步才是推動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源動力。藝術素養是人對“美”的理解,而思想政治教育則要塑造規范的意識,自古就將良好的德行定義為“美德”,可見人對于“美”的追求早就升華為對“德”的標準。德行是思想政治教育人的重要內容之一,形成良好的意識和德行也是其目標,所以從藝術素養和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識視角看,二者存在必然的“共通”之處,即塑造“美”的意識。
其次,藝術素養和思想政治教育塑造意識的過程共通。藝術素養是一種人對美好事物的理解和鑒賞能力,其必須依靠長期“美”的熏陶,借助審美經驗和過程來塑造良好的審美意識乃至行為。思想政治教育的過程也是借助諸多外化的教育形式來影響人的意識形態。從過程而言,二者都是由外而內的塑造過程。藝術素養的形成依靠的是“藝術美”“自然美”“社會美”“人文美”等,借助外部營造的美好氛圍,使得人對于“美”的理解更加全面和高尚。思想政治教育中也借助諸多社會實踐、榜樣力量、理論解說等來幫助人客觀地認識世界、社會,由此形成相對趨同的意識形態,建立共同的社會目標乃至精神訴求,最終產生社會合力而推動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發展。由此可見二者塑造意識的過程都是對人“精神”世界的營建,所借助的材料都是客觀現實、客觀環境、客觀規律。
美育作為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的中介,是二者之間的重要紐帶,藝術素養對思想政治教育的直接影響,是“以美引善”的客觀本質,其關系、作用、價值體現是通過美育中介來實現的。藝術素養與思想政治教育之間存在“意識”上的共通性,對人的自我意識和自我發展有著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