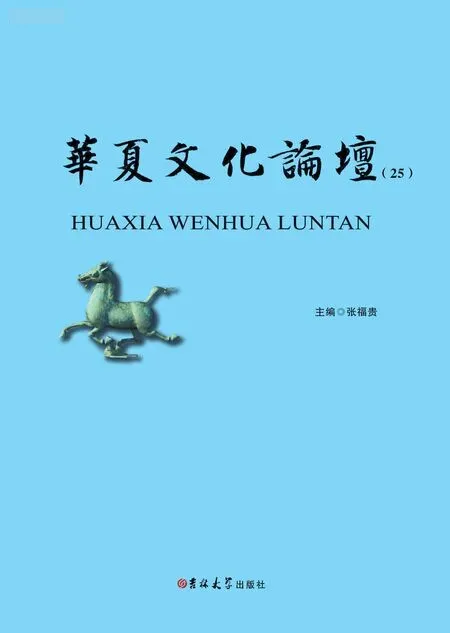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非現實”的現實:“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形上追問
于 洋 殷曉峰
產生于20世紀20年代法國的超現實主義,作為重要的文藝流派之一,深深地影響了文學藝術的創作風格、審美思維和形上追問,“在雕塑、建筑、電影特別是繪畫等方面,直到今天,我們仍然可以感受它的重大影響”。因為,超現實主義以超越現實的方式重新理解了現實,提出表征現實的創作路徑、體驗現實的審美原則、追問現實的形上準則。從超現實主義的先賢堅持“解放欲望”開始,超現實主義就在超越浪漫主義的意義上重新定義現實的本質。從超現實主義的思維來講,現實不是實存的固定,而是主體反抗實存的固定性與給予性能力的本質力量的具體化。超現實總是能夠從日常的平凡中發現神奇與超越,從夢幻與潛能中發現真實與力量,從幽默與重組中發現邏輯與秩序。超現實主義以非實存的“非現實”重新理解現實的思維范式一方面來源于先鋒文藝家對一戰的反思,另一方面則來源于資本主義發展邏輯宰制的強化。超現實主義從“夢境”“潛能”“欲望”中來重新挖掘現實的本質,并不是簡單地要把現實的本質還歸于非理性,而是理性安排下創造力缺失的一種形上突圍。
超現實主義繪畫作為超現實文藝流派中的中堅力量,一方面具體地體現了超現實主義的形上追求,另一方面以獨特的藝術話語與創造方法推進了超現實主義的形上追問。因為,繪畫雖然在直觀上是借助于物象、色彩、形體等來表達對存在的理解與追問,本質上卻是本體語言、色彩要素、創作技法、審美體現來建構對現實的理解。超現實主義繪畫特別以其“怪誕”的創作主題、“離奇”的創造手法勾勒、反應和實現藝術家心中的現實本身。一方面以作品呈現的方式拉開與現實的“距離”,以藝術的方式再現了現實的維度,具有否定性與超越性,在審美過程中通過藝術家與觀者的再度融合與創造形成作品的主題,表達作品的意義;另一方面則以具象化的作品肯定了藝術家對現實超越性的理解與建構,通過觀者的審美共鳴從而達到自我的內在創造性與現實實存性的辯證統一。因此,超現實主義繪畫轉向內心、追求現實的藝術創作不是還原既定的物象存在,而是對現實的一種形上追問。
一、現實與超現實
安德烈·布勒東在1924年發表了《超現實主義宣言》,批判了現實性的平庸、道德的自負、價值的固化,提出了精神的自動主義。這既宣告超現實主義正式登上舞臺,又表達了一種關于現實的觀念。超現實主義對現實既存性的否定、邏輯確定性的蔑視、價值一貫性的輕視,一方面擊中了理性主義現實主義現實觀的根本問題:對人主體性的限定,另一方面又提出了由人主體精神產生夢、潛能等內在因素的存在論意義。或者說超現實主義力圖走出實證主義的思維范式與價值觀念來重新理解現實,從而將人的精神性力量再度推到前臺。超現實主義從精神先驗層面來追問現實的理念,是對實存邏輯與定存的一種突破,通過糅合人的本能、潛意識和夢等精神經驗來重塑現實的理論與價值追求,展現了一種近乎幻想的現實觀念。超現實主義以此表征了無意識的存在論意蘊,動搖了實證主義現實觀念的存在論根基,超現實主義畫家則以夢幻的奇異、精神的自主和方法的另類將此匯聚于作品之中。超現實主義繪畫以此“撕裂”現實的方式,藝術地強化了非現實,以“縫合”非現實的方式表征了對現實的向往。
超現實主義繪畫藝術化地實現了超現實主義對現實的否定,凸顯了超越現實的非現實的存在論意義,也敞開了超現實主義繪畫創作的基本維度。其一,在主觀主義超現實主義畫家看來,超現實主義繪畫在突破傳統繪畫范式的基礎上重塑了繪畫。弗朗西斯·皮卡比亞和塞爾·杜尚就認為,“我們所接觸到的不再是繪畫,也不是詩歌或者繪畫原理,而是一個早就向其自我極地進發的人的某些內心景致。”面對人的內心景致轉變了繪畫主題選取的藝術視角,表達人的內心景致革新了繪畫創造的技法邏輯,呈現人內心景致的現實生成了繪畫審美的價值觀念。其二,超現實主義繪畫沉溺于無意識自動狀態的藝術態度,以自主繪畫的方式確證了無意識的現實性。自動主義繪畫的創始人安德烈·馬松總是以動物這種自然存在物與建筑這種人為創造物組合在一起,在自主“寫作”中表達自己的現實觀念。比如他的作品《自主繪畫》(Automatic Drawing
)就顯然超越了繪畫物象的前定限制,在詩意的靈感中跨越了現存現實的界線,使人從理性的狹隘中解放出來的同時創作了一堆由自動線條組成的圖像,從而確證不被意識、不被干預的內心的現實性。其三,超現實主義以打破現實的方式重組現實,預示現實并非是現存在的物象定在,更是人重組的存在。被譽為“最超現實主義的人”胡安·米羅(Joan Miró)就特別善于在打破中重組,“沒有任何人能夠像他那樣,準備同不可能聯合在一起的聯合,并且無情地把我們不敢期望到其破碎的東西打碎。”在《小丑的狂歡節》這一作品中,我們就發現各種現實不可能組合成物象自然而和諧地共存于畫面之中,無序與凌亂只是實存留給我們的刻板印象。藝術家呈現給我們的現實恰恰就是這種跨界的組合,這一方面符合人存在不斷超越自我界限的事實,另一方面也體現藝術家被所謂現實捆綁的不自由。超現實主義繪畫以魔幻的藝術手法與視角沖擊力,在與常識的現實拉開距離的前提下建構一種能夠體現的現實存在。在超現實主義繪畫創作中有兩種基本創作手法,一是擬態的抽象,在形變的意義上來表達潛意識、夢境等非理性意識的現實支配性;一是割裂邏輯邊界性的幽默和自動寫作,在與實存的距離中重審現實,表達無意識。無論超現實主義繪畫中的寫實還是精神表達,都力圖超越既定的束縛,追求現實。或者說,超現實更加認可那種必然實現出來的“非現實”本身。在超現實主義繪畫中,固定的時間與空間不再是物象與主題的標準座架,恰恰是錯置的時間與空間才是現實的表達方式。就是時間與空間本身也是變動不居的,任何歷史空間中滯留下來的節點,都不過是時間與空間的偶然相遇之后的永恒記憶。1931年達利創作的《永恒的記憶》無疑就是代表。時鐘的折疊與空間的死寂不過宣布現存現實生命力的耗盡,螞蟻和蒼蠅活動于鐘表之上則預示著現實由偶然際遇組成,平靜如鏡的海和一馬平川的海灘不過是固定下來的實在,時間的折疊不過是隱喻了實存現實觀的非現實性。因此,超越永恒、獲得生命才是現實本身存在的方式。因此,當觀者站在諸多《永恒記憶》這樣的作品面前的時候,其顛覆常識的物象形態絕對不是藝術家怪異與個性的表達,而是藝術思考現實的思想沖擊。
超現實主義繪畫不僅不再停留于常識的時間與空間座架,更愿意借助形體錯置與嫁接來表達現實的存續。超現實主義打破物象形體、重構生存形態是對事物的質疑,藝術家在作品中對物象形體進行拆解、形變和夸張,然后在組合、安置和復寫,一方面已經打破形體給予觀者視覺上的沖擊,另一方面表達著主體意識對存在的重新安排。這樣的繪畫意味既定的形體下面隱藏著不為人知的秘密,錯置與嫁接不過是表達現實可能存在的面相。在恩斯特所創作的《女子、老人與花》這幅作品中,女子的嬌態與柔美不再通過肌膚的質感與神情的媚惑來表達,一個大大扇面作為青年女子張揚個性的頭飾,質感突出的工業化的馬甲勾勒出青春的體態,臀部的肌理構成自然身體的渾圓,手指的纖細結合著胳膊的豐柔,……這些元素共同構成了對一個年華正茂女子的刻畫。這一重構的女子,我們第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一個與現實同行的時代女子。而與此對比的老人沒有特意去描繪面目的滄桑與行動的遲緩,只用褲管中的棍狀物就完成對了衰老的表現。這是什么?這就是現實,年齡不再借助于身體的體態來表現,而只需“簡單”借用時代性標志形體就達到了絕對的視覺沖擊。這自然會讓人們去思考一個問題,現實是什么呢?是那個老態龍鐘的病態,還是嬌媚叢生的脂粉?都不是,是現實生活中將現實的元素自身構成化的存在形體。超現實主義繪畫把現實從現存的定在拉到了現實存在的表達之中,這種表達在于現實總是由于某種內在的神秘力量不斷錯置已有形體,嫁接成全新的樣態,銘記著時間與空間的印跡。
超現實主義繪畫還特別注意超越現實所帶來的對比沖擊力,一方面是藝術家以荒謬的視覺效果將現實與超現實進行二元的拆解,另一方面是觀者在審美體驗中不斷去縫合這種對比,從而形成一種改變現實的內在力量。談到這里,我們就不得不簡單地述及超現實主義入世的政治取向。如果我們考查超現實主義的發展史就會發現,超現實主義深受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將改變世界的政治實踐作為自己重要的內在追求之一。這一點其實也深刻地體現在超現實主義繪畫創作的方法論與審美觀之中。從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圖像特征上看,我們發現超現實主義繪畫堅持超越現實的圖像表達、體現藝術家個性與幻想的色彩表達和體現“精神自主”運動的主題表達。超現實主義繪畫首先就是拒斥實體理性對圖像的思考與安排,在激活精神內在動力的前提下去表達藝術家和觀者內心的現實世界。這一方面體現了超現實主義繪畫具有突破現實陳述的藝術勇氣(在此意義上超現實主義是先鋒派中不可或缺的一員),另一方面則表達了現實必然要通過某種渠道表達自身。而且,超現實主義繪畫特別注意色彩的沖擊力,一方面力圖用絢麗的色彩使觀者脫離現實的灰暗達致內心的純凈,另一方面則希望表達現實存在可能還有另一個樣態。精神自主運動作為超現實主義流派的理念一直體現于超現實主義繪畫的作品之中。正如布勒東所說,“因為他們相信人類只能再創一種多少是有關他之事物的適巧意象,畫家們在選擇他的對象這點上所表現的態度已經太過懷柔了。他們的錯誤乃是相信一個對象只能從外在的世界里獲得,或者相信它只能從此地獲得……這是一個不可原諒的舍棄……如果造型藝術乃是在于迎合一種現實價值之完全的根本的需要,在于迎合一種今日大家所同意的事物的需要的話,則他們因此更應該尋求一個純粹內在的世界,不然就停止存在吧。”
因此,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形體構造、表現語言、創作手法造就了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獨特的藝術地位和獨立的藝術風格,其吸引人的色彩、震撼人的形體以及感動人的體驗給觀者帶來獨特的視覺沖擊與審美享受,更使觀者不得不進入到藝術家的生活背景、創作時代和生存體驗中去追問藝術家的形而上學拷問。因為,在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創作中,藝術家們以藝術的手法否定了現實、再創了現實,在消解現實與超現實的實然界限的藝術表現與審美體驗中,一方面通過藝術化表現超現實的方式使人與現實拉開距離,另一方面則以作品具象化非現實的方式使人重回現實。這意味我們必須深入討論超現實主義繪畫中為什么必須堅持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的問題。
二、肯定與否定的繪畫統一
超現實主義繪畫超越本身就意味著否定。但當我們綜觀超現實主義繪畫的時候卻發現諸多藝術家都在自己的創作中不斷肯定早年的生活經歷、曾有夢境臆想以及時代給予他們的生存體驗等。肯定與否定的并存似乎肯定了超現實主義繪畫是一種矛盾叢生的藝術。事實上正是肯定與否定并存于超現實主義繪畫的創作邏輯和審美邏輯之中的時候,才構成了超現實主義繪畫獨特的魅力,也才構成了超現實主義繪畫對時代與存在的藝術反思。總體上而言,超現實主義否定的是作為幻覺的實存、表達確定的關系和呈現意義的物象,肯定的則是生存體現的現實、夢境與無意識的存在性和潛意識的自由性。當然,超現實主義繪畫作為一種激進的藝術流派,其更多注重的是否定意識的藝術表達,而非肯定意識的藝術再現。如此看來,超現實主義繪畫雖然強調潛意識、夢境、神秘性等非理性要素,本質上卻是理性主義的方式重新追問“畫什么”與“怎么畫”的根本問題。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成其核心的方法論就在于以否定既成繪畫主題的方式重構和肯定了現實本身。
超現實主義繪畫質疑物象與指稱之間的確定關系,以敘述手法切入主題的同時去肯定藝術家獨特的生存體驗。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我們知道一個人的生存經歷都會內化成個體獨特的潛意識,人們潛意識的表現都可以在還原其形成過程的時候追溯獨特的生存經歷。公認的觀點是認為超現實主義繪畫受意識理論、精神分析和馬克思主義的深刻影響。這意味著,我們必須深入到超現實主義繪畫否定物象與指稱之間確定性關系的問題之中去追問其否定性的本質。按照李夏商先生的觀點,超現實主義肯定具象世界與抽象世界之間的統一,在渴求內在精神要素真實性意義上否定外部世界的具體性,是超現實主義一貫的基本邏輯。因此,超現實主義的否定本質上是對現實深化的理論策略,其肯定則是印證非現實之現實性的根據。如果我們把這一觀點具體化為超現實主義繪畫的時候就會發現,超現實主義繪畫形成了處理肯定與否定的獨特的藝術路徑。
在超現實主義繪畫創作中,無論是復制、截取既定形體,還是自主繪制無意識的潛在意識,抑或拼貼與重組,都具有濃厚的敘事特點。也就是說,超現實主義繪畫的本體語言、表現色彩與創作技法都具難得的直白性。這既使超現實主義繪畫和傳統繁復的描繪區別開來,又使之和現代其他流派專注色彩和形體區別開來。平實的敘事,本質上就是對存在絕對的肯定。但是,超現實主義繪畫的超越性又使之不斷否定。敘事作為人類講故事的哲學方式,一方面將自己與動物區別開來,另一方面又以內在的線索肯定共同體的存在。敘事平和的語言與直白的言說淋漓盡致地體現了肯定的邏輯。就此而言,當雷尼·馬格利特以敘事的手法創作超現實主義的名作《情人》的時候,我們看到的不是愛情的熱烈似火,而是愛情的朦朧與曖昧、距離與無間。其肯定愛情的方式簡單直接:以白色面紗否定那日常愛情的卿卿我我,肯定了情人之間因獨立而愛得深沉。白色的面紗是否定情人之間距離的藝術話語,面紗相依的陰影則是情人之間的無間與親密。我們無從知曉面紗背后男女的俊俏與姣好,只知道情人的關系產生于相互吸引的異性之間。諸如馬格利特的敘事手法作為超現實主義繪畫的用語方式我們還可以舉出許多,如達利的《我媽媽的肖像》等。但如果我們深入去體味這一用語的方式就會發現,正因為超現實主義充分發掘了敘事語言在藝術表達中的肯定與否定的辯證統一性,才使得超現實主義繪畫在形象而夸張的色彩、零亂而穿越的構圖中內蘊著嚴密的故事情節。這也是為什么說有學者認為超現實主義繪畫本身就是非理性的理性敘事。
否定作為超現實主義繪畫建構超現實意象的創作方法,其根源則在于對常見物像部分或者是重復的肯定。正如前面我們提到的那樣,復制、重組、再構是超現實主義繪畫經常采用的創作方法。而當我們駐足于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之前時,我們自然就會發現構成超現實意象的那些要素與成分我們都似曾相識。為什么呢?因為那些都是來自對日常不可轉移關系物像否定之后的解構要素,而日常生活的邏輯與體驗又使之躍然紙上。這不得不說是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的重要魔力之一。因為,超現實主義繪畫在對常識(當然直接對象是物像)的從屬性與視角否定中,凸顯了日常存在不可見而又現實的一面。或者說,超現實主義繪畫之否定是將主體從常識中拉出來的藝術手法,而這種藝術性的拉卻是要根本上肯定常識性的存在。這當然和超現實主義幾次宣言中提出的改變現實、解決人生問題的宗旨分不開。但更為重要的是,超現實主義這種基于肯定的否定在直觀上打亂物像實存、引發視覺沖擊的同時,更讓主體深入去探問那物像、主體和意識之間的內在關系。也正因為如此,才有超現實主義繪畫中將光的白畫成色的黑,將活的馬與死的樹交織在一起,才有石頭一樣的蘋果和不是煙斗的煙斗這類的藝術“奇觀”。表面上看,這是語言上能指與所指的混亂,實際上卻是“意象”的含混與藝術的挪移。其根本目的在于,在重組與建構之中,貫穿一種“扯斷日常聯系,另眼看世界”的幽默觀念,表達一種主體超越世界的認識論方式,建構一種主體生成的存在觀念。
否定更是超現實主義畫家陌生化現實、肯定藝術超越性的創造方法,不僅使超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具有獨特的視角效果,而且更加凸顯了否定作為創作方法的對于精神的影響力。我們知道,任何一種藝術創作都力圖與現實拉開距離,但是超現實主義陌生化常識的方式特別值得人尋味。因為,超現實主義繪畫通常將自由拼合作為否定常識定在的藝術方法。拼貼似乎是藝術家對物像、時空的隨意安排,本質上講卻是藝術對既有秩序的懷疑與否定,以及對新秩序的設想與追求。問題在于,經過拼貼創作的作品所呈現出來的畫面與藝術家所要表達的主題之間的統一恰恰是對拼貼之否定性的藝術肯定與存在理解。而且,超現實主義的拼貼類似波普二維組合對象的藝術風格,但是卻比波普拼貼藝術更加激進和徹底。特別是超現實主義通過對空間的切割與拼貼更是改變了日常物像的呈現方式,一方面使拼貼之后的畫面具有獨特的立體感與層次感,另一方面是空間與物像之間的拼貼更加肯定了物像在空間中呈現的事實以及空間感表達對物像分割與組合的依賴。這意味著在超現實主義繪畫的拼貼中,物像與空間之間的關系被藝術進行了打亂與重構,其反常的視覺效果與幽默的藝術風格既讓人體驗到藝術眼光的犀利,又讓人內視地直面自我潛意識。無論是達利的《記憶的永恒》還是《天降》,或是馬格利特的《愉快的捐贈人》,無一不是超現實主義繪畫中拼貼的代表。當我們遭遇這些藝術作品的主題與畫面,直觀的感覺是藝術家在和我們開玩笑,而一旦我們沉浸于作品之中時,我們會突然發現畫面本身就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斷地無意識重復的活動而已。這種直指內心的審美觀照,顯然肯定的不是畫面上雜亂無章、違反日常的拼貼,而是人內心那個不受理性規制的潛意識自主的表達。或者說,藝術家通過拼貼的方式,在否定日常中呼喚出了另一個真實的主體。
因此,超現實主義繪畫在創作方法上的否定性并不是形而上學直觀否定,而是融合肯定的藝術方法。對肯定與否定的藝術統合,更切合了超現實主義繪畫表達夢境、表征潛意識的存在論追求。客觀地講,超現實主義繪畫因其對物像、時空乃至意義的一種割裂與重構,很容易使人們產生虛無主義的印象,但是超現實主義繪畫作品的完成因其否定與肯定的統一從來都不是由藝術家自身獨立完成的,而是由觀者在審美過程中不斷內視、不斷想象、不斷增加而完成的。因為,否定本身就具有激發象征意向的藝術功能,肯定則有主體確證功能。超現實主義繪畫雖然遵從繪畫語言不能從單一視角解讀的傳統,但是卻更加依賴觀者的主體性體驗及其象征性意象的闡發。比如馬格利特就特別注重“幻覺景象”的象征性意象問題。其“逼真的”超現實主義作品《錯誤的鏡子》就極為具體地體現了超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根本特點。因為,眼的自然形態與鏡子的明澈組合,加之黑斑的中間凸顯,以及鏡片內在的天際等等,我們顯然可以將之解讀為自然物像的拼貼與組合,但是我們會更加看重其凸顯出來的象征性意象。我們會去追問,錯在何處?是物像之錯?結構之錯?還是我們主體的視覺之錯?一旦我們追問這些問題的時候,我們自然就會開始深切地關注我們的眼睛之視覺功能。是還原?還是再照?這些問題會層出不窮地映現在我們的腦海中。這一過程顯然不是單一的作品呈現,而是觀者象征性意象的產生以及作品的完成。而這恰恰就是對否定與肯定的存在統一。
三、守護繪畫本體與追問存在
超現實主義繪畫之超現實,并非是脫離現實的不現實,而是在對傳統繪畫的批判與重構中,以“純視覺藝術”守護繪畫本體,以無意識的“觀看”來追問存在。雖然超現實主義借助夢境的看與依賴精神分析的純粹受到了實證主義的詬病,但是超現實主義繪畫以超現實的現實觀念突破現代主義繪畫同一性邏輯的宰制卻從根本上推進了對存在的藝術追問。
超現實主義繪畫夢境的看與精神的純粹是突破不在場隱喻控制的藝術方法,在反叛傳統繪畫同一性邏輯的基礎上重拾繪畫本體的藝術追問。傳統繪畫之所以走向非藝術,成為社會敘事法則的線上木偶,根本原因在于藝術家之看不是主體之看,而是社會現實符號傳達的方式。繪畫本體與繪畫主體的遮蔽源于社會現實的藝術化,而非藝術現實的社會化。超現實主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根據精神的純粹性與夢境的非現實性使繪畫藝術一方面獲得藝術語言的獨立,重述繪畫的本體;另一方面則是邏輯中斷的幽默使繪畫藝術擺脫歷史與現實的糾纏、價值與文學的支配。當超現實主義繪畫以否定的方式質疑形體再現與語言指稱的同一性的時候,就從根本上切入了繪畫語言的本體性問題。馬格利特在《詞語與圖像》這一著名的語言—視覺的文章中重點談到了物像符號化的任意性、取代性和現實性的問題。他的這一觀點顯然是深化與推進了達利對視覺與物像符號相對獨立的思想。視覺語言與符號語言的平等在傳統繪畫因同一性宰制而消弭不現,因而凸顯視覺語言對于現實的表達就成為繪畫核心的藝術追求。因此,在馬格利特《這不是一只煙斗》這一作品中,符號語言與視覺語言之間的矛盾與差異表面上看是藝術家生硬的否定,實質上講卻是在否定一致性的前提性追問視覺語言的不可還原性、不可轉述性等本體論特質。如此看來,在超現實主義繪畫中,視覺不是認識的補充與物像的再現,而是對現實的把握。這一方面因為藝術和哲學、科學一樣是可以直接觸及真理的文化形式,具有天然的純粹性,另一方面則是因為藝術家切近世界的方式是藝術的直觀,類似于現象學的方法有不可還原性。超現實主義繪畫正是看到繪畫語言這種獨特的本體性,才在繪畫的創作以純粹的精神與不受社會“污染”的夢來形成創作的主題和言說的方式。
超現實主義繪畫在追問繪畫本體的過程中,通過逼問繪畫語言內涵的方式切入了對主體如何確定所指與能指的存在論追問。超現實主義繪畫在此完成的形上追問主題的轉換,預示了物像的逃逸詞匯與繪畫的可能性。這意味超現實繪畫只有重建本體才能夠真正融合主體的所指與繪畫語言的能指問題。這就意味著畫家不再是在看世界,而是表達世界,無論是夢境的內涵還是精神的純粹,都是藝術家體驗的現實本身,也是其追求的現實本身。所以在馬格利特的《望遠鏡》中,我們看到透明玻璃的“藍天與白云”和窗戶縫隙中的“漆黑無邊”。這既意味看的貧乏,又意味在的真實;既體現出看的無力,又體現出真的穿透;既呈現了想象的必要,又呈現繪畫的必需。也就是說,在超現實主義繪畫看來,繪畫語言作為一種本體,不是對物像的體會,而是現實的自我呈現——無論呈現的內容是夢境還是自動寫作表達出來的精神的結構。因此,超現實主義通過繪畫語言表達的本體性,不僅捍衛了繪畫藝術的獨立性與不可還原性,而且意味繪畫的本體其實就在于作品本身——那種自然地呈現出精神的內在性與本體性的作品。如此看來,超現實主義繪畫鐘情夢境與精神,并不是因為這二者是現實不同的另類存在,而是因為夢境和精神能夠從本體上超越社會文化的預設與物像系統的干預,是現實藝術澄明的手段與方式。這從根本上解決了實存作為被符號截取與閹割存在的局限性問題,是對符號秩序的一種藝術反抗和對現實存在的藝術建構。在此,我們可不必借助弗洛伊德凝縮和位移的夢就可以感知和認可拉康的重要判斷:夢具有某種文字形式的結構,但是這種結構只有不被文字編碼,而被直觀畫面展示出來的時候才是現實的。從某種意義上講,正是因為繪畫的本體論特質,才使超現實主義畫家相信,不是畫家在畫,而是畫在畫其自身。超現實主義繪畫的自動寫作就是最好的例證。
超現實主義繪畫呈現夢境與精神結構除了藝術上的守護繪畫以外,更是直接指向了人內心的慰藉。超現實主義繪畫的這一形上向度在于“建構一個與物化世界判剖有別,將現實生活與本能沖動、無意識和夢的經驗交融貫通卻能主宰整個生活世界的超然境界,借此獲致個體的本真存在。”追問本真的存在正是超現實主義繪畫的魅力所在。因為,超現實主義將夢境作為唯一的希望即是意味著夢境是一個能夠還復人性、表達存在的純然存在,無論夢是曾有生命經驗還是生活經驗的意識化,或是人潛意識或無意識的表現,都可以在不受社會現實編碼的意義上完整地敘述存在本身。達利就在自己的畫作中不斷回溯原初的夢境,并且宣布“超現實主義是指人的充分自由及做白日夢的權利。”當然超現實主義繪畫并不是要在此向人們宣布只有在夢中才是現實,而是說夢的無意識本身是一種改變生活、改變世界、建構存在的意識力量。這種力量來自原初的、未曾剪輯的整體性使主體能夠獲得整全的存在體驗與整個世界。比如馬格利特也一直在自己的繪畫作品中重復無面孔的身體形象。因為臉其實是一種被雕琢的面相,既有主體自覺的雕琢,又有主體非自覺的雕琢。因此,去除特異性的面孔直面身體本身,就使人真正超越了福柯所言的“權力框架”與“政治架構”,在不與他者相遇的途中與自己相處。
因此,超現實主義繪畫在形成自己創作方法的過程中,并不是簡單地改變運筆的方式與調色的策略、選題的視角與造型的角度,而是從繪畫本體的角度來思考畫與人、人與畫之間唯有藝術才能言說的本真關系。超現實主義不是技術性改造了創造手法,而是形而上學地思考了存在的藝術表達。在其創造的邏輯之中,既體現了這種繪畫藝術對現實歷史的藝術直觀,又表達了現代人存在的生存焦慮,更是從藝術的角度去重建了現實與非現實的藝術張力。超現實主義繪畫在對非現實的現實性的形上追問中,使繪畫從現代繪畫的父權中脫離出來,自由地敘述不穩定的穩定性來反抗穩定性的暴力和現實的暴政。這就可以解釋為什么超現實主義會在一戰之后興起,并積極地介入政治;超現實主義繪畫為什么總是將夢境與自由勾聯,將精神與主體同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