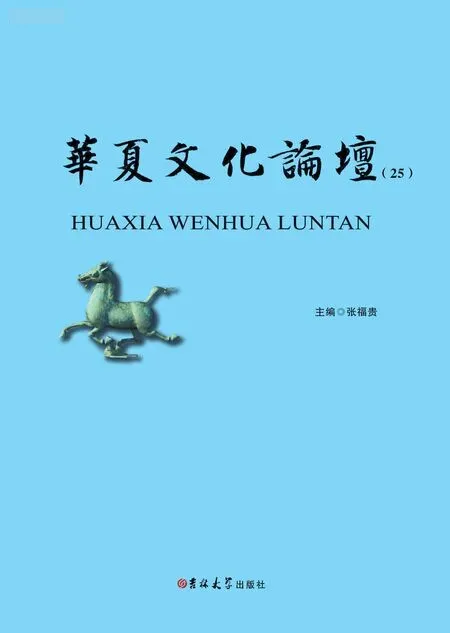審思萊考夫的概念隱喻真理觀
李慶麗
與傳統西方哲學思想對隱喻的認識不同,萊考夫將概念隱喻置于人類生活中認知層面的知識探索與科學研究中,認為概念隱喻完全是一種認知思維、認知手段,無所不在并不可避免地參與指導著人們的思想意識和生活實踐。從研究隱喻本質到關注人類對生存世界的認知,萊考夫以經驗主義為基礎對真理問題進行探討,可以說是以認知科學對峙先驗哲學,樹立了第二代認知科學的哲學觀和方法論。
一、概念隱喻真理觀的形成
傳統西方文化的哲學焦點在于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之爭,在很多流派的哲學家觀念中二者持堅決對立的哲學立場。客觀主義認為存在完全客觀、無條件的、絕對的真理;主觀主義認為真理完全以人的意識為轉移,是純粹的主觀建構。萊考夫提出真理的另一種經驗主義闡釋,批評客觀主義無條件的絕對真理的觀點,也不接受主觀主義完全以意識、想象為認知起點,不受環境制約的純粹主觀性。他認為,真理與概念系統緊密聯系,而概念系統是人類思維的建構,本質上都是隱喻的,不存在完全客觀的、脫離經驗的絕對真理,明確提出“隱喻是富于想象力的理性”。這就使得隱喻作為重要工具,生成了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之外的基于理解的經驗主義綜合。
這種經驗主義闡釋彌合了原本對立的主觀主義和客觀主義之間的鴻溝。客觀主義沒有意識到,由理解而獲得的真理來源于人們的文化概念系統,此概念系統不是客觀的絕對存在,而是依賴于人的認知,人們總是會以對一種事物的豐富想象來理解另一種事物,隱喻無處不在地影響著概念系統的產生。主觀主義沒有意識到,即使是最富有想象的理解,仍然依據本質為隱喻的概念系統,而隱喻性理解和概念系統的生成均涉及隱喻蘊涵、范疇化和推論,這一過程并非是完全非理性的,相反,隱喻蘊涵是一種富于想象的理性形式。
(一)概念隱喻思想在真理中的作用
概念隱喻思想中投射理論、范疇化理論在探討“隱喻之真”和“真理之真”等關鍵問題上發揮了不可替代的有效作用,成為萊考夫概念隱喻真理觀建構的基石,為揭示真理的經驗主義闡釋的本質提供了理論支撐。
投射理論在真理中起到了幫助人們對事物的方位、空間等建立基本認識與理解的重要作用,這是人們充分了解外部世界的前提。源自人們直接經驗的形式投射出的方位范疇使人們自然地認識和理解了“物質”“物體”“上—下”“左—右”“前—后”“目的”“起因”等基礎概念。人們通過感知來確定事物的位置、方向、大小、形狀,并以此來確定自身的位置、坐標,形成空間、方位的系統建構,然后概念化為人們所熟知的表達方式,用以溝通交際、相互理解。例如,人們基于身體直立向上的生存特征,產生了“地上”“地面”等直接經驗,將相應的感知經驗投射到不同角度的平面,產生了“墻上”“天花板上”等方位表達。當產生直接經驗的自然范疇不適用時,人們又將已形成的范疇投射到沒有直接經驗的物質世界的某些方面,對原本沒有明確邊界和表象的實體賦予一定的邊界和外表。比如“天上”“森林內部”等并非是某個具有清晰界限的平面或空間集合,但根據人們的感知和與人的相對位置,產生了很容易被理解的概念。在日常生活中,人們通過給物質或物體投射方向和實體結構來了解和認識世界,這種通常的認知方式表明真理是相對于人們理解的。
范疇化在真理中起到了幫助人們對事物進行分門別類、凸顯特點、判斷真實陳述的重要認知作用。萊考夫認為,人們對物體的范疇化來自自然維度,包括感覺器官對物體構想生成的知覺維度,物體之間運動交互特征生成的肌動活動,人們對物體功能構想生成的功能維度,特定情況下人們對物體使用生成的目的維度。這些維度組成了人類范疇化的基本完形,每個自然維度都意味著一種互動屬性。范疇化通過凸顯某些特征,同時淡化或隱去某些特征來標識一種物質或物體,以人們的某些目的為指向來描述世界。真理本身是概念系統的一種功能,離不開范疇化的真實陳述,人們所做的真實陳述都是以范疇化的事物為基礎,通過那些范疇自然維度所凸顯的特征來構建概念系統,這就必然聚焦一部分特征、忽略其他特征。由于范疇自然維度并不是事物本身的特點,它們來自人們與世界的互動,是以人的感覺系統、器官功能、概念系統為基礎的互動產物,因此基于人類范疇所論斷的真實陳述也具有相對于人類機能的有意義的互動特性,而不是事物本身的特性。真理基于真實的陳述內容及邏輯,就必然對范疇和范疇化方式做出選擇,這種選擇與人們在一定環境和文化中的知覺和目的密不可分。范疇是以人類理解為目的,以核型理論和家族相似性為主要特征來劃分和界定的輻射狀結構,一事物屬于某個范疇或范疇化的方式都取決于范疇的人為目的。那么,一個陳述是否為真實則取決于陳述中所使用的范疇是否合適,真理是相對于一定情境和文化中人們的目的而判斷的。萊考夫認為,真理至少在四個方面取決于范疇化:(1)一個陳述只有相對于某一種理解時才是真實的;(2)理解通常會涉及人類的范疇化,這種范疇化是非固有的互動特征以及源于經驗的維度在發揮作用;(3)陳述的真實與陳述中的范疇所凸顯的特征有關;(4)范疇既不是固定的,也不是統一的,是通過原型或家族相似性來界定的,不同目的、不同情境的范疇化結果未必相同。可見,概念隱喻思想的范疇及范疇化理論對真理問題的研究發揮著十分重要的基礎作用。
(二)概念隱喻思想的真理本質
萊考夫對真理問題的宏觀探討始終圍繞著經驗闡釋要素,這種闡釋以人的理解和人們為何對理解情境做出分析為基礎。人的理解分為直接理解和間接理解。首先,直接理解是指人們通過直接接觸物質或物體來認識事物,通過這種物理接觸實現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人們將自己視為有清晰邊界的實體來建構自身和其他實體結構,接觸同樣有邊界的可感知的眾多實體。在了解實體的基礎上,人們通過各種實體事物在所處環境中的不同位置與變化建構了空間方位結構,這就有了上下左右、前后里外、中間邊緣等意識和概念。人們不斷地通過一些經驗維度與其他人以及自然環境、文化環境直接交互,對實體事物進行自然地范疇化,再通過范疇化的結果將直接經驗范疇化,形成不同維度的經驗完形。范疇化使得在人們所理解的情境中建立了不為人們所意識到的豐富的認知背景,情境又將作為一個經驗完形的實例被用來理解與該完形維度相吻合的情境要素,這就使得人們通過直接接觸物體或事件來與所處環境產生互動循環。
其次,間接理解是在直接理解的經驗基礎上,對非自然經驗維度的對象和范疇進行認知和界定,比如情緒情感、抽象概念、道德、心理、時間、制度、工作等。人們憑借已認知的實體和經驗,尤其是已范疇化的實體和經驗來理解它們。通過概念隱喻投射過程內建于人們的感覺系統,依據明晰界定的事物和概念來分析理解未知事物,形成推理和再范疇化,間接理解充分利用了直接理解的資源。在這樣的過程中,必然需要隱喻作為必要的概念化工具來實現,因為大多數間接理解都是依據一類實體或經驗來理解另一類實體或經驗。間接理解通過方位隱喻說明方位結構,通過結構隱喻形成經驗維度和經驗完形,經驗完形則通過隱喻在理解中起到背景作用,同樣是通過隱喻使得事物的某些特征被凸顯,同時其他特征被淡化或隱藏。總之,通過直接理解和間接理解的共同作用,才使得人們對世界的認知有了真實與否的判定。人們通過概念系統來理解情境,以概念系統組成的陳述是否被理解為真便決定了人們對真實和真理的認知,真理是概念系統的一種功能,而概念系統本質上是隱喻性的,因而真理是以理解為基礎的人們對事物及其規律的判別表述。
萊考夫概念隱喻思想的真理本質可以概況為真理取決于人類的理解。這一認識具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具有真理符合論特點。真理的陳述和世界上事物和事件的狀態直接的吻合表現出真理陳述的客觀意義,這種客觀意義指定該陳述為真的條件。萊考夫的真理觀是與概念系統相關的,以理解為基礎的,真理必然要符合一定情境中人們的理解。二是具有真理連貫性特點。真理依賴于連貫性,表現在人們理解事物或事件需要根據概念系統將其吻合到一個連貫的圖式中。三是具有真理實效論特點。理解需要經驗基礎,經驗范疇及構成這些范疇的概念系統不僅來自經驗,還不斷得到人類文化的成功驗證。四是具有真理的非絕對性特點。與純粹客觀主義不同,經驗主義真理觀不承認存在純粹絕對的客觀真理。五是具有真理的非同一性。不同文化、不同情境、不同概念系統的人理解世界的方式可能截然不同,這就存在不同的真理和真理的判定標準。
二、概念隱喻真理中的真實研判
概念隱喻思想的真理本質反映了萊考夫對于真理問題的宏觀認識,從這一真理探討的提出到范疇與范疇化研究的深入,萊考夫對真理的關注逐漸聚焦于微觀層面對客觀事物及事實的真實考量及其研判依據,更加突出概念隱喻及其所支持的具身實在主義在真實研判過程中所發揮的關鍵作用,充分體現了真實本身所具有的具身性特點。
(一)隱喻與真實
概念隱喻思想認為隱喻無處不在,概念本質上是隱喻性的,人類的概念系統和日常思維都是隱喻的。這些觀點并非僅從語言學角度對傳統隱喻理論提出質疑,其理論本質已經深刻切中哲學基本問題的要害,涉及人類為何物,如何理解外部世界,什么是現實,什么是真實,語言如何與世界關聯,是否有客觀知識存在,甚至什么是道德等。這些與傳統隱喻理論所輻射到的現實觀、真實觀、語言觀、知識觀、道德觀針鋒相對。讓人們輕易地否定多少世紀以來已經達成共識的世界觀及其哲學理論是件極其艱難的事情,然而概念隱喻思想體系的建立卻給出了清晰而有力的證據回應。針對傳統隱喻理論的主要原則,萊考夫以例證對其進行了逐一辨析并反駁其錯誤根源,詮釋了“隱喻之真”。
隱喻更重要的是思維問題,先有隱喻性思維才能產生若干種可能不同的隱喻性語言表達,通過跨域映射的形式,語言只是思維的邏輯反映。隱喻性語言是人們對事物的概念化理解與推理的自然形式和日常方式,屬于普通慣常性語言。隱喻思維是人們再正常不過的思維方式,這源于人們對客觀事物或事件的真實感知與體驗。日常語言中很多常規隱喻表達都是具有認知現實性的十分鮮活的常規性概念隱喻,并非死喻。隱喻所反映的相似性是隱喻概念如何進行定義與理解,隱喻蘊含如何賦予形式以意義以及如何產生新意義,證明了相似性是通過隱喻映射產生的,是映射創造了相似性。
各種會聚性證據表明,人們通過概念隱喻真實地描述和反映著與人們相互作用的客觀世界,可以看到人們普通日常理性都是隱喻思維的表達。萊考夫認為,隱喻思維具有許多哲學蘊涵。基本隱喻在人們的日常經驗中不斷產生,將人們的主觀經驗判斷與感覺運動體驗相關聯,為抽象概念的形成提供感覺運動體驗的邏輯和意象性的定性感覺,人們在認知無意識的自然狀態下不自覺地形成和運用了思維的隱喻模式。大多數抽象概念都是通過概念隱喻有效界定的,概念隱喻的基本作用就是把喻源域的推理模式映射到目標域中,因而推理都是隱喻性的。隱喻思維使得抽象的科學能從理論上具體闡述成為可能。隱喻概念是具身性真實,與傳統的離身性真實符合論相矛盾。理性與概念并非獨立于人類身體之外,并非是超驗的,理性與概念結構依賴于人類身體、大腦和在世界中的功能模式而形成。綜上,這些都是無意識隱喻思維博大精深的哲學蘊涵,概念隱喻使得大部分抽象思維成為可能,哲學的隱喻品格促使科學思維是真實的,這是人們能夠理解自身經驗的特有手段,是人類偉大的智力天賦。
(二)實在主義與真實
對于真實的研判是認知層面的問題,從形而上學實在主義到帕特南的內在實在主義,再到萊考夫和約翰遜的經驗實在主義,對意義、指稱、認識和理解的認識論經歷了不同程度的變化,這些都是圍繞“真實”問題展開的基本討論。由此形成了認知科學的兩代構想,萊考夫將其概括為第一代“離身性心智的認知科學”和第二代“具身性心智的認知科學”。第一代認知科學基于解析哲學,建立在特定的先驗論哲學承諾基礎上,具有功能主義特點,認為心智本質上是脫離身體與大腦具有離身性的,思維形式是基于符號的形式操作處理,無須考慮符號的意義。因此,心智表征是符號化的,通過與其他符號和外在現實的關系獲得意義,同時憑借必要充分條件定義范疇,并且所有意義都是字面意義,不存在隱喻意義。真實即為客觀的離身的真實,與人的理解毫無關系。第二代認知科學發現概念域理性強烈依賴于人類身體,概念化中心與推理想象過程都來自隱喻,對隱喻、意象、核型理論、心智空間和輻射狀范疇的新發現反駁了英美解析哲學理論。具身性心智的認知科學主張概念結構來自人們的感覺運動經驗和神經結構,并非無意義符號而是人們的身體和具身經驗的聯結賦予了心智結構的本質意義;基本層次概念來自人們的肌動模式和整體感知能力及意象模式的形成;基本隱喻是通過人們大腦結構化將感覺運動域的激活模式映射到更高皮層區而產生的;概念結構包含使用不同推理形式的多樣核型,大多數概念不具有充分必要條件;理性是具身的,屬于人們推理的基本形式,身體的推理形式通過隱喻映射到抽象推理模式。總之,這種具身性理解在人們的意義和思維結構與內容的所有方面發揮著中心作用。兩代認知科學是“離身性”對峙“具身性”,或是“形式解析哲學的假設原理”對峙“非形式解析哲學的假設原理”,不同的哲學方法論使得對“真實”的研判也有不同。
各種指稱理論與真實問題的探討是解析哲學的中心議題,因為解析哲學的分析程序依據它們來填補符號與世界之間的裂隙(gap)。解析哲學的符號系統實在主義使得指稱與真實問題的重要性更為沉重,在訴諸真實符合論的前提下,抽象符號與指稱世界之間的鴻溝需要對應性聯結的彌合。解析哲學具有兩種指稱理論,一是認為指稱為何取決于語言表達式的意義,二是認為特定人的指稱行為決定其指稱為何,即指稱的決定是有因果的。作為符號的詞語形式與世界之間的裂隙被呈現為:(1)自然語言句子與命題之間的裂隙,命題是由抽象符號構成的語言中立結構;(2)符號結構與世界之間的裂隙;(3)自然語言與形式語言中用來表征自然語言各方面符號之間的裂隙;(4)形式語言符號與語言集合論模型中的任意抽象實體集之間的裂隙;(5)世界的集合論模型與世界本身之間的裂隙。這些裂隙都是難以彌補的棘手的問題。具身實在主義的介入對“真實”問題的理解則有助于科學的通情達理,它區分了不同的理解平面,真實與否是相對于不同理解的科學解釋層面的。比如一個物理主義者主張只有客觀存在的事物,即獨立于任何物理的身體的任何理解的存在,而對物理事物概念化的過程離不開理解過程。從具身實在主義的角度看,不存在主客二分的認識論與對世界本質研究的分離,認為“真實”取決于“理解”,則對物理主義者所顯示出的含義可以理解為關注的是科學解釋與激發的性質以及為科學解釋的目的而被視為的“真實”。這意味著真實被定義為相對理解的真實。
與宏觀層面真理取決于理解一樣,微觀層面的真實同樣取決于人們的理解,這種真實是具身性的。沒有理解就沒有真實,任何真實都必須以人類的概念化、范疇化與可理解的形式存在。具身性真實與理解緊密關聯,并不是絕對的客觀真實,它不同于人們在傳統理論中對“真實”的看法。同時,具身性真實也不是純粹主觀的真實,主觀真實是完全以人的意志建構的真實,與客觀事物及世界毫不相干,具身性真實需要人們與外部世界進行交互作用而獲得理解,包括對人類交際、文化、制度、活動的理解與經驗。這些可成為社會性真實,社會性真實只能是具身性真實,因為脫離了理解則意義無存,例如道德、民主、權利、義務、自由、公平、正義等概念。具身科學實在主義引發了相應的科學具身真實觀。萊考夫所認為的真實進入了認知科學的范疇,因為這有賴于人類理解的本性,包括何為概念、何為隱喻以及如何為情境設定框架。基于具身性的多重平面性,萊考夫所指的“真實”可解釋為人們對于所處環境中現實情境下所需要的概念上的設想,或人們為了生存、達到特定目的對自身所處環境的妥當且可行的理解。
三、概念隱喻真理觀評析
萊考夫概念隱喻真理觀以經驗主義立場、具身實在主義觀點力駁純粹客觀主義和主觀主義真理問題要害,以概念隱喻思想為利器,用聯系的、發展的哲學觀點重新審視了真理問題,形成了概念隱喻的建構真理觀。具體表現在:首先,真理不是獨立于人的身體、大腦而客觀存在的,而是基于人的心智、對世界及自身的理解,作為人的心智產物真理是被建構的;其次,真理不是脫離客觀世界的人的主觀臆造,而是基于人的感覺系統、肌動組織與外部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的交互作用產生的,作為人的理性認知真理是被建構的;再次,真理不是先驗不變的意義表述或系統符號,而是經由概念隱喻映射產生,與情境性理解目的吻合,是相對于概念系統的,作為人的隱喻思維真理是建構的;最后,真理不是靜態的、封閉的、永遠正確的絕對真理,而是符合相應情境的客觀世界的相似性描述,是動態的、開放的、需要不斷完善的理想真理的逼近,不會存在絕對真理。這種隱喻建構真理觀,相較于之前亞里士多德的符合真理觀、布萊克的視如真理觀以及戴維森的替代真理觀,在對隱喻的認知和對哲學的真理問題研究上都具有開創性的思想進步和理論發展。
盡管如此,概念隱喻真理觀仍存在一定的不足,表現為語境性局限。一是關于“真理之真”與“真實之真”的有關“真”的探討稍顯薄弱與模糊。通過研讀對比萊考夫著作原本與譯本,研究發現文中頻繁出現的“truth”一詞在其不同階段出版的著作里指代較為模糊和混亂,在前期出版的《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一書中“truth”多指真理,但在探究真理的例證之中真理、真實與真值的各種表述常常含混,難以區分;在后期出版的《肉身哲學:親身心智及其向西方思想的挑戰》一書中“truth”多指真實,例如“實在主義與真實”、“隱喻與真實”的論述,由于其論述的具身性和概念隱喻多個會聚證據等具體問題多處于微觀層面,討論的是陳述的真實問題和真實與否,因而“truth”多譯為真實。但同時這里的研究已是基于成熟的范疇化研究和認知無意識、具身心智及復雜隱喻研究的基礎之上,進一步提升到認知科學和哲學層面的探討,對于真理問題的系統研究是顯得欠深入的。二是對真理本質的表述尚處于片面的、不完善的模糊表達。盡管萊考夫竭力論證了真理不是客觀存在的絕對真理,不是主觀臆想的脫離客觀世界的任意想象,真理不是獨立于人類身體、大腦的離身的對事物及其規律的判斷,真理不能脫離人與外部世界的交互作用等,但真理的科學表達理應為何并未給予明確的說明,僅以排除法賦予真理更多的不可為,抑或是以“真理取決于理解”、“真理是經驗主義的”、“真理是具身性的”、“真理是情境性的”、“真理是永遠逼近理想真理的”等特征性作為表達方式來詮釋真理義涵。如此,對真理本質的研究尚顯不夠明晰和精準。但無論怎樣,概念隱喻真理觀的建構已然為萊考夫體驗哲學的提出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本研究嘗試進行了一次對萊考夫真理觀的系統性挖掘,由于企盼對其相關研究面面俱到,不免有疏漏之處,希冀所有對此研究的學者繼續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