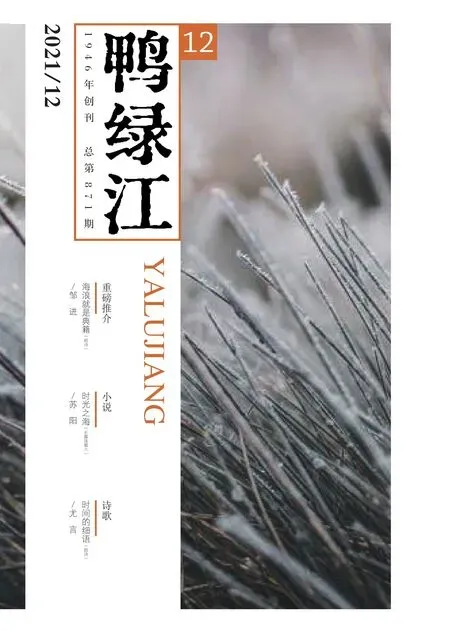站在天一閣的時(shí)間微光里
張冰瀅
在《風(fēng)雨天一閣》中,余秋雨說:“不知怎么回事,天一閣對(duì)于我,一直有一種奇怪的阻隔。”學(xué)者言真,對(duì)于平凡的我也是一樣,一次次錯(cuò)過。站在天一閣門前,已是盛夏。沒有風(fēng)雨,清晨的陽光安閑地灑下點(diǎn)點(diǎn)碎金。黛瓦墨門,不高的院檐被層層夏木濃蔭覆著,隔著時(shí)間的光陰看過去,這個(gè)“南國(guó)書城”,顯示出讀書人特有的低調(diào)、謙遜。
進(jìn)得園子,我看見古樹枝葉橫斜在上空。這座有幾百年歷史的園子每個(gè)角落都顯得蔥蔥郁郁,仿佛依然生活在盛年。踏著園內(nèi)苔痕深深,嗅著草木之息,吹著月湖畔來的風(fēng),不禁神思縹緲,穿越到一個(gè)溢滿書香的故事里。
這個(gè)故事當(dāng)從嘉靖四十年開始。時(shí)間的微光里走來一位年過半百的官員,大襟、右衽、寬袖、青色袍衫、髯須飄飄,平靜的面色中略帶喜悅之色。宦海沉浮中,他最大的收獲除了秉持不畏權(quán)貴濟(jì)天下的為官原則外,就是聚書刻書。如今致仕歸里,他最想做的事就是給這些年收藏的書建一個(gè)家。為書而生,為書而亡,書是他的精神家園。于是,這位號(hào)東明的癡心人,建了東明草堂,又稱“一吾廬”,這里成為他最早藏書的地方。如今的“一吾廬”雖幾經(jīng)復(fù)建,但低矮的屋檐,明代家具的簡(jiǎn)約,仍表現(xiàn)著當(dāng)年范公作為讀書人的謙遜。一盆蘭花在書櫥旁靜靜立著,于是過往的書香有了現(xiàn)代的生命。
江南多煙雨,煙雨成就了許多千古佳文,卻使承載詩文的宣紙潮濕、生蟲,難敵時(shí)間考驗(yàn)。所以文化長(zhǎng)河茫茫,浩繁的卷帙中流傳至今的畢竟只是少數(shù)。范欽顯然深知這一點(diǎn),他決定修筑一幢藏書閣,這個(gè)閣還必得有先進(jìn)的藏書良方。這個(gè)藏書閣便是我們今天看到的范欽于月湖宅東建造的藏書樓,一排六開間兩層木結(jié)構(gòu),書怕火,而“天一生水”,故名為“天一閣”。這座藏書樓坐北朝南,為磚木二層結(jié)構(gòu)小樓,一層分六間,二層則為大通間,以樟木櫥為間隔,可惜暫未開放。天一閣沒有我想象中的富麗堂皇,相反它有些殘舊低矮,但它帶著讀書人的清高、傲氣,巋然不動(dòng)地屹立了四百多年。站在一樓,從門廳看過去,雕花窗外,綠樹蔭濃,清風(fēng)穿堂而來直到心底,許多讀書的好時(shí)光被一一還原,給人無限的遐思。
走在天一閣,你會(huì)驚訝地發(fā)現(xiàn),與其說這是一處藏書處,更不如說這是一處雅致的江南園林。天一閣前的天一池,以太湖石壘成“九獅一象”,栩栩如生,園子不大,卻疊合起伏有致。亭臺(tái)樓閣,碧水環(huán)繞,群魚嬉戲,小丘上綠樹蔭濃,形成天然屏障,使這個(gè)園子冬暖夏涼,恍如世外桃源。古人對(duì)建筑的講究和審美情趣,以及讀書人要的清靜、出世,這里都有了。然而當(dāng)年修閣之時(shí),范欽可能不曾想到百年之后的天一閣會(huì)成為中國(guó)最古老的藏書樓之一,亦不曾想過自己的姓名從此和“天一閣主人”聯(lián)結(jié)在一起吧。
在天一閣,我們聽說了一段因書而起的哀傷故事,這個(gè)故事和一位女子有關(guān)。清嘉慶年間,寧波知府丘鐵卿有個(gè)才貌雙全的內(nèi)侄女,名繡蕓,在“女子無才便是德”的時(shí)代,她卻酷愛詩書。當(dāng)聽說范家藏書后,竟愿以托付終身為代價(jià)嫁入范家。只是世事難料,她不知道范家有規(guī):“書不出閣,女不上樓。”范家嚴(yán)苛的祖訓(xùn)和規(guī)矩是不容他人破壞的,即使身為范家媳婦也不得有半點(diǎn)逾越。那個(gè)仰慕天一閣已久的才女錢繡蕓用盡一生也未能登樓。繡蕓的婚姻不為錢財(cái),不為愛情,只為讀書,這份對(duì)書的癡迷頗令人感動(dòng)。
春來閣前的池水碧綠,風(fēng)過微瀾,不知道曾經(jīng)多少次吹皺癡心女子的心。冬日飛雪,閣前一片沉寂,油盡燈枯,這個(gè)癡心女子終是懷著遺憾郁郁而終,留下那樣卑微又虔誠(chéng)的遺憾:“我之所以來汝家者,蕓草也,蕓草既不見,生亦何為?君如憐妾,死葬閣之左近,妾瞑目矣!”天一閣園子墻頭,青草在風(fēng)中搖曳,向我們傳遞著400多年前繡蕓那份對(duì)書欲罷不能的深深幽怨。我們沒有在天一閣尋見繡蕓冢,但卻在展示館得知蕓草還是一直在天一閣被用來防蛀,宛如繡蕓靠著書,永不分離,覺得冥冥中彌補(bǔ)了繡蕓的一點(diǎn)遺憾。
展館有一處雕塑,為我們還原了天一閣“代不分書”家規(guī)的故事。月色晦暗的夜,如豆的燈火映照著范欽枯瘦的身影。年事已高的范欽意識(shí)到生命將盡,遂將長(zhǎng)子和次子媳叫至跟前,將家產(chǎn)分為兩部分,次子一房得到了萬兩白銀,長(zhǎng)子范大沖一房則接受了父親這一份沉甸甸的托付,成為天一閣及其藏書的傳人,也是“代不分書”的第一任接班者。
范欽享年79歲,從此,范家子傳孫,孫傳曾孫,范氏一族一代代虔誠(chéng)地守護(hù)著這幢樓。但“禁以書下閣樓,非各房子孫齊至,不開鎖”的嚴(yán)苛制度漸使得天一閣再無人登樓,無人看書。長(zhǎng)此以往,天一閣成了一片圣地,同時(shí)也成了一片禁地。樓外的人遙望著,用他們的生命擋住時(shí)間的洪流,分出一條可供書躲藏的縫隙;樓里的書沉睡著,在這一條時(shí)間的縫隙里微弱地呼吸,延續(xù)著它們的生命。于是長(zhǎng)久以來,對(duì)天一閣,人們陷入了隱隱困惑:這樣的祖訓(xùn),究竟是對(duì)書籍的守護(hù),還是對(duì)文化的桎梏?
這樣的困惑在清康熙十二年(1673)迎來了轉(zhuǎn)機(jī)。這一年,著名學(xué)者黃宗羲請(qǐng)求登上天一閣。范氏子孫商議之后,同意了這一次外姓人的首次登樓。黃宗羲進(jìn)入書閣后,開始編制書目,并撰寫《天一閣藏書記》。范氏后人看著這關(guān)于天一閣的新生文字,忽然發(fā)現(xiàn)再多的書,關(guān)著也無用,應(yīng)該讓書有更多人讀,讓書真正“活”起來!自此以后,天一閣逐漸有選擇地向一些大學(xué)者開放,使這一座水庫中積蓄了百年的文化之水終于得以沖出桎梏文化的堤壩。
郭沫若說天一閣“良書播惠九州”,隨著天一閣古籍的流傳范圍越來越廣,書中所錄文字為越來越多的文化研究考證工作提供著有力的證據(jù)與合適的參照。書香不再是為了陳列供奉,更是為了文化的傳承——這些古書,實(shí)在是最好的講述者與見證者。它們見證了能從紛亂的世間堅(jiān)韌不屈地保存下來一種文化的家族信仰的存在;見證了一個(gè)保護(hù)藏書的隊(duì)伍從少到多、由小而大的歷程;見證了一座書閣如何由個(gè)人愛好變成了民族文化符號(hào)。天一閣是7萬冊(cè)藏書曾經(jīng)存在的最好證明。作為聞名遐邇的私人藏書樓,雖幾經(jīng)毀滅,然精神永存!我們?cè)谌肟趬ι系摹稁旆窟M(jìn)出及藏品出入庫制度》《庫員崗位責(zé)任》上看到從前天一閣出入的家規(guī)被沿用下來,比如“雙人雙鎖,同進(jìn)同出”“霉季或陰雨天,不得提看各類藏品”,這是范欽對(duì)書那份愛與憂的承諾,更是對(duì)讀書崇文精神的繼承。
今天的天一閣,苔痕,綠意深深地嵌在斜陽深巷每塊席磚縫內(nèi),好似范欽一生與書割不斷的情緣。雕花木窗內(nèi)的樟木書架上依然散發(fā)著沁入心底的悠悠書香;雕花木窗外,天空一碧如洗,波光云影處,分明是點(diǎn)點(diǎn)文心在閃爍。想那煙波四面的玲瓏閣,日里,蟬聲閉閣好讀書;入夜,讀罷開閣納微涼。我立著,似見時(shí)間的微光里,一位古稀的讀書人憑欄而望,大襟、右衽、寬袖、青色袍衫,髯須飄飄,一身月華。閣前香樟枝滴清露,鳥雀棲息,我分明聽見一聲長(zhǎng)嘆:“吾當(dāng)早啟書閣,則天下少有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