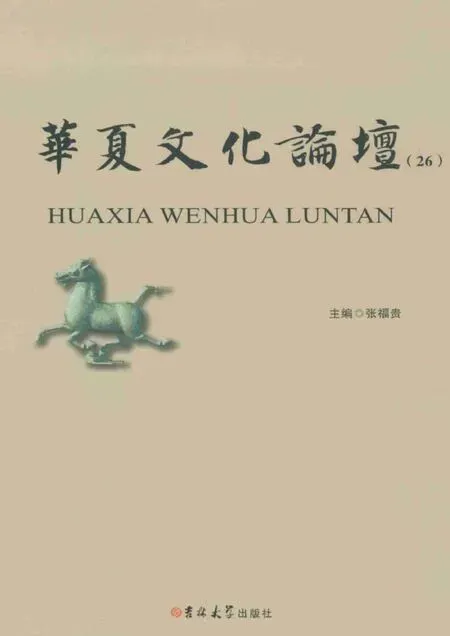易安詞的女性空間書寫
劉淑玲 李 靜
1974年,法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 )在著作《空間的生產》中對空間的社會屬性做出開創性闡述,開啟了空間地理的社會學以及哲學的思維向度。空間作為世界構成的維度之一,也是促成文學文本生成的重要元素。文學作品中的物質空間以及空間關系,都為解讀文學作品鋪設了不容疏忽的背景意象。中國古典詩詞更是如此。空間理論的生成和蕃昌固然起于西方,以西方理論工具闡釋中國古典文學現象也曾引起關于文學闡釋方法以及“新批評”話語的跨洋學術論戰,然而,正如學者江弱水所言,“用西方作為參照物對中國古典遺產加以考察,并非因為‘古已有之’型的民族自大狂再度發作。傳統的活力來自不斷的再闡釋,這是一種拂拭與擦亮的行為,它將使疏離的傳統與當代重新發生關系,從而激發出活性并生成新的意義。”
就易安詞而言,其“能曲折盡人意”的微約含蓄,與“林下之風”的宏大歷史敘事,既呈現了人在線性時間中的浮沉流轉,也展現出不同空間系統內人與物的互動互建。詞作中對于女性空間的書寫,或設色明麗,或沉郁空靈,皆為蘊涵豐富的文本背景。文本中“文學性”的女性空間來自現實空間,又作用于現實空間,二者相互指涉,相互呈現。
一、易安詞中的女性空間維度
列斐伏爾在“空間三一論”中著重關注空間中“物理、精神、社會”的三重構成維度。他指出任何社會生產出來的空間都是由“表征空間”(space of representation)、“空間表征”(representation of space)和“空間實踐”(spatial practices)三者構成。“表征空間”指生活空間,是居住者使用的物理空間;“空間表征”屬構想空間,是由社會空間秩序制定者構想和規劃而成,規定著“空間實踐”;而“空間實踐”則是日常生活的體現,在“空間表征”的滲透和制約下,“空間實踐”常常體現為規約的空間行為,但不排除對規約的逾越。此“空間三一論”在易安詞中表現為通過構建一系列帶有女性符號的表征空間,與空間實踐敘事,來體現空間表征秩序的主體與空間的互動共鳴。
1.表征空間——“閉塞”的女性空間
易安詞中通過“幕簾”“軒窗”“重門”“庭院”等意象符號建構了深具傳統文化特征的女性空間。而此四重物象層次分明、由內向外地構建了宋代女性生存的四重封閉的表征空間。有研究者統計表明,李清照“有58首詞中,有16首提到簾意象,約占28%。”如此高頻率書寫的“幕簾”建構了女性閉塞空間的第一重屏障。簾絕非僅為閨房裝飾之物,而是具有內外相分、空間相隔的功能,無論簾卷簾垂,它都是易安詞中所構建的女性空間內與女性最為切近之物。也就是說,簾內空間所營造的是純粹的女性生存的物理空間,它的“空間表征”意涵與其所傳遞的空間語言構成直接對應性關系。在《規訓與懲罰》一書中,福柯提出紀律的實現需要與眾不同的、自我封閉的空間,空間的邊界就是紀律的邊界,空間的封閉性才能保證權力的順利運作。
在早期的易安詞《如夢令》中,李清照寫道“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幕簾垂下,女性便被區隔在閨房的內部空間之中,在封閉的空間內部,若非借助詢問,或移步空間之外,女性便對空間以外之事一無所知。簾的空間語素表達著女性空間的封閉幽私,然而,“情以物遷,辭以情發”,在后期的易安詞中,由于其人生境遇的突變,幕簾所承載的情語也發生遷移。在《念奴嬌》中有“樓上幾日春寒,幕簾四面,玉闌干慵倚”,宣和二年(1120)趙明誠為萊州知府,李清照獨居青州,作此名篇寄到萊州。詞人以一個春情寂寥的傍晚為背景,用飽蘸深情的筆觸,抒發了揮之不去的離情別緒。在《浣溪沙》中的“小院閑窗春已深,重簾未卷影沉沉”中,“簾垂四面”“重簾未卷”都構建了一個封閉孤寂的女性空間,簾卷時,女性空間得以延展開放;簾垂時,女性空間被區隔禁錮,使得簾內人徒生憂郁。實際上,簾的文化內涵也同其發音關聯密切。簾與“憐”字同音,幽閉清冷孤獨的女性空間以及詞中女子的自憐憂傷由幕簾四面之境可以想見。在中國傳統文化體系中,關于言象互動的關系,汪裕雄說“中國文化基本符號的構成,有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即語言與意象的平行互補。這個‘言象互動’的符號系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觀念的載體和交流媒介,深刻影響著傳統文化觀念的形成與傳播,影響著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這種簾內孤寂封閉的女性情愫在“天上星河轉,人間幕簾垂”(《南歌子》)中更加明顯。天上與人間,一轉一垂,一動一靜,外面世界喧嘩嘈擾,簾中已經物是人非,封閉依然,孤寂依然。易安詞中多次出現的簾字便構建了宋代女性生存的第一重表征空間。
簾和窗都是視覺載體,主體以此獲得與外界聯通。由簾到窗,看似女性空間的延展,然則空間依舊封閉幽凄。在古代建筑結構中,“窗”既使得室內與室外建立聯系,又將內外空間以此區隔。自唐宋起,窗子有了開合的功能,其靈活性的功能轉變增添了窗的文化內涵和詩學意蘊。在《聲聲慢》中“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玉樓春》中“道人憔悴春窗底”,《鷓鴣天》中“寒日蕭蕭上鎖窗”,《攤破浣溪沙》中“病起蕭蕭兩鬢華,臥看殘月上窗紗”、《臨江仙·乙亥春日》中“簾影沉沉銀箭悄,殘陽消盡余溫。小窗閑倚待黃昏”等詞作中,塑造了一個“守窗”“望窗”的意象。一方面,“窗”建構了一個與外界似開似閉的通道,然而“憔悴”“蕭蕭”“病起”等詞又構成了窗的空間背景,空間的封閉性造成了人物對“窗”守望的空間實踐,是主體向往同外界交流的行為表征。
“庭院”是以家庭為單位棲居的建筑空間,“重門”是此封閉空間與外界交集的通道。而“重”字所建構的空間嚴閉性更體現出閨房的幽深以及院中女性居住于封閉空間的焦慮感。在“帝里春晚,重門深院”(《怨王孫》),“蕭條庭院,又邪風細雨,重門須閉”(《念奴嬌·春情》)等詞作中,層層重門的物象成為詞人情感的載體。在京城暮春的時節,門庭重重,院落深深,望不見傳情鴻雁,因此幽恨綿綿。而庭院中景色蕭條成為人物空間實踐的背景,層層院門緊閉,人物情志愁悶,因此人惱天氣。詞中庭院深幽,重門緊鎖,女性禁錮于此,縱然可以“枕上詩書閑處好”(《山花子》),但也不免“試燈無意思,踏雪沒心情”(《臨江仙》)。
在由幕簾、軒窗、重門、庭院所建構的女性表征空間中,區隔閉塞的女性“萬千心事難寄”(《念奴嬌》)。王國維在《人間詞話刪稿》中說,“一切景語皆情語”。空間內的物品,也增強了空間物語,“窗前誰種芭蕉樹?陰滿中庭。陰滿中庭,葉葉心心,舒卷有余情”(《添字采桑子·芭蕉》)。
2.空間表征——“卑從”的女性地位
“每一種社會形態都生產自己的社會空間。”在列斐伏爾的社會空間理論中,“空間”已經不再是地理學或物理學的概念,而是一個社會學概念。空間是特定意識形態之下生產的特定產品。列斐伏爾在《空間的政治》中指出:“空間是政治的、意識形態的。它真正是一種充斥著各種意識形態的產物。”依據列斐伏爾的界定,“空間表征”作為空間的社會屬性表征“主要是政治經濟的產物,是被生產之物。”由此看來,空間的存在是在空間制造者的某種意圖之下被生產出來的,空間的建構帶有政治性特征。而宋代庭院即具有家國同構的文化特征,同樣是體現統治者政治思想的產物。“傳統建筑庭院以層次分明、等級有序的顯著特點成為家國同構的原型。”易安詞中從庭院、重門、軒窗到幕簾,每一層次空間都代表一種文化符號和豐富的社會政治意涵。
易安詞中建構的女性空間,作為現實空間的鏡像,所展現出來的空間表征表達社會空間秩序制定者的目的和意圖。“庭院深深深幾許,云窗霧閣春遲”(《臨江仙》)一句言辭蘊藉深沉,卻將庭院的幽靜深遠表達盡致。然而,庭院幽深,并且重門、軒窗、幕簾的景觀序列作為女性空間的建筑構造,均持續不斷地作為隱蔽的權力機制,對女性構成規約和訓誡。
庭院是宋代女性的主要活動空間,據考古資料顯示,宋代女性庭院之內的活動主要包括“女紅、侍奉父母公婆、主理家政、撫育子嗣”等。這些女性實踐屬于空間性的,也就是說在特定的空間范疇中特有的空間性行為。“空間性”是說空間所賦予事物及行為的屬性,“與空間層面的內外相對應的是職責層面的內外”。宋代女性的家庭職責是作為男人的輔助而料理家庭事務,在家庭地位上從屬于男性,社會規范不僅在對其空間范圍上有限定,而且對其行為上還有“不預外事”的思想。在“《有宋徐令人墓記》中有稱贊徐氏,‘在官則內言不出,未嘗纖毫敢與外事。’”宋代社會對于女性的行為規約和道德約束與深閨庭院的建造是同構的。
司馬光“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思想是對庭院內部女性活動空間的限定和行為的規范。“重門”的空間建筑,便充分體現了宋代社會統治階級維持社會秩序以及女性行為規范的思想。相對而言,“軒窗”和“幕簾”也同樣展現了女性空間內的權力規訓。在整個女性空間中,無形的權力符號通過空間結構的設置、塑造著空間內的個體。也就是說,“人在特定的空間中被鍛造。”這種特定女性空間中的主體屬性同福柯在全景敞視主義(panopticism)中提及的“全景敞視建筑”中的“被囚禁者”相類。在全景敞視建筑中,被囚禁者處于特定建筑結構中被監視的境況中,由于其處于“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以庭院、重門、軒窗和幕簾所構成的女性空間中,盡管空間內部層層區隔,但空間結構具有穩定性,屬于不可見中的可見結構,結構本身就具備對主體監督和規訓的作用。因此,易安詞中的女性空間與人物主體也自然處于規訓/被規訓,觀看/被觀看的二元結構之中,這個女性空間是顯性空間,其隱性的建造者是規約的制定者,也即父權社會制度中的男性主體。這種閉塞而卑從的女性空間是宋朝統治者有意圖地生產出來的,“它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產出來的。”
二、易安詞中女性空間的越界
“越界”(trangression)所表達的是一種空間關系,是指對一切既定的規約、秩序、界限以及禁忌的解構與重建。越界的前提是對空間邊界的認定。在列斐伏爾看來,界限是維持空間穩定和統治者政治意圖的重要工具。對界限的消除和跨越就是對原有空間秩序的突破和挑戰。越界理論之父巴塔耶(George Bataille,1897—1962)對現代社會秩序充滿憎惡,然而規則與懲戒建立起來的社會規約作為界限本身,其存在又可以看作是激活人類超越界限的動能。在福柯看來,“越界源于人類內心深處對于終極自由的追求,越界是開拓和冒險的姿態,也是對勇于挑戰秩序和理性的批判姿態。”
以男權為核心的宋代社會對女性進行規約和訓誡建構起女性生存的秩序空間,出于周朝禮教,在宋代仍被嚴格恪守的“三從四德”規定女子遵循“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為了維護父權制下的男權穩定,將女性置于“男尊女卑”的從屬地位。將女性空間封閉成為男性馴服、限制、規范女性的工具和手段之一。然而,反抗作為同壓迫相對立的二元結構中的一端,它也是權力擠壓的產物。根據巴塔耶理論,人類自身都具備解構秩序并沖破界限的本能,宋代社會的女性群體也不乏為尋求自由與男性政權抗爭的事例。在當時的政治社會氛圍之下,尋求自由包括沖破對女性生存空間的限制,是對既有界限的破除和跨越。在易安詞中,越界實踐則主要表現在主體于現實層面或思維領域對既存空間的厭斥與跨越。
1.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
易安詞中鮮明的空間越界之作當是《如夢令》。“常記溪亭日暮,沉醉不知歸路。興盡晚回舟,誤入藕花深處。爭渡,爭渡,驚起一灘鷗鷺”。“溪亭、輕舟”隸屬“公共空間”范疇,是同“庭院、重門”的“私人空間”相對的空間實踐背景,后者被賦予鮮明的政治色彩,或曰統治者思想的物化和空間實現,是一種相對穩定的女性空間布景。而詞人卻在日暮時分,突破并超越了當時社會對女性生活的空間規約,且醉飲而歸,此逾矩之舉顯然是與封建禮教相悖的。然而全詞造語清麗,充滿活力生機,人與自然活潑互動的畫面“語語如在目前”。可見詞人往昔被封閉空間壓制的靈動之心在越過空間界限后得到了充分解放和舒展。
從深閨庭院到公共場域,活動空間得以充分延展,主體的心靈體驗也隨之開朗、豁達起來。《怨王孫》一詞的上闕中寫道:“湖上風來波浩渺,秋已暮、紅稀香少。水光山色與人親,說不盡、無窮好”。在“秋已暮、紅稀香少”的暮秋背景之下,如果遵循中國古代文人慣有的悲秋情結,這應該又是一首悲秋之作。然而,詞人卻一反哀怨詞調,開篇即以“浩渺”一詞展現了廣闊遼遠的秋日景觀。以心觀物,則物現其心。“水光山色與人親”一句中景與人親、物我交融的勝境進一步描繪出人物主體在突破封閉、狹仄的“私人空間”的限制,越界至寬闊、曠達的“公共空間”中產生的自由、開闊的美好感受。“說不盡、無窮好”一句與前文的“秋已暮,紅稀香少”構成鮮明對比,盡管從視覺和嗅覺的感官角度,已經不能充分捕捉到暮秋之美,然而,因為空間性質的變化,對它的美好體驗竟然言之不盡。此處,“湖”與“山”構成的公共空間擺脫了“私人空間”中的權力壓迫性,固有的人物身份被暫時消解,于是實踐主體便產生具有強烈對比性的情感體驗。
2.從“現實空間”到“夢幻空間”
在“酒醒熏破春睡,夢遠不成歸”(《訴衷情》)中,詞中女子在春睡中被濃郁的梅香薰醒,驚醒之后,更覺哀怨惆悵。由于夢境被打破,無法在夢中實現歸鄉的愿望,因而悵然若失。此時的詞人正遭遇南宋政治變故,中原淪陷,避亂江南,開始顛沛流離的生活。“夢遠不成歸”表達詞人背井離鄉后的“憂心悄悄”期待在跨越到“夢境空間”后得到短暫慰藉,怎奈夢碎更添愁緒。在“永夜懨懨歡意少。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蝶戀花·上巳召親族》)一詞里,漫漫長夜使得詞中人心情抑郁,久別的家鄉只能在夢境中得以相見。夢中的京都和京城街道都非常熟悉,“長安道”作為帶有故園標簽的公共空間,是現實記憶的關聯和依附,成為遠行旅人思鄉之情的載體,尤其當個體由于遠離而產生一定空間距離后,它便被轉化為個人感情的承載符號。在夢中得見昔日京都和街道凸顯出詞人深沉的戀地情結,唯有依靠夢幻空間才得以完成和實現。
故鄉對于個體意味著扎根的地方,它與安全感、歸屬感相關。夢中思歸是一場從實到虛的越界,一種蘊含豐富的個人體驗。同樣地,“被冷香消新夢覺,不許愁人不起”(《念奴嬌·春夢》)一詞則描寫冷冽春寒、衾被清冷,在香火消盡后,夢斷初醒,宿年愁緒襲來叫人再難安臥。此時的易安居士正獨居春閨,與丈夫趙明誠離散兩地,盡管詞中并未明確交代夢境的內容,但“不許愁人不起”一句流露出夢醒后襲來惱人的“萬千心事”與離愁別緒。無論是思鄉還是念親,現實空間都是無法實現的愿望,詞人并非就此被動接受,而是于詞作中構建出可供越界的虛幻夢境空間,使其得以滿足。
3.從“此時空間”到“彼時空間”
“詩詞中所創造的空間形態,也有許多是通過時間的移換,將現實中的空間與想象或回憶中的空間交織在一起,故此形成了詩詞審美空間的多重意蘊及靈動感。”這也是易安詞在空間制造上的一大特點。詞作常常突破了時間的線性順序,因而也以此打破空間存在的限定性和靜止性,讓空間變得更加具備開放性特征,增強了主體于共時狀態下在歷時空間中穿越的自由度,同時提升了詞境的張力。
“風住塵香花已盡,日晚倦梳頭。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語淚先流。聞說雙溪春尚好,也擬泛輕舟。只恐雙溪舴艋舟,載不動許多愁”(《武陵春》),詞中人物主體在“此時空間”中看到的是“風住塵香花已盡”,感受到的是“倦梳頭”“欲語淚先流”。暮年易安,孑然一身,唯覺悵對流光,愁思滿腹。基于感傷孤獨境遇營造的“此時空間”中,話鋒突轉到曾親歷過的“彼時空間”——“雙溪”,而這個空間意象已不僅僅是載物功能,而是美好過往的載體。曾承載歡悅往昔的雙溪舴艋舟,如今已經載不動愁情憂緒,已經由“欲語淚流”到“泛舟雙溪”,從“此時空間”到“彼時空間”,此類空間越界盡管以意識流的形式發生于思維世界,但是人生的輾轉流蕩已在此處形成實與虛的鮮明對比。本首詞中,詞人使用了“聞說”“也擬”“只恐”這樣表現不確定性的詞匯,本質上也是此時空間越界到彼時空間的過程虛化。
易安詞中三類主要的空間越界書寫,無論是真實空間的越界,抑或思維層面的虛幻越界,皆表現出詞人鮮明的女性意識。從“私人空間”到“公共空間”,通過越界突破了傳統規范限定內的女性生存空間界限,展現了女性開辟新的生存空間的可能性,同時也是對女性主體性和自由性的構建,是針對男權社會對于女性空間束縛的挑戰和抗爭。從“現實空間”到“夢幻空間”以及從“此時空間”到“彼時空間”的越界,盡管發生在精神層面,呈現出一定程度的虛幻性,然而,意識擺脫了現實的障礙完成對現實的暫時性改寫,同樣不失為構建主體在空間創造中的主觀能動性的一種方式。
三、易安詞女性空間內的身體敘事
身體是人存在于空間中的基礎要素,是生命及各種各樣的意義爆發的根基。身體也是空間的一部分。身體的行動和實踐是同空間秩序與規則密切關聯的。將身體放置于社會權力運作的中心位置進行社會學角度的探究源于福柯,他將身體附上政治化標簽——“權力關系對身體進行直接控制、干預,將其打上標記,并對其規訓和折磨,迫使它完成任務、展現儀式并發出某些信號。”約翰·奧尼爾(John O’Neill)在福柯之后推出了關于身體形態的五種構想,其中的兩種便是“社會身體”和“政治身體”。兩人研究的一致點在于承認身體象征著政治社會的秩序和價值。以此套理論為基礎探究易安詞女性空間中的身體敘事,可以發見宋代社會中父權政治思想體系之下構建的“女性身體傳統”,以及女性身體所體現的階級性、物化性和從屬性。
1.身體敘事與女性空間困境
按照敘事學的觀點,身體具有敘事的功用。女性身體是易安詞中大量出現的意象,多數詞作均圍繞對女性身體的敘事展開,展現出身體的政治論征象以及宋代女性的生存困境。在《減字木蘭花》中,女子于“賣花擔上,買得一枝春欲放”,花朵美艷絢麗,“猶帶彤霞曉露痕”,俏麗女子與嬌美之花本無相斥,然而,有“郎”在場的情境之下,女子竟起與花爭勝之心:“怕郎猜到,奴面不如花面好”,于是“云鬢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此處以“郎”為代表的男性成為女性美貌的標準制定者,他與詞中“云鬢斜簪”的女子構成了看/被看,評判/被評判的二元結構,觀看者作為行為主體是權力的代表,而被觀看者作為行為客體,是被規訓的對象。
在“視覺與主體關系”問題上,米歇爾·福柯提出“凝視蘊含權力”之說。“最早將‘凝視’所蘊含的權力來應用在兩性關系上的是約翰·伯格,他首次提出了‘男性觀看/女性被看’的概念,他說:‘女性自身的觀察者是男性,而被觀察者為女性。’”觀看者是主動的,代表著權力的實施者;被觀看者是被動的,代表權力受體。在宋代社會的兩性關系當中,男性是經濟基礎的支柱,主內的女性在物質需求和生命存續上依賴男性,因此女性身體在社會形態的塑造下,其純粹的生物性特征已經轉變為社會價值意識的載體。詞中的男性觀看者是標準的制定者和裁判者,而被看者女性自然作為“被物化”的客體,處于接受權力審視、規訓的困境之中。
在“繡面芙蓉一笑開,斜飛寶鴨襯香腮。眼波才動被人猜。一面風情深有韻,半箋嬌恨寄幽懷。月移花影約重來”(《浣溪沙·閨情》)中,“繡面”“香腮”“眼波”都是對年輕女子身體的描寫,女子如此風韻嬌美,皆因與心上人相約幽會而精心妝扮,女性為取悅男性審美,并按照男性的審美標準來打造自己的外表,以男權的標準衡量自身,是女性困境的另一表征。
相應地,若女性長期置于被男性觀看和審視的境地之中,這種被審視的姿態將在女性意識中逐漸內化成為一種堅定的行為律令,如果男性缺席或者離場,則會造成女性審美的缺失,因此而無心妝容。“瑞腦香銷魂夢斷,辟寒金小髻鬟松”(《浣溪沙》)以及“風住塵香華已盡,日晚倦梳頭”(《武陵春·春晚》)均描寫了男性觀者缺席,或者昔人已去后的女子境況。“觀看者”離開了觀看產生的場域,權力體系中的施權者已經離開,權力受體便失去了既存秩序中的原始平衡。容顏為誰呢?所以女子已經懶于妝容,無心梳理。身體不是一個封閉孤立的系統,它是人接受外界信息的感應器,易安詞中女性身體的敘事,是女性對外界信息做出的反應體系,是女性被男性規約、限制而“身不自身”境遇的寫照。
2.身體敘事與女性空間重構
女性空間內的身體敘事是易安詞中“精神物質化”的表現技巧之一。封閉而卑從的女性空間顯露著空間內女性主體的困境和焦慮。她們一方面感受到身體所遭受的孤寂、限制和壓力,另方面,也為國破民困的現實而感到失落痛心。“天接云濤連曉霧,星河欲轉千帆舞。仿佛夢魂歸帝所,聞天語,殷勤問我歸何處。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漁家傲》),在這首記夢詞中,夢魂在夢境中來到天國。福柯在《烏托邦身體》一文中闡明靈魂在身體里“以一種不可思議的方式運作”,強調靈魂與身體的一體性,他說“靈魂住在身體里,但它知道如何逃離”。因此,靈魂記事也是身體敘事的一部分。詞作中天帝“殷勤問我歸何處”,是詞人對當下執政者失望的對比性書寫,若現實中的帝王能如夢中天帝一般溫和、愛民,百姓便不會嘗辛嚼苦。“我報路長嗟日暮,學詩漫有驚人句。九萬里風鵬正舉”在回答天帝詢問中,作為詞中主體表達家國情懷的話語時援引了屈原《離騷》中語“路漫漫其修遠兮,我將上下而求索”和《莊子·逍遙游》中“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表達對國家存亡以及國民前途的憂慮,在意欲如大鵬振翅般逃離當下社會的想象中,顯示了詞人對時政的不滿和厭離之心,并暗示出欣求嶄新政治生存語境的理想。“風休住,蓬舟吹取三山去”一句是詞人對女性空間的重建。載著詞人的“蓬舟”是流動的女性空間,勁風若能將其吹去三山,便可享受不受這人間規約限制的美好空間,自由自在、無拘無束。這里表達著詞人對打破現存女性空間秩序、重新建構女性生存領域的強烈愿景。
綜上,慣以“婉約”風格為人稱譽的易安詞表面看來主要表現宋代女性的情感生活和閑愁別緒,然而,透過對其女性空間書寫三個維度的分析,不難看到的是,詞人對男權社會中的女性地位、命運以及家國前途同樣充滿擔憂與關切。在對女性空間的越界與重構的敘事書寫中,顛覆了父權制下女性封閉、卑從的社會屬性,解構了男性主導、女性邊緣的空間秩序,重新建構起自由、獨立、擺脫男性“凝視”的女性新空間,展現了詞人在封建制度下體認女性價值、重塑女性地位的勇氣與思想進步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