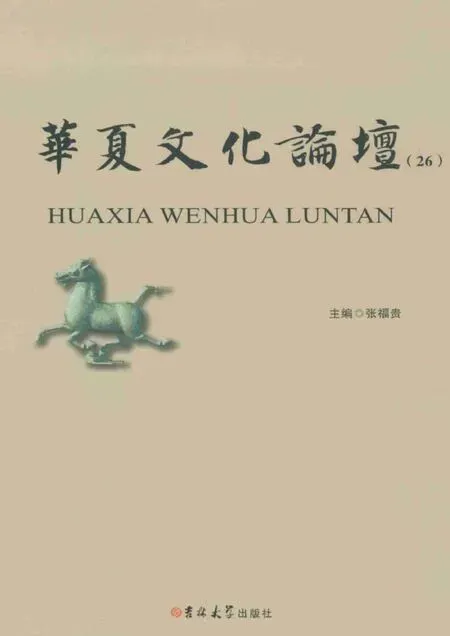《玻璃邊界》:現代性的空間書寫與回應
張 蕊
墨西哥作家、批評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在1990年出版的文論隨筆集《勇敢的新世界》中寫道:“在過去五個世紀的每個階段,我們都曾經對現代性懷有熱望,或是圍繞它進行爭論,或是對它予以排斥。”在作家看來,現代性不僅是20世紀中葉發生在拉美大地上具有顯學意義的“學術大討論”,更是貫穿拉美五百年歷史的深邃精神和文化訴求。對其而言,“現代性是一種文明,換言之,是各種可以被揚棄、可以被超越的技術集合。但是,也存在一種文化的現代性。”富恩特斯對現代性的觀照是一種批判性的接受或揚棄,他既不會被動地被裹挾其中,也不會不加分析地全盤否定。他將現代性理解為一組“矛”與“盾”的關系,他以“文化”之矛刺“文明”之盾。這種現代性的“矛盾”之刺,始終貫穿在富恩特斯的寫作中,1995年出版的小說《玻璃邊界》更是以獨特的方式呈現。小說中空間不甘示弱地從背景中前顯,與現代性互為鏡像。胡里奧·奧爾特加認為,“現代對于富恩特斯,對于從達里奧、巴耶霍和博爾赫斯開始的拉美文學,不是同質之物,而是從內部在閱讀中打開的另一個空間”。實際上,富恩特斯走得更遠,他是在寫作和閱讀中都打開了另一個空間,在其中回應現代性的“矛盾”。談論《玻璃邊界》,必然要提及一份協定,即1992年簽署、1994年執行的涉及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這份協定雖然并不能構成作品寫作的單純理由,卻顯然成為其創作的重要背景。美墨之間無論是在地緣政治、社會經濟還是文化生活層面的關系都是久遠、錯綜且復雜的。從地緣政治角度來看,墨西哥的命運一直緊密地與美國的抱負與政策聯系在一起,兩國關系常現暴風驟雨,“1846-1848年美墨戰爭造成美國吞并了墨西哥40%的領土,并從此開啟了長達一個世紀的美國對墨西哥經濟與政治事務的干預”。《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讓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更加緊密,尤其體現在經濟層面的依賴上,“墨西哥工業增長的重心已從北面轉向了兩國之間的邊境地帶”。《協定》的完成也“激起了加工廠的爆炸性增長。……由于加工廠的快速增加,這一北部邊境地帶帶動了重要的制造業和城市化行為。……美國邊界這一側的一個顯著特征是,它也從曾經的一個農業區域迅速轉變成了以工業為主的區域。”除了上述巨大的社會變革,人口的流動,邊界地帶合法的、非法的移民遷徙也始終是兩國的“邊境性問題”。對于《北美自由貿易協定》的簽署,富恩特斯的態度是開放的,帶有期許,但也有著自覺的警醒。在既不傷害墨西哥主權也不損害美國安全的意義上,富恩特斯認為,“《北美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是一個商業協定,更是墨西哥和美國的一種新關系。”
一、邊界:一道傷口,一道傷疤
“墨西哥和美國之間2500英里的邊界是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之間唯一可見的邊界。盎格魯美洲和拉丁美洲的邊界也始于此。它也是一道未完成的邊界,如同那些為了阻止西語裔移民的柵欄、壕溝、圍墻——所謂的玉米餅窗簾——被快速修筑起,旋即又被放棄,竣不了工。”在富恩特斯看來,美墨邊界是地理版圖與地緣政治意義上真實的存在,是固定且具體的,但同時也是變化和流動的,是橫跨在民族、種族、性別、階級甚至是歷史等一系列社會文化觀念中不可見的邊界,也是隨著兩國政治經濟關系的變化時而清晰時而模糊的邊界。2500英里的可見邊界是可跨越的,如同書中在邊界地帶不斷流動遷徙的人們的表現,不論是穿過邊界入住高檔酒店的教父和教女,或是去美國求學的墨西哥青年,再或是僅在周末穿過邊界務工的墨西哥工人,甚至是通勤去墨西哥邊界城市上班的墨西哥裔美國人,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邊境人在書中穿行。書中的九篇故事中到處可見穿越邊界的身影,乍看之下,小說呈現出了邊界空間人頭攢動、熙攘穿行的景象。但如果我們走近觀察每個人的生活,就會發現個人生活的窘迫和邊緣。公共空間的窒息感,“國恨家仇”的不甘,權力和暴力的延伸膨脹,讓每一個人在搭乘通向現代性的列車時都身負沉重的包袱。那道看似可以跨越的地理邊界線永遠隱形地橫亙在前面,現代社會物理空間與更加廣闊和抽象的政治和話語空間、個人和歷史空間之間的聯動關系和互動影響使這條“線”愈加錯綜、復雜。
有學者將富恩特斯的寫作歸入奇卡諾文學和邊界寫作的范疇。格勞里亞·安扎杜爾說,“美墨邊境是一道敞開的傷口,在那里第三世界與第一世界摩擦流血。在結痂之前,它再次出血,兩個世界的生命之血相融形成第三個國家——一個邊境文化。”富恩特斯則在不同的文本中多次提到“美墨邊境是一道疤痕。”安扎杜爾在美墨邊境中看到了存在于二者之間無法避免的沖突,以及在沖突之中尋求并產生的一個嶄新的文化地帶,亦此亦彼的空間。盡管在富恩特斯的作品里也很大程度上體現著安扎杜爾的觀點,不過,當他提到“邊境是一道深深的疤痕”時,則更多是從一種歷史的維度看待這一空間的形態的。“(邊界)是一道疤痕,因為,在那兒,我們在1847-1848年的戰爭中丟失了一半的領土……,我們不會忘記。工人們也不會忘記。……穿過邊界的墨西哥工人正在穿越的不是一道邊界,他們正在穿越的是一道疤痕,朝向他們認為是自己的土地。在這里我不是無身份的。沒有身份的是美國人。……我比他們早來。這是我的土地。”歷史的傷疤趴伏在美墨邊界之上,歷史的記憶烙印在這一空間里。在曾經屬于自己的土地上以異鄉人的身份更甚者以偷渡者的身份生活,是難以釋懷的不甘。更令人不甘的是此刻安居其上的美國人忘記了這一段歷史。所以,《掠奪》中的墨西哥大廚狄奧西尼奧決定“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純正的墨西哥語言、人種和美食的大炮重新征服他們。”換言之,用墨西哥的文化征服美國。空間的收復以另外的形式完成,用墨西哥的記憶喚起美國的遺忘。但是,如果我們以為作家是站在一種絕對的歷史立場上來完成邊界穿越的話,就會陷入到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中。雖然這是一道深深地刻在所有墨西哥人心里的疤痕,但遺失之痛不僅僅來自鄰居的空間掠奪,更在于這片土地在別人手里有著更好的面貌或面容而生出的“恨其不爭”的隱痛,以及伴隨其間的對這一外來文化的肯定和吸收。“如果美國人沒有從我們手里搶走這些土地,所有這一切都不會存在。在墨西哥人的手里,這兒會是一片大荒地……”。顯而易見,這是一種“邊界”的視角,即不是站在對地理空間的占有和掠奪層面絕對的、純粹的單向度體察和考量,而是立足于伴隨著空間劃分產生的不同文化的流動、互動的雙向且多維的視角。作家在另一個故事《打賭》中重申了自己的文化態度。《打賭》描述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時刻,一個別有深意的邊界空間。當西班牙女導游作為游客與負責文化旅游路線的墨西哥司機兼導游站在迭戈·里維拉描繪征服史的壁畫前,寥寥數語談及征服、印第安文化、墨西哥文化和歐洲文化時,歷史和現實的空間重合,不同的文化交織在一起。《打賭》也是《玻璃邊界》這部小說中唯一一個在其中打開了西班牙空間的文本。16世紀西班牙征服、掠奪了印第安人的土地,19世紀美國人掠奪了墨西哥的一半土地,今日的墨西哥與西班牙和美國之間的羈絆是歷史的也是現代的,這構成了富恩特斯寫作的“邊界”特質。正如何塞·埃米利奧·巴切科所說,富恩特斯的作品“一邊與西班牙對話,另一邊則是與美國。”
在富恩特斯文本中與“疤痕”關聯的另一個詞語是“暴力”。富恩特斯說,“暴力是20世紀最被認可的身份證明”。在《玻璃邊界》中展示的暴力空間比比皆是,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打賭》中受人欺凌的傻子小巴科,他智力不足,住在閣樓,有唯一一扇夜晚不上鎖的門,住所整潔干凈,喜歡白天在廣場上享受陽光的愛撫。然而這一切都讓“你”和你的伙伴們感到不適,于是“你們”通過打賭,弄臟小巴科的閣樓,并在廣場戲弄他,“你”甚至對小巴科拳打腳踢,全然不顧他的哀求。盡管在內心“你真正想揍的是你的朋友,那些小混混……”。小巴科生死未卜,最終“你”被一名自稱是其父親的人脅迫,以打賭的方式在幽暗的隧道中開車逆行,撞上了迎面而來的車。如篇名《打賭》所暗示,暴力是無常的,是隨意的行為,不計后果。暴力無孔不入,不論是個人空間——小巴科的閣樓,還是公共場所——廣場,暴力都可以橫行。此外,以暴制暴又導致暴力之間形成了惡性循環。此刻,我們也會想起那位串聯起整部小說的人物——墨西哥資本家萊昂納多的死亡,五顆高強度射擊的子彈穿透他的身體,他被謀殺了。原因很簡單,盡管他是邊界地帶的風云人物,富甲一方,但他終究不是美國人,所以利益糾紛中,他是被犧牲的那一個,且還是以暗殺的方式。更加血腥暴力的場面則是一群光頭黨成員,他們圍攻墨西哥勞工,對著后者瘋狂掃射,揚言要入侵墨西哥,屠殺墨西哥人。射殺之后,“其中一個人把棒球帽戴在光頭頂上,對著空氣,對著他的同伙,對死者,對沙漠,也對著夜晚說:‘今天我把死亡的閥門開得夠大!’他露出獠牙,下嘴唇內側刻著紋身:we are everywhere”。暴力不僅是這些極端民族主義分子的暴行武器,更是一場瘟疫,蔓延在各個角落。“同樣是這個國家,到處是害怕走在街上與他人眼神交錯的人,擔心對方是理念不同就有權殺死我們的山達基教教徒、從精神病院和超負荷的監獄里釋放出來的殺人犯、攜帶艾滋病毒針管報復社會的同性戀、隨時想把所有深色皮膚的人都斬首的光頭新納粹分子……它要如何變得有序?”如果說,小巴科、“你”以及萊昂納多都是“身體”暴力的犧牲品,在其他的篇章中,暴力則以權力之名,以各種偏見和觀念對他人實施“精神”凌辱。《朋友》中房主艾米小姐咄咄逼人的種族歧視,《加工廠的馬琳切》中女工們承受上級的謾罵和性騷擾,胡安·薩莫拉因為同性戀身份承受的羞恥和痛苦,邊境巡警丹對墨西哥移民的仇恨、對墨西哥下屬的懷疑和挑釁,以及那些被需要時可以順暢進入美國務工,不被需要時則被驅逐的成千上萬的墨西哥勞工。暴力是身體的疤痕,是精神的創傷,是現代社會的癥候。
二、(生)活在他處:“烏托邦”之夢與“異托邦”之淵
“烏托邦一直都是滑翔在我們蒼穹之下永恒的雙翼,但它也是我們西西弗斯事業最重的一塊石頭。如同柯勒律治的信天翁,過去的某一天曾經飛翔,而今天看來更像是壓彎我們脊背的負擔。”烏托邦和現代性的關系在富恩特斯的思想中交纏,很難說是誰先塑形了誰。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開拓了一種前全球化的視野,也開啟了現代性的進程,烏托邦的概念術語也隨之成形。16世紀至19世紀間,烏托邦從歐洲對美洲空間的渴望轉向美洲對歐洲現代時間的渴望。而自19世紀上半葉拉美絕大多數國家相繼獨立后,烏托邦關系也出現在美洲大陸內部,出現在盎格魯美洲和拉丁美洲之間。顯然,前者成為了后者的烏托邦,成為了后者的現代性追趕對象。對此,與美國為鄰的墨西哥感受頗深。在歷史的大洪流中,個人被裹挾其中,宏大的烏托邦愿景成為了個體降格的烏托邦夢想,離開故土,去到他鄉,過上比現在好的日子,即使僅為生存,這樣的信念推動了從19世紀后半葉開始的多次墨西哥移民潮。
《玻璃邊界》中的最后一個短篇《格蘭德河,布拉沃河》的名稱是同一條河的不同稱呼。美國這邊的名字是格蘭德河,墨西哥這邊的是布拉沃河。一條河一分為二,這一邊是貧窮的自己的家,另一邊則是別人的家,那個可以是烏托邦的地方。在這個篇章中,富恩特斯對前文出現的人物做了交代,彼此之間沒有關系的人物瞬間形成了網狀的聯系。《朋友》中的墨西哥女仆何塞菲娜家族的移民史由于貝尼托·阿亞拉這個人物的出現變得清晰。1914年左右,其曾祖父福爾圖納托是家族中第一個離開墨西哥來到美國的人,為了躲避革命,也為了生計。在30年代的失業潮中曾祖父被趕出美國。二戰期間,他的兒子,另一個福爾圖納托作為短工合法入境,對于他而言美國只是暫作停留的地方,他的愛留在了河的另一邊。之后是成為“濕背人”的貝尼托·阿亞拉的父親薩爾瓦多,成為“濕背人”也即偷渡者是逼不得已的選擇,是為了能讓家人在布拉沃河一邊活下去而要完成的烏托邦冒險。現在輪到了貝尼托,他清楚“每個時代都很艱難,但當下卻比任何時代都更難。因為現在仍有需求,但也有仇恨。”幾代人跨河而來,隱忍著恐懼和仇恨,他們從來都不是為了實現一個人的烏托邦,而是一個家族的烏托邦,為了一個降格的烏托邦夢想:讓自己和家人生存下來。
如果說墨西哥社會底層人民的烏托邦夢想是悲壯的,那么特權階層的烏托邦之夢則難脫矯情之氣。在富恩特斯看來,烏托邦以兩種方式運作,其一是看向過去,其二則是面向未來。它或是一種指向源頭的假定社會的美好,或是指向未來一個更好的完美社會。不論哪一種,不論是懷舊還是向往,都不是對當下的指涉。在開篇《首都女人》中,女主的祖母拉博爾德在家族失勢后,依然無法從過往生活的榮耀中醒來。然而現實無法改變,能做的只有懷舊。懷舊的方式就是收集一切舊物,各式各樣的舊物,以至于“所有人都如夢方醒:在她的抽屜里,她的柜子里,這位老人保存的是一座金礦,是回憶之銀,記憶之珍寶……她是懷舊的女沙皇啊!她最有文化的孫子說。”抽屜和柜子成為了承載記憶的地方,這些在此刻的空間成了非此刻的空間,是一個個小小的烏托邦。不僅如此,女主人公雖沒有見證過家族的榮耀,卻也時常生發出懷舊的情緒。她選擇在婚禮上穿舊式的禮服,在夢中被圍困在修道院。不論是她的有意識的選擇,還是無意識的夢境,都映射出她對于現實下一切的不滿足。
福柯在《另類空間》中提出了與烏托邦空間不同的空間概念——異托邦。在福柯看來,異托邦與烏托邦一樣具有普遍性,在各種文化中都可見到。不同于烏托邦,異托邦“是真實存在的空間,扎根于現實之中,然而卻迥異于它所反映或者映射的一切場所。”異托邦是存在于現實中的異質空間,是“世界中的世界,既映射出外部的世界又與其存在差異。”“異質”指涉出異托邦中包含的多重關系,甚至是矛盾的并置,在《玻璃邊界》中我們可以選取兩個有代表性的異托邦,一窺其對于現代社會的隱喻。一是《首都女人》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教父萊昂納多的府邸,一個叫迪士尼樂園的街區,樂園中充斥著各種異國風情,“希臘式柱頭的宅第……”“……阿拉伯清真寺”“新古典主義風格的檐廊”。不僅如此,這個街區“沒有一片瓦、一塊土坯,只有大理石、水泥、石頭、石膏還有鐵柵欄,鐵柵欄后面還有鐵柵欄,里面還有鐵柵欄,前面還是鐵柵欄,一座柵欄圍成的迷宮。”二是《加工廠的馬琳切》中每個周五女工們一起去放松的迪廳“馬里布”。在那里“一切都被允許,所有丟失的情緒,禁忌的姿態,被遺忘的感受,都在這里得其所哉,名正言順,縱情享樂——特別是享樂,這才是最好的。”我們會發現,這兩個空間分別具備了福柯對異托邦的若干特征描述。此外,二者也恰恰構成了異托邦與真實空間關系的兩個極端情況:創造出一個幻象空間,或是創造出另一個補償性的空間。第一種情況也與鮑德里亞的“超現實”高度契合。“……這個幻象空間顯露出全部真實空間更加虛幻……”。萊昂納多的迪士尼樂園就是這樣一個幻象空間。“迪士尼樂園”的名字以及樂園之中各種仿古風格體現出的奢華都在傳遞這樣一個信息:這就是萊昂納多一家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就在此處。然而一層一層的鐵柵欄將這個華美的街區包裹得更像是一座監獄、一個牢籠,不斷暗示他們不想生活在此地,這不是他們想要的生活,他們的生活在別處。萊昂納多的妻子和她的名媛圈會在豪宅中被夕陽的奇觀震撼,“那二十個女人沉默地望著日落,就像在哭泣著參加她們自己的葬禮。”而他們的兒子只想在一個印第安人的農莊里讀書、聽音樂。萊昂納多本人的真實生活如這座富麗堂皇的府邸般虛幻,權勢滔天的他輕易地被五發子彈穿透了身體。作為補償性空間的“馬里布”迪廳則以另一種方式宣告了真實生活的窒息。她們的家庭、工作、甚至是愛情都不能善終;一切的隱忍卻可以在這個叫做“馬里布”的迪廳中得到宣泄。
三、阿萊夫:語言、想象和空間
《玻璃邊界》的文本結構是特別的,是立體的、空間的。它是由九個短篇組成的一部長篇小說,因此,體裁是跨界的,既是長篇小說,也是短篇小說集。這不是富恩特斯第一次采用這樣的形式,很明顯,作家對這樣一種形式有所鐘愛。因為這一特殊結構或敘事方式打破了小說慣常的時間推進,而以空間并置的方式使其獲得完整。前八篇故事可以獨立成篇,閱讀順序完全可以打亂,如果只有這八篇,那么這部作品還不能稱之為長篇小說,叫作短篇小說集更加合適。富恩特斯自然不會這么做。所以書中的第九篇即《格蘭德河,布拉沃河》既起到了畫龍點睛的作用,又發揮著體裁轉換的功能,并給予作品總體靈魂。整部作品形成了一種圓錐形的結構,一而多,多而一,其中的各面既可以獨立成篇、獨當一面,四方輻射、各自玲瓏,又面面相覷、面面相連,中心輻輳,集成一個整體。對此,富恩特斯說道:“《玻璃邊界》,是在短篇中尋找統一,更是抵達一種整體,但是是還未完結的整體,它允許你繼續再創敘那些它自身的未終結所摻裹的敘事可能性。”整體意味著包容和接納、拒絕、排外和仇外。“沒有排外的現代性,它必應是包容的。”作家在《玻璃邊界》中的文學創作觀念與其現代性思想描畫出相同的軌跡。
我們需要注意,富恩特斯強調的是整體而非統一,因為前者意味著多樣和異質的并置、包容,后者則偏向同質和單一。富恩特斯在評述福克納時談道:“人類瓜分土地,而且……也離間了自己。集體的重建——遺失的土地,人類比起被歷史打敗更像是被自己打敗,因為他們分割了自己的靈魂就像他們劃分了自己的土地一樣……”。這些話語也再一次回響在這部作品中。其中的第四篇《忘卻之線》是很獨特的一篇,撇開第九篇的特殊性,在其余的八篇中《忘卻之線》的位置正好處在中間地帶,篇名似乎在作品中畫出了一道線,形成了一道邊界。主人公是一位癱瘓坐著輪椅的老人,不知什么原因他被放置在夜晚的街道上,他不能講話,不記得自己是誰,忘了自己的名字。作品整篇都是這位老人的內心獨白以及與自己的對話。他看到腳下一條涂了磷的發光的線,“它妨礙大地成為大地。大地沒有分界,那線條說有。那線條聲稱大地分裂開了。那線條將大地變成別的東西。……那條線是與大地相異的另一種東西。大地不再是大地。變成了世界。”顯然,那條線是人為的,是人類離間自己的證明,將完整的大地變成了世界,擁有了時間和空間。在其中,人類以種族、階層、性別、利益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理由互相傷害。隨處可見的透明邊界,一道道隱形的屏障阻隔交流,人們變得冷漠,感到孤獨,疏離;權力濫用,暴力增長,強者欺凌弱者,弱者欺凌更弱的人,直至相互摧毀。人成了最卑微的存在。“我是個人。我不比一條線更有價值嗎?”面對大地的分裂,價值的踐踏,作家能做什么呢?正如富恩特斯所言,“文學早就明白其政治職能不可能僅以一些純粹的政治術語就會行之有效,這種職能要通過作家在可交流的想象和重固的語言層面影響社會價值來實現。”富恩特斯認為,正是以這種方式,現代文學創造了一種聚合的傳統,將美學要素和政治要素聚合,將藝術處境和城市處境都納入其關注視野。
《格蘭德河,布拉沃河》中有一個身影最應受到矚目,一個騎著哈雷摩托車穿梭在邊界的年輕人何塞·弗朗西斯科。他是墨西哥移民的后代,站立在河的中間,左邊是格蘭德河,右邊是布拉沃河,或者相反。他出生在格蘭德河一側,卻久久凝望布拉沃河那一側。他不愿意把名字何塞改成喬,因為那樣他“會變成啞巴的”,他不想成為啞巴,他“想讓人聽見他的聲音,他想寫東西,他想給予自己從小就聽到的所有故事一個聲音,關于移民、偷渡者、墨西哥的貧困和美國的繁榮的故事,尤其是關于家庭的故事,這是邊境世界的財富,大量未被埋葬、拒絕死去的故事,如幽靈一般從加利福尼亞到得克薩斯四處游蕩,等待著有人講述它們,寫下它們。”在他的筆下,如同在富恩特斯的筆下,所有的無名者、無聲者都有了一席之地。他書寫的不是西班牙語,也不是英語,而是奇卡諾語言,一種誕生自雜糅文化的雜糅語言。我們會不由得想起大廚巴科在美食講座上,面對講英語的大學生,使用從墨西哥裔美國電影演員處學的口音,“和大量從西班牙語直譯過去的句子,使眾人聽得津津有味”。
何塞所做的就是要通過聚合功能的語言、文字還有想象,超越那道人為地將大地和自己都離間了的線。他想要做的,也是富恩特斯已做的,用語言和想象構建出一個霍米·巴巴的雜糅空間,一個索亞的第三空間。或許,富恩特斯更愿意將自己在文學中打開的這個空間比作博爾赫斯筆下的那個包羅萬象的阿萊夫空間。富恩特斯和索亞都對博爾赫斯的阿萊夫空間備加推崇不是沒有緣由的,兩人在對文化的理解上有著共同的著力點,他們都希冀一種“想象”的空間,在其中,我們能夠以超越而非對抗面對自我和他者。
結語
富恩特斯在《玻璃邊界》這一作品中為現代性打開了一個新的思想空間,他以“邊界”作為空間意象表征與書寫對現代性的批判和反思。也許用作品中的兩段話來總結作家對現代性的空間書寫應該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說“可憐的墨西哥,可憐的美國,離上帝那么遠,離彼此那么近”是現代性語境中美墨關系令人不甘的現實,那么,“難道不是每片土地都有它看不見的復體,在它身外的影子,走在我們身畔,就像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不為自己所知的第二個‘我’并肩而行?”則是對這一現實的思考與回應。書名取自其中的一篇同名短篇,作者以此篇的篇名作為本書的書名并非隨意,這篇故事本身如同美墨關系的一個縮影。其次,使用“玻璃邊界”這一表述在某種程度上也成為二者關系的形象隱喻。玻璃雖不是現代才有的材料,但因為其特別的材質屬性以及在現代建筑中的大面積使用讓其與現代社會產生了更加緊密的互涉關系。玻璃透明的物理屬性衍生出“顯”和“隱”“真實”與“虛幻”共在的引申意義。玻璃是透明的、又是隔離的,是透明的隔離,又是隔離的透明。邊境是有形的空間,邊界則是更為廣泛、復雜的隱形的空間。無論是哪一種空間,空間都不應是“你”與“我”的阻隔或威脅,富恩特斯所要表達的是我們應該創建一個“我們”的空間,那個跨越、超越而非對抗的包羅萬象的阿萊夫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