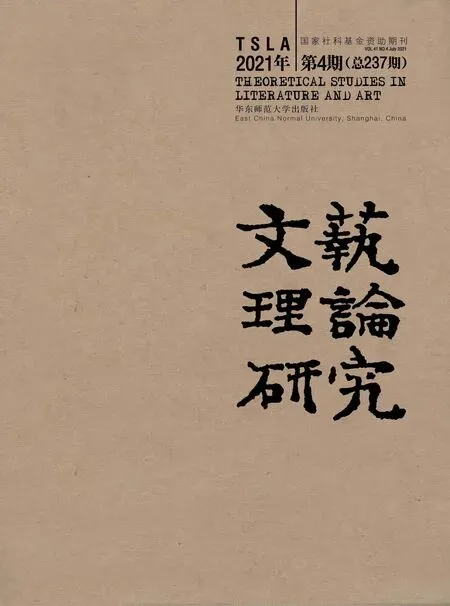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人物形象
許子東
一、 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官員形象
這基本上是學界的共識: 現代文學最重要、最成功的人物系列是知識分子和農民形象。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在他們的合作論文《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中指出:“與‘改造民族的靈魂’這一總主題相聯系,在20世紀中國文學中,兩類形象始終受到密切的關注: 農民和知識分子。在這兩類形象之間,總主題得到了多種多樣的變奏和展開: 靈魂的溝通,靈魂的震醒,靈魂的高大與渺小,靈魂的教育與再教育的互相轉化,等等。”(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7)但是閱讀20世紀中國文學,從胡適、魯迅讀起,還是從梁啟超、李伯元讀起,有很大分別。在20世紀初的晚清四大名著中,主人公并不是“士農工商”,而是各種各樣的官員。官員形象雖然在“五四”以后的小說中被有意忽視,但是到當代小說中又成為重要人物系列。所以,本文認為,有必要考察官員/官場形象在20世紀小說中的發展變化(官員、官場、干部,在本文中均為中性概念)。
李伯元對晚清“官本位”現象的無差別批判,分為四個層次。第一是解析無官不貪的人性原因——貪腐是剛需。清朝后期半數官員是捐的,捐官投資,官員家庭開銷,以及向上級送禮(“政治保險金”),合起來超過官俸部分,必須靠實缺貪腐。這幾乎是經濟學原理。第二,普遍貪腐必然導致教育、經貿、軍事、吏治,還有救災、慈善、外交等等官場全方位失職。而且從知縣、臬司、藩臺、巡撫,直至軍機處的中堂,層層貪腐層層保護,反正“佛爺也知道,通天下十八省,哪來的清官”。清廷非常體諒,現實當中的慈禧也沒有派人到租界去抓小說家,反而把小說當作官場反貪的線索。《官場現形記》人物太多,沒有突出的文學典型。但其作為群象刻畫,對中國社會的理解,卻是后人所不及的。“五四”以后,人們以為“官本位”現象一去不復返,其實中國的傳統文官制度,歷史悠久,也可能來日方長。中國小說家在100年前就已看到,后來國人忙于追求革命或現代性,居然沒有足夠重視。
第三個層次,晚清小說認為貪腐之可惡,不僅在于社會成本太高,或者延誤軍機政事,更在于官員道德墮落、違反儒家倫理(最觸目驚心的底線,是官員將女兒送給上司做妾)。文學始終是人學,但晚清重視“人倫”,五四最關心“人生”,延安以后強調“人民”,80年代重新回到“人生”。第四個層次,李伯元等人的寫作動機,是真心認為中國病了,病因就在官場。官員怎樣,百姓就怎樣,上行下效。所以,批判拯救官場,正是拯救國家的關鍵。
晚清四大名著,還有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主要人物都是官員,差別只是李伯元冷嘲,吳趼人熱諷。《孽海花》男主角身兼官員和讀書人,藝術價值最高的《老殘游記》,關于官場的立論也最令人注目——清官可能比貪官更壞。
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和官員(干部),有一個“互相改造”的過程。在晚清階段(只有在晚清階段),知識分子自以為擁有巨大精神優勢,或如梁啟超在體制外設計國家前途(還極為精準),或如李伯元寫小說把官員當學生教訓。這些晚清小說中的官員主角,到“五四”新文學,幾乎忽然全部消失——這是一個學界似乎還很少討論的文學現象。從1918年的《狂人日記》,到1943年的《小二黑結婚》,中間二三十年的中國現代小說,極少以官員為主要人物。僅有的少數例外或有1938年的《華威先生》,以及茅盾早期中篇《動搖》等。
為什么晚清作家認為官員/官場是中國問題的關鍵,到了五四文學官員/官場卻好像被突然忽視了?這是一個可以從中國作家生態變化、民國出版審查制度、社會政治思潮變化,以及現代文學本身發展規律等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討的課題。
第一,魯迅說過,“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共和使人們變成沉默”(魯迅,第三卷554)。在軍閥和國府管制下,文學要在報刊審查制度及警察暴力下批判官員(民國后改稱“干部”),比在租界嘲諷晚清官員難度更大。
第二,辛亥革命、北伐“清黨”等等政局變化,讓人們看到即使舊官場被打倒,新官上任也未見得會變好。所以關鍵并不在官員和官場。“五四”作家不再像李伯元、劉鶚那樣有信心教育官員,也不再只將官民對立視為中國危機的關鍵。魯迅看到,在傳統禮教和社會秩序下,官員和民眾都有被人壓迫和欺負別人的兩重性。“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魯迅,第一卷224—227)因此,“五四”文學的批判重點就不僅是官,也不僅是民,而是官民共享的國民劣根性。“五四”文學的確主要寫知識分子和農民,但是往前上溯到晚清,往后延伸到50年代,我們就會看見官員這條人物主線,只是曾經“中斷”了一段時間。
第三,民國文學中“官場”貌似缺席,其實是隱避,而不是真正消失。魏連殳做了將軍的秘書,顯示“孤獨者”的尷尬處境。“狂人”最后病愈候補實缺,做官等于失敗墮落。茅盾的《動搖》詳細記錄了北伐前后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如何選舉、怎樣戀愛,也是早期民國官場一角。官府依舊迫害民眾,只是作家不讓高官直接出場。只有鴛鴦蝴蝶派小說如《啼笑因緣》《秋海棠》才會直寫軍閥作惡。“五四”小說更注重渲染官場的幫兇爪牙,給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比如《藥》里的康大叔,比如《駱駝祥子》里的孫偵探。
官員(干部)形象再次成為現代小說的主角,是在1943年的《小二黑結婚》里。主人公名義上是小二黑、小芹,最出色的形象是三仙姑、二諸葛,但是對劇情起關鍵作用的是村武委會主任興旺、村鎮委員金旺、婦救會主任金旺老婆,當然,最關鍵的還有區長(也是趙樹理小說與故事原型的最大不同)。
《小二黑結婚》重新出現了傳統審美的“善惡對立”的格局,但不只是晚清的貪官欺壓民眾,還有好官為民做主。官分善良邪惡,民分先進落后,從1943年一直到70年代末,中國小說里一直貫穿著這種人物四分法——既要改變晚清的“官-民對立”情節模式,又要延續民間文藝的“忠-奸對立”審美習慣,區別好官壞官,依據國共或者路線,劃分群眾的標準,依據年齡或財產。這個時期的官員/干部形象,內心(格物、致知、修身)和工作(齊家、治國、平天下)沒有矛盾。《紅旗譜》中地下黨教師賈湘農一心革命,發動農民造反。地主馮老蘭兒子認識國軍司令,鎮壓學運。《紅巖》里的許云峰、江姐心胸高潔,為民眾謀解放;反派徐鵬飛、嚴醉等,態度虛偽,手段毒辣。《紅日》里的沈振新軍長有將軍風度,只有張靈甫稍微復雜一點,臉譜化中有點變化。
黑白分明、善惡對立既是戰爭文化需要也是通俗文學規則。《林海雪原》里,國軍殘余土匪相,203首長像王子。《青春之歌》中林道靜的前后兩任地下黨男友既是戰士又是君子。革命歷史小說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中青年,英俊正氣。舞臺劇中則是年輕美麗的女性吳瓊花、韓英、江姐等,被丑陋的老男人南霸天、彭霸天、徐鵬飛等審問迫害。性別斗爭悄悄融入革命題材。
從文學角度看,晚清小說中的“官員”形象,除了狀元官金雯青與行醫文俠老殘,一般共性多、個性少。五四文學“官場”雖被忽略,魏連殳、華威先生的性格還是充滿了矛盾或戲劇性。50年代文學的主人公,比較知名、比較感人(也比較有文學意義)的形象,大都是已有“干部”之心,尚無“官員”之位(如許云峰、江姐、盧嘉川等)。“干部”和“官員”這兩個概念重新發生聯系,是在50年代的《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兩者的大規模被混淆,則是在80年代以后,尤其是在通俗文學中。
晚清寫官是無差別批判,五四寫官是有差別忽略,“十七年”寫官是黑白分明,第四個階段,更準確地說是70年代末開始,官員形象不僅重新回到了中國小說的中心舞臺,而且至少分化成五個類型。
第一類是許云峰、江姐等英雄形象在新時期的延伸,內心品德高尚,做事也有益于社會。比如喬廠長,《平凡的世界》中的田福軍,《芙蓉鎮》里的谷燕山,都胸懷坦蕩,把民眾利益放在首位。組織部的林震是這類形象的先鋒。
毛澤東早在《組織部來了個年輕人》中就看到了官僚主義,指出了“干部”與“官員”這兩個概念之間的聯系。喬廠長、田福軍因為身處改革開放時代,更容易得到上級的支持。比起許云峰這種一代英雄,他們也可以有些小缺點,比如喬廠長急急忙忙找女工程師結婚,比如田福軍開會以前要摳腳,谷燕山在戰爭當中被打成性無能等等。小缺點是為了糾正“高大全”,使英雄更有人情味。
仔細想想,張承志歌頌的幾代哲合忍耶教主,好像也都是內心善良、行為高尚的“領導”。
第二類,就是負面的官員形象——徐鵬飛、張靈甫及金旺、興旺的繼承人。這些人內心丑惡,行為害民,至少也是“精致的利己主義官”(如韓常新)。這類人物在“新時期”文學中相當豐富。《芙蓉鎮》里的李國香因為性心理不平衡,才要在政治運動當中出風頭。《古船》里的趙多多與趙四爺,一個粗野,一個文雅,都是貧苦出身,最后變成新惡霸——趙四爺是個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學典型。《平凡的世界》里有幾位在“文革”后期積極打擊農民村“資本主義”的干部,有的隨形勢轉向,有的一直有問題,不是睡寡婦,就是搞權斗。在新的路線斗爭格局下,他們屬于反改革的反派人物。《平凡的世界》當然主要寫農民,但與農民對話的不是知識分子,而是各級干部——在大部分現當代小說中,“民”與“官”之間(之外),總有一個“士”的角色與角度,比如路見不平的老殘,目睹閏土、祥林嫂的“我”,聽福貴講如何“活著”的文青。只有《平凡的世界》(及《官場現形記》)例外,沒有出現“士見官欺民”的現代小說常見模式(這也是士、民、官三種形象的最基本組合關系)。或者是路遙、李伯元隱身在作品中,讓民眾自己面對官員或干部。這兩部被人低估的作品比較能體現中國國情: 百姓受難時,哪里總有(哪里需要)讀書人在一旁目睹同情?
第三類官員是80年代文學的新品種,在五四、延安時期和“十七年”都沒出現過,卻成為20世紀晚期小說中最常見的干部/官員形象。通俗講就是“好人做壞事”,分明是好官,卻壞了老百姓的事情。
李順大辛苦積累蓋房材料,結果被“大躍進”折騰沒了。區委書記劉清同志,一個作風正派、威信很高的領導人,特地跑來探望他,同他促膝談心,最后硬是把國家應有的賠償給勸沒了,勸得李順大還流淚感動。另外一個吳書記,看到農民陳奐生躺在車站,身體不舒服,好心叫車把他送進縣委招待所,沒想到一晚上住宿費五塊錢,把陳奐生進城賣農副產品的收入去掉了大半。劉清同志、吳書記在高曉聲筆下都是好人,可是做的事情分明害了農民。
更典型的案例,當然是余華的《活著》。農民土地入社,忙于煮鋼鐵,然后大饑荒等等,都是聽從隊長的指揮的結果。農民都相信隊長,隊長是好人,可是好人領導大家走向了災難。縣長夫人生病,福貴兒子抽血死了。偏偏縣長春生和福貴原是國軍戰友,又是好人辦了壞事。只能流淚,不能問責,只寫細節,不論背景。這種好心卻做壞事的傳統,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鹿原》——20年代共產黨員鹿兆鵬就鼓動農民運動,結果砸了祠堂毀了鄉約……
閻連科《受活》里的茅枝婆是好干部的最后一個榜樣。一個老紅軍,幾十年來領了一村的殘疾人入社、煉鐵、度荒年、經“文革”。茅枝婆革命道德絕對高尚,可是她一生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害了受活莊的鄉親,最后她非常后悔。
第四類官員形象是“官僚主義者”,是一種從理想朝氣漸漸變成世故犬儒的干部。最典型的當然是50年代的劉世吾,他年輕時可能也是一個林震,經歷多年“官場”,百般錘煉,成熟了,有涵養了,也變得世故了,明哲保身,事不關己,高高掛起了。這種官僚化(干部變成官員)的過程到底是中國特例還是普世規律——王蒙提出的問題,在中篇《蝴蝶》里,還有韋君宜的長篇《洗禮》里,都有更細致的探討。總體上,作家相信經過“文革”洗禮、忘了初心的干部,能夠在人民的感化下重新成為好戰士、好官員。同時,中國作家也愿意想象或期待干部/官員的知識分子化——如果某官員愛讀書,尤其是愛讀文學書(特別是《靜靜的頓河》《契訶夫全集》之類),通常內心里(或曾經)是個好官。這種一廂情愿的官場想象,至少是從《孽海花》開始的。
第五類官員形象特別奇葩,分明不是“好人”,他們在人格道德上都有明顯缺陷,卻能在客觀上為民眾辦實事。比如《受活》里的柳縣長,追求個人崇拜,相信白貓黑貓,想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但是他的“政績”絕術團的確幫殘疾人賺了人民幣。想買列寧遺體,要不是選錯政治符號,如果修個伏羲或西施墓,也完全可能振興當地經濟。還有另外一個讓人忘不了的官員——《白鹿原》里的白孝文,做過國民黨保安團長,小說結尾又做新社會的縣長,他將來會不會有政績呢?還有閻連科新作《炸裂志》里的領導,以及余華《兄弟》里的李光頭,即使不是官員,也很有權勢。明明是個壞人,怎么居然也可能做好事呢?這又是一個嚴峻的問號。
在以上五種干部類型中,以第三和第四種最有文學意義。中國現代文學最重要的人物系列就是農民、知識分子和官員。第三種“好心辦壞事”,是農民對官場的基本想象,第四種“好干部愛讀書”,代表知識分子對官員的美好期待。
二、 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
《管子·小匡》說:“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黎翔鳳400)士農工商也是20世紀中國小說里人物形象重要性的一般秩序。知識分子一直是主角,一來作家身份就是知識分子,是創作主體;二來大部分小說的主人公也是知識分子。20世紀小說里的知識分子形象,最簡單的概括就是吶喊與彷徨的交替——晚清是吶喊,五四是彷徨,50年代又吶喊,80年代又彷徨。
百年來,晚清時期中的知識分子主人公(或敘事者)最勇敢也最有信心,或為“國師”頂層設計(《新中國未來記》),或在租界(局外)毫無顧忌地批判清朝(《官場現形記》)。作家與主人公心態高度重合,感時憂國救世救人。梁啟超不僅首先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還主張“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梁啟超,《新小說》1902年11月14日第一年第一號)。從黃克強、李去病開始,20世紀小說中很多知識分子主角,都有指點江山指導官場的使命感。李伯元在小說結尾說他批判官場的目的就是教人怎么做官。《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中的書生主角“九死一生”,也說要跟各種骯臟“怪現狀”作斗爭(實際上有很多妥協)。《孽海花》的主人公原型是同治七年狀元,官至內閣學士;老殘更是晚清知識分子文俠形象的典型代表: 雖有高官賞識提拔,依然堅持街頭行醫,路見不平,看見官府執法不公,就挺身而出,像俠客一樣仗義執言(當然身上帶著“尚方”信件)。
晚清小說中文人主角的政治能量被他們自己高估了,而晚清小說的文學史價值卻被后人低估了。五四和晩清的關系,現在學界頗有爭論。僅就白話文和感時憂國而言,五四作家與梁啟超、劉鶚基本一致。關鍵的不同在于,晚清小說家從感時憂國出發,寫出了救國家救百姓的黃克強,寫出了批判怪現狀的“九死一生”和俠客老殘;魯迅等人也從感時憂國出發,筆下的知識分子形象卻主要是“病人”、弱者和孤獨的人。
五四主流作家比起晚清報人小說家(梁啟超除外),實際社會地位其實更“高”一些,作品影響也更大,但是他們筆下的讀書人形象,卻更“弱”,且充滿矛盾——“狂人”是個精神病患者,大聲疾呼反禮教,自己卻去候補做官;魏連殳能夠流淚長嚎“象一匹受傷的狼”(魯迅,第二卷90),但也要茍且擔任將軍的秘書官;《沉淪》男主角躲在妓寨寫愛國詩;冰心的超人既相信尼釆又相信小花;莎菲既喜歡男色又追求革命;“財主底兒女們”只能“在幻想里預嘗著這種甜美的荒唐和悲慘”(路翎13)……總之,現代文學里的知識分子,既想喚醒農民也要改造官場,又懷疑、悲觀、動搖。懷疑無力喚醒農民,悲觀也無法改變官場,兩面作戰,好像均無勝利希望,于是只好彷徨困惑。民國小說家寫知識分子,基本上就三個類型——病者、弱者、孤獨者。
到了50年代,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又成了勇敢的戰斗型人物。很多主角不僅在心態上,而且真的身兼干部身份(如許云峰、江姐、賈湘農、少劍波),或者選擇干部做愛人(林道靜、盧嘉川、江華)。讀書人如果不做干部,其他選擇就很有限,不是甫志高就是余永澤,都是反派。主人公的處境是危險的,甚至要犧牲生命;作家的寫作策略卻是安全的,集體創作,廣受歡迎。在當代文學生產機制中,“三紅一創”的作者們,先當干部再做作家。當時知識分子普遍要接受的“洗澡”等改造過程,則要滯后大約二三十年才進入小說。
80年代(準確地說是1978年)以后,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再次變得比較復雜——也還有勇敢俠氣,最多是彷徨苦悶,以及各種懷疑超脫。張承志《金牧場》的抒情男主角如俠客般抵抗投降,梁曉聲、韓少功筆下的知青也堅守理想。抒情主流是苦難歷程中的彷徨苦悶——《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好像在重復郁達夫式的情欲/思想苦悶(不同在于郁達夫想“啟蒙”女工,張賢亮則是被農民“救亡”。這是中國知識分子與農民關系史的一個縮影)。在另一些作家那里,技巧實驗伴隨著種種懷疑: 殘雪《山上的小屋》懷疑家庭,馬原《錯誤》懷疑江湖,王朔《動物兇猛》、王小波《黃金時代》懷疑究竟什么是“流氓”……也還有一些前所未見的知識分子,神奇如白鹿原上的朱先生,無聊如《廢都》中的莊之蝶……
知識分子形象在“五四”前后的反差尤其值得注意。之前國家不幸,小說人物像英雄、如俠客;之后革命來臨,知識分子主人公不是瘋狂、憂郁,就是孤獨。究其原因,一來是科舉被廢,士無法“仕”,斷了讀書人傳統救世之路。二來因為現代小說注重人物心理,外表看著像俠客英雄,內心恐怕也是孤獨彷徨。三是五四文人覺得拯救中國,“國民性”比“官場”更重要——既是文化上的悲觀設想,也是政治上的天真期望。
瘋狂、憂郁、孤獨,這三個知識分子的性格類型,早就出現在魯迅的小說里,代表人物分別是狂人、孔乙己、魏連殳。這三種知識分子形象,后來也貫穿了中國小說100年。
雖然魯迅自己很悲觀,他最后讓狂人重新做官,但是至少狂人在“病中”的清醒、勇氣、戰斗精神,引導了20世紀不止一代的知識分子。覺慧、林震、蔣純祖,還有還沒被冰心感化的“超人”,《古船》中的抱樸,《金牧場》里的“人民之子”,甚至《白鹿原》里面對各種軍閥政黨都毫無懼色的白鹿書院的朱先生……這些人物天真、勇敢、執著,像狂人一樣呼喊“不要吃人”“救救孩子”。他們都是努力在黑屋子里開窗的戰士,也不管開了窗以后能不能開得了門,也不管屋子里的人是真睡還是裝睡,或者會不會責怪他們。甚至許云峰、江姐他們也是這種救世傳統,也有狂人的遺傳。
這是20世紀中國小說里的第一類知識分子——“狂人”,中國的堂吉訶德。
第二類讀書人從孔乙己開始,明明社會處境很慘,精神上卻還殘留著儒家教育的優越感。吃飯喝酒都沒錢了,腿也被人打瘸了,還洋洋得意地教旁人“茴”字的四種寫法。如果孔乙己也有機會用第一人稱抒情,他其實也像郁達夫筆下“袋中無錢心頭多恨”的多余人,基本特點就是身體已在社會底層,心里仍想著五洲四海。這種零余者形象令早期的沈從文很有共鳴。5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又有大量機會在底層“洗澡”或勞改,可以有意無意保留“天降大任于斯人”的士大夫基因。生態心態形成巨大反差,一直發展到人們今天說的“地命海心”。勞改犯章永璘饑餓中讀《資本論》,最后還到大會堂去感謝綠化樹。知青們年紀輕輕葬身沼澤地,堅持說“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秦書田低聲下氣刷標語,要求從“右派”改為壞分子。孫少平和其他搬運工的不同,在于他在工地點油燈讀西方小說。王蒙在80年代回首審父,發現倪吾誠其實也是喝洋墨水的“孔乙己”——自己陷于亂世,沒法修身,更難齊家,被家中女人潑了一身綠豆湯,仍念念不忘歐洲的種種先進文明。總之,后來無論“右派”平反或知青下鄉,其共通點都是生態心態的強烈反差形成反諷,“身處低賤心比天高”成為20世紀中國小說中知識分子的一個寶貴傳統。
“五四”文學有“狂人”和“多余人”,80年代后,小說中出現了“狂人”與“多余人”之混合,就是身處社會底層,仍做思想先鋒的人物形象。地主兒子苦讀《共產黨宣言》,勞改犯枕著《資本論》睡覺,金牧場草原培養“人民之子”,這些符號后面,是安全策略操作,但也有真的傳統和信仰。
“孤獨者”是現當代小說中知識分子形象的第三個類型。這些人也感時憂國,但不如“狂人”般勇敢堅定。他們的社會處境也不如意,但沒有孔乙己們那么悲慘。基本上,他們的生活水平還在一般民眾之上,他們的主要特點是內心痛苦、憂郁、矛盾、彷徨、孤獨。在“狂人”戰士看來,他們的憂郁多少有點自作自受;在普羅大眾看來,他們的煩惱又有點矯情,自作多情;但是在這類知識分子自己心里,心理危機就是一切,是最真實的世界。有時這種孤獨可以很深刻,比如《在酒樓上》中的呂緯甫懷疑自己對禮教的態度,比如《孤獨者》中的魏連殳做官也很痛苦。有時這種孤獨連著身體,靈肉沖突,性苦悶,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共鳴,比如《沉淪》。這一系列形象,包括有心無力、追求愛情的涓生,包括“承上啟下”的覺新——既承受上一代重托,又理解弟妹的反叛,也包括整天不需要操心經濟人生,可以專職追求愛情,但還是孤獨苦悶的莎菲女士等等。
這類憂國憂民無力、社會地位小康、內心好像特別痛苦的孤獨者形象,主要集中在20年代到40年代。50年代以后,知識分子被編入不同級別的干部隊伍,要么像林震般革命,要么學韓常新“上進”,“多余”“孤獨”都是奢侈品了。
除了魯迅小說里的狂人、孔乙己、孤獨者等三種知識分子類型以外,還有第四種,魯迅沒有寫,錢鐘書等人補上。這種讀書人形象缺乏憂國憂民的志向,也不接受別人對他的拯救或者改造,他在社會生存中只能作些無奈的選擇和掙扎,雖然于事無補,卻也于世無損。比如《白金的女體塑像》里的醫生,《梅雨之夕》中為陌生女子撐傘的上海男人,還有無用才子方鴻漸,缺乏憂國憂民傳統、不會救人也不要人來救的一個知識分子。90年代模擬頹廢的莊之蝶,以性愛作精神武器的王二,某種意義上也是方鴻漸的傳人,也是拒絕救人和謝絕被救的“消極自由”的追求者。
簡單概括,百年小說里的知識分子,晚清是俠客救世,五四是彷徨孤獨,50年代是英雄為民(很少多余人),80年代后主流是“地命海心”,有人堅持抵抗投降,有人追求消極自由。
三、 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農民形象
農民形象當然貫穿于20世紀中國小說的各個階段,而且有一個被欺壓——被欺亦欺人——翻身/分化——很苦很善良的變化過程。《官場現形記》里農民、丫鬟、仆人等都是被迫害者,《老殘游記》里“民眾”定義寬泛,有雇工、妓女,也包括地主,并非特指耕地的農戶。所以吳福輝認為:“只是到了‘五四’,[……]文學才發現了農民。”(吳福輝174)雖然在他看來,五四知識分子觀察、審視農村農民的立場態度,“和晚清文人,和鴛鴦蝴蝶派文人截然不同”(14),但在小說里,農民還是很苦很愚昧的弱勢群體,從麻木的閏土,到賣人奶、被抽血的《官官的補品》中的農民夫婦,從《生死場》里忙著生忙著死的東北婦女,到沈從文筆下將妻子送出來賣笑的農民丈夫……還有茅盾的《春蠶》、葉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等,主要都強調農民苦境。最大的不同是五四也有作品寫農民不僅被欺而且欺人,《阿Q正傳》既代表又超越了那個時代的農民文學。
《小二黑結婚》以后,農民形象被分化——不是在被欺和欺人的兩重性上分化,而是分化成了先進和落后。從周立波的《暴風驟雨》、趙樹理的《三里灣》、柳青的《創業史》一直到浩然的《艷陽天》《金光大道》,農民都被劃分成先進和落后。男主角如梁生寶、蕭長春常常兼任基層干部。小說中的中間人物,如二諸葛、郭世富、梁三老漢等,是比較成功的文學形象——因為“落后”的內涵比“先進”豐富,包括“迷信”等知識及信仰系統,包括宗族祠堂文化的殘余,包括“紅牛黃牛能夠耕地就是好牛”的農民哲學……
到了70年代末,農民在小說里又從幸福翻身主體變回受欺負的苦難群體。在高曉聲、茹志鵑筆下,麻木善良的農民辛苦勞作幾十年,經歷了“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或者“十年”等多次社會危機,承受了最實實在在的損失。李順大、陳奐生,流著阿Q的血,延續阿Q的命,既狡黠又麻木,好像打盡小算盤,還是糊里糊涂在底層“幸福”掙扎。這些農民的命運與“好心辦壞事”的干部之間,形成了一種“互相依存”的矛盾關系,可以象征50年代官民關系的基調和主流。這種關系偶然也有不和諧,如張一弓《犯人李銅鐘的故事》寫農民搶糧。《平凡的世界》和《插隊的故事》里農民做小生意都會被批“走資本主義道路”。《芙蓉鎮》里賣豆腐發財,要變成“新富農”。《活著》的主角是地主兒子,小說中卻有太多感人的細節。“很苦很善良”,原是對勞動人民的精神概括,可是善良的中國讀者,看著看著也就忘了階級斗爭這條弦,認同福貴似乎就代表了幾十年中國農民的典型命運。
只有極少數作品,不僅寫農民很苦很善良,也寫他們很壞很愚昧。《白鹿原》中鹿三和他的兒子黑娃,分別代表農民的麻木、忠厚和暴力、殘酷。《受活》中的農民,殘疾人被人欺,圓全人也欺人。貌似又回到了魯迅一早分析過的農民的兩重性。
官場與農民的“矛盾依存”關系,也有歷史演變過程。晚清小說是官場壓迫農民及地主;“五四”后官府主要壓迫貧農,地主是幫兇。但農民被欺亦欺人。延安以后,農民分成先進和落后,官員也是黑白分明。好官拯救人民,不聽從好官,便不屬于“人民”范圍——官民關系,有一個互相證明的邏輯關系。80年代農民回首往事,雖然被人欺負,但官員大多數還是好人,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辦了壞事。農民很苦很善良,想想終究是好官,所以也就原諒了。訴苦是和諧社會的安全閥門(《活著》持久暢銷),但多細節,少分析,多流淚,少問責。
農民與官場,是矛盾依存的關系。知識分子與農民,則是“啟蒙救亡”的關系。晚清五四,知識分子想啟蒙民眾;50年代知識分子身處底層,接受再教育,但其實不是農民讓他們在底層,農民反而真的在“救亡”——救章永璘等人于生存底線。到了80年代,知識分子又再啟蒙大眾。小說里知識分子與農民關系的復雜性,黃子平等學者已經分析過,有“靈魂的溝通”(國民性無處不在?還是沈從文理解柏子,蕭紅描寫王婆賣馬?),有“靈魂的震醒”(開始是讀書人想喚醒昏睡的大眾,后來要倒過來,農民用白面饃饃等震醒知識分子的靈魂,再后來有了“裝睡”一說,人們已不知誰應該震醒誰的靈魂或肉體,或者究竟什么是“睡”,怎樣是“醒”),也有“靈魂的高大與渺小”(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7)(從《一件小事》開始的知識分子對農民的崇拜),還有“靈魂的教育與再教育的互相轉化”(知青-農民的最佳同框文本是史鐵生《插隊的故事》)。
四、 20世紀中國小說中的工人和商人形象
比起“士”和“農”,20世紀中國小說中著名的工人形象確實較少。有現代文學史評論郁達夫《春風沉醉的晚上》“表達了對被壓迫的勞動者的深切同情”(唐弢230),20年代中期,郁達夫一邊描寫青樓文化抒發性苦悶,一邊積極提倡無產階級文學。他的《薄奠》也寫了人力車夫。人力車夫雖然不是嚴格的產業工人,但顯然也不是農民或者職員。
如此分類,祥子就是現代文學最重要的工人形象,特別是在自己的生產資料早早被兵痞搶走以后。和煙廠女工詛咒自己從事的煙廠不一樣,祥子把人生希望建筑在自己工作上。另外,《子夜》里也有一些工人群像,罷工斗爭當中有大公無私的,有投機叛變的,有貪圖私利的。《淮南子·齊俗訓》里說: 士農工商,“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610)。所謂“言巧”,指的是工藝、技術。從這個角度看,寫工人的文學,真是老舍最實在——只有祥子,曾經全心全意地追求他的工藝技術、他的生產工具,還有他的職業道德。
到“十七年文學”里,工人階級名正言順地成了領導階級,但在文學史上有定評的作品,以工人為主角的仍然很少。有意思的現象是,“紅色經典”里的主人公自己是干部或者農民,是職業革命者,可是他們都被安排有一個不用出場的產業工人父親。《紅旗譜》里,領導農運的教師賈湘農,祖父是農民,父親是工人;《青春之歌》里的盧嘉川、江華,還有《紅巖》里的許云峰,他們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許云峰還是工委書記,在長江兵工總廠當過鉗工。總體上,這些工人身份標志,符號意義大過文學內容。
到了80年代以后,這個情況還是沒有很大的改變。“重放的鮮花”里林震要下工廠調查,改革文學中的喬廠長也要抓工業生產,《平凡的世界》有工地搬磚、煤礦工下井等等,但這些小說要么寫的是工廠,不是工人;要么主題還是農民“進城”,是農民變成工人。
為什么在近百年中國小說里,相比之下,士農工商中的工人形象比較單薄?甚至在“十年”期間,大批判都用“無產階級”的名義,怎么就沒有描寫無產階級同時也有藝術價值的小說?《朝霞》的工人創作比例高了,文學意義恐怕仍然存疑。這也值得研究者思考,尤其是據說現在中國城市人口已經超過農民了,人民的主要成分已經發生了變化。
中國小說的三大主角是知識分子、農民和官員,相對來說,工人和商人是“弱勢群體”——不是劇情里的弱勢,而是較少有機會成為小說主人公。如果還要再比較,商人其實比工人受到更多的關注,尤其在20世紀上半葉。
“十七年文學”和“十年”文學當中,讀者記得住的工人主角,不分男女,實在很少。以后須多些閱讀,再作研究。反過來,講起商人,人們馬上想起吳蓀甫、趙伯韜、“財主底兒女們”、還有《林家鋪子》里的林老板等等(大部分就靠茅盾一個人在寫)。現當代文學怎么寫商人,倒是非常值得討論的題目。
按照《淮南子》的說法,“商與商言數”。晚清小說里的官員來往,議政少,言數多。他們并不關心國事,整天討價還價: 這個官位,任期多少年,值多少銀子;上面來了巡視組,下面交多少錢,要交的太多,寧可坐牢去……官場有不少生意。
許地山寫過《商人婦》,主要是寫婦人命運,很少言及“商”。全面剖析商家歷史處境,還是需要有政治經濟學理論武裝的茅盾。《子夜》中的商人群像,簡單說有四類: 一是趙伯韜買辦;二是吳蓀甫民族實業家;三是在這兩者之間投機,既想辦實業又想多賺錢的杜竹齋;第四類最慘,就是像馮云卿這種在鄉下的土財主,進城經商,到處失敗,最后用女兒做工具騙情報,白白賠了千金和白銀。晚清小說里的人倫墮落,到了茅盾筆下變成商人沉淪的標志。人們一方面佩服茅盾作為小說家對于都市商界各色人物的觀察興趣,另一方面也可惜茅盾的商人分類有時候太遷就階級分析的理論框架。相比之下,在更多激情、更少理論的路翎筆下,商人蔣捷三和他的后代是比較難以定性、也比較復雜的商人形象。嚴格來說,張愛玲筆下的男人也大都可算商人。喬琪喬和季澤是花心、沒有出息的商人。范柳原雖然跳交誼舞,背詩經,戀愛的基礎還是有錢幫女主角訂頭等艙船票和淺水灣海景房。之后情人一到手,馬上又要坐船去英國做生意,盡顯商人本色。最有意思的是佟振保,他的商人性格并沒有表現在他怎么開廠、如何辦實業上,而是一發現老婆出軌,氣昏了頭出門,居然沒講價就上了黃包車。能讓一個商人氣到忘了講價的地步,該是多么令人激動、憤怒的事情。
50年代以后,“三紅一創”里很少有商人形象。劉思揚作為革命者,出生于有錢的家庭,但那只是背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靜有同學貪圖物質,下嫁權貴。總體上前30年,公私合營,商人也不見了。
80年代,張煒《古船》里老隋家的兩個兒子抱樸和見素,可以視為新時代商人形象的代表,而且代表兩種不同的發展方向。弟弟以惡抗惡,不擇手段,反抗他的家族所蒙受的不公正的歷史遭遇。所以,他拼命要搶奪家族粉絲企業,要爭著承包,也要到城里去投機打拼。當然,張煒把他寫成失敗者。出身更低且性格比較類似的,還有《兄弟》里的李光頭,在余華筆下,他非常無恥地在新時代從成功走向新的成功。哥哥抱樸,張煒把他寫成一個韜光養晦、等待時機、積蓄力量,同時又苦苦研讀《共產黨宣言》的人。所以,最后他發展了商業,復興了家族,還拯救了父老鄉親。這是一個知識分子化的商人形象。放在20世紀文學背景中,《古船》頗有野心地虛構想象了中國式新時期資本主義的兩種發展可能。
80年代以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商人在中國改革開放當中就扮演起越來越重要的社會角色。電視劇里,也有更多晉商的傳統、大宅門的歷史、胡雪巖的傳奇等等。總之,有錢人也要有光榮歷史。在全面回顧民國史的《白鹿原》中,白嘉軒和鹿子霖是財主,是地方上的“族權”和“政權”的代表,但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是善于講數的商人。買賣土地、銷售鴉片、創辦學堂、建造白塔,有意無意地還培養書記、縣長等家族接班人兼政治代理人。歷史的經驗表明,做生意首先要做官——晚清作家早就告訴各位了。白嘉軒和鹿子霖的形象,正好補充了“三紅”系列當中有錢人形象的歷史缺失。補得是否合適,是另外一回事。
雖然商人形象不多,但90年代前后中國、最優秀、最有影響的一些長篇小說,如《白鹿原》《活著》《古船》《生死疲勞》等,主人公卻都是“財主底兒女們”,似乎不是偶然現象。
綜上所述,倘若現代文學最重要的人物形象系列只是知識分子和農民,那么“啟蒙救亡”關系便是最重要的文學主題。但是從晚清開始重讀20世紀中國小說,不難看到官員/干部形象顯然是知識分子與農民之外另一個重要的人物系列。因此,在考察小說中知識分子與農民關系的同時,我們也應該梳理知識分子與官員形象之間“互相改造”的歷史過程,同時探討小說中農民命運與官員/官場的矛盾依存關系。
“互相改造”有個過程,晚清小說中知識分子想改造官場、教育官員;“五四”主人公退一步,視仕途為墮落;50年代是革命改造作家(主角干部化);80年代后小說家對知識分子和官場的關系有更多元的想象: 或者回顧苦難歷程,身處底層,心中仍然充滿政治使命感;或者寄希望于干部/官員的知識分子化;或者尋求不同的脫離政治的方法,下棋、做愛、受戒等等。
“矛盾依存”關系也有復雜的演變。晚清是直接對立,官府壓迫農民;“五四”還是官壓民苦,但官員不是焦點,主要寫幫兇爪牙;延安以后官場/干部分化,或是敵人或是救星;80年代再回首,發現還有官員欺負農民,但是“好心辦壞事”,有時甚至“壞官”也可能為農民謀幸福。
從文學性而言,官員形象總體上并不如知識分子和農民形象那么有成就,并沒有產生阿Q、祥子、七巧、方鴻漸或者章永璘、白嘉軒、福貴那樣的典型人物(雖然也有華威先生、劉世吾或江雪琴)。但是在晚清和當代,小說中如果沒有官員形象存在,中國故事便無法講述。
本來是兩種人物形象系列合成一個主題線索,現在要考察三種人物形象系列,同時出現至少三條主題線索,多了很多變數,于是,小說里的中國故事更加復雜了。
注釋[Notes]
① 顧頡剛《〈官場現形記〉之作者》一文記載:“《現形記》一書流行其廣,慈禧太后索問是書,按名調查,官交有因以獲咎者,致是書名大震,銷路大廣。”參見魏紹昌: 《李伯元研究資料》。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16頁。
② 傅斯年在《新潮》(第一卷第一號,1919年1月1日)發表文章《人生問題發端》,主張:“拿著人的自然解釋人生觀念,簡捷說拿人生解釋人生,拿人生的結果解釋人生的真義。”“所有我們可以知、應當知、以為要緊,應當以為要緊的,都是和人生有關,或者是人生的需要。”可參考周展安: 《現實的凸顯及其理念化——對“五四運動”思想與文學內在構造的再思考》,《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論文集2019》。武漢: 長江文藝出版社,2020年。第20—43頁。
③ 毛澤東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國務會議第十一次(擴大)會上的講話(后改為《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同年3月12日宣傳工作會議的講話中都談到了王蒙小說發現官僚主義的問題。參見黎之: 《回憶與思考——1957年紀事》,《新文學史料》3(1999): 123—139。
④ “生活的卑微,在這卑微生活里所發生的感觸欲望上進取,失敗后的追悔,[……]人人皆覺得郁達夫是個可憐的人,是個朋友,因為人人皆可從他作品中,發現自己的模樣。”參見沈從文: 《論中國創作小說》,《郁達夫研究資料》(下冊),陳子善,王自立編,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363頁。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黃子平陳平原錢理群: 《論“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文學評論》5(1985): 3—14。
[Huang, Ziping, Chen Pingyuan, and Qian Liqun. “On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Literature’.”Literary
Review
5 (1985): 3-14.]黎翔鳳: 《管子校注》(上冊),梁運華整理。北京: 中華書局,2004年。
[Li, Xiangfeng.Annotated
Guanzi. Vol.1. Ed. Liang Yunhua.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梁啟超: 《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新小說》1902年11月14日第一年第一號。
[Liang, Qicha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iction and Social Governance.”New
Fiction
16 November 1902.]《淮南子·齊俗訓》,陳廣忠譯注。北京: 中華書局,2011年。
[Liu, An, et al. “Placing Customs on a Par.”Writings
of
Huainan
Masters
. Ed. Chen Guangzhong.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1.]路翎: 《財主底兒女們》(上冊)。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
[Lu, Ling.The
Children
of
Moneybag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4.]魯迅: 《魯迅全集》。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
[Lu Xun.The
Complete
Works
of
Lu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5.]唐弢: 《中國現代文學史》。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
[Tang, Tao.A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98.]吳福輝: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
[Wu, Fuhui.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