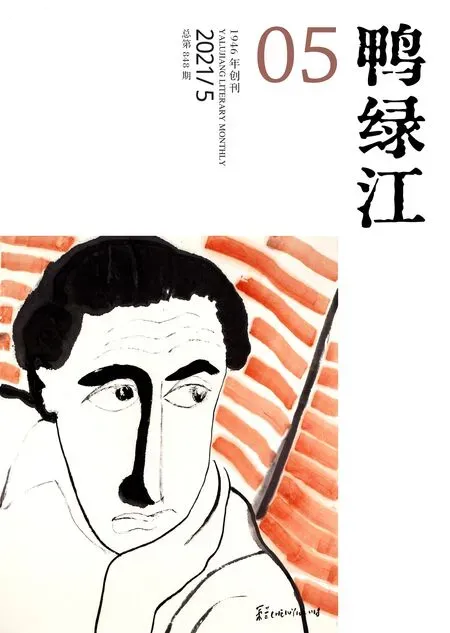馬曉麗筆下的罪與罰
賀 穎
我愿意成為那樣的讀者:在無(wú)限地解讀面前的小說(shuō)時(shí),也一并接受小說(shuō)無(wú)限的稽考。在我看來(lái),有價(jià)值的小說(shuō)作品,無(wú)一不是經(jīng)由故事的波譎云詭或風(fēng)平浪靜,去直視、探索、呈現(xiàn)以至對(duì)決那陰郁幽微、晦暗難辨的復(fù)雜人性:或壓抑焦慮,或溫情感人,或自救與救贖,或殺伐決斷與鮮血淋漓。馬曉麗筆下的英雄氣與兒女情便都是如此。盡管我讀過(guò)的十余個(gè)中短篇作品題材不同,風(fēng)格有異,但品咂之間不難發(fā)現(xiàn),其內(nèi)里的氣脈走向統(tǒng)一完整,仿佛一個(gè)人的多重分身,于數(shù)卷之中改頭換面、穿梭往返卻能做到游刃有余。馬曉麗的小說(shuō)常常通過(guò)懸疑性、哲思性與荒誕性建構(gòu)美學(xué)體系,完成對(duì)人性深刻復(fù)深邃的靈魂評(píng)估,是罪也是罰,是解剖也是啟示。
人之初的本性良善,怯懦包裹下的卑鄙邪惡,理想與現(xiàn)實(shí)激發(fā)出來(lái)的慘烈掙扎,無(wú)法抉擇之際的茫然猶疑,孤獨(dú)之生命與絕望之靈魂,一念地獄一念天堂間命運(yùn)走向的委曲微妙……對(duì)這林林總總的介入與表達(dá),仿佛都帶有自身的亮光。借助寓意悠長(zhǎng)的明喻暗喻,使諸般人性樣貌,其紋理脈絡(luò)的伸展走向,都如呈現(xiàn)于顯微鏡下的細(xì)胞一樣清晰可辨。這難免不讓人聯(lián)想到尼采所嘆:人性的,太人性的!是呀,尼采這位思想的巨擘,并不吝嗇對(duì)人性的肯定,相信尚有更深更廣闊的人性領(lǐng)域可以挖掘。但同時(shí),他也總是更激烈地表達(dá)對(duì)人性弱點(diǎn)的尖刻譏諷,指認(rèn)人性的劣根時(shí)毫不客氣絕不留情。然而,恰恰是這樣充滿悖論的思慮,又能分蘗出新的枝芽。經(jīng)此,如果足夠走運(yùn),我們又可以在這交相輝映的枝芽之外,找到第三莖鮮嫩的苞蕊,那就是:對(duì)人性依舊滿懷深情的希望。這是被尼采稱為“自由精靈”的希望,而它,只屬于那些可以超越傳統(tǒng)思維方式、傳統(tǒng)道德觀念而抵達(dá)自由思想的人。當(dāng)然了,希望也常常脆弱渺茫,希望的存在,有時(shí)倒似乎更為印證失望乃至絕望,比如當(dāng)人們發(fā)現(xiàn),人人厭棄的黑暗與惡竟是人性的第一底色。那么,說(shuō)好的人之初性本善又在哪兒呢?在千古不易的善惡之爭(zhēng)中對(duì)于惡的懲罰又如何實(shí)現(xiàn)呢?而決定一個(gè)靈魂最終走向地獄或天堂的道路又該怎樣鋪就呢……
我所讀到的馬曉麗的小說(shuō),即是對(duì)人性的多重演繹歸納,直至朝向精神的最深處去執(zhí)拗勇毅地溯因善惡。當(dāng)然了,這樣的發(fā)掘與勘察往往徒勞,甚至危險(xiǎn)。可文學(xué)之魅力,藝術(shù)之魔性,不恰恰在于不避失敗直面挑戰(zhàn)嗎?
1
人工創(chuàng)造的東西,總是攜帶著宿命的刻意,所以,“藍(lán)玫瑰”的意象本身就有點(diǎn)虛幻。《手臂上的藍(lán)玫瑰》也算是馬曉麗作品中的另類筆墨了,那泥沙俱下的市井語(yǔ)言,在第一人稱的敘述中異常生動(dòng)鮮活,對(duì)一個(gè)具象的普通人在世俗生活中的樣態(tài)與軌跡進(jìn)行了極具辨識(shí)度的全方位示現(xiàn)。這種示現(xiàn),顯然并不單指某個(gè)個(gè)體,而是對(duì)一種或幾種群體的全息關(guān)涉。“我”的生命歷程與精神屬性,使內(nèi)在極度孤獨(dú)的“我”不可遏制地仰視舒姐的生活并充滿向往,對(duì)舒姐的情誼百般感念與珍惜。不過(guò)在這塵世凡間,又有誰(shuí)對(duì)誰(shuí)能心心相印呢?連惺惺相惜都很困難。可有了信任,下意識(shí)的托付就會(huì)出現(xiàn),于是押寶一樣,“我大華”將自己努力掙脫出竅的靈魂,誠(chéng)心誠(chéng)意地交給了舒姐。溫情、熨帖,如生活中的一束暖光,直到真相突破了極限認(rèn)知,“我大華”才知道,這束暖光,其實(shí)是一枚隱于生活表象之下的滾燙手雷。爆雷后的大華是驚遽的,理智與情感的沖突讓她暈眩,一個(gè)個(gè)體生命的精神城邦由此坍塌。而真正令人悲傷動(dòng)容的,是大華在靈魂世界的殘磚碎瓦間對(duì)往昔的不舍,是自欺欺人的不舍,是不屈不撓的不舍。她是在拼湊曾經(jīng)的記憶嗎?抑或在拼湊自己灰飛煙滅的薄脆的意識(shí)?顯然,令人動(dòng)容的不只是悲情。當(dāng)我沉浸于“藍(lán)玫瑰”時(shí),不知為什么,總會(huì)情不自禁地想起與它天差地別的卡爾維諾小說(shuō)《寒冬夜行人》:“這部充滿了各種感覺(jué)的小說(shuō),常常被一些不知深淺的旋渦隔斷,猶如你希望生活得充實(shí),結(jié)果卻發(fā)現(xiàn)了生活中的無(wú)邊空虛。”原來(lái)是這樣!這不啻是對(duì)大華生活的精準(zhǔn)寫(xiě)照。可憐的自卑、對(duì)他者的希望、希望的殘破衰敗,以及生活中永遠(yuǎn)無(wú)法真正充實(shí)起來(lái)的空虛。然而,問(wèn)題之復(fù)雜還在于,站在舒姐的立場(chǎng),這一切又都理所當(dāng)然,都順理成章,畢竟善惡本無(wú)界呀。那么,何為審判之律法呢?又應(yīng)該由誰(shuí)來(lái)審判呢?小說(shuō)結(jié)尾時(shí),大華一發(fā)而不可收地當(dāng)街哭號(hào),氣蘊(yùn)綿長(zhǎng)而細(xì)思極恐,孰罪孰罰終無(wú)分辨。也許,唯有那令人絕望的、讓人無(wú)奈的、毀天滅地又須臾不曾消弭的黑暗,在頑強(qiáng)地從人性的深淵之中升騰出來(lái)時(shí)才真正可觸可感。
面對(duì)“我大華”的靈魂托付,我們會(huì)發(fā)現(xiàn)生而為人,我們其實(shí)永遠(yuǎn)無(wú)法規(guī)避人性中的黑暗。這黑暗,或許就是薩特口中的“地獄”——“他人即地獄”。不得不承認(rèn),我們無(wú)法離開(kāi)這個(gè)世界單獨(dú)生存,我們不可遏制地寄希望于他者,哪怕是“地獄”。然而我們同時(shí)亦是“他人”,也會(huì)有意或者無(wú)意地化為“地獄”。曾經(jīng)讀過(guò)一則公案:有人問(wèn)禪師,他覺(jué)得周圍的人都不夠好,他該怎么辦?禪師沒(méi)有回答,只是點(diǎn)燃了一根蠟燭,蠟燭剎那間把周圍映亮,唯獨(dú)蠟燭之下仍黑暗一片。禪師說(shuō),這根蠟燭就是人心。那人又問(wèn),如何能讓蠟燭之下的黑暗也亮起來(lái)呢?禪師又點(diǎn)起一根蠟燭,于是,前一根蠟燭的周身都被照亮。問(wèn)話的人瞬間開(kāi)悟,要想驅(qū)走內(nèi)心的黑暗,必須借助他人的光,而為了得到他人的光,也要點(diǎn)燃自己的心。每個(gè)人都燃起心燈之光,地獄也許就變成了天堂。
人生在世,畢生都將扛在肩上的最重負(fù)擔(dān),其實(shí)是罪與罰的終極公審,這,沒(méi)有誰(shuí)逃避得了。就像《催眠》中的醫(yī)生和作家,以及世界上更多無(wú)處遁形的人,哪怕刻意令自己進(jìn)入睡眠狀態(tài),終于也是無(wú)從脫身。《催眠》中的催眠行為,是逃遁的隱喻,亦是徹底降服并交出自己的釋然。《催眠》的背景是特殊的戰(zhàn)爭(zhēng),敵人就是災(zāi)情。而小說(shuō)是如此背景下對(duì)人性極致化的窮追不舍,是生存悖論的刺目呈現(xiàn),是被囚于無(wú)法救贖的戰(zhàn)爭(zhēng)災(zāi)難應(yīng)激障礙牢籠之后的突圍努力。
作家與戰(zhàn)士,同樣的精神遭遇,仿佛彼此映照于河面的倒影互為鏡像。不曾預(yù)料的是,最后亟待被解救的,還有醫(yī)生這個(gè)第三者。這是一場(chǎng)準(zhǔn)戲劇演出,劇中人皆與寫(xiě)實(shí)意義上的或象征意義上的催眠主題息息相關(guān)。盡管結(jié)尾處貌似達(dá)成了催眠,但事實(shí)上,它成了一次計(jì)劃之內(nèi)的無(wú)疾而終。令人叫絕的倒不在于這樣奇巧的鋪排,而在于這個(gè)文本自身就是一場(chǎng)完美的催眠術(shù)。此處必須指出的是,如果催眠術(shù)果然存在,那么它應(yīng)該是一條河,類似忘川的那種,并且不僅用于忘卻,最重要的是之后的重生。災(zāi)難撕開(kāi)了人類最后的遮羞布,于是一切無(wú)法示人的秘密都要被迫暴露于舞臺(tái)的正中。一束束追光之下,無(wú)處遁形的頑癥隱疾只能猶如晝夜交替時(shí)尷尬的幽靈。從戲劇的角度審視《催眠》,它那略顯荒謬與混亂的情節(jié)結(jié)構(gòu),那機(jī)警而又敏感的戲劇臺(tái)詞般的對(duì)白,那簡(jiǎn)單干脆卻能驚艷獨(dú)絕的表現(xiàn)形式,所營(yíng)造的氣氛,所生成的意趣,所具有的多重況味與深刻隱喻,完全是在向貝克特的《等待戈多》脫帽致敬。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性命攸關(guān)?到底什么才值得人性為之無(wú)限趨近?又都有什么才配得上我們以生生不息的心魂捍衛(wèi)堅(jiān)守?顯然,這是一場(chǎng)以哲學(xué)為背景的攻防戰(zhàn),只是沒(méi)法簡(jiǎn)單地估量勝負(fù)得失,在舞臺(tái)之上,在追光之下,恐怕只有無(wú)盡的迷茫,而不可能找到確切的答案。
好在這一場(chǎng)攻防的炮火,也許因?yàn)榇輾Я恕笆У碌臇|西”吧,終于使得士兵與作家為此而獲救。當(dāng)然,還有被復(fù)活了的醫(yī)學(xué)倫理,還有那些比醫(yī)術(shù)重要千百倍的人性之光。那是一種格外醒目的高貴光芒,在災(zāi)難或戰(zhàn)爭(zhēng)的背景之下,尤其能彰顯出神性的例外,而那自然是美國(guó)天文學(xué)家卡爾·薩根所提及的例外:戰(zhàn)爭(zhēng)之下,滅絕是常態(tài),生才是例外。
沒(méi)錯(cuò),在常態(tài)的滅絕面前,生,是個(gè)例外。
2
時(shí)代的灰塵落到任何一個(gè)微小的個(gè)體頭上,都是一次滅頂之災(zāi)。“沈陽(yáng)兵”注定會(huì)成為命運(yùn)的一個(gè)隱喻,在醫(yī)生、作家、士兵的生命間游移閃現(xiàn),又必將成為人們終生縈繞心頭的提醒:關(guān)于生命、良知、勇氣、德行、犧牲、妥協(xié),關(guān)于靈魂的審慎或迂腐、怯懦或無(wú)畏、屈從或迷失。而這一切,也同樣適用于《左耳》。
盡管,老齊從不承認(rèn)自己左耳失聰,就好像在指責(zé)作者或告白讀者,他的耳朵沒(méi)有毛病,不可能也不應(yīng)該供人大做文章,但《左耳》這篇小說(shuō),仍然可以令人反復(fù)淚目。戰(zhàn)爭(zhēng)猶如利劍,能刺穿和平年代里人心那層麻木的厚膜瓣,戰(zhàn)火硝煙間,無(wú)論粗獷驍勇,抑或“溫良恭儉讓”,所有的付出與犧牲,所有的堅(jiān)忍與悲壯,必定源于巨大的精神信仰,堪稱人之為人的莊嚴(yán)超越。“溫良恭儉讓”的戰(zhàn)友,在生死抉擇面前選擇了后者,掩護(hù)了同伴,化身成為永遠(yuǎn)的英雄。而活下來(lái)的老齊,失去了大義赴死的戰(zhàn)友的老齊,永遠(yuǎn)喪失了左耳聽(tīng)力的老齊,其實(shí)只在物理意義上以一種慣性延續(xù)著生命,他的靈魂碎片,早與英雄“溫良恭儉讓”的身體碎片混合起來(lái),共同鑄就了戰(zhàn)爭(zhēng)的錐心刺骨,也成就了一個(gè)左耳失聰?shù)娜碌睦淆R。老齊已經(jīng)不再是之前的老齊,他成了一個(gè)個(gè)體歷經(jīng)一次“革命”后的解構(gòu)與結(jié)構(gòu),他那大多數(shù)時(shí)候沉默的左耳,其實(shí)就是那個(gè)在微笑中永生了的“溫良恭儉讓”。如果再次重溫卡爾·薩根的那種例外,我們將具體看到的是,在常態(tài)的滅絕面前,這一次獲得例外的生的是老齊,同時(shí),也是化身為老齊沉默左耳的“溫良恭儉讓”。卡夫卡說(shuō)過(guò):沉默包含了多種力量,咄咄逼人的進(jìn)攻只是一種假象,一種詭計(jì)。英雄“溫良恭儉讓”在老齊的頭顱上沉默著,果然就充滿了力量,這不能不時(shí)常令人產(chǎn)生錯(cuò)覺(jué),比如那顆地雷,那些戰(zhàn)爭(zhēng),也許真的就是卡夫卡所說(shuō)的假象。但愿如此吧。但愿世界上的每一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都不過(guò)是一場(chǎng)噩夢(mèng)的假象,而一切死亡與硝煙,其實(shí)從未發(fā)生。
然而,事實(shí)也許剛好相反。沒(méi)有什么比戰(zhàn)爭(zhēng)更堪當(dāng)人性之惡的多棱鏡了:貪婪、野蠻、殘暴、血腥、卑劣、無(wú)恥……無(wú)一不是戰(zhàn)爭(zhēng)的重要伴生物。毫不夸張地說(shuō),一部人類發(fā)展史,完全是一部由傷殘和死亡書(shū)寫(xiě)的人類戰(zhàn)爭(zhēng)史,這便是戰(zhàn)爭(zhēng)永遠(yuǎn)的原罪。那么罰呢?要誰(shuí)來(lái)承受?
云端,兩個(gè)同名的女人,兩個(gè)女人共同的名字,戰(zhàn)爭(zhēng)的原罪于此猶如映射災(zāi)難的萬(wàn)花筒,在作者奇思妙想的故事結(jié)構(gòu)中,在層出不窮的情節(jié)遞進(jìn)中,將這原罪既輕描淡寫(xiě)又濃墨重彩地展示了出來(lái),讓人幾乎無(wú)法直面:
她倆都愣了,一起低下頭看槍,一時(shí)搞不清是誰(shuí)把槍弄響的。
血出來(lái)了。她們看見(jiàn)了血,看見(jiàn)鮮血正從云端的胸前汨汨地流淌出來(lái)。兩雙手同時(shí)痙攣了一下,又同時(shí)松開(kāi),槍一下掉下來(lái)了。
血還在汨汨地往外流,云端臉上的紅暈像退潮一樣漸漸退去……洪潮猛然驚醒過(guò)來(lái),不顧一切地?fù)涞皆贫松砩希檬制疵ザ履莻€(gè)血窟窿,但怎么也堵不住……
死亡就這樣來(lái)了。在戰(zhàn)爭(zhēng)的后方,戰(zhàn)爭(zhēng)的原罪同樣在生長(zhǎng)仍然在延續(xù)。《云端》中的兩個(gè)戰(zhàn)爭(zhēng)寡婦,兩個(gè)刻骨孤獨(dú)的女人,多像一枚硬幣的正反面呀。兩個(gè)敵對(duì)陣營(yíng)的陌路人,共同擁有一個(gè)并非大路貨的別致的名字,如此的巧合所制造的懸疑,令人忍不住要急切地揣測(cè)結(jié)尾。兩個(gè)優(yōu)雅的云端,是戰(zhàn)火中遺失的同胞姐妹嗎?否則,怎么會(huì)有如此神秘的淵源?當(dāng)然沒(méi)有。或者說(shuō),作者根本就沒(méi)想到去設(shè)計(jì)這一類型的細(xì)枝末節(jié),因?yàn)閼?zhàn)爭(zhēng)它要的是毀滅,要的是情感、生命、文明、世界的統(tǒng)統(tǒng)灰飛煙滅。而貯滿戰(zhàn)爭(zhēng)的目光中,不容易出現(xiàn)或者說(shuō)也不屑于出現(xiàn)那些雕蟲(chóng)小技類的細(xì)枝末節(jié)。但孤獨(dú)和絕望,那種靈魂的孤獨(dú)和精神的絕望,卻從來(lái)都不屬于細(xì)枝末節(jié),因?yàn)樗切悦募榔泛蜕畹臓奚嫶蠛蛷?qiáng)大得足以覆蓋所有的情感、生命、文明、世界。當(dāng)戰(zhàn)爭(zhēng)的力量已然主宰這個(gè)塵埃星球,或許敢于蔑視死亡并把必勝的號(hào)角朝戰(zhàn)爭(zhēng)吹響的,唯有孤獨(dú)與絕望。是的,孤獨(dú)和絕望,已經(jīng)越來(lái)越成為人類的真實(shí)宿命,于是對(duì)死亡的奔赴,也就成了它們必定會(huì)戰(zhàn)勝戰(zhàn)爭(zhēng)的不朽鐵證。
從這個(gè)意義上說(shuō),我相信不論哪個(gè)云端,都不會(huì)毅然放棄生的權(quán)利,但同時(shí),她們也都有勇氣主動(dòng)選擇死亡。
3
宇宙浩瀚,塵世蒼茫,每個(gè)人都是一顆星球,孤零零地在天地間飄搖游逛。如此,每個(gè)心靈不死的人便都會(huì)生出強(qiáng)烈的渴望:渴望理解,渴望相知相愛(ài),渴望找到一種叫作“彼此”的存在方式。這種不可救藥無(wú)法解脫的渴望,源自本能源自潛意識(shí),源自某種與生俱來(lái)的生命需要。在《殺豬的女兵》中,馬曉麗對(duì)這種需要的挖掘抵達(dá)了極致。
馬曉麗將主人公僅僅設(shè)定為沒(méi)有名字的“她”,一個(gè)殺過(guò)豬的退伍女兵。這種設(shè)定能格外凸顯主人公的符號(hào)化意象:她也許只是她自己,也許更是一切有著同樣精神境遇的人群之代指。名字已經(jīng)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她的經(jīng)歷與內(nèi)在的心靈訴求,是她形而上意義的暗示與明示:
她聽(tīng)見(jiàn)周圍觀摩的人群安靜下來(lái)了,她知道現(xiàn)在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自己的身上來(lái)了。她感到了興奮,心跳加快,血管賁張,心中充盈著激昂的豪情。
她看到了那只已經(jīng)捆好了的豬。她調(diào)整了一下呼吸,掂了掂手里的刀,用力攥緊刀把,使勁兒地捅了進(jìn)去……
但此刻的豬卻是她丈夫,一個(gè)讓她在意的人,或許,還是唯一讓她在意的人。小說(shuō)結(jié)束了,丈夫沒(méi)死,但是,這依然不能對(duì)這個(gè)故事的殘酷性有所緩釋,甚至因?yàn)檎煞驔](méi)死,因?yàn)榻獬苏`會(huì),因?yàn)殡p方都已經(jīng)或者在將來(lái)肯定會(huì)知道對(duì)方正是由于在意自己才傷害自己,這樣便使這個(gè)故事不僅更加殘酷,還在殘酷之外又多了幾許辛酸和感傷。
是的,對(duì)于犯下殺業(yè)的她來(lái)說(shuō),一旦把夫妻間的誤會(huì)解釋清楚,所受的懲罰會(huì)尤其深重,恐怕再也沒(méi)有什么能比這種命運(yùn)更配得上絕望了。但小說(shuō)通篇的流暢與荒誕、驚悚與無(wú)助,似乎又不止于把絕望的結(jié)論交給讀者就算了事。它的那種殘酷的平靜,最終所生成的,竟是一股能將人引入宗教反省般境地的思想的力量:被精神之“殺業(yè)”纏身的“她”,還能得解脫嗎?還會(huì)被救贖嗎?值得慶幸的是,在《陳志國(guó)的今生》中,蓮花山寺廟鐘聲的驀然響起,終于點(diǎn)亮了讀者眼中的燈盞,敞開(kāi)了讀者閉塞的心扉。《陳志國(guó)的今生》巧妙地將懸疑性設(shè)置為最大的技術(shù)亮點(diǎn),而結(jié)尾的鐘聲,則是馬曉麗諸多作品的精魂所在。顯然,馬曉麗深諳懸疑之道,于層層遞進(jìn)環(huán)環(huán)相扣間信手拈來(lái)地使用細(xì)節(jié),嚴(yán)絲合縫地組織情節(jié),耳目一新地把個(gè)陳志國(guó)的身份問(wèn)題敘寫(xiě)得一波三折、翻云覆雨。從開(kāi)篇的生病哀號(hào)需要人陪伴,到男性第三人稱“他”的使用,讓人判斷這是一個(gè)命不久矣的老年男子,而后,又稱呼女兒為他的姐姐,這又令人錯(cuò)覺(jué)為“他”大概是家里收養(yǎng)的一個(gè)男孩。繼之的所有表述,都將讀者牢牢地拴在這條線上,直到結(jié)尾時(shí),作者那狡黠而又頑劣的一萬(wàn)多字幾乎寫(xiě)完,陳志國(guó)的身份才清晰起來(lái),讀者也才恍然悟到:原來(lái)這陳志國(guó),根本就不是人類,而是一只漂亮的寵物——狗?對(duì)了,但其實(shí),是否真的如此也未定準(zhǔn),因?yàn)橹钡秸≌f(shuō)結(jié)束,“狗”的字眼也沒(méi)出現(xiàn),讀者只能憑生活中的常識(shí)經(jīng)驗(yàn)去對(duì)號(hào)猜測(cè)。
當(dāng)然了,不論陳志國(guó)是什么或不是什么,也許都不重要,因?yàn)樽髡哂诖艘庠谡f(shuō)明的只是生命,只是純粹意義上的生命本身,只是有靈的眾生。或許,陳志國(guó)依然只有符號(hào)的意義,不僅指代哲學(xué)的維度,也彌散出宗教的氣息。貫穿全文的紀(jì)伯倫的《我曾七次鄙視自己的靈魂》,將文本連綴成一個(gè)詼諧卻燒腦的故事,順理成章地完成了紀(jì)伯倫式的靈魂拷問(wèn),并且這拷問(wèn)還是無(wú)限次的,仿佛一個(gè)靈魂所歷經(jīng)的無(wú)限的哲學(xué)循環(huán),又如同面對(duì)上帝時(shí)永恒的自我審視。
這篇小說(shuō),幾乎同時(shí)發(fā)起了對(duì)人性、獸性以及神性的本質(zhì)探尋。顯然,這才是它更為深刻和深遠(yuǎn)的主題:關(guān)于眾生平等,關(guān)于萬(wàn)物有靈,關(guān)于三善道與三惡道,關(guān)于一切有情眾生在三世六道之間的輪回……以及更多必然歷久懸置的質(zhì)疑或希冀,甚至還包括了對(duì)“人類中心說(shuō)”的隱諱反思:古希臘普羅泰格拉說(shuō)“人是萬(wàn)物的尺度”,由之表達(dá)了最早的人類中心主義思想。可來(lái)自陳志國(guó)的啟示卻不由我們不試圖繼續(xù)往柏拉圖的身邊靠攏一點(diǎn),去遙想“神是萬(wàn)物的尺度”……佛家認(rèn)為,有情眾生無(wú)一例外地要在過(guò)去、現(xiàn)在、未來(lái)三世之間無(wú)窮流轉(zhuǎn),同時(shí),因?yàn)樗鼈冊(cè)谌乐械摹皹I(yè)力”各不相同,就決定了他們?cè)诿恳粋€(gè)世界六道中的位置也都各有不同。那么,也許真如作者所言,在陳志國(guó)的概念中意識(shí)里,其實(shí)“他”此生身處的是三善道,而與身處三惡道的“他”的族群是不同類的。
忽然覺(jué)得,若果真如此,若“我”的女兒的幾個(gè)夢(mèng)都曾真實(shí)發(fā)生,那該多好呀。人世間所有的罪與罰,恐怕也都會(huì)因此而開(kāi)啟全新的運(yùn)勢(shì),并以此來(lái)完成對(duì)馬曉麗小說(shuō)內(nèi)在意蘊(yùn)的契合與呼應(yīng)。
木心在《哥倫比亞的倒影》中說(shuō):“生命,就是時(shí)時(shí)刻刻不知如何是好。”掩卷之際,木心的這句話驀然躍出。沒(méi)錯(cuò),正應(yīng)該永遠(yuǎn)不知所措,永遠(yuǎn)進(jìn)退兩難。我所讀到的馬曉麗的數(shù)篇小說(shuō),或繁復(fù)跌宕,或不動(dòng)聲色,各有千秋然而殊途同歸,都能直抵人性的最糾結(jié)處,都能直逼刻錄在或鮮活或僵朽靈魂上的每一樁罪愆與每一次責(zé)罰。這些作品喜歡摒棄俗常的體裁意義上的故事性結(jié)構(gòu),而以一個(gè)個(gè)水到渠成的開(kāi)放式結(jié)局傳遞出一種信念,即人性之翼終將自人性的黑暗囚籠中突圍而出,而每一盞心燈也終將被點(diǎn)亮。似乎,馬曉麗得到了某種啟示,很愿意相信突圍成功會(huì)是真的。當(dāng)然,我也愿意相信她的相信,哪怕這突圍只能是一次遙不可及的浪漫眺望,猶如眺望此刻窗外的斑斕星辰。畢竟,人生長(zhǎng)路寂寥蒼茫,荒蕪的夜空里,總應(yīng)該有一束只為我而閃爍的光亮,透過(guò)邈遠(yuǎn)寒涼,現(xiàn)出珍稀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