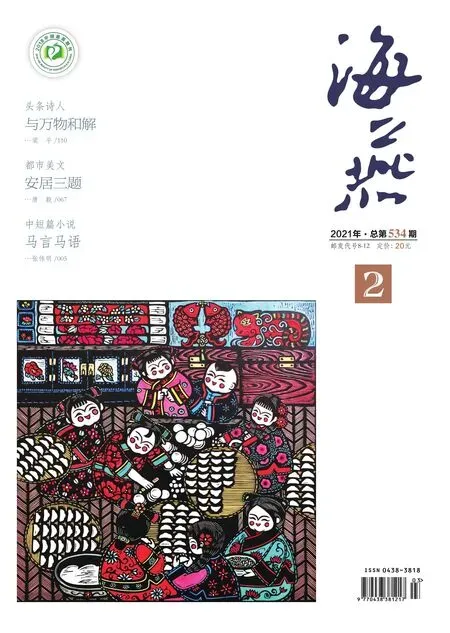與萬(wàn)物和解
文 梁 平
與口罩一起過(guò)年
與口罩一起過(guò)年,
嘴邊的“拜年”被咳得七零八落。
城市與城市之間打了封條,
雪花、雨滴、落葉都有了籍貫,
一只螞蟻爬行也有了戒備。
鄰里之間門(mén)與門(mén)隔離,
小區(qū)拉起警戒的繩索,
陌生面孔和外來(lái)口音就此打住。
七大姑八大姨定好的餐聚,
取消了。有喪從簡(jiǎn),簡(jiǎn)到幾百字,
從生到死。有喜推遲,無(wú)承諾,
或者春暖花開(kāi),或者,或者。
街道的冷清比季節(jié)的凜冽,
更讓人窒息。這是不得已的選擇,
也是最有效的選擇。
誰(shuí)也不愿意過(guò)年是這個(gè)樣子,
假期都延長(zhǎng)了,在家多呆幾天,
比出門(mén)遭遇庚子年蒙面的“劫匪”,
安全。前線與后方已經(jīng)模糊,
有事無(wú)事居家,有人惦記就夠了,
“你若安好,便是晴天”
庚子年正月初五,聽(tīng)風(fēng)
醒來(lái)想起趙公明,
天還黑黢黢的,窗外奔跑的風(fēng)聲,
從峨眉山下來(lái),那是玄壇黑虎拉的風(fēng)。
以前有朋友說(shuō)聽(tīng)見(jiàn)這風(fēng)聲,
就是數(shù)鈔票的聲音,就有好光景。
而今天聽(tīng)到刀光劍影的喧嘩,
趙公驅(qū)雷役電,降妖除魔。
天快亮了,書(shū)架上《封神榜》還在深睡眠,
我聽(tīng)見(jiàn)的風(fēng)不絕于耳,摧枯拉朽。
信這一回,在陽(yáng)臺(tái)上伸展運(yùn)動(dòng),
卸下精神的盔甲,如果看見(jiàn)了黑虎,
說(shuō)聲感謝,盡管我徹底的唯物。
此時(shí)此刻,風(fēng)正在高調(diào)地行走,
喜歡這樣的高調(diào),正月初五,
把那些垂頭喪氣的恐慌,一掃而光。
立春
這個(gè)春天沒(méi)有迎春的準(zhǔn)備,
一直心神不寧。今天立春,
去茶店子看孫兒,沿途嚴(yán)陣以待,
車(chē)轱轆消毒,額頭上測(cè)溫,
熒屏前刷臉,大門(mén)咔地一聲打開(kāi)。
好像從來(lái)沒(méi)聽(tīng)到過(guò)這“咔”的聲響,
周邊太安靜了。
春天撕開(kāi)了一道門(mén)縫,
進(jìn)去和不進(jìn)去都得小心翼翼。
相信季節(jié)的萬(wàn)物復(fù)蘇指日可待,
但我滿心的歡喜遲遲不來(lái)。
孫兒不知道春天有什么幺蛾子,
在陽(yáng)臺(tái)上看見(jiàn)飛機(jī)從樓頂上飛過(guò),
要我猜,上面有多少人?
我說(shuō)剛才我遇見(jiàn)的公共汽車(chē),
都是空的,除了司機(jī),沒(méi)有人。
聽(tīng)柴可夫斯基《悲愴交響曲》
生活被圈禁了。
上床下床一日三餐,手機(jī)、電腦,
全天候記錄行走步數(shù),不及二百。
沉悶。交響作背景在房間循環(huán),
有傷痛的氣息在身體里擴(kuò)散,
鍵盤(pán)敲出每一粒漢字都是奢侈。
這個(gè)時(shí)候意外闖入的俄羅斯老柴,
可夫斯基,面對(duì)死亡的悲愴,
埋伏安魂的博弈、抗?fàn)幒蜎Q絕。
二百步也能合上交響的節(jié)奏,
不可思議。這是生命上演的最后樂(lè)章,
被病毒感染的大腦比病毒頑強(qiáng)。
音樂(lè)未被感染,可以修復(fù)受到感染的
陸地和海洋。即使老柴轟然倒下,
也站在高山之巔,能夠仰望。
非常時(shí)期,一個(gè)巨人留下的絕唱,
在喑啞的日子里,無(wú)邊蕩漾。
鬧元宵
對(duì)于雪白的湯圓已經(jīng)窮于想象,
圓潤(rùn)、凝脂、甜美,這些詞
不再貼切和匹配。
開(kāi)鍋的水,在翻滾,在哭泣,
在鬧。湯圓沒(méi)戳就破了,
流淌的都是殷紅。
昨夜天空有風(fēng)的哨子,折斷,
廚房鍋碗瓢盆掉一地。
取下口罩的碗,無(wú)論口徑多大,
也裝不下湯湯水水的含混。
喇叭別傳
吹喇叭抬轎子都是配套,
由來(lái)已久。喇叭呼喇呼喇地吹,
卯足勁,吹喜迎親,吹喪出殯,
靠的是嘴上功夫。
這陣子的喜怒哀樂(lè)被圈禁,
唯有牽掛和祈禱,唯有
管好自己足不出戶。
原以為喇叭找不到調(diào)調(diào),
沒(méi)有了生意,可以消停。
真是幼稚了,長(zhǎng)江寄生的幺蛾子,
“疫”流而上,翅膀拍打的雜音,
比喇叭更字正腔圓。
喇叭只有一張嘴,沒(méi)有臉,
幺蛾子發(fā)出嗡嗡的聲響,
不要臉。我在長(zhǎng)江的上游,
力所不逮,報(bào)紙上油墨太重了,
讓我黑色的眼睛找天青。
與萬(wàn)物和解
蝙蝠長(zhǎng)出兩米的翅膀,
蝗蟲(chóng)撲天蓋地,新冠神出鬼沒(méi),
我在措手不及中努力接收人類的信息,
很弱,很卡,眼睛突然色盲,
只有黑。伸手不見(jiàn)五指,
觸摸冰冷的絕望。
我開(kāi)始懷疑時(shí)間的暫停鍵失靈,
重新啟動(dòng)的陽(yáng)光還有多遠(yuǎn)?
人和人,人和自然拉開(kāi)的距離,
需要人來(lái)修復(fù),而人已經(jīng)羞于做人,
生不如死。我只想做一條魚(yú),
用我七秒的記憶忘掉所有——
過(guò)度的貪婪和欲望,深重的罪孽,
以及大自然飽受的創(chuàng)傷。
把這些想清楚,天就亮了,
時(shí)間還會(huì)回來(lái),多一些藍(lán)天和白云,
就少一點(diǎn)罹難。英雄與人民,
都有同構(gòu)的身軀和骨骼,
一個(gè)生命倒下,所有活著的人,
傷痛扎得更深、更狠。
躲過(guò)一劫,頌歌與祭文的誦讀,
每個(gè)字句都不能省略,喚醒良知,
與萬(wàn)物和解,相親相愛(ài)。
只有久違的吻還記得愛(ài)情打過(guò)封條,
親愛(ài)的口罩,守護(hù)親近、親愛(ài),
成為幸福的寶典。
這個(gè)春天為什么不可以寫(xiě)詩(shī)
誰(shuí)也不愿意春天支離破碎,
這個(gè)春天的劫難,沒(méi)有人置之度外。
時(shí)間暫停,人和人漸行漸遠(yuǎn),
擦肩而過(guò)都成了奢侈。
適用于春天的詞已經(jīng)格格不入,
戰(zhàn)場(chǎng)和前線以漢字坐實(shí)悲壯的情景。
不見(jiàn)硝煙的戰(zhàn)場(chǎng)戰(zhàn)事告急,
越來(lái)越近的前線,近在眉睫。
戰(zhàn)爭(zhēng)讓春天生死攸關(guān),所有人卷入,
不是所有人都能沖鋒陷陣。
我不能每天以淚洗面,不能
圈禁在家里指指點(diǎn)點(diǎn),更不能
熟視無(wú)睹無(wú)動(dòng)于衷擺一副假模假樣。
春天的樹(shù)葉一片一片泛白,
驚恐、隔離、封城、逆行,
樹(shù)枝上倒掛的陰影,讓空氣稀薄。
問(wèn)問(wèn)自己看到什么,想到什么,
問(wèn)問(wèn)自己在做什么,做了什么,
再問(wèn)問(wèn)自己,該做點(diǎn)什么?
不著一字不一定潔身自好,
留下文字也非饅頭蘸血。
一個(gè)詩(shī)人在這個(gè)春天保持沉默,
如果把沉默引以為至高無(wú)上,
比一個(gè)戰(zhàn)士臨陣脫逃,更可恥。
這個(gè)春天為什么不可以寫(xiě)詩(shī),
身在其中,被一千種情緒包裹,
任何一種情緒的表達(dá)都是釋放,
多聲部音色可以不完美,但它是
這個(gè)春天的證詞,白紙黑字。
太安靜了
萬(wàn)人空巷,
十萬(wàn)人空巷,
百萬(wàn)人空巷,
千萬(wàn)人空巷,
千千萬(wàn)人空巷。
只有人的數(shù)字,
只有床位的數(shù)字。
沒(méi)有來(lái)的人不算,
已經(jīng)走的人不算。
數(shù)字沒(méi)有聲音,
人走沒(méi)有聲音。
落花和流水,
沒(méi)有聲音。
太安靜了,
自己的心跳,
也聽(tīng)不見(jiàn)。
一個(gè)詞不幸被感染
一個(gè)很好的詞,被感染,
在一個(gè)失血的春天。這個(gè)春天,
花開(kāi)都是罪過(guò),就像太多的笑臉貼圖,
被拒絕。這個(gè)詞染上病毒的時(shí)間更早一些,
那些古裝的連續(xù)劇長(zhǎng)期征用,
詞性在金鑾殿變了味道,
晉級(jí)為大詞,成為新的皇冠。
這個(gè)詞被人提醒,高高舉過(guò)頭頂,
如果吞吐的是紙做的蓮花,
只能放在祭壇上了。
這個(gè)詞每個(gè)人都享有版權(quán),
或?yàn)槟嗤痢⒂晁筒菽径?/p>
或?yàn)樯忻恳粋€(gè)太陽(yáng)而生,
這才是這個(gè)詞應(yīng)該的去處。
現(xiàn)在被感染的這個(gè)詞,異常敏感,
四面圍追堵截,生死未卜。
還是讓這個(gè)詞不要死吧,有病治病,
把它放在清水里好好洗一洗,
找回它原來(lái)的詞義,不需要調(diào)教,
也不需要任何添加劑,
作為生命的回饋,沒(méi)有人糊涂。
健康信用卡
01
確定我身份有很多證件,
我在我的祖國(guó),或者祖國(guó)之外,
自由穿行,像鳥(niǎo)兒一樣可以舒展翅膀。
庚子年二月的春天,又頒發(fā)一個(gè)二維碼,
讓我獲得了健康認(rèn)證。
我把健康隨身攜帶,出入超市、商場(chǎng),
出入有人群的公共場(chǎng)所,健康與健康接頭,
上線與下線,省略了所有的暗號(hào),
整個(gè)世界向我行注目禮。
02
風(fēng)走不動(dòng)了。生活的每個(gè)通道,
都在排隊(duì),前胸貼后背的隊(duì)伍,像絞索,
地鐵、公交、安檢、售票口,
被勒得像纏絲的兔。
退后一步、兩步,給呼吸留個(gè)過(guò)道,
改改隊(duì)形改一種打擁堂的以往。
拉開(kāi)距離的美,等來(lái)的都是驚喜,
放松的密度行云流水,
一個(gè)淺淺的回眸,百媚生。
03
吃葷的吃素的都是自己的事,
該吃什么不該吃什么,
就不能隨心所欲了。
蛇、鼠、蝙蝠、果子貍、穿山甲,
地球生物鏈上的物種,與人類相安無(wú)事,
偏偏成了盤(pán)中餐,而且吃相難看。
偷偷地吃,明目張膽地吃,
都是嘴惹的禍。那些寄生的病毒,
成功入侵,你就是它們的宿主。
04
一雙幼年的手洗到了成年,
還是不停地洗。洗泥土洗灰塵洗病菌,
洗干凈了的手舉止清白,
拒絕藏污納垢。
眼睛看不見(jiàn)不一定就干凈,
臟東西已經(jīng)狡滑到了無(wú)孔不入,
道貌岸然防不勝防。
你就是千手觀音也要好好洗,
手洗干凈,就干凈了身體和名聲。
05
八大碗九大碗全副武裝上陣,
十幾雙筷子穿插、挺進(jìn),深入淺出。
酒肉穿腸,伴以煙霧繚繞,
這樣轟轟烈烈的場(chǎng)面由來(lái)已久,
城市與鄉(xiāng)村根深蒂固。
形同虛設(shè)的公筷寂寞難耐,
千呼萬(wàn)喚的分餐異常艱難。
是時(shí)候了,情感交流換一種方式,
心與心的靠攏,不在桌面。
06
“上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這樣的小提醒并不陌生。
這是某個(gè)私密場(chǎng)所,也是公共場(chǎng)所,
這是私密行為,也是公共行為,
尺度很小,不能沒(méi)有規(guī)矩。
散漫也好,著急也好,偏離了方向,
腳下流湯滴水。一小步不拘小節(jié),
出門(mén)再怎么裝扮都不會(huì)光鮮,
有風(fēng),尾隨而至。
07
好端端的口罩惹了誰(shuí)?
人與人、族群與族群之間太多強(qiáng)加,
口罩被妖魔化,蒙受不白之冤。
被冷眼、被驅(qū)趕、被圍追堵截,
甚至被視為封嘴、蒙面。
僅僅就是尊重他人和保護(hù)自己,
僅僅就是一個(gè)衛(wèi)生常識(shí),
我就愛(ài)上了口罩,以后的日子,
它將成為隨身飾物,生活伴侶。
08
壩壩席、百人宴、千人聚餐,
紅喜事、白喜事,大吃大喝。
有些風(fēng)俗和習(xí)慣上了年紀(jì),
一塊老年斑貼在生活記事薄上。
其實(shí)沒(méi)有人喜歡老年斑了,
街坊相逢一個(gè)微笑,彼此輕松,
老鄉(xiāng)見(jiàn)老鄉(xiāng)落座一杯清茶,
炒幾個(gè)拿手菜,邀一輪家鄉(xiāng)的月亮。
真情從來(lái)不湊熱鬧,歲月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