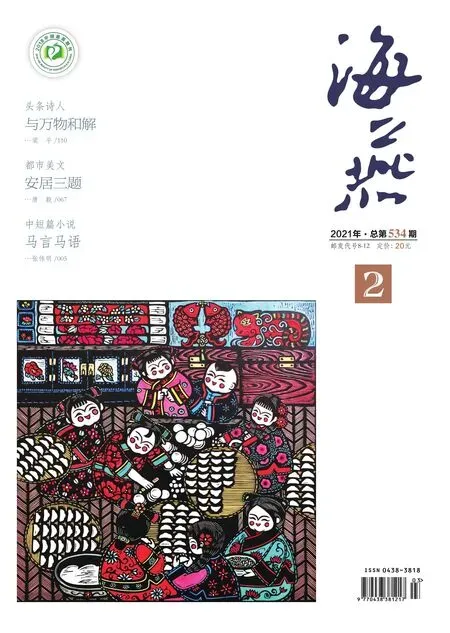行吟者的精神地理
——論鄧朝暉詩歌的生命質感
文 ?聶 茂 李馨然
鄧朝暉具有行吟詩人的氣質,此“行吟”不取古希臘詩人荷馬的街頭流浪之形式,也不取戰國時期楚國詩人屈原披發澤畔的哀慟愛國之情感,而是指鄧朝暉的詩歌所體現出的“自我流放”的生命質感。“流放”不是“放逐”,靈魂隨意放逐,生命便沒了根據,鄧朝暉的“流放”源于對自我生命的體認與理解,源于對生存空間的想象性重建與文化性追溯。在這個靈魂逐漸趨于空洞與疲乏的時代,讀鄧朝暉的詩,靈魂飄蕩過田園牧歌式的河流村莊,飄蕩過異質性的原始文化圖騰,在盡頭會猜測生命或許存在另一種亦夢亦幻的真相空間。
詩評家霍俊明曾評價鄧朝暉的詩作“呈現了行走詩學的可能性”,亦是此理。“行走”不是移步換景,而是在多重空間尋找生命想象與體驗,從湖南常德澧水到沅江,詩人的腳步跟隨了思想的火花,河流、族群、村落、文廟、碼頭、渡船,皆跳入了詩人的文本之中,化為詩人個人性的詩歌空間,構成其詩歌世界的地理基礎。因此,這不僅是一個行吟者的自我生命表達,在“樊籠者”復歸自然與探索更多文化奇觀之后,生命得到了充盈,其遺留的足跡和個體生命體驗、地理文化想象一起,以點聯結成面,成就了這方水土在精神維度層面的邊地空間。
一、出離:自我的生命體認
這是一個行吟者離開出生地的開始。從蘭江橋到澧水,從十字街到解放路,從戲園到城關醫院,再到澧州文廟內的狀元橋與月亮池,“我”便不能再往前去向那“荒野的郊外”了,“我”的腳步被“孤獨”與“習慣”困在了出生地之中。行吟者也曾吟唱過這片土地,寫下這片土地澧州文廟中的真與美,梨園戲院里書生小女的愛與恨,甚至是街邊石獅背后隱藏的客死他鄉的愁與苦,就連一片銀杏“三分之二的圓”,也曾被細心雕琢悉心描繪。與這浮躁的塵世比起來,她更像一個靈魂已然枯竭的故居者,徘徊在出走與堅守、遠方與故土的選擇之間,進退維谷。
徘徊是一種細密而綿長的疼痛,詩人渴望探尋自己生命中更豐盈美好的靈魂,然而在故居之地已經只剩殘存的記憶。因此,在鄧朝暉關于自己所在故土的日常性描寫中,“無名”成為了一個反復書寫且極為重要的關鍵詞,是其詩歌中一條潛隱的線索。在《出生地》組詩當中,“梨園”沒有名字,所謂“梨園”只是“我”固執的叫法;“十字街”沒有名字,它是“我”通往城中心與人民醫院的中心匯聚地;“文廟”沒有名字,它是“我”童年時期的一個秘密的院子;“石獅”沒有名字,沒有人知道它的歷史來源于“華陽王”……“無名”是對歷史的遺忘與遮蔽,它們的“無名”匯聚在一起,是故鄉文化意義上的“無名”。因此“故鄉”在詩人心中也“缺席”了,她故而生出諸多質疑與困惑:“我屬于它嗎?/屬于這片朋友圈里轉發的最美村落?/……我親近過它嗎?/沒有童年/沒有土地/也沒有故人。”借此,不難看出詩人心中的迷茫與困頓,靈魂失所,恐怕是身處這個時代最大的病痛。人在劇烈變革的時代,即使沒有漂泊于他鄉,也會在故土失去根基,成為心理上無序的“他者”,造成靈魂游離與分裂的撕扯感與疼痛感。
正如詩人自己在《無法回避的疼痛》中所說:“一個人的出生地是他無法選擇的,可他有權選擇自己長久的居住地。而我不同,多年以前就想飛離這座小城,但這么多年來,卻總是將走出去的時間推了又推。一直以來,我在理想與現實之間掙扎,不愿留在這里卻又總是離不開。”這種掙扎、糾結構成了詩人的情感創作基調,一切關于故鄉與歷史的流逝、關于現在與未來的思考與探索,皆出于此種躁動不安的出離欲望,但這種欲望又是潛藏于安靜溫和的表面之下的。在《梨花、梨花》長詩中,詩人將自己“已過不惑的中年”比喻為“腐爛的菠蘿味”,借以說明生命與死亡的同質化悲哀。這是一種近乎麻木的疼痛,“仿真”的生與“腐爛”的死沒有區別。除非“遠行”,離開“春天”,穿行在路途上,面見“一棵暮春的梨樹”,遇見自己短暫而又熱烈的葬禮,“一個在生的人目睹了自己的葬禮”,就等于從麻木的生活中重生了。這首詩應當是詩人“出離”的象征之作。生與死都被詩人以“植物”類比,“玫瑰月季”等南方嬌艷的花映射的是人內心的干涸枯竭,“梨花”作為“死亡之花”卻象征著生命的熱烈與飽滿。生死的意義在詩人筆下被顛覆了,生即是死,死才是生,“梨花”成為了“肉身的菩薩”,只有祭奠枯萎的生,穿過內心的空,才會得到葬禮之上靈魂的充盈與豐沛。關于“生死”如此重大的話題,詩人仿若一個旁觀者,在“奢侈”地目睹了自己的葬禮之后,靜謐而溫和、熱烈而詭譎地踏入了另一層靈魂得到自由的廣闊天地。
于是,詩人作為行吟者出發了。
二、追溯:重構的田園牧歌
孤獨的行吟者的腳步是緩慢而悠長的,她以溫潤的眼光愛撫自己的出生之地。在察覺到陌生與異樣后驚異于它的變化,為它的滄桑與文明辯駁,為它的消逝與繁華哀傷。行吟者回到生命之源,那是記憶最初始的地方,從那里開始,也許可以追溯到屬于生命本真的田園牧歌,屬于靈魂純粹的家園故土。也因此,在鄧朝暉的詩歌中,能看到一幕幕澧水河畔詩人對自我生存空間的想象性重建。回憶中的特定性場景、家族代際中的人與事、澧水河畔的傳統文化與建筑,都鑲嵌在故土的文化性背景之中,給詩歌帶來了多維地理空間的呈現與復雜隱秘的人世命運的更迭。
詩人在創作談《粗糲之花》中言及自己童年時代的澧水,那里隱藏著自己的童年記憶:“年輕的父親和母親、他們隱秘的愛情、早熟的姐姐、潮濕的碼頭、童年的伙伴、夭折的小青、杉樹林、桑葚、月亮池、古城墻、荊河戲……” 這些具體的物象都是一個個回憶點,在詩人筆下生發成一段段故事,破碎的意象因而得以重新拼接。詩人在現實與想象的碰撞中重構畫面,重新譜寫屬于行吟者自己的生命想象、故土想象。
在《五水圖》組詩中,有一首近似于紀實類的詩歌《小營門42號》,記錄的是一家人的命運代際,“穿軍裝的繼父”“轉在山路上的娘”“擔水洗紅心蘿卜的姐姐”和“走向未知巷口的我”。詩歌的寓意模糊深邃,拼接式和斷聯式的畫面跳轉起伏,轉瞬間便切換了幾個時空。“遠方的命運”沒有被詩人訴說,無人知曉無人應答,也就是在這樣一種模糊深邃的命運主旨里,似乎浮現出湘西世界朦朧神秘、如夢如煙的生命之詩,那里有著美好的人性,也有著人生不可知的命運,就像沈從文《邊城》結局中所喻示的:“這個人也許永遠回不來了,也許明天回來!” 未知的命運被“淡藍色門楣”的“孤獨的河水”包圍,迷離奇幻的微妙氣氛在“雨水”被“外婆的小腳接住”中推向極致。靳曉靜評價這首詩“有些巫氣” ,的確是恰如其分。
另一首長詩《玉堂春》,是詩人對一段戲曲的回眸,原有馮夢龍纂輯的《警世通言》中的話本小說《玉堂春落難逢夫》,后有戲曲《玉堂春》,詩人每一節取其戲曲中兩句詞作為一個畫面場景,繼而進行自己的創作想象,譜寫成嵌入悲憫與血淚的命運長詩:“你七歲賣身入娼門/豆蔻之歲遇公子/當千金散盡/公子落難苦讀求功名/你落于富商之手/遭毒婦陷害頂替罪名/……當你終于成為泥土/……蘇三,你只在卷宗里/在洪洞監獄的死牢/你上過枷受過刑/徘徊在幾尺見方的洞口……/為一個來歷不明的官司/劃一個皆大歡喜的句號。”不同于戲曲與戲文中的“大團圓”結局,詩人重構了關于玉堂春這位青樓女子的歷史想象,將她置于現實性的處境之中,去想象另一種人生命運真相的可能性,另一種“歷史”(虛構)被文本遮蔽的可能性。“高潮與深淵素來就有秦晉之好”,美好與殘酷亦如是。因此,詩人在這里的想象重構,更近乎于揭示命運的文本顛覆性。戲外的人不能幫你看到,歷史不能幫你看到,唯一知道的僅有自己而已,只有你自己才會了解自我生命的真相以及抵達的終點。
以上在詩人對個體生命回憶的想象性重構的詩歌中,物象、幻象并不在很大程度上“具備特定文化群體共同認可的喻義”。它們都是獨屬于詩人個體的生命經驗意象,在詩人的組詩與長詩中曾多次出現,實際上成為了詩人獨特的情感符號,表達詩人獨特的詩歌文本內涵,甚至于地域空間內的地理建筑,詩歌中所反復描繪的碼頭、渡船、月亮池、狀元橋,都成為其獨特的地理空間符號。在情感符號的加持之下,地理空間符號就具有了詩人特定的精神資源附屬,即詩人所追溯的那段“田園牧歌式的模糊記憶”。值得說明的是,詩人對童年記憶的追溯,所構成的這部分田園牧歌式的想象重建,雖然充滿了悠遠、恬淡的畫面感,但始終抹不去一種關于“消逝”的疼痛之感。無論是記憶,還是歷史,一切的人事都在消逝中漸漸隱匿、淡無,或許最終只留在了詩人想象的文本之中。關于故土和遠方,在寫下這些詩歌時,詩人一定是眉頭不展的。
這是一個行吟者在眺望過去時的神情。
行吟者曾說:“故鄉是用來眺望的”,而她對遠方的渴望還未曾到達。“沒有人告訴我/蘭江橋的前面還有一條孤獨的河流叫澧水/過了澧水還有一個村莊/村莊連著村莊/如同大海連著大海。”至此,行吟者開始了她真正的遠行。
三、遠行:原態的詩性世界
沿著沅江上溯,是行吟者的起點。途經許多支流,在懷化市麻陽縣,在一個叫漫水的村子,在大湘西許多的村落與小鎮,詩人頭頂虔誠,遇見了足以震撼靈魂的文明與史詩。那些遙遠到幾乎與世隔絕的史前文明與美麗傳說,那份無際的敬畏與熱愛,在詩人心中打開了一個缺口,從此在詩人的文本中,肆無忌憚、遼闊宏遠的想象奔涌而來。詩人將自我“流放”到這片土地上,用眼睛和雙腳抵達了思想所不能及的地方,而后又以瑰麗奇幻的想象文本來呼應這份敬畏與熱愛,形成原態的詩性世界。她是在譜寫河流的史詩,也是在譜寫文明的史詩,更是在譜寫關于人的命運的想象史詩。
在湘西世界的少數民族民俗和傳說中,出現了諸多英雄和敬神者。他們通常擔負著守衛一族命運的責任與使命,但在詩人的文本中,“青面獠牙”只是梯瑪“多愁”的面具,祭祀的歌舞無法撫慰“一生緊促”“崖上立樁”的薩歲。他們在一族命運處于風口浪尖之時挺身而出,而關于寂守與孤獨,卻無人能解。英雄已逝,族人為他們修筑石像,譜寫神歌,祈求保佑,奉若神明,代代流傳。詩人佇立凝視,她看到的是一首英雄的落寞之歌,那是生前之名,身后之苦。一切描繪都以電影鏡頭般極強的畫面感呈現出來。在《梯瑪神歌》中,詩人仿佛以手搖鏡頭切入,先入遠景,祭祀的“擺手堂”緊閉不語,進而鏡頭前移向下切入中景,姑娘凝神的面龐望向遠方,鏡頭淡出時空切換,黑夜中仿佛篝火燃起,天幕之上煙火盛開,人們肅立默跪,祭祀“大王”。鏡頭平行移動,出現梯瑪之像,手握木刀腰系紅繩,進而接入鏡頭特寫,紋眉紅心的面具之下,是梯瑪的滄桑面龐,鏡頭繼而逐漸淡出,浮現梯瑪的戰爭歲月。《五水圖》第一首詩歌的開頭,便以靜默無言式的鏡頭語言呈現出湘西祭神場面的神秘與遼遠,奠定了整組詩歌的情感基調與畫面氛圍。接下來,鏡頭開始進入“我”的主體視角,講述主體與對象的故事。“我”何以遇見梯瑪?何以想象梯瑪?鏡頭從“戲樓”轉換到“冬日暮晚”,“我”撐一把朱紅傘,遇見梯瑪的一瞬間,鏡頭開始以具象畫面表達人的內心感受,有“碎花和流蘇”,其實是借指詩人靈魂受到震撼的細密感觸,靈魂出竅,鏡頭開始表現詩人的自由暢想。“大風吹過茫茫酉水/牧羊女簾前洗澡落紅飛花”,這是詩人由神對平凡人的想象。二者并無直接關聯,但從詩歌的整體格局來看,詩人由對原始祭神民俗的觸動轉接到了對一種遙遠文明平凡生命暢想的靈魂洗禮,二者故事邏輯的不連洽并不造成想象空間的斷聯,詩歌的整體氛圍仍然是融為一體的,是一場“我”與古老文明、原始神話的靈魂對話。
在這一組詩中,還另有對建筑、動物、河流、山脈的聯想。它們中有些有名字,而更多的是無名的“你”,那是許多不同的人的命運,聯結在一起是詩人對湘西整個原始文化世界觀的想象。詩人在旅途中不斷與他們進行對話、想象、寫作,《青碧》與《青蛇記》是擬人化的動物想象,帶有“聊齋”式的“妖”的演繹方式,書寫了關于狐妖與蛇妖的凄美愛情,詩歌靈動詭譎,神秘妖冶。《薩歲》是“女性英雄”的書寫,在原始的“族”的譜系中,女性通常是作為“母性”的孕育者身份出現的,就連作為“女英雄”的薩歲也是如此。她護佑子孫的神像也被喻為“一棵孕育期的葡萄藤”,困頓卻堅韌地哺育著這片土地。薩歲的形象應是湘西邊地世界女性形象的理想象征,具有史詩性的尊重與崇敬。《響水壩》《上爐到浮石煙》《入銅灣》《去往惹巴拉》這一系列詩歌都是詩人由旅途場景、物象等生發的與無名的“你”的對話,面對響水壩,“我”就這樣進入“你”去等待一場生命的“衰敗”。在上爐到浮石煙的路上,我與“一個少年”有了“母子相連”的心,感受著他的憤怒與多愁。銅灣峽谷瀑布中的自然奇觀與原始文化讓“我”的面色被“鎂光燈”照過,那是被時代喧囂映射出來的無知與彷徨。惹巴拉這片蠻荒之地充斥著失意之人,只有“我”被中了蠱毒的苗女和多情的里耶所吸引,他們的命運在詩人筆下,皆演變為九曲回腸的吶喊。再有《大王殿》與《潕水河》,它們也各自有其命運歷史。大王殿內隱藏的是“盤瓠大王”戰功赫赫迎娶苗族少女生兒育女的傳說,潕水河上流淌的是河流傾吐自我歷史命運的長久嘆息。在《五水圖》組詩中,每一首詩都關乎一個奇特的傳說或想象,都是詩人對湘西世界中人的命運的聯想性書寫。這些廣闊的原始空間為詩人打開一扇靈感的大門,這片土地上的每一個生命,經由詩人的想象都將生發出充滿故事性的光輝。
行吟者終于有了她的“眼淚”和“指引”。鄧朝暉曾在《生活是一出悲喜劇》中說道:“沅江是一條河流,生活是一條河流,時光也是一條河流。我們在河流中奔走、徘徊、飄蕩、或悲或喜。不管是大憂傷,還是小喜悅。我都得感謝,感謝生活賜予的這么多滋味,感謝時光流轉,感謝我手中還有筆,能夠一一記載。”行走對于鄧朝暉詩歌創作的意義是巨大的,因為行走,她的詩歌不再拘泥于生活化、日常性的書寫(《廚房中》《安居》等),而是打開了更為遼闊的邊地書寫空間。她就像一條在黑暗中默然流淌的河流一般,將自我的生命流放到河流的各條支流,去探索更為廣袤豐富的生命圖景,給靈魂以洗禮,給自我以重生。
四、結語
讀鄧朝暉的詩,就像是在讀一個行吟者的生命歷程,在讀個體精神世界中的湘西生命圖景與文化想象。“行吟者”的身份代表了這個時代下無所適從的“分裂者”,熱愛故鄉卻又渴望走出自己,趨于安穩卻希冀靈魂震撼。這種遠方與故鄉、出走與堅守的矛盾性因素一直貫穿于詩歌始終。因此,讀者能感受到詩歌中的糾結與掙扎,詩人即使是在面對湘西原始神話與傳說進行瑰麗奇幻的想象時,其鏡頭語言也是偏向緩慢與節制的。詩人通常是以中近景的表現物象為主,且擅長于以小的鏡頭的位移,或淡入淡出的方式來轉切鏡頭畫面,這是一種隱藏于情感深處的安靜的力量。而當這種安靜的、內斂的、溫和的鏡頭敘事與詩人無邊無際的靈魂暢游式的記錄和想象結合在一起時,于讀者而言,在情感上就生發了諸多具有矛盾性因子的迷人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