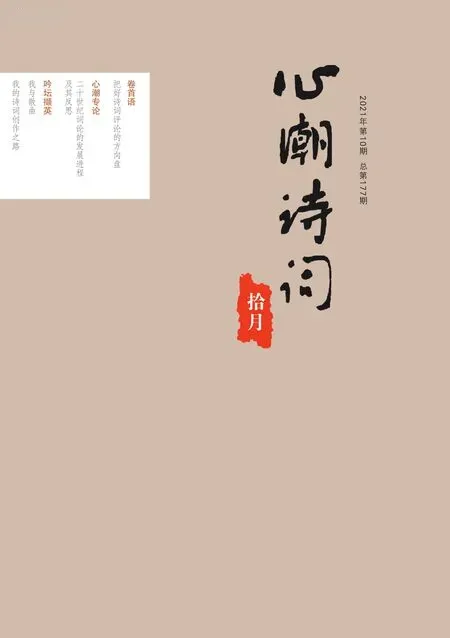二十世紀詞論的發展進程及其反思
朱惠國 付 優
詞論作為詞的“批評之學”,與詞的創作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站在今天的時間節點,從宏觀的層面評價已經過去的二十世紀,可以發現:詞的創作幾乎未能產生影響持久而深遠的作品,但詞論卻經歷了其發展史上變化最大,且絕不缺乏亮點的特殊時期。究其原因,除這百年間產生了《蕙風詞話》《人間詞話》等重要詞論成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從二十世紀初到二十世紀末,中國詞論在詞學觀念、成果形態、傳播方式等方面發生了巨大變化。直觀地看,從南宋王灼《碧雞漫志》以來,以隨筆型、筆記體、印象式、漫談式為特征的詞話批評逐漸讓位于新興的專題式詞學論述,簡言之,就是主流詞論完成了從傳統到現代的轉型。
回顧二十世紀詞論的發展進程,展現每一階段的代表性成果,并在此基礎上梳理其發展演變的內在軌跡,有益于我們正確把握與評價二十世紀詞學,為當下的詞學批評提供可靠借鑒,這是一項具有學術價值與現實意義的重要工作。
一
二十世紀詞論的起點是晚清常州詞學。一般認為,中國詞論有兩個高峰:南宋和晚清。如果說南宋詞論主要是在自唐五代至兩宋詞學高度繁榮的基礎上,對詞的藝術特點進行總結,那么晚清詞論則是在詞的創作經歷最后輝煌之后,在更大時段的基礎上進行總體性的觀照,后者在晚清動蕩的社會背景中融入對時代因素的思考,因此更加全面,也更加強調詞的社會功能。從社會性、文藝性兼顧的角度看,晚清無疑是中國傳統詞論最為繁榮的時期。百年詞論以此為起點,經歷了民國和共和國時期,以二十世紀末的新時期為終點,相比于兩宋以來的千年,時間跨度并不大,但形式與內涵變化巨大。在此期間,傳統詞學不斷式微,現代詞學逐步建立,基本完成了詞論史上最重要的轉變。這是中國詞論史中最值得關注與總結的百年。
對于二十世紀詞學衍變進程的分期,學術界異說紛紜。概而言之,以傳統詞學的終結和現代詞學的建立為主線,大致可劃 分 出1900—1949、1949—1979、1979—2000三個大的發展階段。其中1908年《人間詞話》發表、1931年朱祖謀去世、1933年《詞學季刊》創刊等標志性事件又可作為關鍵節點標識詞學發展的里程。詞論作為詞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二十世紀經歷了以下幾個發展階段:
從庚子事變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900—1949),是傳統詞學的最后繁榮期和現代詞學的創立期。從詞論的角度看,這一時期的繁榮發展主要展現在五個方面:
其一,詞壇名家輩出。這一時期詞學家眾多,大致可以劃分為三大群體。其一,“由內而內”的詞學家,即傳統的詞學家。1904年王鵬運去世后,以朱祖謀為首的傳統詞學家繼續主盟詞壇。他們的詞學思想變化又可分為兩個階段。前一階段,主要表達“黍離麥秀”與“荊棘銅駝”的遺民之感,這在他們的創作及借助詞集序跋表達的詞學評論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后一階段,他們關注的重心逐漸向詞集校勘和聲律研究轉移,更加強調詞的技法。龍榆生曾將之總結為:“一時詞流,如鄭大鶴(文焯)、況夔笙、張沚莼(上龢)、曹君直(元忠)、吳伯宛(昌綬)諸君,咸集吳下,而新建夏吷庵(敬觀)、錢塘張盂劬(爾田),稍稍后起,亦各以倚聲之學,互相切摩,或參究源流,或比勘聲律,或致力于清真之探討,或從事夢窗之宣揚,而大鶴之于清真,弘揚尤力,批校之本,至再至三,一時有‘清真教’之雅謔焉。”其二,“由外而內”的詞學家,即所謂體制外詞學家,以王國維、梁啟超為代表。這類新型的詞學家吸納西方哲學、美學和社會學觀念,從純文學和社會文藝學兩個方向滲透、影響中國傳統詞學,其本質是西學東漸背景下,傳統詞學理論面對西方文藝理論挑戰的應激反應。兩人開創了新的詞學風氣,但所獲的理論回應比較微弱,因而,有學者提出此時期詞學未能如小說、戲劇、詩歌般形成規模化的“文學革命”。直至1927年,胡適出版《詞選》,批判晦澀難懂的夢窗詞,提倡清新剛健的詞風,同時以社會進化論的觀點來觀照詞的發展演變,在具體的論證過程中多采用分析、實證的方法,在詞壇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其三,內外兼修的詞學家,即新生代詞學家,以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為代表。這類新生代詞學家既吸收傳統詞學精華,又能借助現代的分析方法和實證方法進行詞學研究,全面促進了詞壇文學觀念、研究視角、研究手段、成果形式和詞學傳播媒體的更新,最終完成了中國現代詞學的建構。與他們同聲嚶鳴的,還有南北各高校主持講席的詞學教授,如中央大學汪東、陳匪石、王易,北京大學趙萬里、劉毓盤,武漢大學劉永濟,河南大學邵瑞彭、蔡楨、盧冀野,中山大學詹安泰,重慶大學周岸登,暨南大學易孺等。從地理分布來看,這些詞學家又先后形成了滬寧詞學圈、京津詞學圈、廣州詞學圈和成都詞學圈,共同推動倚聲之學的繁榮。
其二,詞社活動頻繁。從庚子事變到五四運動期間,承接湘社、鷗隱詞社、咫村詞社、寒碧詞社遺風,以柳亞子主持南社、朱祖謀主盟舂音詞社為中心,北京有著涒吟社;上海有麗則吟社、春暉社;廈門有碧山詞社;成都有錦江詞社、春禪詞社;臺北有巧社。這些社團不全是專門性的詞社,但詞的創作與討論占據著其社集活動的重要位置。由于南社體兼詩詞文,此階段詞社應屬舂音詞社影響最大,王蘊章稱“海上詞社,以民初舂音為最盛”(《舂音余響》)。從五四運動到全面抗戰爆發前,出現了白雪詞社、甌社、甲子詞社、潛社、聊園詞社、趣園詞社、須社、六一消夏社、漚社、鳴社、蓼辛詞社、蟄園詞社、梅社、如社、聲社、壽香社等詞學社團。其中以潛社、須社、漚社影響較大,活動較多,輯有《煙沽漁唱》《漚社詞鈔》等。抗戰爆發后,神州滿地瘡痍中,詞人弦歌不輟,組織有瓶花簃詞社、午社、雍園詞社、玉瀾詞社、綺社、瓶社、夢碧詞社等。中國詞社素來有立派的傳統,往往在詞社中崇尚、倡導某種詞學傾向。民國詞社情況則稍有不同,應酬、社交的成分多一些,不盡以立派為宗旨,但以上各類大小詞社的社約、宣言、綱領、章程以及社集序跋等文獻材料中,均不同程度體現詞社的創作傾向和美學崇尚,保留著豐富的詞論材料。
其三,詞學刊物興盛。《詞學季刊》和《同聲月刊》是民國時期兩種專業性詞學刊物,為這一時期的詞學研究和詞學評論提供了發表園地,極大影響了這一時期的詞學傳播。1933年4月,《詞學季刊》由龍榆生等人創辦于上海,以約集同好研究詞學為宗旨,主要作者為龍榆生、夏承燾、唐圭璋、趙尊岳、張爾田、夏敬觀、吳梅、葉恭綽、邵瑞彭、周泳先十人。這是近代貢獻最大的詞學專刊,1936年因抗戰爆發而停刊,歷時三年,共12期。每期主要內容包括論述、專著、遺著、輯佚、詞話、近人詞錄、近代女子詞錄、詞林文苑、通訊、雜綴等。《同聲月刊》是龍榆生1940年創建于南京的詞學刊物,前后歷時近五年,共出版39期。此外,陳贛一于1932年創刊的《青鶴》雜志也刊登了大量詩詞作品和評論文章。除了這三家刊物,刊登詞學研究文章的期刊雜志還有《婦女時報》《小說新報》《小說海》《民權素》《禮拜花》《紅玫瑰》《紫羅蘭》《先施樂園日報》《天韻報》《永安月刊》《中華郵工》等百余種。其中,《民國日報》《中華編譯社社刊》《北平晨報》等刊物都曾設有詞論專欄。
其四,詞學著述大量出版。詞學創作與研究的繁榮,加上民國時期機器印刷的推廣,書籍出版更加便利,共同推動著詞學著作的大量出版。1926年,胡云翼出版第一部專門的詞史著作《宋詞研究》,分為上下兩篇,上篇探討宋詞的發展、變遷和整體情況,下篇評述兩宋主要詞人作品。1931年,劉毓盤《詞史》付梓,是為第一部略具規模的通代詞史。全書共十一章,除第一章論詞的起源外,后十章依次詳細論述隋唐五代至明清的詞人群體和流派。1932年,王易出版《詞曲史》,分為明義、溯源、具體、衍流、析派、構律、啟變、入病、振衰、測運十個部分,探究詞曲的體制源流、宮調格律和詞曲二體之異同。次年,吳梅出版《詞學通論》,全書九章,前五章論平仄四聲、詞韻、音律和作詞法;后三章標舉評述歷代詞家得失。四十年代,薛礪若三次修訂出版《宋詞通論》,分七編探索宋詞風貌和詞人嬗替的軌跡。此外,謝無量《詞學指南》、王蘊章《詞學》、徐敬修《詞學常識》、徐珂《清代詞學概論》、葉恭綽《清代詞學之攝影》、胡云翼《詞學ABC》《中國詞史略》《中國詞史大綱》、梁啟勛《詞學》《詞概論》、譚正璧《女性詞話》、盧前《詞曲研究》、伊碪《花間詞人研究》、繆鉞《中國史上之民族詞人》、龍榆生《詞曲概論》、余毅恒《詞筌》、劉堯民《詞與音樂》、孫人和《詞學通論》、劉永濟《詞論》、任中敏《詞學研究法》等著作均為此時段較有代表性的詞史詞論。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七十年代末,是現代詞論的潛伏期。1949年7月,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召開,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被確立為文藝發展的新方向。從“十七年”到“文革”期間,在困頓的境遇中,一方面,張伯駒、夏承燾、黃君坦、寇夢碧、孫正剛、陳機峰、沈祖棻、唐圭璋、丁寧、朱庸齋等詞人百折不撓,默默堅持創作,留下了不少情感熾烈的詩詞作品;另一方面,唐圭璋《全宋詞》、夏承燾《唐宋詞人年譜》、鄧廣銘《辛稼軒年譜》等詞集和年譜的出版,為詞學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文獻支撐。更為重要的是,夏承燾《唐宋詞敘說》(1955)、龍榆生《宋詞發展的幾個階段》(1957)等詞學論文的發表,彰顯著前輩學者志懷霜雪、不辭辛勞地推動詞學研究向前進展的艱苦努力。但由于時代的限制,詞學研究也受到大環境的干擾,偏離了正常學術研究的軌道。其中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將宋詞“豪放派”稱頌為“現實主義支流”,將“婉約派”貶低為“反現實主義逆流”,甚至強行將“豪放派”又劃分為“儒法”二派,把蘇軾和其門下詞人當作“保守儒家”的靶子來攻擊,又將王安石、辛棄疾等人不恰當地理解為“法家詞人”。對當時盛行的詞學議題,我們應該在對歷史背景的理解中批判式繼承。
從八十年代初至世紀末,是現代詞論的新興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解放思想,文藝界的創作和評論環境逐漸恢復繁榮局面。
首先,隨著詞學的復興,詞學專業刊物重新創辦。1981年,華東師范大學施蟄存教授聯合夏承燾、唐圭璋、馬興榮等創辦《詞學》集刊。集刊專攻古典文學中詞學一塊,旨在為海內外專業詞學研究者提供發表研究成果的園地,以利大家“互相商榷,互相切磋,互通信息,互為補益”,共同推動研究,繁榮詞學。刊物的主要欄目有論述、年譜、文獻、詞苑、叢談、圖版等。從刊物的辦刊宗旨、編輯思想,甚至主要欄目設置來看,均有遙接三十年代《詞學季刊》的意圖。該刊是迄今為止國內唯一的詞學研究專業集刊,對新時期詞學的繁榮作出了巨大貢獻。除此之外,八十年代初,廣東創辦有《當代詩詞》、《詩詞集刊》、《詩詞》報等報刊。九十年代,中華詩詞學會創辦《中華詩詞》,東南大學詞學研究所創辦《中華詞學》刊物,這些刊物均促進了詞學的繁榮,也為新時期詞論的發展起了推動作用。
其次,詞論文獻整理取得重要成果。八十年代在詞論文獻整理與出版方面最重要的成果是修訂再版了《詞話叢編》。唐圭璋《詞話叢編》編纂于三十年代,是二十世紀最為重要的詞論文獻之一。1933年8月出版的《詞學季刊》第一卷第二號,在“詞壇消息”中最早報道編纂《詞話叢編》的消息,作者透露了兩方面的內容:其一,匯刻詞話的想法最初由鄭振鐸提出,唐圭璋先生是“重申斯旨”;其二,唐先生已編出初步目錄,計由詞話八十種。此后《詞學季刊》多次發文,跟蹤報道。綜合這些報道,《詞話叢編》收錄詞話的數量不斷變化,經歷了由少(80種)到多(90種),再由多(90種)到少(65種)的過程。事實上,《詞話叢編》刊印時,最終的詞話數是60種,說明唐圭璋先生也經歷了廣搜詞話到嚴選詞話的過程。八十年代,唐先生的修訂本在原來所輯60種詞話的基礎上增加了25種。《詞話叢編》的重新修訂出版,是唐圭璋先生對詞學文獻整理工作的重大貢獻,也是八十年代詞學復興的一個重要標志。除了《詞話叢編》,這一時期還有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金啟華《唐宋詞集序跋匯編》等詞論文獻資料出版,為詞論研究走向深入和精進奠定了基礎。需要說明的是,施蟄存《詞籍序跋萃編》其實編纂于“文革”前,但由于其處境艱難,一直無法出版,能夠在此時面世,正說明詞學研究的環境已發生改變。
再次,各類詞學研究論著陸續出版。晚清以來,各類詞學研究著作不少,但專門的詞論研究著作,尤其是專門的詞學批評史著作十分鮮見,因此,1994年出版的《中國詞學批評史》具有篳路藍縷的開創意義。此書由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四位中青年教師方智范、鄧喬彬、周圣偉、高建中合著,由施蟄存參訂。作者以時間為線索,將中國詞學批評的發展分為兩大階段:從唐五代到明末為第一階段,主要論述以“本色”論為核心的傳統詞學觀和蘇軾的詩化理論,對其特點和影響均作了恰如其分的評價;清代至民國初為第二階段,主要介紹、評價相繼而起的各種詞派。全書以王國維《人間詞話》為終結,以為由此開啟了“西學東漸”背景下詞學批評的新變。兩個階段前后連貫,在介紹詞學家、詞派以及各種觀點的同時,勾勒出中國古代詞學批評史的發展軌跡。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古典文學研究室編的《詞學研究論文集(1949—1979)》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入1949年以來詞學研究的代表性成果,也可視為重要的當代詞學文獻,引起學界廣泛關注。除了著作外,這一階段單篇詞學論文,如施蟄存致周楞伽以《詞的“派”與“體”之爭》為題的幾封書信,吳世昌《有關宋詞的若干問題》《宋詞的“婉約派”和“豪放派”》等,也對詞學研究走向“百家爭鳴”“千帆競發”起到積極的推動作用。
縱觀百年詞壇,在波折中蜿蜒前進,詞的批評之學薪盡火傳,生機不絕,在傳統詞學的基礎上成功孕育了現代詞學學科。
二
在二十世紀波瀾起伏的詞學發展中,詞學理論的演進堪稱重中之重。學者們不辭辛勞,爬梳文獻,研習聲律,力求準確把握住理論演進、形式嬗遞的脈絡,創造了較為豐碩的研究成果。在這些成果中,有三個方面在詞學發展中影響較大,尤其值得關注與探討:
第一,記錄詞壇爭鳴的“聲響”。現代“詞學”體系的建構、作詞是否嚴守四聲的爭議和詞體如何解放的命題,是二十世紀前半期詞壇關注的核心話題。一百年中,絕大部分詞人都曾或主動或被動參與過相關話題的討論。然而,在此前的研究中,我們主要關注的是各個時期代表詞人的觀點,極大程度上忽略了詞壇上廣泛存在的“低音”。以詞體解放問題為例,梁啟超、胡適提倡完全解放詞體,用白話作詞,“推翻詞調詞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胡云翼等青年學者受胡適影響,形成了“詞體并不是一種有多大意義和價值的文體,它的生命是早已在幾百年前的終結,成為文學史上的陳物了”之類的激烈主張;1916—1921年間,陳柱與友人馮振也提出“自由詞”創作理念,倡導打破詞譜約束。三十年代,曾今可、柳亞子與趙景深等人以《新時代月刊》“詞的解放運動”專號為陣地,掀起了廣為人知的“詞的解放運動”。大致上說,曾今可、董每戡、柳亞子等人主張不分別陰平、陽平與上去入,以白話或現代淺近的文言入詞,但要求保存平仄和韻腳;張雙紅、張鳳等人主張完全廢棄詞譜、詞牌,創制新譜自度腔填詞。然而,細細考究,在“詞的解放運動”中還存在更多的議題。例如董每戡大體贊成曾今可的觀點,但又提出“不使事(絕對的)”“不講對仗(相對的)”“要以新事物、新情感入詞”“活用死律”“不湊韻”“自由選用現代語”六條建議;翁漫棲更加激進,提出“我的改善很不像曾今可先生那樣只解放小部份的一小部份(只把陰陽的平仄解放而已)。我以為這種解放腳而不解放乳的解放,似乎太于無聊。所以我自己的改善卻是把詞譜完全解放”;而葉恭綽則干脆指出文體沿革,詩之后有詞,詞之后有曲,“曲之流變應產生一種可以合樂與詠唱之物,其名曰歌”,提出“鄙意應不必仍襲詞之名,蓋詞繼詩,曲繼詞,皆實近而名殊。猶行楷、篆隸,每創一格,定有一專名與之,以明界限,而新耳目”。
與此同時,仍有大量詞人持保守立場,主張嚴守詞譜、師法夢窗、辨明四聲。例如,陳匪石主張嚴守四聲,“若既不知五音,又不辨四聲,則不必填詞可也”;向迪琮亦提出“今雖音律失傳,而詞格俱在,自未可畏難茍安,自放律外,蹈伯時所謂‘不協則成長短詩’之譏”;劉富槐則深信堅守詞體的價值,提出“西方學者知有此體,殆將播諸管弦,列于美術,寧有屏而不御乎”;蔡嵩云更跳出兩派,主張“近年社集,恒見守律派詞人,與反對守律者互相非難,其實皆為多事。詞在宋代,早分為音律家之詞與文學家之詞”。可見,在“詞體解放”的旗幟下,詞人群體的具體思想實則各不相同,而這些細節的差距、微弱的“低音”正是我們深入理解詞學衍變的重要資料。
第二,還原詞論競議的“現場”。二十世紀的詞論著述中,保存著海量有關當時詞人交游、詞社活動、詞作評論的材料,詳細考索,不難還原出眾聲喧囂的詞論“現場”。若論輯錄詞人詞作,匯輯詞壇軼事,可觀陳銳《袌碧齋詞話》、碧痕《竹雨綠窗詞話》、夏敬觀《忍古樓詞話》、冒廣生《小三吾亭詞話》、張爾田《近代詞人逸事》、高毓浵《詞話》、程善之《與臞禪論詞書》等材料。其中,如蔡突靈在《紅葉山房詞話》中假托尋芳倦客評述自己的詞稿兼解釋詞作所隱射政治事件,又如吳梅《與龍榆生言彊村逸事書》談論朱祖謀故事,周焯《倚琴樓詞話》輯錄李劼人、畢倚虹詞事,陳去病《病倩詞話》抄錄友人題《征獻論詞圖》詞作,均有存人存詞之效。若論評騭詞人,甲乙詞作,可觀聞野鶴《怬簃詞話》、黃濬《花隨人圣庵詞話》、朱庸齋《分春館詞話》等材料。如陳聲聰《讀詞枝語》點評近代女詞人丁寧、沈祖棻、陳家慶、壽香館弟子、龍榆生弟子張珍懷、王筱婧;或如錢仲聯《近百年詞壇點將錄》借說部狡獪之筆,為記室評品之文;或如方廷楷《習靜齋詞話》論“鹓雛長于寫艷,亞子工于言愁;鹓雛秣麗似夢窗,亞子俊逸似稼軒”;再如沈軼劉在《繁霜榭詞札》中提出“民初四詞家外,尚有三大名家,竊準漢末成例,擬為一龍。以夏承燾為龍頭,錢仲聯為龍腹,龍沐勛為龍尾”等,均堪稱點睛妙筆。若論記錄詞人交游、詞社活動始末,可觀王蘊章《秋云平室詞話》、蔣兆蘭《詞說》、陳聲聰《讀詞枝語》、陳洵《致朱孝臧書札》(十通)等材料。如陳曾壽《聽水齋詞序》記錄須社梗概;陳聲聰《讀詞枝語》歷數燕京自庚子詞社、聊園詞社、趣園詞社到須社的社集活動與中心任務,又記錄南方漚社、午社、如社參與人員;徐沅《瀼溪漁唱序》記錄“余于庚子之秋與劉語石、金蔗畦、左迦廠諸君結詞社于西泠”;蔣兆蘭《樂府補題后集甲編序》記載“去年庚申歲暮,煥琪宴集程子蟄庵、儲子映波、徐子倩仲及不佞共五人結詞社,名曰白雪,紀時也,亦著潔也”;王蘊章《梅魂菊影室詞話》記錄舂音詞社創社和第一次社集情況,云“近與虞山龐檗子、秣陵陳倦鶴有詞社之舉,請歸安朱古微先生為社長”;龐樹柏《袌香簃詞話》記錄舂音詞社社員和第二次社集情況,都是研究近代詞社詞學思想的寶貴資料。
第三,追溯詞學評論的“脈絡”。考索二十世紀的詞論著述,不難發現,其中保存有大量談論學詞法、作詞法、選詞法、評詞法的內容,足以為我們深入理解中國傳統詞學的現代轉型提供強有力的支撐。如陳世宜《玨庵詞序》記錄了跟隨朱祖謀從《絕妙好詞》入手學詞的經歷;陳柱《答學生蕭莫寒論詩詞書》詳細談論了學詞的步驟、對象和要點。又如翁麟聲提出“填詞之苦,千態萬狀”,“句之長短,字之多寡,聲之平上去入,韻之清濁陰陽,皆有一定之嚴格”;王瀣主張“竊謂詞難于詩,全在會意尚巧,選言貴妍,固不可歇后做韻,尤不可滿紙詞語,竟無一句是詞”;歐陽漸認為“作蘇辛詞,第一要膽大,俯視一切,敢發大言;第二掛書袋子,開口閉口總是吃現成;第三情摯,一肚子不合時宜,不堪久郁,不管是非,滂薄而出之”;譚覺園主張“清、輕、新、雅、靈、脆、婉、轉、留、托、澹、空、皺、韻、超、渾為詞之十六字要訣”,又提出“初學者,以《白香詞譜》或《填詞圖譜》,較為適用。《白香詞譜》,尤以天虛我生之考正本為妥善”;吳東園則認為“今之學詞者,如以空靈為主,但學其空靈,而筆不轉深,則其意淺,非入于滑,即入于粗矣。以婉麗為宗,但學其婉麗,而句不煉精,則其音卑,非近于弱,即近于靡矣”。又如汪兆銘在致龍榆生書札中批評古今選家之弊端,提出“選一代之詞,宜以落落十數大家為主,于此十數大家,務取其菁華,使其特色所在,爛然具陳……于此落落十數大家之外,如有佳作,亦擇其尤精者選之,為之以輔,如此或可兼收眾長而去其弊”。值得關注的是,《漚庵詞話》中保存有較多對王國維“境界說”的反思和修正。一方面,漚庵認為,王氏標舉的“無我之境”實際并不存在。“物境者,景也;心境者,情也;情景交融,則構成詞之境界”,境界即為外在物境與內在心境的化合為一。歷代詞人“以詞心造詞境,以詞境寫詞心,固處處著我,初無‘無我之境’也”。另一方面,漚庵又反對王氏“隔”與“不隔”的區分方式,提出“凡詞之融化物境、心境以寫出者,皆為‘不隔’,了無境界,僅搬弄字面以取巧者為‘隔’,‘隔’與‘不隔’之分野,惟在此耳”。
總體上看,二十世紀是詞學與國族同風雨,在裂變中涅槃的一百年,催生了許多啟人深思的詞學議題,在眾聲喧嘩中譜寫了波瀾壯闊的學科史,時至今日,二十世紀詞論著述依然具有較高的理論價值和文獻價值。
二十世紀伊始,梁任公作《少年中國說》,引用西諺云“有三歲之翁,有百歲之童”。詞論作為一種與詞的創作密切相關的專門之學,發展到今天,也積累了千年有余的歷史,而二十世紀這一段,在西學東漸的歷史大背景下,發生了一場至關重要的蛻變,成為一種既古老又年輕的學問。作為詞學研究共同體的一分子,我們誠摯地期待它能穿越千年的風霜,渡過百年的奔流,仍能承《大學》“日新又新”之誡,秉《大雅》“舊邦維新”之命,在變動不居的時光長河中,煥發出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