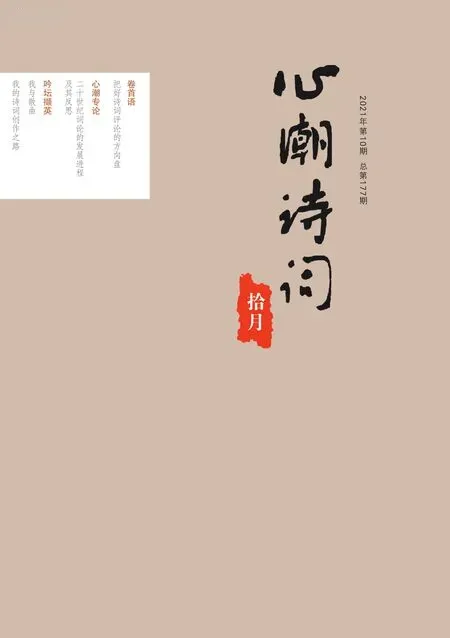詩詞評論的標準
(按姓名音序排序)
高昌
(中華詩詞學會副會長,《中華詩詞》主編):套用“經師易獲,人師難得”這句古語,我用“經論易制,人評難致”來表達對詩詞評論的感慨。經論,指的是出于古今精典的觀點羅列和復制粘貼的月旦之聲。人評,指的是既獨出機杼,自彰靈彩,而又“謹身修行,足以范俗”的心靈之音。強調人評,也是強調基于詩詞文本的一種自主發現、自覺創建的自省能力。詩詞評論的成效檢驗,也可用撞鐘為喻:“叩之以小者則小鳴,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待其從容,然后盡其聲。”詩詞評論一定要在詩詞作品中間去撞擊和發聲,要有專業性的在場意識和針對性的實效創見,而不是人云亦云,更不是喃喃自語。我喜歡謹嚴、勇敢、真摯、溫暖、澄澈的評論文字。涉及具體衡量標準,則以下十個“有”字不可或缺:
第一要有根有據。根,指深厚扎實的詩學修養,是發聲的底氣。據,指準確及時的文本觀察,是發聲的憑證。言之有物,真知灼見,才能提供正確的路徑、健康的指征和切實的成效。
第二要有膽有識。膽指膽略,就是說真話的勇氣。敢于批評是一種勇氣,敢于肯定其實也是一種勇氣。褒優貶劣,才能激濁揚清。識指見識,就是學理性、專業性的見解和主張,直面詩詞創作現場來把脈診病,切中肯綮,引領風尚,實現審美的有效抵達。
第三要有光有暖。一方面保持操守,守住底線,另一方面求同存異,與詩為善。無論理論職責和使命多么堅定,無論批評鋒芒多么銳利,而建設性的態度和審美啟迪的初心,則都是評論家專業精神中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四要有容有量。容和量,指的是理論包容的胸懷和突破學科壁壘、門戶偏見的度量。評論是在多元化、多樣化大背景下確立自己位置的,其說服力和影響力是以開闊的視野和兼容的態度為支撐的。唯我獨尊的批評邏輯以及黨同伐異的圈子做派盡管表面上大殺四方、威風八面,而其缺少和喪失的恰恰是最寶貴的理論公信力。只有各種風格、觀點之間的貫通圓融,互為鏡鑒,才更有助于找到(或無限接近)詩詞審美的最大公約數。
第五要有滋有味。目前的詩詞評論有“迷之粗鄙化”和“迷之學理化”兩種令人憂慮的風習。前者可謂市井消費,后者可謂庭院經濟。二者缺少的正是格調滋養和性靈風韻。能夠深入人心的評論文章還是要深入淺出,鮮明生動,朝氣蓬勃,讓人能夠讀得進去,而且有營養,有收獲,有閱讀快感。
如果挑選心儀的古今詩論,我首推孔子的“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寥寥數語而及詩及人,澄懷味象,豐盈厚重,成色十足。三百篇的閱讀積累是他論斷的文本基礎,思無邪的詩學體認則是他獨出機杼的審美發現。孔子在這里進行的科學闡釋和睿智涵概,為后世樹立了一個豁然開朗的實踐標桿。最后,我想在詩詞評論的文字標準之外,也為評論家的自身操守提一個“一言以蔽之”的標準,而我的答案也是這三個字:思無邪。
宋湘綺
(中南大學當代詩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點評模式中,講一首好詩詞“有境界”,往往點到即止。這是印象式批評的含蓄、直觀。妙處難與君說?藝術批評的使命就是言說其妙。使命,是事物存在的理由,這種言說本身就是一種理論創造。筆者認為應該在詩詞鑒賞止步的地方,向詩詞藝術批評出發,創造當代詩詞藝術批評的理論話語,言說詩中“只可意會,不可言說”之處。怎樣的作品才叫“有境界”?百年來王國維境界說被當成認識對象,難以測量,難以進一步指導文藝創作。施議對先生說王國維所說的境界是可以測量的,這個觀點施先生1997年就提出了,二十年過去,至今尚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對此,筆者專門請教了施先生。施先生的解釋包含三層意思:第一,說境界是一個疆界,是可以測量的,即指可以用文學批評的標準,用科學的現代話語對作品的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做出客觀的評價;第二,說境界是意境,是時間和空間加上時空里面的人和事。以實踐存在論的生成觀看,人生境界永無止境,詩詞創作一步一步走在人生境界的攀登之路上。意境和境界的關系,是足跡和歷程的關系。第三,說境界是境外之境,王國維所說境界,在境之外,而非在境之內。
施先生的解讀擺脫了認識論思維,把詞學提升到哲學,從境內到境外,“另構新境”就是精神生產,就是人生實踐的“內環節”。
眾多學者將把意境、境界當作認識對象,混為一談,爭議不休。這是詩詞認識論研究本身跨越不了的方法局限。筆者以實踐存在論分析意境,發現作品意境與作者人生境界之間的關系,是實踐與實踐者的關系,是存在與存在者的關系,是精神足跡和精神歷程的關系。
實踐存在論認為人生境界不是自然產生,也不是主觀臆想;境界,是在人與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建構的實踐存在活動中形成的精神形態;具有個體內在性和生成性,它是個體覺悟而生的內心靈明。“生成”指境界永遠處在“進行時”。作品“意境”保留了作者創作作品這一瞬間的“境界”。
提出具有學理深度和時代高度的當代詩詞批評標準,離不開王國維境界說這個現代詩詞美學的奠基之石。任何理論創新都不是拔地而起,創新始于“創舊”。評價一首詩詞“有境界”,從文學批評的角度,闡釋其境界何在?需要審美價值觀、社會歷史價值觀、人性價值觀、道德價值觀、文化價值觀五方面綜合分析、判斷,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的分析,進一步打開了詩詞文學批評的闡釋空間。
在現實主義、現代主義、后現代的喧囂嘈雜中,“多談現實,少談主義”是一種境界。王國維境界說,作為批評模式,在天、地、人的三足鼎立中,以境外與境內的共生互動,明確創作與批評的現實關懷和理想之維。境外之境中包含的“于事未必有,于理必可能”的文學性,為當代詩詞指明了方向。有了疆界、意境、境外之境的理論分析,王國維境界說將更好地應用于文藝批評。從這個角度看,中國傳統文論話語有待于進一步轉換成清晰的現代學術話語,才能對當代文藝批評產生積極有效作用。
王賀
(中華詩詞研究院編輯部副主任):切斯瓦夫·米沃什曾說:“我們仍然浸染在我們的時代中,我們的判斷也就應預先被評估為不確定。”(《詩的見證》)所謂“評估”的“不確定”性,就是說當代評論標準首先是流動不居的、永遠進步的,而非一個放之古今、四海而皆準的永恒標準。當代詩詞評論標準的確立就應該是走在正確道路上的、不斷進步的各種藝術標準的吸納與認定,充滿了“不確定性”。盡管詩詞評論的標準有著諸多“不確定性”,但評論的原則卻有必須堅守的底線。比如評論必須遵守科學精神,也要參照個性體驗,更要言之有理,言之有度。公正的態度與科學的精神,是當代詩詞評論要遵守的首要法則。詩詞講究藝術的真實,而非科學的真實。王安石評價李賀“黑云壓城城欲摧,甲光向日金鱗開”稱:“方黑云壓城,豈有向日之甲光?”惹得文學家紛紛嘲笑。盡管我們不能以科學真理去批評詩詞真實,但要以科學的精神對待詩詞評論。只有秉持追求真理的精神,才能對詩詞文本進行相對客觀的評論,公正而坦然,不會因外界的影響隨意更改評論準則與方向。
詩詞是融合了詩人對世界萬物個人化見解的藝術,是詩人在客觀現實基礎上的主觀創造,具有獨特性與不可復制性。那么以詩詞作為評論對象的批評家就不能完全“酷不入情”,需要以個體經驗去理解詩人與詩詞,去揭示詩人在詩詞文本中隱藏的、特有的美學密碼。只有這樣,詩詞評論才親切可感,容易產生共鳴,得到最為廣泛的接受。因此,我們說批評家個體經驗的主動參與,是詩詞評論“廣接地氣”且言之有理的重要法則。
蘇東坡有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無論畫還是詩,都不只是詩畫本身,而是別有氣韻、格調甚至“道”,這就需要詩詞評論通過文本細讀揭示這內蘊于文本的許多意義。評論也如詩畫,若只局限于具體文本的解讀,那充其量不過是一篇詩詞精解,而無法上升到詩詞評論的高度。每一篇詩詞評論都應該代表著批評家的聲音,是批評家詩學理論的一個注解,也就是說文本細讀的最終目的是“六經注我”而非“我注六經”,它所有的表述都是在闡述批評家詩學理論與詩學主張的“冰山一角”。因此,文本細讀作為基礎的理論升華,是詩詞評論不斷攀上哲理高峰、促使人類永恒思考的不二法門。
秉持科學的精神,提倡批評家個體經驗的積極參與以及詩學理論的升華,是“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文藝方針下我們要遵守的評論原則。以包容、開放的態度,去容納多向度、多層面甚至過于猛烈的批評,去謹慎學習與理解批評家的立場與主張,必然可以促進詩詞評論的真正繁榮。
星漢
(新疆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中華詩詞學會顧問,新疆詩詞學會會長):將文藝創作和評論比作古代馬車之兩輪,空中飛鳥之兩翼,是非常確切的。如果沒有文藝批評,那么文藝創作,也就很難前行。詩詞創作必須全面貫徹“二為”方向和“雙百”方針。無論創作還是評論,如果偏離了“二為”方向,那就有可能“南轅北轍”或是“飛鳥各投林”。我們的傳統詩詞,是文學藝術的一部分,只是“百花齊放”中的一朵花。創作猶如對花兒的“栽種”,評論猶如對花兒的“管理”。至于這朵花的形狀的大小,花香的遠近,就看我們如何栽種和管理了。詩詞評論的樣式很多,理論文章、書評、序跋、對話、訪談、點評等等,甚至公眾號后面的留言,也應當看成是評論的一種方式。詩詞創作者要“各盡其能”,而讀者是“各取所需”,評論者是“各展其才”。一首詩詞發表了,就允許各色人等評頭論足。作為作者要有雅量,批評者只要不是惡意攻擊,都要認真對待。對方說得對,就虛心接受;說得不對,也沒有必要火冒三丈。
評論者評論的優劣,和評論者的閱歷、學識、修養、地位等是分不開的。閱歷不同,對待文學作品的感受就不一樣,作出的評判也就不同。講一個真實的故事。我家大嫂給孫女講她小時候餓肚子的事兒,不料孩子瞪大眼睛問:“奶奶,你沒有飯吃,為什么不吃餅干呢?”這和“何不食肉糜”有“異曲同工”之“妙”。我想,作者經歷過的環境,評論者沒有經歷過,那評論者就無法感受作者的心態。例如,就今天的新疆而言,交通、通訊的方便,拉近了人們感情的距離。新疆人恐怕很難對王維“西出陽關無故人”的詩句產生共鳴。
“詩無達詁”,“作者不必然,讀者何必不然”。詩詞評論,對于每位評論者來說,很難有個統一的標準。但是,“當代詩詞”必須有“當代”的氣息。時代變了,我們詩詞的內涵,也要“與時俱進”。就說分別吧,誰再去“臨歧折柳”,人家就會說是破壞生態環境了。有些詩人西裝革履,坐著飛機,非要來個“白帆”“驛站”什么的,這樣的詩詞當然不能給予很高的評價。
批評別人的詩詞,出發點一定是善意的,不能諷刺挖苦,更不能謾罵。“至于罵一句爹娘,揚長而去,還自以為勝利,那簡直是‘阿Q’式的戰法了。”(魯迅語)
今天以詩詞得名者,應說是功底厚、學養深、識見廣、創作勤的一批人。他們或是以創作宏富見稱,或是以發表精品鳴世。但是,也不排除其他因素,有些評論者往往摻雜著朋友的情面、長官的職務、異性的情懷等,也就難免褒揚過當。
詩詞有異于其他文學樣式,其平仄、用韻、對仗,也是評判優劣的標準。一般來說,詩詞的平仄不合或是用韻混亂,就不美聽。當今詩詞的用韻,要么是平水韻(或是后來依平水韻而來的《詞林正韻》),要么用《中華通韻》,因為它們都是“國標”。律詩如果不用對仗,或是對仗不工,總是一病。創作者不能以皎然的“散律”《尋陸鴻漸不遇》和崔顥《黃鶴樓》為借口,不用對仗或是對仗欠工,因為你沒有皎然和崔顥那兩下子。我想,王之渙的《登鸛雀樓》和杜甫的《絕句》(“兩個黃鸝鳴翠柳”),之所以能被選入《千家詩》,除了內容外,對仗工穩應當是重要的因素。
楊景龍
(安陽師范學院文學院二級教授):南宋姜夔《白石道人詩說》有言“難處見作者”,認為增加創作難度,才能脫棄凡庸,寫出上佳的作品。其實評論何嘗不是如此?和創作一樣,當前舊體詩詞評論堪稱繁榮。但毋庸諱言,大多數評論文章以鼓勵為主,多說好話,廣結善緣,是詩詞評論領域的普遍現象。氣可鼓而不可泄,適度的鼓勵當然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失去了分寸,不顧所評論作品的思想藝術的實際水準,洋洋灑灑,天花亂墜,動輒許以妙語奇句,名篇杰構,甚至聲言追逼李杜,邁逾唐宋,顯然就違背了實事求是的精神,是一種對評論對象和評論者自身都不負責任的行為。當代人評當代作品,在目前的社會和文學生態環境下,實話實說,顯然是有困難的。如果仿照姜夔“難處見作者”的說法,我們是否也可以說“難處見評論”。然而也正因為其“難”,才見出評論者的真知灼見和操守擔當。
當代詩詞評論面臨的難處,主要是來自主觀和客觀兩個方面。就客觀方面來說,評論者與作者同處一個時空,那些躲不開、磨不掉的人情和面子,必然導致說真話變得困難起來。茲事非筆談短文所宜討論,按下不表。但有一點是必須在此加以強調的,那就是評論者一定要有求是精神,作者也要有傾聽批評意見的雅量。對于評論者而言,當下需要的是一點“至仁無親”“大仁不仁”的“忍心”和“狠勁”,這樣才庶幾能夠保證批評的公正和準確,才能讓批評對象真正受惠,知所損益,改善提高。對于作者而言,只要還想進一步提升詩藝,就需要評論者指出存在的問題,建議改進的方法,這比一味肯定和贊美更迫切更重要,更有理論價值和實踐意義。作者尋求知音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適度的自信和自負也是需要的,但一定不要自信自負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的程度(曹植《與楊德祖書》)。作者一定要保持清醒的頭腦,虛懷若谷,從善如流,如此方能蟬蛻魚躍,有望進乎技矣。
就主觀方面來說,當代詩詞評論的難處,在于評論者是否真正建立起來批評的標準和尺度。詩詞評論界的當務之急,是提高評論者自身的專業素養。要使自己具有“真賞”的眼光,言必有中,成為佳作“千載其一”的知音(劉勰《文心雕龍·知音》),就要以中國詩歌史上真正一流的作者如屈陶、李杜、蘇辛、柳周的名作,作為衡量的標準和尺度,然后放開眼光來一覽眾山,審視眾作。同時還要參酌時代的因素和外來的資源,深入研究文藝美學和詩學理論,仔細講論古今詩法、詞法類著作,包括域外的文論著作。使自己不僅能從思想藝術的總體把握上判別高下,而且能從意象、語言、字法、句法、章法、聲韻、格律等修辭技巧的細部,去錙銖較量,分辨良莠,從無量數的現當代詩詞作品中,擢優汰劣。面對當代星海汗漫的舊體詩詞創作現狀,評論者進行準確的價值取舍無疑是困難的,所以不妨借鑒劉勰的“博觀”尤其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六觀”評鑒方法,來助力自己作出接近正確的評判和論斷。
張桃洲
(首都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很長一段時間以來,詩詞評論處于十分尷尬的地位:它普遍被認為是詩詞創作的附屬品,與后者相較而言是次生的、第二位的。其間的“理由”似乎很“充分”:一則有了創作才有評論,若無創作,評論就無所依傍;二則相當多的評論不那么“爭氣”,跟風似的表揚、毫無節制的追捧、不著邊際的拔高,不一而足。表面上看,情況確如上文所述。不過,倘若深究下去,就會發現實際情形并非全然如此。當前詩詞評論誠然有諸多不盡人意之處,但一味地指責或人為造成創作與評論的對立,終究不具建設性,也無益于評論本身的改善。從建立詩詞評論標準的角度,一個重要乃至根本的前提是:要重新確認詩歌評論的獨立性,或者借用已故詩評家陳超的說法就是“自立”性。這一方面是指詩詞評論應該與詩詞創作保持平等對話的姿態,另一方面意味著詩詞評論自身也必須“立”得住。這既應當成為從事評論者的一種意識,又是評論者對待自己工作和評論對象的一種態度。只有這樣,詩詞評論才能獲得自尊與自信,才有可能建立人們所期待的良性標準,并在此基礎上得到健康發展。
總的來說,詩詞評論的任務無外乎如下方面:要么對詩詞創作進行歷史總結和史實梳理,要么對個案進行剖解、對現象展開評析或者對作品進行賞讀。不管是致力于哪一方面,詩詞評論都確實要遵守某些內在法則或“行業”標準。不過,依筆者之見,談論詩詞評論標準,與其說要為詩詞評論制訂一種固定的規則或模式,不如說是希望在詩詞評論過程中逐漸形成一些“共識”——這里所說的“共識”,并非指向某種一致性或趨同性,而是從理論到實踐、從觀念認知到具體操作所應遵循的最基本的規約,或可稱之為詩學“共同體”。究竟哪些算得上詩詞評論的“共識”呢?筆者不揣谫陋,略作闡述。
其一,詩詞評論的定位。詩詞評論應在堅持“自立”的前提下,充分意識到自己能夠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要有所為、也要有所不為。評論者不是粗暴整肅詩詞創作的“巡邏兵”,也并非手持道德利劍的裁判,更不宜充任立法者和布道者的角色,其首先要做的是詩詞之中真善美的發現者、宣揚者——當然,誰都知道真善美是融為一體的。
其二,詩詞評論的功能。詩詞評論固然要及時回應一些詩人的最新創作和不斷涌現的新現象,不過更重要的是善于凝練問題、提出問題,有時候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緊迫。詩詞評論不是簡單地對詩人、作品進行臧否,也不是對詩人、作品做出“蓋棺定論”式的評判,而是以鮮明的問題意識,啟發后來者持續加入對詩人、作品的闡發中。
其三,詩詞評論的文字。既然是品評詩詞,詩詞評論的行文就不能枯燥乏味,在文字上雖不能與詩詞本身媲美,但也不應粗糙浮泛。完成一篇詩詞評論,不必故意堆砌華麗的辭藻或繁復的術語,而應做到文從字順,條理清晰,要言不煩,切中肯綮。
總之,詩詞評論對于評論者來說,既激發智慧、冶煉性情,又磨礪心志、攢聚耐性,是需要調用綜合素養才能完成得好的,不可輕慢待之!
周嘯天
(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教授,中華詩詞學會顧問):關于當代詩詞的評論標準,我的意見有三條:一曰書寫當下,二曰銜接傳統,三曰詩風獨到。因為不書寫當下,沒有時事,沒有開放的思想意識,題材是傳統題材、思想是陳舊思想、情調是士大夫情調,或者為標語口號傳聲筒,“雷同則可以不有,雖欲存焉而不能”(袁宏道)。不銜接傳統,就不是詩詞,就該去寫新詩、新民歌、“東江月”。同時,銜接不等于復制,任何經典文本,它的美都是不可復制的。復制不及原創。希臘神話如此,唐詩如此,宋詞亦如此。當今作者,只能學習傳統、銜接傳統,我手寫我口。缺乏藝術個性,你寫我寫一個樣,則沒有必傳的理由,所謂“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有了書寫當下、銜接傳統這兩條,允稱小好;加上詩風獨到這一條,堪稱大好。書寫當下,涉及詩詞取材。我的意見是,題材不是問題,關鍵看它是不是作者的菜。換言之,就是要看這個題材打動作者沒有?是不是情動于中,非形于言一吐為快不可?例如,我曾多次參觀九院(鄧稼先生前工作單位),但從來沒有想過寫《鄧稼先歌》。直到有一天,看電視訪談《魯豫有約》之鄧夫人許鹿希訪談,使我大受觸動:原來獻身可以到這種程度,必須徹底隱姓埋名,人間蒸發。做什么,不能告知家人。什么時候回家、什么時候離家,不能告知家人。談不上物質享受,穿得像農民,常常是水還沒開,面條就下鍋了。處理核事故現場,挺身而出,義不容辭。超劑量輻射導致其英年早逝。鄧稼先卻說:“只要我做成了這件事,我這輩子就沒白活。”楊振寧安慰鄧夫人的話是:“希望你從更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待稼先和你的一生。”就是這些東西,深深打動了我。于是我覺得,如果不為這樣的人寫一首詩,我就對不起自己的良知。媒體把“不蒸饅頭爭口氣”之句炒得盡人皆知,而《鄧稼先歌》真正的主題句是:“神農嘗草莫予毒,干將鑄劍及身試。”這首詩曾獲第五屆華夏詩詞獎一等獎,評委說,鄧稼先的事跡打動了你,你的詩神完氣足,讀來感人。如果不是深受感動,而是應景作詩,寫出來將是另一碼事。
就是以人民大眾為題材,作者也必須是本來就關心民生的人。例如,四川詩人何革寫過一首《隔窗看建筑工人雪天勞作》:“一窗相隔兩重天,我沐春風他冒寒。往日偏憐白雪美,今朝何忍用心看。”隔窗看建筑工人雪天勞作,這樣的生活經驗可能人人都有。通常認為,這不過是社會分工的不同。很少有人想到,憑什么我過得比他舒服。看農民打稻、拾麥子,你或許也有類似的生活經驗,這再正常不過——農民和農民工就是這樣生活。惟具有悲憫情懷者才會受到觸動。從而寫出“一窗相隔兩重天,我沐春風他冒寒”,令讀者一讀難忘。你要說這是一首建筑工人的頌歌也可以。刻意寫一首建筑工人頌歌,未必能寫得如此感人。詩人把自己放進去,有“念此私自愧,竟日不能忘”之意,與白居易的精神暗合。
我還有一個意見,詩有兩種好:一種叫想得到的好,別人也會這樣寫,其詩好處也就有限;一種叫想不到的好,詩人要追求的,就是想不到的好。比如《人民英雄紀念碑前》這個題目,多數人要么寫不好,要么寫成想得到的好。重慶詩人張榕是這樣寫的:“拋頭灑血為蒼生,青史何曾著姓名。肅立碑前思痛哭,幾人無愧對英靈?”這首詩的前三句,可能別人也想得到,最后一句直面現實,發人所未發,如斗大橄欖,耐得咀嚼。因為和平的歲月太長,戰爭的殘酷,先烈的犧牲,容易被世人淡忘。一經指出,便令人猛省。詩忌公共之言,喜獨到語、未經人道語。當然,首先要意思好。意思好還不夠,還得語言到位,有想不到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