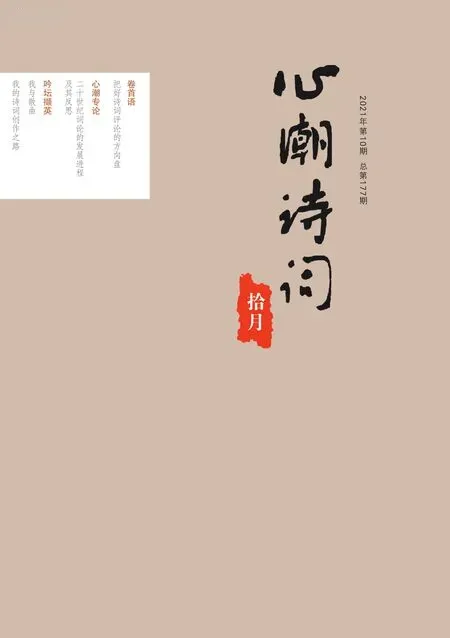挖掘語言潛能 拓展詩詞空間
——從詩詞語言的認識誤區說起
張金英
鐘嶸強調詩歌創作必須以“風力”為主干,同時“潤之以丹彩”,風力與丹彩均備,才是最好的作品;蕭統的“事出于沉思,義歸乎翰藻”中的“翰藻”當指廣泛的語言美,包括音韻、對偶、辭藻等;杜甫的“語不驚人死不休”足見他對詩語嘔心瀝血的追求;賈島的“推敲”之典說明賈島重視詩語的錘煉;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中一個動詞的選用……以上種種,都說明了詩歌語言對傳達思想情感的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說,語言運用能力是衡量一個人詩詞水平的標尺之一。只有深諳詩詞語言藝術,才能夠嫻熟地駕馭詩詞。本文就語言與詩詞的關系做一觀察與分析。
一、詩詞語言的認識誤區是阻礙詩詞進步的關鍵因素
不可否認,有不少當代詩人駕馭語言的能力是很強的,但也有不少人沒有意識到語言運用的重要性,以至于走進了認識的誤區。就筆者觀察,主要存在以下幾種情況:
1.作品的思想性與藝術性不能統一
我們常說,意在筆先,強調了立意的重要性,尤其是思想性強的作品,其立意更是高遠,這樣的作品首先成功了一半。但是,筆者發現,有不少這樣的作品,其語言表達卻極為生硬,甚至讀起來非常別扭,常常出現詞不達意的情況,而作者卻毫不知曉或只滿足于深刻的思想性。究其原因,一是作者本身欠缺語言功底;二是沒有將語言進行藝術錘煉,直接用生活化的語言入詩;三是對語言的重要性認識不夠,覺得作品有思想性即可,忽略了詩詞的美學價值。
2.用韻之爭對詩詞語言能力的忽略
詩詞界一直存在新舊韻之爭,而且矛盾非常尖銳。新韻作手覺得古韻缺乏靈動之美,古韻作手認為新韻作品沒有古雅之味。其實,以用韻來判斷一首詩詞作品的質量高低是極為可笑的,也是很不科學的。用什么樣的韻,是決定不了詩詞的質量的。有的人用平水韻創作,寫出來的作品一樣沒有高古之味,同樣是叫囂味十足;而有的人用新韻創作,同樣能寫出高雅之作來。從中說明了決定詩詞質量的不是用韻問題,而是語言運用能力。因此,用什么樣的韻全憑個人習慣,是沒有爭執的必要的,雙軌并行,各行其道,兩不相干,只要能達到最終表意的目的就行了,所謂“殊途同歸”是也。
3.新舊詩的“相輕現象”是詩詞發展的“絆腳石”
新詩作者和古體詩作者在當代詩壇中亦是相互排斥的,主要源于不同的語言觀。新詩作者覺得古體詩是“戴著鐐銬跳舞”,自由度不夠;古體詩作者認為新詩作者膚淺通俗,詩語美感不夠。當然,不同形式的詩體出現語言分歧是很正常的,問題是出現排斥、抵觸的現象就不夠正常了。這樣的認識觀對兩種詩體的發展都不利。
4.“泥古”與“創新”的極端表現
有的當代詩人為追求古典詩詞的“古雅”,喜歡模仿古人詩詞,謂之“泥古”派,這種類型的作品為模仿而模仿,缺乏真情實感,容易走進“無病呻吟”之死胡同,如東施效顰。即便模仿的語言像極了古詩詞,也終歸是“仿制品”,是難以打動人心的。反之,有的當代詩人為“標新立異”而與眾不同,語言多有“創新”,過于“尖新”,失之“浮滑”,甚至發展到“不知所云”。這兩種語言追求均是沒有正確認識詩詞語言的本質,即語言是為思想情感服務的載體。“泥古派”向過去看齊,“尖新派”一味追求語言的“新奇”,過度“求巧”,以至于都走向了極端,陷入“認識悖論”的誤區。所以,只有認識詩詞語言的基本特征,才不會走進詩詞語言運用的誤區。
二、認識詩詞語言的特性是提高詩詞質量的前提條件
不同文體的語言特性是不一樣的,不能混為一體。《詩人玉屑》卷六中曾提到王安石說的“詩家語”,說明詩歌有自身的語言要求。筆者認為,詩詞作為文學藝術的頂尖藝術,對語言的要求更高。然而,至今還有不少詩詞創作者對詩詞語言的特性認識不夠,導致作品讀來寡淡無味,甚至寫了幾十年的詩詞,依然在詩詞門外徘徊而毫不自知。只有從根本上扭轉這種認識觀,真正了解詩詞語言的特點并有意識地去改變已有的用語習慣,才有可能提高詩詞水平。當然,社會在進步,人們的用語習慣也在不斷變化,同是詩詞體裁,不同時代的詩詞語言亦有所不同,但其基本特性是不會隨意改變的,現就古典詩詞語言的基本特點做一分析:
1.筆墨凝練
中國古典詩詞常常以精煉的筆墨表達出豐富而龐大的內涵,其篇幅短小,要用緊湊簡練的文筆,進行高度的藝術概括,從而達到記事、詠物、抒懷的目的。從古至今,具有一定詩詞造詣的詩人從不會隨意浪費一個字眼,甚至每一字均有豐富的含義。他們遣詞用字已經達到了“惜墨如金”的程度,往往一首短短的五言絕句就囊括了讓人品之不盡的意味,如王維的《竹里館》:“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其中巧妙的敘事藝術、空靈的寫景技巧、豐富的內心世界均蘊含在這二十字的仄韻詩當中。又如虞世南的詠物詩《蟬》:“垂緌飲清露,流響出疏桐。居高聲自遠,非是藉秋風。”比興寄托,可謂虞世南“夫子自道”也,其中“垂緌”“清”“流響”“疏”等字詞的運用皆是意義深遠,轉結更是將深刻的為人哲理通過十個字傳達得巧妙非常,是為千古佳作。再如李商隱的《樂游原》:“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簡短的五絕包含了巨大的涵義:反映了作者的傷感情緒——家國之悲,身世之感,古今之情,人天之思,錯綜交織,所悵萬千,殆難名狀。后兩句將時代沒落之感,家國沉淪之痛,身世遲暮之悲,一起熔鑄于黃昏夕照下的景物畫面中。詩人李商隱透過當時唐帝國的短暫繁榮,預見到社會的嚴重危機,而借此抒發內心的無奈感受。這兩句詩所蘊含的博大而精深的哲理意味,被后世廣泛引用,并且借用到人類社會的各個方面;也引申、升華甚至反其意而為之,變消極為積極,化腐朽為神奇,產生全新的意義。因此它具有極高的美學價值和思想價值。
魯迅說過,寫詩詞主要在于煉字煉詞,一首詩詞的精妙之處往往在于一個傳神的字詞,賈島的“推敲”之典即是明證。王安石的《泊船瓜洲》“綠”字的使動用法,易十余字,方定下“綠”字,足見煉字的前提是首先煉意。所以,在古典詩歌創作中,切忌散文化的語言傾向,要善于運用白描手法,粗線勾勒,使詩語更加精煉,留給讀者更大的想象空間,詩味即出。
2.形象生動
形象生動是詩詞語言的重要特征,緣于比喻、擬人、夸張、通感、移情等藝術手法的運用,詩詞語言才具有無限的想象張力,筆下的事物形象也更加飽滿、渾圓,栩栩如生,充滿立體感。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中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把白雪比作梨花;李煜的《虞美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東流春水寫愁緒;李賀的《馬詩》“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鉤”的雙喻;賀知章的《詠柳》“不知細葉誰裁出,二月春風似剪刀”等等名句均采用了比喻的修辭手法,語言極富形象性,給人想象,故流傳千古。同樣,讓人耳熟能詳的李白諸多詩句大都采用了夸張的藝術手法,那種想落天外的氣勢難有人及,從而充滿了浪漫主義色彩的獨特魅力。通感、移情更是詩詞中常見的藝術手法,將人物與事物巧妙融合,情意相通,感覺相連,產生了意想不到的表達效果。可以說,使用通感手法的詩句即為“詩家語”,否則難以言詩也。通感的運用突破了語言的局限,豐富表情達意的審美情趣,起到增強文采的藝術效果,故使詩語更加形象生動而有趣。所以,在詩詞創作中要有意識地運用各種藝術手法,使詩語富有活力。
3.表達含蓄
好詩如茶,不是白開水,讓人一眼見底。含蓄的詩語正如茶之裊裊余香,讓人品之不盡。當代詩詞創作中,有太多淺露直白的作品,讀來味同嚼蠟。究其原因,均是不明“詩貴含蓄”之理,即使明白,然不善以含蓄法表達。如晚唐著名詩人溫庭筠的五律《商山早行》描寫了旅途寒冷凄清的早行景色,字里行間流露出游子在外的孤寂之情和濃濃的思鄉之意。整首詩雖然沒有出現一個“早”字,但是通過霜、茅店、雞聲、人跡、板橋、月這六個意象,把初春山村黎明特有的景色細膩而又精致地描繪出來,尤其是詩的頷聯“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用感情的紅線穿起了一串名詞之珠,為我們構成了一幅別具情彩的早行圖。前人評論“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一聯為“意象具足,始為難得”。這兩句詩用十個名詞構成,每字一個物象,合起來有無窮意蘊。這十個名詞所表現的都是具有特征性的景物,都表現出“早行”之“早”;寫早行的情景,繪聲繪色,如在目前。元代馬致遠的《天凈沙·秋思》中有“枯藤老樹昏鴉,小橋流水人家,古道西風瘦馬”的名句以九種景物并置,言簡而意豐,抒發了一個飄零天涯的游子在秋天思念故鄉、倦于漂泊的凄苦之情,亦是“列錦”法的運用。這種意象疊加的方法不僅使詩語凝練簡潔,而且表達含蓄入味。一切景語皆情語,故而內心的情感無需直接道出,借物抒情即是最佳的表達方式。
4.節奏鮮明
詩詞的節奏和語句的結構是有密切關系的。一般說來,詩詞的一般節奏,也就是律句的節奏,五字句分為二三,七字句分為四三,這是符合大多數情況的。但是,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的一致性也不能絕對化,有些特殊情況是不能用這個方式來概括的,比如折腰句按語法結構是“三一三”,如陸游的“一點烽傳散關信,兩行雁帶杜陵秋”。如果按兩分法,也只能分為上三下四,而不能分為上四下三。
詞在節奏上有它的特點,那就是非律句的節奏。有些五字句為一字豆加四字句,特別是后面跟著對仗,四字句的性質更為明顯;有的五字句也可以是上三下二。四字句也可以是一字豆加三字句;七字句也可以是上三下四;八字句往往是上三下五;九字句往往是上三下六,或上四下五;十一字句往往是上五下六,或上四下七。
一般說來,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的一致是常例,不一致是變例。當節奏單位和語法結構發生矛盾的時候,矛盾的主要方面是語法結構,所以歸根到底,還是語言安排運用的問題。只有合理運用詩語,才能寫出節奏鮮明的詩詞。
從藝術手法上說,互文、頂針等修辭手法的運用也大大增強了詩詞語言的節奏感。如杜牧《泊秦淮》“煙籠寒水月籠沙”和王昌齡《出塞》“秦時明月漢時關”的單句互文;《木蘭詩》“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當窗理云鬢,對鏡帖花黃”“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的對句互文;《木蘭詩》“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的排句互文。李白送劉十六歸山的《白云歌送劉十六歸山》就采用了頂針手法:“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處處長隨君。長隨君,君入楚山里,云亦隨君渡湘水。湘水上,女蘿衣,白云堪臥君早歸。”讀來朗朗上口,節奏分明。
5.音韻和諧
在創建格律體時,聞一多提出了具體的主張,就是三美:詩的實力不獨包括著音樂的美,繪畫的美,并且還有建筑的美。音樂美是指詩歌從聽覺方面來說表現的美,包括節奏、平仄、重音、押韻、停頓等各方面的美,要求和諧,符合詩人的情緒,流暢而不拗口——這一點不包括為特殊效果而運用聲音。如上所述,詩詞的節奏僅是構成音樂美的一個因素。古典詩詞其實就是一門音樂藝術,王維的詩歌造詣高與他精通音律、繪畫極有關系;溫庭筠、李清照這些詞家亦是對音律頗有研究的。所以,音韻和諧是詩詞之美的基本元素,這就要求我們一定要重視語言的調用。只有掌握好語言的音韻,才能創作出音韻和諧的詩詞作品。
三、挖掘詩詞語言潛能是成就高質量詩詞的重要方法
語言的資源是無限的,因為會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更新。只有善于挖掘詩詞語言的潛能,才能使詩詞更好地表現社會生活,才能提高詩詞質量。筆者認為可從以下五方面挖掘詩詞的語言潛能:
1.傳承古典詩詞中富有生命力的語言,注入時代生活元素
古典詩詞中能夠沿襲至今的語言是富有長久生命力的,這樣的語言不存在“過去式”,應該繼續沿用,為當代生活服務;反之,有的生僻少用或者已經不用的語言已經“奄奄一息”,于今不具備表現力了,這樣的語言完全可以淘汰,以減輕語言負荷。傳承古典詩詞的經典語言,當以注入時代生活為要,有的因時因地而改變了原有含義的詩語更是豐富,應充分發掘并注意使用。
2.提煉時語,豐富詩詞內容
社會生活的方式不同,語言的表達方式亦有所不同;社會的發展必然催生出新事物,新事物必然催生出新詞語;時代生活的新內容亦會產生相應的語言,謂之“時語”。以時語去表現當代生活是當代詩詞的一個特征,但有的時語入詩,會破壞古典詩詞的“大雅”,所以,時語入詩,一要注意選擇,二要注意提煉。要選擇適合的時語入詩,并加以提煉,使之更加藝術化,從而更好地反映當代生活。
3.融入新詩語言,增加古典詩詞的空靈之味
新詩和古體詩同屬于詩歌體裁,在語言要求上有相似之處,新詩語言同樣具有精煉、含蓄、新穎的特點。新詩也講究煉字,尤其是動詞和形容詞的錘煉,正如“你裝飾了別人的夢”的“裝飾”之于全詩;王安石的“春風又綠江南岸”的“綠”之于全詩。一個“詩眼”,全詩增輝。詩語的新穎是“人人心中有,個個筆下無”的語言材料,通過詞語翻新和意象翻新可以達到用語新穎的目的。新詩、古體詩的區別主要在于形式,語言特點是相近的,當相互借鑒。古體詩應融入新詩詩語的靈動,可大大增加詩詞的新鮮感和可讀性。
4.選擇富有美感的行業術語,增強詩詞的趣味性
歷來的古詩詞常會嵌人名、藥名、詞牌名,隨著社會生活內容的不同,尤其是當代社會生活的內容更為豐富多彩,各行各業自有其術語,有的術語還可衍生出豐富的含義。在詩詞創作中,可有效借鑒行業術語,將不同領域且具有美學價值的專業術語表現詩詞內容。還可巧妙利用術語的豐富含義,“跨界”使用,正如“通感”以感覺互通增強語言的表現力一樣,各行業的術語亦可根據需要通用,如科學術語可用于文學領域,醫學術語可表現日常生活等等。有的術語的字面意思可以派生出其他含義,有效借鑒這樣的術語能夠增強詩詞的趣味性。
5.創設社會語言環境,發展詩人的語言個性
個人的生活環境與個性特征是造成個人語言風格的原因。不同時代造就不同的詩人,不同的詩人有著自己的語言風格,即使風格相近,具體的作品呈現出的語言特點亦有所區別。如陶淵明、李煜的平淡質樸。陶淵明的《飲酒》“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表面看來句句平淡,其中卻蘊涵著詩人超脫塵世,悠然自得的情趣。又如李煜的《相見歡》“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于平淡之中見新奇。王維、孟浩然的清新自然。王維的《山居秋暝》“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風格清新淡雅,最能代表其山水田園詩的特色。孟浩然的詩歌清淡簡樸,生活氣息濃厚,如《過故人莊》:“故人具雞黍,邀我至田家。綠樹村邊合,青山郭外斜。開軒面場圃,把酒話桑麻。待到重陽日,還來就菊花。”李賀、李商隱的絢麗飄逸。李賀的詩風絢麗華美,如《李憑箜篌引》中“昆山玉碎鳳凰叫,芙蓉泣露香蘭笑”,以玉碎山崩喻眾弦齊鳴,以鳳凰鳴叫喻一弦獨響,以“芙蓉泣露”摹寫琴聲的悲抑,以“香蘭笑”顯示琴聲的歡快。又如李商隱的《錦瑟》“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以及“昨夜星辰昨夜風”“相見時難別亦難”二首無題詩,詩風于工麗中略帶沉郁,優美而不失厚重。白居易的簡潔明快。其特點是言簡意賅,一語中的,干凈利落。如《大林寺桃花》:“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陸游、李清照的含蓄委婉。陸游《臨安春雨初霽》“小樓一夜聽春雨,深巷明朝賣杏花”,以“小樓”“深巷”點明環境靜謐幽邃,襯托出詩人客居臨安的寂寞,以“春雨”“杏花”點出江南早春的氣息,預告一個萬紫千紅的局面即將到來,這兩句中有春天到來的喜悅,也有流光易逝的感慨。又如李清照的《如夢令》:“昨夜雨疏風驟,濃睡不消殘酒。試問卷簾人,卻道海棠依舊。知否?知否?應是綠肥紅瘦。”詞人惜花,為花悲喜,為花醒醉,實際是含蓄地表達了青春韶光短暫、好花不常的惋惜之情。杜甫、陸游、辛棄疾的沉郁頓挫。他們用一種蒼老遒勁的筆調去描繪廣闊的社會生活,而在所描繪的生活畫面上籠罩著凝重深沉的憂郁色彩和悲劇氣氛,配之以嚴格的詩律和鏗鏘的音韻。杜甫之詩,為沉郁之極致。陳子昂的悲壯慷慨。他的《登幽州臺歌》是最激動人心的悲慨之詩。劉邦、項羽、曹操、王昌齡、王之渙的雄渾壯麗,力的至大至剛,氣的渾厚磅礴。李白、蘇軾的豪放曠達。李白是豪放風格之集大成者——情感激蕩,格調昂揚,想象奇特,夸張出格。“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將進酒》)氣勢浩蕩,一瀉千里。蘇軾的詞除了豪放外,更多的是曠達的詞風。曠達即疏狂不羈,通脫豁達,高潔特立。有雄才大略而又懷才不遇的蘇軾,既要堅持不茍合隨俗,又要隨緣自適;既要“盡人事”,又要“知天命”,使其性格中帶有典型的“曠達”的特征。“人生如夢,一尊還酹江月”(《念奴嬌·赤壁懷古》)、“老夫聊發少年狂”(《江城子·密州出獵》)這樣的詩句,就帶有明顯的曠達的色彩。
隨著社會的發展,詩詞的語言機制也面臨著改革,更需要當代詩人適應社會,發展語言個性。確確實實,有的詩人在這方面也做了一些嘗試,但嘗試的效果有待時間進行檢驗。
綜上所述,在紛繁變化的社會生活中,在龐大豐富的語言系統中,我們只有善于挖掘表現社會生活的語言,使之藝術化,才能更好地為詩詞主題服務,才能表現日新月異的當代生活,才能創作出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的詩詞作品,從而有效地傳承并發揚中華詩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