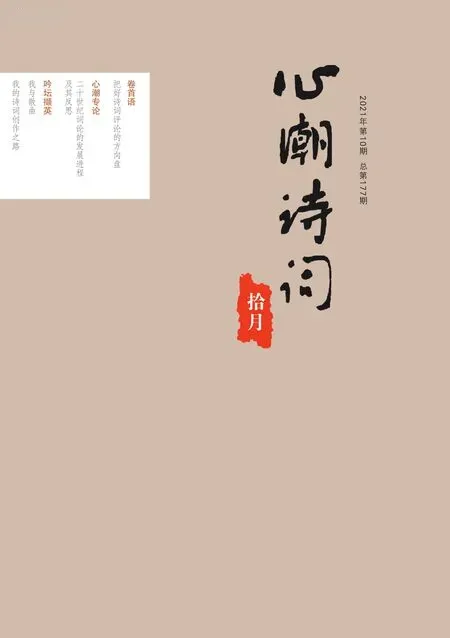中國文學傳統復興的時代之問
宋湘綺
在2019、2020連續兩年召開的“全國詩歌座談會”上,舊體詩歌的創作和研究者人數占比上升,達到四分之一。世紀之交新、舊對立的僵局開始被打破。2020年8月《中華辭賦》歸口《詩刊》社,標志著新世紀詩體多元并存的局面已形成。
文學是時代文化土壤上最美的花朵,文學傳統復興是文化創新的突破點和著力點。當詩詞創作蓬勃復蘇時,需要詩詞批評、理論與創作形成有效互動,才可能使復蘇走向復興。在現行學科體制下,舊體文學和新文學涇渭分明。那么,五四運動后邊緣化的詩詞復蘇后,應當何去何從?今天,我們該如何評價舊體詩歌?
一、舊體詩歌的形式之義
文學不是僅僅停留在對經驗世界中人、事、歷史的情感描摹,而是創造,以創造拓展人的精神性和可能性。我們對中國文學傳統的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更多建立在形而上的層面,以舊體文學的形式創造、豐富人性,不斷開拓人的境界,以境界影響世界。當下,我們對舊體文學形式意義的重視遠遠不夠。一切藝術都離不開節奏,舊體文學的形式原則直接規定了一個相對穩定而又開放的創意框,便于表達我們不同的情感、情思、情緒。比如,正是因為對聯創作的形式要求,才形成了上下聯之間的對稱和思想張力,遙相呼應的結構表達了任意兩句難以表達的豐富想象;詩詞的平仄、韻腳、相粘等規定都便于調動創作思維,從而抵達創作目標。有經驗的詩人說,舊體詩的格律要求開始是束縛,熟練以后是召喚,喚起語言的覺悟,把悟到的“意”牽引出來。詩詞創新絕不是“舊瓶裝新酒”這么簡單,這種說法是內容、形式的二分法,是典型的認識論思維。每次創作都是“瓶”和“酒”的相互召喚,是感性和理性的無數次碰撞,是對“瓶”和“酒”的全新創造,絕不是“套格式”。這是當前文學創新迫切需要的創造論文學價值觀,也是舊體文學情感表現論拘泥于經驗世界的局限所在。
二、新、舊詩歌的質變
文學性從本質上體現為對人類命運的深深悲憫和改造現實局限的超越性精神力量,以無用之大用的方式影響人的精神世界。從《詩經》到唐詩、宋詞、元曲都與當時經濟狀況、物質基礎、政治氣候和文化生態密切相關。我國詩歌在這一漫長的發展過程中不僅積累了豐富的藝術經驗(如比興的手法),創立了成熟的藝術形式(從四言到五言到七言,從古體詩到格律詩),而且在創造思想上也形成了深厚的現實主義傳統,如杜甫提出的“別裁偽體親風雅”,白居易提出的“非求宮律高,不務文字奇,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等創作主張,都與《詩經》和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一脈相承。賦比興是中國詩歌的主要創作方法,以寫實為基本特征。當代詩詞可以寫實,但不能拘泥于寫實傳統。文學的發展需要百花齊放,現實主義、現代主義,甚至更多“主義”爭奇斗艷,才有萬紫千紅詩詞之春。“主義”是一種理論、思想、方法,往往誕生在現有經驗解釋不了的現實困境中,都是為解釋、解決新問題而創造的話語體系。比如,現代主義是人類精神的一個轉折點,舊體文學發展到今天和所有藝術一樣,都要面臨現代人的生存處境,毫無例外與當代文學共同面對現代主義、乃至后現代主義語境。一切文學本質上都是人的自我認識,認識自我,歸根到底是為了創造理想自我,舊體文學只有和當代文學共同走向形而上,走向超越,走向虛構和創造,才能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當代性”,塑造出唐詩宋詞中未曾出現的“理想自我”,這樣才能創造出新時代的“新人”。
三、詩歌的無用之大用
現實主義和現代主義詩詞并存的歷史事實,恰好說明當前正是詩詞古今演進的過渡期。從創造論文學價值觀看,現實主義、乃至批判現實主義詩詞都是來自經驗世界的、面向行為的書寫,缺乏更具有現代人創造性和想象力的、凝視人性深淵的、面向行為動機的審視。
以《抒懷》和《沁園春·塞罕壩精神贊》為例,對比一首新詩和一首當代詩詞,或可體會現代主義“無中生有”的創造性與現實主義書寫。兩首均有意境,仔細品讀,可以察覺其中的不同之處。
抒 懷
李少君
樹下,我們談起各自的理想
你說你要為山立傳,為水寫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寫真集
畫一幅窗口的風景畫
(間以一兩聲鳥鳴)
以及一幀家中小女的素描
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樹下為山水寫史立傳,還是拍一套云的寫真集?《抒懷》中的分歧是兩種價值選擇的分歧。前者是常人的“規格”,后者是詩人的“高格”。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詩性是突破有限、向往無限的一種超越性,追求人的可能性和人類共同的精神性。他不再是行吟傳統的現實主義寫法,而是“無中生有”的創造;他不是體驗過去,而是超越現實、創造未來。超越的沖動如此強烈,激活現實渴望和似曾相識的記憶,沒有女兒的詩人在詩中創造了一個“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樹下的女兒”——神秘、永恒、純潔、空靈,象征著包容萬物的時間,讓一切存在成為可能。
沁園春·塞罕壩精神贊
黃炎清
一面紅旗,三代青年,百里翠屏。正鷹翔壩上,清溪束練,云浮嶺表,林海濤聲。北拒沙流,西連太岳,拱衛京津百萬兵。凝眸處、邈蒼煙一抹,綠色長城。 曾經歲月崢嶸。況覽鏡衰顏白發生。憶荒原拓路,黃塵蔽日,禽遷獸遁,石走沙鳴。滄海桑田,人間奇跡,山水云霞無限情。春來也、聽奔雷擊鼓,布谷催耕。
該詞創造了一個藝術疆界,有意境,但與《抒懷》所引發的無限宇宙、歷史、人生感懷相比,則顯得稍欠火候。
王國維所說的境界,包含疆界、意境、境外之境三層意涵。
第一層,境界是疆界。《沁園春·塞罕壩精神贊》中“紅旗”“翠屏”“清溪”“林海”一系列意象展現了塞罕壩“邈蒼煙一抹,綠色長城”的盛景。現實的塞罕壩,被《沁園春》這個詞牌所規定的字數、平仄、韻腳攝入藝術時空,并與往日荒原、黃塵、石走、沙鳴形成巨大反差,構成了特定的疆界。
第二層,境界是意境,意境由人、事、時、空構成。其中,意義由人、事構成。“北拒沙流,西連太岳,拱衛京津百萬兵”,黃塵蔽日,磨老少年,“衰顏白發”。這就是“一面紅旗,三代青年”創造“百里翠屏”的意義。而境由時、空構成,一首小詞書寫三代人崢嶸歲月的時間變遷,開辟出一個“滄海桑田,人間奇跡”的廣袤空間,在這書寫出的時、空中承載了前所未有的塞罕壩精神,“山水云霞無限情”,令人神往。
第三層,境界是境外之境,在形上。王國維說“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于理想”,強調意境不可或缺的現實根基和理想之維。《沁園春·塞罕壩精神贊》有扎實的現實根基和理想情懷,既有從“鷹翔壩上,清溪束練”的現實場面,也有“春來也、聽奔雷擊鼓,布谷催耕”的希望,用意象展現了三代人的開拓精神,情景交融,意境鮮活。
然而“意境有深淺之別”,深,指一流作品不僅有意境,還有境外之境。從境內到境外,從形下到形上,該作還有更上層樓的可能性。好詩要“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從一己感受,寫到普遍感受。從塞罕壩三代人思及“天、地、人”的命運和關系,使用涉及的意象營造意境,其實質是從自我到自然,虛實相生,以致無窮。從有限到無限,抵達人類的精神家園——自由。
換言之,“奔雷擊鼓,布谷催耕”在境內;“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樹下的女兒”在境外。又比如,李煜寫雕欄玉砌的故國繁華是境內,寫春花秋月的往事生生不息,而充滿希望,由此發出“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的悲憫、慨嘆,慰藉人類千秋萬代的憂愁,則抵達境外,被王國維稱為“人類喉舌”。
從認識自我、社會、世界,到建構更美好的自我、社會、世界;從表現現實生活,到創造美好境界,正是傳統詩詞到當代詩詞的觀念的轉折點。這也是舊體文學參加文化創新的起點,通過境界影響世界的過程,正是馬克思所說的精神生產。詩詞行吟傳統中“行”和“吟”不可分,前者是物質生產,后者是關乎意義、價值、夢想的精神生產。馬克思的墓志銘上寫著:歷史上的哲學家總是千方百計以各種各樣的方式解釋世界,然而更重要的在于改造世界。實踐論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精華,馬克思所說的實踐包含物質生產、精神生產等一切社會活動。這使我們更深刻地反思抒情言志這樣的精神生產對物質生產的作用,以及物質生產對境界、意境的影響。常言道“功夫在詩外”,就是指詩歌的意境來自人生實踐的磨礪。馬克思的精神生產觀對于我們把詩詞創造活動與當前文化創新聯系起來有重要的理論指導作用。
文化、文學、文體、詩體的演進是緩慢的,人的生命相對這個漫長的過程只是短暫的一瞬。生命有限,而藝術、學術無限。把有限的學術生命與中國文學傳統復興這樣的時代命題聯系起來,像水滴融入大海,才能奔騰不息。傳統中有民族心魂的種子,文學傳統復興要善于發現種子里更多的可能性,并在時代氣血的作用下,培育時代之“花”,綻放出前所未有的“當代性”。文學是人性之學,文學傳統的現代轉換,實質是“人”的現代轉換,需要把傳統中更多尚未發現的可能性挖掘出來,培育創造性人格,形成守正開新的民族氣質,塑造出創造新時代的“新人”。今天我們提出“創造論文學價值觀”,就是把中國文學傳統的復興的時代命題落實到詩的“創造”上,落實到“境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