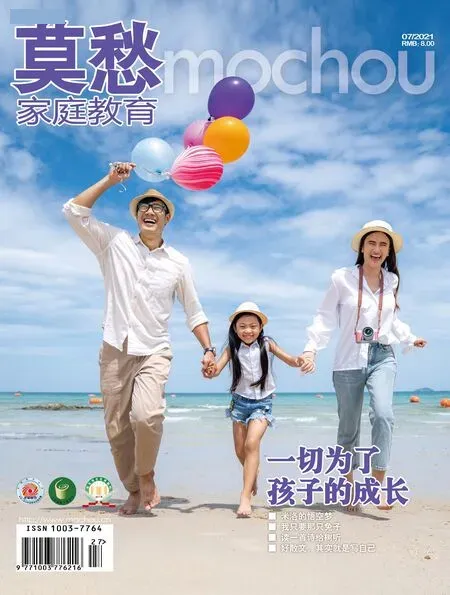好散文,其實(shí)就是寫自己
?蔡明
后現(xiàn)代主義者德里達(dá)有個(gè)著名的觀點(diǎn):“文本之外,別無他物。”這是在說人類的認(rèn)知,對前人經(jīng)驗(yàn)、智慧的接受,對往昔的認(rèn)識和把握。而我想說,散文是“誠心之外,別無他物”的文體。散文的寫作也是如此。
誠心,是真實(shí)的心,真誠的心,充滿著大愛的心。對學(xué)習(xí)寫作的人來說,過不了散文這一關(guān),再想拓展詩歌、小說之類,那是比較困難的。雖然朱光潛先生說,要養(yǎng)成純正的文學(xué)趣味,最好從讀詩入手。
相對于寫詩來說,寫散文就容易多了。因?yàn)樯⑽氖亲顬樽杂伞㈦S意的一種寫作。可以敘事,可以抒情,可以議論。正如作家曉雪所言:“我喜歡散文,就在于它的隨意性和多樣性,就在于它是一種沒有固定格式的最自由自在的文體。”
怎樣才能寫出一篇好散文,這是同學(xué)們最關(guān)心的問題。
我們從許多寫作教科書上收獲的一定是“形散神聚”。
對于這樣的總結(jié),我沒有懷疑過。畢竟,從散文寫作教學(xué)的角度出發(fā),這還是比較易于指導(dǎo)的。但即使這樣去欣賞,去指導(dǎo),還是有很多同學(xué)寫不好散文。
我以為,散文是一個(gè)非常自我的寫作,愛、美和文化是優(yōu)秀散文的最本質(zhì)的特征。無論筆下所寫的是什么人、事、物、景,一定要用最恰如其分的優(yōu)美語言,把寫作者自己的愛融入進(jìn)去,自己的感受、體驗(yàn)、情感、審美、文化、修養(yǎng)和思想滲透其中,讓字里行間始終閃動著語言優(yōu)美、生命美好和人生意義。讀者閱讀你的散文,是與美的語言對話,與作者筆下的人物、景物、故事、場景交流,更是經(jīng)由文本與作者進(jìn)行生活的、工作的、成長的、生命的傾訴與碰撞,不斷產(chǎn)生知識、文化、情感、靈魂的共鳴,形成審美的體驗(yàn),收獲知識、見識、智慧和精神的富足。這才是一篇好的散文,這才是散文寫作應(yīng)該有的姿態(tài)和追求。
我以為《東風(fēng)》就是我們學(xué)習(xí)散文寫作的一個(gè)樣本。(編者注:《東風(fēng)》刊于《莫愁·小作家》2021年3期,作者韓麗晴。)
起筆三個(gè)自然段,就有美不勝收的快感。
首段,第一句,“東風(fēng)一吹,串場河的水由北向南,流得更歡暢了,與天上輕盈滑行的燕子們呼應(yīng),形成高高低低的音符。”剛一亮相,就美得驚艷。水在歡暢地由北向南,燕在天上輕盈滑翔,高高低低,悠悠揚(yáng)揚(yáng),視覺的、聽覺的、感覺的、動態(tài)的美在東風(fēng)吹拂下生機(jī)盎然,自然天成。朱自清筆下的“東風(fēng)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似乎也在這里。
“泥融飛新燕,水暖層冰化。大地,醒了。”詩一般的語句,顯示了長句與短句、散句與整句的巧妙配搭,更是對這幅自然美景的詩化、凝練和畫龍點(diǎn)睛。東風(fēng)拂來,串場河水,暖了;冰,化了;燕子,唱了;大地,醒了,一切都活了。一幅嶄新的、詩意的、流動的春醒圖,美得讓你心曠神怡。
緊接著第二、三自然段,是串場河畔別具風(fēng)情的捕魚、食魚的農(nóng)家樂。男將們“網(wǎng)開一面”的捕魚情景,飄著蔥香的魚湯,手里捧著米粒亮眼菜飯的孩子,喜鵲喳喳叫,黃狗尾巴搖,萬物歡欣的畫面,不由得你不口齒生津,耳熱心跳。那習(xí)俗,那情調(diào),那氛圍,撩人的喜悅,誘人的滋味,好一幅愜意的村民幸福生活圖。
這樣的美麗場景,美得讓人頓生嫉妒。而這一切,只是為主人公的登場精心布置的生活背景而已。真正讓你美得心旌搖蕩的是站在這一背景中央的主人公。
她叫仁英。“仁英”在接下來的800余字里,出現(xiàn)了14次,算上人稱代詞“她”和“自己”等,有20次之多。平均40字,“仁英”就要出場一次。而每次出現(xiàn),總是那么自然、不經(jīng)意,又是那么恰到好處。非對“仁英”的喜愛入之骨髓,決不會時(shí)刻掛在嘴邊。這種喜愛滿溢在敘說之中,感染和影響著讀者,仁英的名字和形象不知不覺中烙印在讀者的靈魂深處。
何以如此呢?
其容不改,行止有章。歐陽修《左氏辨》中說:“君子之修身也,內(nèi)正其心,外正其容。”文中的仁英,心正,正到?jīng)]有一點(diǎn)抱怨,無論生活如何,她都安靜地過好;心純,純到從沒有一點(diǎn)私心雜念,無論“女紅”在市場上多么暢銷,也從不坐地起價(jià);心靜,靜到一輩子做好一件事,日復(fù)一日,年復(fù)一年,做女紅,安安靜靜地做女紅。因?yàn)樗小澳枪尚膭拧薄?/p>
“那股心勁”,無論在桃花樹下的串場河邊,還是在豪華大都市的黃浦江畔,“莫不靜好”;她手中鉤出的衣衫,能把自己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更能讓世上萬千女性穿出“不同的好看來”。“那股心勁”,無論何時(shí),剛剛中學(xué)畢業(yè)的日子里也好,去往上海的三十年中也罷,她始終“勤扒苦做”“活得好看”。作者的總結(jié)很有味道,“那股心勁”,源于“東方女子柔韌溫婉的品性”,這是世代相傳的中華女性的優(yōu)良美德。
其實(shí),讀完文章最后一段,你會發(fā)現(xiàn),“那股心勁”之所以能夠生機(jī)勃發(fā),如此美麗,正是因?yàn)橛辛恕皷|風(fēng)吹拂”。何止是仁英,整個(gè)村子已經(jīng)走上了致富的康莊大道。由此,我們便會發(fā)現(xiàn),“東風(fēng)”二字作題,真乃神來之筆。
等閑識得東風(fēng)面,萬紫千紅總是春。自然的東風(fēng)如此,政策的東風(fēng),社會的東風(fēng),改革的東風(fēng),奔小康的東風(fēng),中國夢的東風(fēng),無不如此。如此獨(dú)運(yùn)之匠心,都在結(jié)尾處的寥寥數(shù)語之中:“東風(fēng),木風(fēng)也,吹開樹木百草,驚醒鳥獸魚蟲。有風(fēng)拂來,無論種子、無論桃花,也無論落在何處,如同世間女子,靠著那股心勁,始終是其容不改,莫不靜好。”
這就是散文,這就是韓麗晴的散文。自然隨性,簡樸清靈,敘述干練,細(xì)節(jié)生動,行文優(yōu)雅,內(nèi)蘊(yùn)豐厚,富有張力。《東風(fēng)》富有強(qiáng)大的召喚力,能夠滿足任何一個(gè)有品味讀者的審美期待。作者把自己的愛給了筆下的每一個(gè)文字,給了串場河,給了仁英,給了東風(fēng)。作者也把愛給予了每一位能夠參與二度創(chuàng)作的讀者,相信有讀者介入的仁英會更美,作品會更美,會發(fā)現(xiàn)與仁英形影相隨的秀外慧中。
仁英,這是中國文化滋養(yǎng)下的仁英,亦如這篇散文一樣,處處散發(fā)著中國文化的芳香。“仁”是中國文化之精髓,是儒家思想之核心。仁人君子,仁者愛人。“英”呢?《桃花源記》中的“芳草鮮美,落英繽紛”,那是多么迷人的美景。“桃花落在肩上,落在茶盅里”,落在安安靜靜地坐在桃樹下挑著鉤針鉤著衣帽的仁英,陶公筆下的世外桃源在東風(fēng)吹拂的串場河畔成為現(xiàn)實(shí)!亦如作者文末轉(zhuǎn)述之《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shí)者謂之秀,榮而不實(shí)者謂之英。”于草本而言,開花已讓人驚喜;而于普通人而言,只問開花,以美示人,而不問結(jié)果,這又是何等的風(fēng)韻呢?更何況“英”在中國文化中,早有隱喻,才能智慧過人者謂之英!“仁英”,人中精英。是啊,“大包的口罩寄給鄉(xiāng)下的養(yǎng)老院”,找資料、想辦法,幫助家鄉(xiāng)搬遷化工廠,這是何等的境界與格局啊!“投她以東風(fēng),她必報(bào)之以明亮美盛。此乃東方女子柔韌溫婉的品性。”仁英身上有作者欽羨的美德,溫文爾雅,有大愛,有大美!
提及文化,不得不說,這是散文寫作的魅力之所在,也是寫好散文的功力之所在。《東風(fēng)》不只給我們描繪了串場河畔的風(fēng)光,給我們塑造了柔韌溫婉品質(zhì)的仁英形象,歌頌了改革東風(fēng)帶來的欣欣向榮的新氣象,還給讀者豐富的文化滋養(yǎng),什么是網(wǎng)開一面,什么是康莊大道,什么是行步走奔,什么是東風(fēng)秀英,什么是投桃報(bào)李等等。而更為讓人驚嘆的是,這些文化的介入是那么的自然契合,渾然天成。一方面,文化隨文思共進(jìn),無突兀違和之感;另一方面,文路因文化的出現(xiàn)自然榫接,文旨又因文化的滲透巧妙升華。記不得是誰說過的一句話,好的散文,不只是給人美,給人愛,也會給你知識和精神的分享。但記得黃庭堅(jiān)曾經(jīng)說過:“取古人之陳言入于翰墨,如靈丹一粒,點(diǎn)鐵成金也。”我以為,這里的“陳言”一定是優(yōu)秀的中華文化。
散文不是小說,不靠故事情節(jié)的推動,只有生活長河中的一朵朵浪花,而正是這些始終撥動心弦的點(diǎn)點(diǎn)滴滴、零零星星而又美不勝收的筆墨,愛和文化,不經(jīng)意中給我們塑造了一個(gè)名叫“仁英”的來自串場河畔的女性形象。
感謝東風(fēng),致敬仁英,更要向作者學(xué)習(xí)。好散文,其實(shí)就是寫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