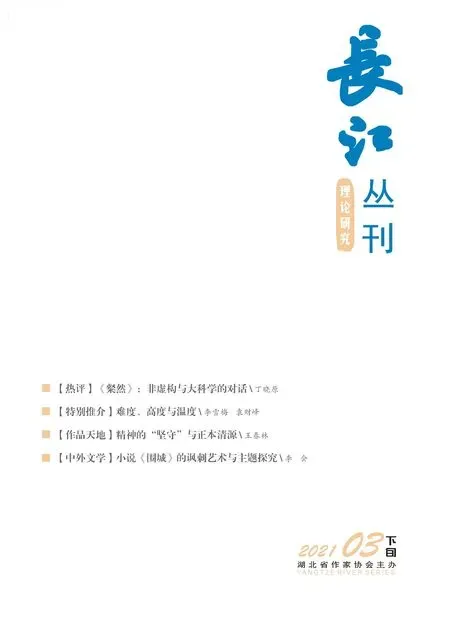打造大國重器的可貴記錄
——葉梅新書《粲然》讀后隨想
■
一
在葉梅的新書《粲然》的封腰上,印著兩行醒目的廣告語:“全景式展示中國第一個大科學裝置北京正負電子對撞機建造始末”。就這兩行字,足以引人注目。
想探究人的起源、地球的起源、宇宙的起源,一直是人類的渴望。從“盤古開天地”“女媧造人”的傳說到“上帝造人”的猜想,都充滿了好奇;而從牛頓關于“神的第一推動力”的感嘆到康德對“位我上者浩渺的星空”的敬畏,也都披露了科學巨人、哲學大師的內心困惑。記得一位著名的天體物理學家曾經指出,迄今為止,人類關于宇宙起源的許多研究都難以圓滿解答那些根本問題。也許,關于宇宙的起源永遠都只能在猜測與探索的軌道上緩慢運行。而人類渴望揭開宇宙之謎的好奇心、求知欲也永無止境。不知要到何年何月!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粲然》一書讀來引人入勝:在“宇宙展開一條條‘隧道’,不斷往前延伸,隨之呈現的秘密變得更加精細和奇異,尋找答案也變得更加復雜和困難”的思想空間里,作者通過廣泛的閱讀、采訪,梳理出從居里夫人到葉企孫、葉銘漢叔侄、袁家騮、吳健雄夫婦,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以及其他許多中國科學家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前赴后繼、薪盡火傳的跋涉足跡。其中,尤其是關于那些為了祖國的科學事業,雖幾經折騰仍無怨無悔,不斷開拓進取的故事,特別令人感動。
時而是政治運動的折騰(從“大躍進”到“文革”),時而是基本建設緊縮的約束,時而還有科學家之間的意見分歧,都使相關研究“七上七下”,可謂曲曲折折、坎坎坷坷。然而,科學家們的求索與追趕的熱情卻不曾熄滅,甚至愈是遭遇了強大的阻力,愈是燃起更強烈的追求欲。書中披露了“十八條好漢”在1972年上書周恩來總理的塵封歷史,就充分表現出科學家對折騰耽誤科研的不滿,體現出憂國憂民的歷史使命感與緊迫感。其中,關于上書人與楊振寧在“預先研究要不要有目標”方面的分歧,以及“排除‘左’右傾思想的干擾”的提法都很有史料價值。這封上書使人不禁想到了1978年,安徽鳳陽小崗村十八位農民以“托孤”的悲壯方式,冒險立下生死狀,毅然在土地承包責任書上按下紅手印,自發開始改革求生的歷史一頁。都是在歷史的歧途,都是十八位好漢,都是自發與極左路線決裂,憑著不甘沉淪、要掌握自己命運的勇氣,創造了歷史。這一頁,因此譜寫出動蕩年代里人們“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新篇章。
我注意到書中不止一次提到1972年:那一年,楊振寧再度回國,李政道也在那一年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受到了周恩來總理的接見,而且都與大陸的科學家共謀發展大計,為中國的科技發展建言獻策。一切僅僅是巧合?其實,從那個年代過來的人都知道,那一年也是非常年代里思想復蘇的一年。因為1971年的林彪事件促成了人們的猛醒并漸漸開始了對政治狂熱的反思,由此重新出發。當年,教育界開始重整旗鼓,悄然恢復了注重提高教學質量的努力(后來被極左思潮攻擊為“修正主義教育路線回潮”),至今為人緬懷;當年,一批文學青年也悄悄開始了“地下文學”的寫作。楊健就在《中國知青文學史》中指出:“在1972年之后,隨著批林整風運動的展開,各地的知青文學沙龍和藝術群落如雨后春筍般破土而出。以知青點為背景,以沙龍為據點,一股現代主義詩歌創作的潛流開始地下涌動”,“白洋淀詩群”就是其中的代表……1972年,因此成為格外值得記住的一年。
由此可見,盡管中國風云多變,前行的道路格外曲折,但總有一種力量在人心中躍動,促使有責任感的人們挺身而出,鐵肩擔道義,有一份熱,發一份光。而且,常常為改變民族的命運作出了始料未及的貢獻。
二
書名“粲然”來自《詩經》。沒錯,是古老的《詩經》。一個高深的物理名詞如何與《詩經》相聯?
“粲夸克”最早來自英文的“charm guark”,意為“魔力夸克”。是中國物理學家王竹溪將其譯成了現在這個名詞,使其與《詩經》中“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的“天問”天衣無縫地聯系在了一起。這有趣的譯名看似得自天啟,其實也有深意。此書中多次點化“物理與哲學”“物理與美術”“物理與文學”的神奇關聯,寫出了科技與人文的相通玄機,正與這些年教育界大力推行的“通識教育”息息相通。
例如關于李政道對藝術的酷愛。他熱衷于與藝術家交往,常常請吳作人、李可染、吳冠中參加高等科技中心的活動,與他們切磋“如何從簡單到復雜”這樣玄妙的話題,從中尋覓想象與創造的玄機。他還喜歡手繪賀年卡給朋友們送上祝福。還有關于美國著名物理學家蓋爾曼興趣廣泛,對文學、歷史、大自然、烹飪都興致勃勃,隨時捕捉創造的靈感,因此才得以能夠借用中國的八卦說成功進行粒子分類,他提出的“八重法”因此轟動了學術界。還有王貽芳與畫家黃永玉的友誼,對黃永玉畫作的欣賞,以及黃永玉對“觸類旁通,藝術和科學都是一個道理”的思考,也都表達了一種“通識”。我因此想到了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從傳教士帶回的中國《周易》中發現八卦可以用他的二進制來解釋的著名佳話。在學科越分越細、人們的思維也變得越來越狹窄的當今之世,從上述科學家打通科學與藝術、哲學的成功努力中,是可以收獲寶貴的啟迪的。不同的學科之間存在著曲徑通幽的小道。只有視野開闊、思維活躍的求索者才有可能在一般人的認識偏見與盲區中洞燭幽微,發現新知。事實上,很多優秀的科幻文學經典(如《海底兩萬里》、《三體》)已經顯示了科技與文學結合的強大魅力。德國詩人歌德寫出過研究色彩理論的《顏色論》,英國哲學家培根也是著名的隨筆作家,美國作家納博科夫在研究蝴蝶方面很有成就,中國詩人郭沫若還是非常睿智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這些也都是文學與科學水乳交融、幽然貫通的成功范例。由此可以使人產生遐想:如何盡可能發展個人的興趣與愛好?怎樣在科學與文學、哲學之間尋找創新的靈感,而不止于坐井觀天、畫地為牢?甚至,即使懂得了此理的玄妙,面對知識的汪洋大海、幽深隧道,如何發現那神秘的通途,仍然有不可測、不確定的因素存在。所以,牛頓才把自己的發現看作幸運的眷顧。
三
由《粲然》,我還想到了徐遲那篇鼎鼎大名的報告文學《哥德巴赫猜想》。那篇寫數學家陳景潤在極其孤獨、困難的條件下攻克世界數學難題的杰作曾經鼓舞起一代人學科學的熱情,也成為當代報告文學的一座里程碑。
文學是人學。說到科學家,雖然都絕頂聰明、刻苦用功、甘于寂寞、書生氣十足,但其實還是有各自不同的個性。如何寫出那個性的獨特與不凡?《哥德巴赫猜想》的成功就在于寫出了陳景潤的孤僻與古怪,以及那個性的可愛、可嘆。“怪人”的形象在文學史上并不少見(如雨果的《巴黎圣母院》中的鐘樓怪人、契訶夫的《套中人》和魯迅的《狂人日記》中的主人公都是),而《哥德巴赫猜想》卻成功揭示了陳景潤癡迷數學的持久。
在這方面,《粲然》也有令人難忘之筆:例如李政道,除了寫出他對藝術的熱愛,還寫了他的固執與堅韌。他為大陸的博士后爭取提高基本費用,在一位領導那里碰了釘子以后仍然堅持,直到在鄧小平接見時再陳己見,得到鄧小平當場同意,這一筆就相當耐人尋味。還有謝家麟,在回國途中受到美國聯邦調查局的阻撓,就想方設法委托朋友代取裝有重要器材的八只箱子,化整為零捎回國內,足見其處世的機警靈活。到了“文革”的政治學習中,他“明里讀文件,暗中卻在交流科研”的往事,也相當典型地寫出了他機敏的個性本色。許多讀書人都是這樣在逆境中讀書、做自己的研究,自得其樂的。還有方守賢,在清貧中很知足,常常加班到半夜,就是一碗方便面作夜宵,連加一個雞蛋也得自己掏腰包。他仍然自得其樂,使人想起當年的顏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的君子遺風。
正因為這些科學家保持了自己難能可貴的個性,才能“八面來風吹不動”,憑著自己的才華去追趕偉大的科學目標。這是一群堅定、樂觀、知足、團結、銳意進取的科學家。《粲然》為他們的豐功偉績留下了寶貴的記錄。由此也想到,這些年,關于世道澆漓、人心不古的議論不脛而走,相應的也就產生了“美德有什么用”、“老實人吃虧”甚至“好人命不長”的牢騷、抱怨與嘆息。一方面,輿論仍然是以宣揚甘于奉獻的先進人物為主旋律,另一方面,各種貪腐案例的層出不窮、各種江湖騙局的花樣翻新都使得人們越來越明哲保身、同時滿腹狐疑。然而還應該看到,這世上仍然不乏“好人有好報”的美談:從許許多多志愿者付出了很多也獲得了贊譽與一些實惠,到科學家越來越受到社會的尊重與嘉獎,從扶貧濟困、捐資助學、救死扶傷、全民抗疫的暖新聞也此起彼伏,擴大了正能量的影響,到盡孝、重義、誠信、尚學的風氣漸漸重回大地……都是“美德并沒有離開”、“美德仍然支撐著我們的生活和信念”的證明。由此看來,像《粲然》這樣的文學作品不僅記錄了一樁重大工程的建設歷程,也通過講述幾代科學家前赴后繼、愚公移山的感人事跡,彰顯了一個民族“自強不息”、和衷共濟、艱苦奮斗、建功立業的民魂和學魂。而且,他們的付出得到了應有的回報。
在談到“兩彈一星”元勛的事跡時,新聞里常常用到“隱姓埋名幾十年”這個詞,令人深深感動。隨著他們的事業終于大功告成,他們的姓名也為人知曉了。盡管如此,還是有許多名氣不如那些元勛的科學家,也做出了不平凡的事業,關于他們的事跡,也應該被時代銘記吧。《粲然》既寫到了楊振寧、李政道、丁肇中這些鼎鼎大名的科學家,也講述了“十八好漢”等數十位科學家的不平凡業績。這樣也就寫出了中國追趕現代化的一個特點:上下齊心,多方聯絡(直至聯合起國際力量),全力以赴,集體攻關,創造奇跡,如同新時代的愚公移山。還有什么比這一條更加令人感動的呢?“兩彈一星”就是這樣創造出來的。電子對撞機也是這么創造出來的。聽多了“一個中國人是條龍,三個中國人是條蟲”的嘆息,也看多了諸如此類的鬧劇,但是,中國仍然不斷創造出齊心協力、成龍騰飛的奇跡。《粲然》就是又一證明。
四
還有一點啟迪。
都說科學如探險。的確如此。在攀登科學高峰的道路上也常常會遭遇歧途。例如書中披露的楊振寧“舌戰群儒”就直接關系到高能物理研究的發展方向;“十八好漢”的上書中談及相關研究“五起五落,方針一直未定”產生的彷徨與郁悶,還有中國的對撞機升級改造以后立刻引領世界先進水平,以至于美國康奈爾大學的加速器竟然失去了存在的意義,美國科學家開始在北京的對撞機上找到新的探索平臺……這些寥寥幾筆的點染都烘托出一個道理:具有遠見卓識不易。能否找準科學發展的遠大前景,尤其是在一時還看不清楚全景的起步時刻,需要遠見,還需要各方面的調查研究、各部門的支持、協調配合。否則,稍有差錯,就可能失之千里。事實上,當年,三門峽工程的失敗就足以令人警醒。在當今的競爭愈演愈烈、淘汰也越來越無情的局勢下,有些學科不知不覺就進退維谷,以至于后繼乏人,也是值得深刻總結的教訓。因此,具有遠見卓識才格外不易。莫道“世上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差之毫厘,謬以千里”的悲劇并不少見。《粲然》寫出了這一點,雖然沒用濃墨重彩,寥寥幾筆,也可以引人深思。有時,偶然真的決定成敗。正所謂:“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杜甫:《秋興八首》),“天意從來高難聞”(張元干:《賀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所謂“憂患意識”,與命運的變幻莫測有關吧。像“天有不測風云,人有旦夕禍福”,“人算不如天算”這些俗語的家喻戶曉,也充分體現出這一點。好的文學作品,應該寫出哲理的底蘊,才具有啟人心智的豁然感。這,也是“人學”的題中應有之意吧。
因此,我覺得這本《粲然》具有多方面的啟迪意義:既是一曲充滿正能量的科學贊歌、英雄頌歌、美德禮贊,也是一部了解關于高能物理研究的教科書,還能夠生發出對于“科學與人生”、“科學與藝術、哲學”之間微妙聯系的思考,給人的教益多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