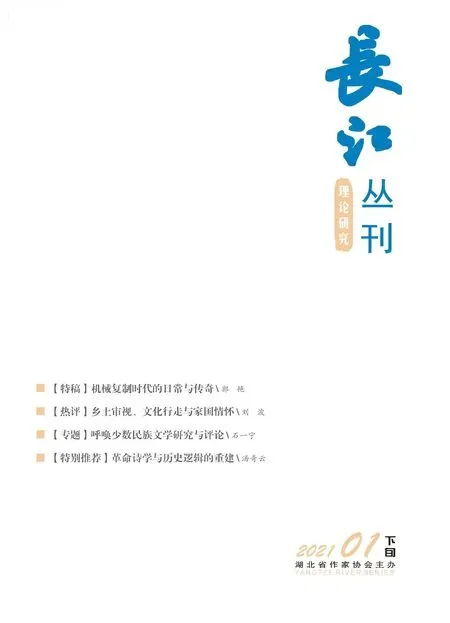論魯迅小說中的農民問題
■王 宇/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
一、農民形象中的“精神勝利法”和“看客式”無聊
“精神勝利法”一詞是魯迅在小說《阿Q正傳》中塑造的阿Q形象,并把這個人的精神勝利法稱為阿Q精神。具體表現為他妄自尊大、自輕自賤、欺弱怕強、麻木健忘等。魯迅在小說中利用長達九章的篇幅塑造了生活在未莊的農民形象,通過阿Q的性格和言行,揭露了辛亥革命前后農民思想中存在的劣根。阿Q是一個落后不覺悟的、帶有精神病態的農民形象,這主要體現在他的階級屬性。
阿Q首先是一個被剝奪得一無所有的貧苦的農民。作品中的阿Q沒有姓名、沒有家庭,也沒有可靠的經濟來源。他希望有所改變,現實卻是趙太爺罵他不配姓趙、和吳媽表白釀成悲劇、好容易有了生計又走向末路、直到后來革命不被允許不說,最后連命都搭上了。造成阿Q貧苦的原因固然有當時的社會背景,但從其思想落后性也可看出阿Q身上具有小生產者的不良習性。魯迅說阿Q“有農民式的質樸,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阿Q是一個不敢正視現實的人,他常常靠“精神勝利法”來麻痹自己。小說二、三章優勝記略中多處描寫他被別人欺負、打敗后在精神上健忘不服輸的舉動,這本令人同情,而從欺負比自己弱小的尼姑一事又可看出他的畏強凌弱。
阿Q還有著“看客”式的無聊。殺頭本來是一件無所謂炫耀的事,而阿Q卻把看到的殺革命黨一幕分享給未莊人說。阿Q的不覺悟主要體現在他對革命的態度和認識上。一開始他認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深惡痛絕。而當他為現實生活所迫,辛亥革命波及到未莊時,他卻簡單因為平時欺負他的趙太爺、錢太爺們害怕革命而走向革命。可他所謂的革命思想卻又是封建傳統觀念的小生產者狹隘保守意識合成的產物。從作者對阿Q的心理描寫“第一個該死的是小D和趙太爺”、“走進去打開箱子來:元寶,洋錢,洋紗衫”可見阿Q落后不覺悟的階級意識。直至最后第九章中被要求畫押、綁縛刑場后都不能一下子明白造成自己悲劇結局的原因。
二、農民形象中的愚昧無知和麻木不仁
魯迅曾講道自己棄醫從文的原因是要喚醒民眾的精神。而在當時國人身上所存在的問題還有國民素質的低下。其具體表現為愚昧無知和麻木不仁。這一點可以在小說《藥》與《風波》中得以體現。
《藥》的創作取材于魯迅自身。他在《我的父親》里用諷刺的筆調抨擊了庸醫誤人,以兩個“名醫”的藥引一個比一個獨特,表現了某些中醫的故作高深,通過他們的相繼借故辭去,體現出父親的病一步步惡化,通過家庭的變故表達了對名醫們庸醫誤人、故弄玄虛、勒索錢財、草菅人命的深切痛恨,在感嘆中讓人體會人生的傷悲。作品通過清末革命者夏瑜慘遭殺害,而他的鮮血卻被愚昧的勞動群眾買去治病的故事,真實地顯示了中國舊民主主義革命的不徹底性和悲劇性。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是華老栓。華老栓是一個迷信、無知、落后而愚昧的農民形象。兒子小栓得了癆病,他雖然表現出了作為一個父親的關心與愛護,但卻不懂得求助于醫生的幫助,而是靠在半夜買沾有革命者鮮血的饅頭為兒子治病。從康大叔的語言描寫“包好,包好!這樣趁熱的吃下。這樣的人血饅頭,什么癆病都包好。”可見農民的愚昧無知不只是華老栓一個人的行為,而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農民普遍具有的通病。根據后文康大叔否認“大清的天下是我們大家的”可以看出生活在舊社會農民階級身上的落后不覺悟思想。
《風波》的背景是1917年張勛復辟時期江南的一個偏僻的農村。小說通過發生在鄉場上的一場因“皇帝又要坐龍庭”而引起的復辟與剪辮風波,揭露了辛亥革命后中國農村的停滯、落后和農民的貧困、愚昧與精神麻木。小說中七斤是一個愚昧落后的農民形象,當他得知皇帝又要坐龍庭后,他首先想到的是“我沒有辮子。”而在趙七爺反復的恐嚇聲中,卻又覺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七斤嫂在打聽到形勢不利于七斤時對他百般斥責,而在風波過去后又和村人一樣對他相當尊敬。作者通過對剪辮風波的描寫,生動地刻畫了農民身上的卑怯和勢利心理以及麻木不仁的性格特征。小說最后寫到雖然風波過去了,但七斤的女兒六斤依然沒有停止纏足的陋習,由此可見辛亥革命的結果并沒有使得廣大農民從思想上徹底擺脫封建文化傳統觀念。
三、農民形象中的思想保守和安于命運
思想保守和安于命運是舊社會農民身上的又一個病根。魯迅在小說《故鄉》中刻畫了閏土這一人物形象,通過對他的動作描寫和語言描寫,寫出了農民身上的思想落后、安于命運。作者以第一人稱“我”為敘事視角,敘述了“我”和閏土小時候的美好童年回憶。然而時隔多年后當“我”再次見到閏土,展現在眼前的卻是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他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有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又粗又笨而且開裂,像是松樹皮了。”根據這段對閏土的相貌描寫可見,他這幾年的生活十分窘迫,農民勞動者生活的貧困清晰可見。而當“我”向他打招呼,他卻現出歡喜和凄涼的神情;動著嘴唇,卻沒有吱聲。然后態度恭敬地叫道“老爺”。一聲“老爺”顯示了閏土深受封建傳統等級思想毒害后的精神麻木,以及在無出路之中把命運寄托于香爐和燭臺的迷信和愚昧。
安于命運這一點在阿Q和閏土身上都可體現出來。首先,阿Q雖說總被人欺負,但精神上的勝利導致了他自輕自賤,這便是一種安于現狀的表現。他沒有想辦法從生活上徹底改變自己,而是靠耍嘴皮子取一時之勝。當他最后被殺的那一刻,沒有強烈地憤恨與反抗,而是稀里糊涂地喊聲“救命”。閏土封建迷信、精神麻木的背后也體現出了他生活上的安于現狀。通過小說中對閏土后來的外貌描寫可見,他后期的生活并不樂觀。然而卻沒有試圖努力改變,而是依然選擇了貧困。當然,思想上的局限也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他的追求進步意識。
四、國民性背后的反思與啟示
魯迅生活的年代正值清末民初,親歷近代以來各種“救亡”運動的魯迅意識到:中國社會之所以積貧積弱,根本原因在人。中國人如果不能走出愚昧,中國社會就不可能真正走向進步,社會危機也不會得到解決。造成中國人愚昧的根源,主要在于中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歷史的封建專制主義國家,專制體制下的封建宗法制度加上儒家傳統思想扼殺了國人正常發展的人性。魯迅在小說中通過農民形象對其大力批判。正是因為封建宗法制度的存在,中國人難以獲得健全人格,難以擺脫愚昧。
既然中國社會的危機根本原因在人,那么在封建宗法制度的桎梏中使得廣大農民群眾的思想得以解放便是需要探討的問題。從魯迅的農民題材小說中還可以看出,他在無情批判民族劣根性的同時,也表現出了對小說人物的同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沒有完整的“人性”意識,中國古典文學對人的認識是以宗法制度下人的社會身份為依據,像君、臣、父、兄、妻、子等,體現的并不是平等的人類意識而是倫理意識。魯迅在小說里描寫的農民形象都是社會中的下層人民,甚至還有許多不幸者,對這些人魯迅給予了深切同情。魯迅在文中表達的同情不是自上而下的施舍,而是對人性的尊重。
“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向來是魯迅小說中表現的基本態度。他同情這些人物在宗法制度摧殘下的悲慘命運,但又無法接受他們逆來順受、安于現狀的奴性哲學。當這種習性走向極致,便會自然走上“自戳”或施暴者幫兇的道路。魯迅通過對小說人物悲慘遭遇的同情和憤怒,揭示出“人”之所以為“人”的重要特征。魯迅曾受過嚴復翻譯的《天演論》的影響,從生物學角度說明人與人之間并無多大差別,只是在社會學角度看,人類產生了不同的等級和類型。根據唯物主義觀點,人的第一性應是自然性,其次是社會性,人與人之間的平等才是大自然賦予人類的本質屬性。但中國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強調的倫理道德殘酷地壓制了人類的自然性,刻意追求社會性的畸形發展,這便導致了傳統文化思想中對“人性”的扭曲,形成了所見到的魯迅筆下那些農民形象。
在魯迅的作品中,多處提到“人”字。由此可知“立人”思想始終是魯迅做文的核心。兩千多年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儒家綱常倫理道德極大地壓抑了人類的靈魂,扭曲了正常的人性。魯迅固然一度對國民性現狀持悲觀絕望的態度,但并未從根本上對國民性的潛力乃至人性失去信心。他希望青年人在沒有被封建禮教毒害下健康成長,追求個性與自由。在對待民族文化上要以“拿來主義”的態度辯證對待他國文化。
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在其發展過程中都不可避免地帶有自身的劣根性,而只有正視本民族的問題,在借鑒外族文明的同時,對傳統文化進行批判、繼承,從而發展、弘揚優秀文化,這個民族才能是有希望的民族。
注釋:
①③⑥⑧朱棟霖.中國現代文學史[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②魯迅.且介亭雜文·寄周刊編者的信(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④魯迅.阿Q正傳(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⑤魯迅.藥(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⑦魯迅.故鄉(魯迅全集)[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
⑨李怡.魯迅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