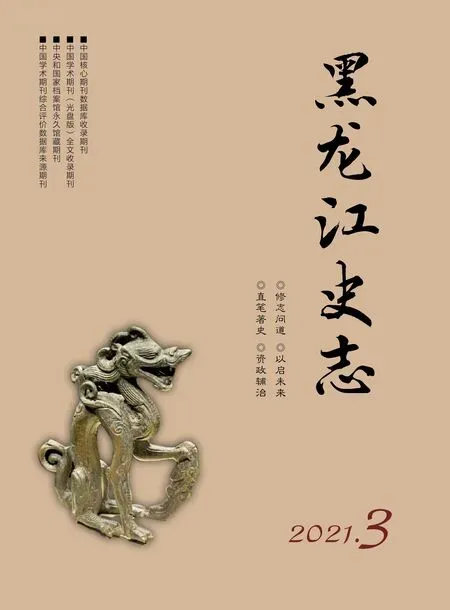學科建設視角下民國統(tǒng)計對年鑒的影響
徐佳佳
(江西省社會科學院 江西 南昌 330000)
清末民初,統(tǒng)計學隨著其他西方文化一起被傳入中國,并被快速運用在政府工作、學術研究和出版經營等各個領域,成為一門快速本土化且產生較大影響的學科。年鑒也在幾乎同一時間被傳入中國,并在發(fā)展的過程中受到統(tǒng)計學的廣泛影響。民國時期,統(tǒng)計學不僅豐富了本土年鑒的理論、為本土年鑒的編纂提供了方法論和資料,還為本土年鑒的發(fā)展提供了機構保障和人才,這些都促進了本土年鑒的發(fā)展。然而與統(tǒng)計學在1926 年就被南開大學納入教學課程,并于1931年在該校的經濟學院下設統(tǒng)計學系,統(tǒng)計學被中國高等教育體系認可不同,由于缺乏理論基礎、機構支持、法律保障,運用范圍較窄,傳播不廣泛等原因,年鑒學至今仍沒有建立起來。對這些問題進行深入思考,對于解決當前年鑒學科發(fā)展存在的問題,促進年鑒學的發(fā)展,具有一定參考價值。
一、民國統(tǒng)計學豐富年鑒理論
17世紀上半期,統(tǒng)計理論在西方得到快速發(fā)展,迎來統(tǒng)計發(fā)展的高潮,并被后人稱為“統(tǒng)計時代”。隨后統(tǒng)計學在西方各國不同學者的細分研究下,形成不同的統(tǒng)計理論流派,如德國凱特勒將概率論與國勢學等統(tǒng)一,形成“凱特勒統(tǒng)計思想”,而英國則以凱特勒的思想為基礎形成了數理統(tǒng)計學。統(tǒng)計學的不斷發(fā)展不僅對數學、經濟學等學科產生了影響,對歷史等人文學科也有較大沖擊,其中就包括中國的文史學科。1922年,梁啟超在東南大學史地學會作題為《歷史統(tǒng)計學》的專題演講,開啟了中國現(xiàn)代意義上的“計量史學之先河”,讓歷史的研究不再僅憑大勢觀察,歷史的事實、細節(jié)成為梳理歷史的重要新思路。在這種新的思路下,歷史被認為是一門可以被實證的科學。在梁啟超的倡導下,大量民國學者,如丁文江、郭斌佳、衛(wèi)聚賢、胡樸安、吳貫因、李則綱、翦伯贊、胡秋原等均在各自論著中呼吁將統(tǒng)計思維運用于歷史研究中。
正是在這種學術氛圍中,清末民初被引入中國的年鑒被民國歷史學界高度重視。在民國歷史學者眼中,年鑒是一種通過收錄大量歷史細節(jié),尤其是大量統(tǒng)計資料,能夠真實還原、記錄歷史的重要工具書。在西方年鑒傳入中國的過程中,較早組織翻譯西方年鑒的盧靖就曾在《新譯世界統(tǒng)計年鑒》序中介紹,“其所以不知比較之故,又豈不源于無統(tǒng)計。是故,統(tǒng)計年鑒者,合世界萬有之現(xiàn)象,條理而貫串之,放之則縮為一冊,不出戶庭而周知天下”。在他看來,年鑒是可以知曉天下大勢的工具書,而使得年鑒能夠有該功能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年鑒擁有大量統(tǒng)計資料,通過這些統(tǒng)計資料,能夠將歷史發(fā)展條理化、具象化,從而實現(xiàn)實證歷史的目的。在盧靖等早期年鑒學者的推廣下,《世界教育統(tǒng)計年鑒》《歐美教育統(tǒng)計年鑒》等大量的統(tǒng)計類年鑒被翻譯引進中國,成為史學界的重要參考書。而清末民初,統(tǒng)計類年鑒也逐漸成為中國本土年鑒早期發(fā)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種類。
到民國時期,年鑒發(fā)展過程中廣泛運用統(tǒng)計思維,并以此突出年鑒的存史功能成為一種普遍現(xiàn)象。《申報》經理史量才在《申報六十周年發(fā)行年鑒之旨趣》中介紹,“日報者,屬于史部,而更為超于史部之刊物。因之,本館與日報月刊之外,乃復有年鑒之編輯。以月刊輔日報,乃又益之以年鑒,俾日報月刊為經,年鑒為緯”。在他看來,年鑒是一種以年度為周期的史料,“結集各種統(tǒng)計,以供按索,為年鑒之職責。”在他看來,統(tǒng)計與眾不同的價值在于它更加真實、客觀,能夠用數字記錄社會歷史,“論時治史者得日報為之備載無遺,月刊為之征引提舉,而年鑒之統(tǒng)計史表,則又足以包舉日報月刊而增補其未能詳于旦夕經月之間者。合三事錯綜以觀之,庶足無掛漏之虞,繁瑣之患乎?”這種編纂思路被廣泛實踐于民國《申報年鑒》編纂中,成為《申報年鑒》編纂的重要理論基礎。
民國末年,隨著計量史學被廣泛傳播,年鑒中更為廣泛使用了統(tǒng)計思維。董顯光在《中華年鑒》1948卷序提出,“挽近以來,統(tǒng)計之學日昌,調查之術精進,舉凡國家建設之進度,社會變遷之軌跡,咸可藉數字表現(xiàn)其真相。而國內學術界亦一掃過去專重理論、競尚空談之積習,日益增強對于統(tǒng)計調查之重視。此種東鄉(xiāng),不僅為學術前途開朗之曙光,抑且為國家建設孟晉之征兆。……就后一點言:則結集資料,匯編年鑒,以供按索根據,實為協(xié)助促進利用之一種重要工作。”在他看來,統(tǒng)計的出現(xiàn)也讓年鑒在內的各項研究擺脫主觀的推斷,讓人們從大量的史料中能夠歸納出客觀真實的規(guī)律,更有說服力。因此在編纂年鑒時,他鼓勵運用統(tǒng)計思維,并期盼其成為推進社會發(fā)展的一項重要工作。
因此,從中我們可以大致觀察出民國年鑒發(fā)展的基本思路,即在民國時期隨著統(tǒng)計學的實證性被廣泛認可,史學界對統(tǒng)計思維逐漸接受,被學界認為是一種重要史料的年鑒更注重凸顯實證性和客觀性。因此,本土年鑒逐漸形成了以客觀材料,尤其是數據來記錄歷史的量化史學思維,大量民國時期的綜合年鑒將內容全、數據真作為年鑒質量的重要評判標準。
二、民國統(tǒng)計為年鑒提供方法論
清末民國時期,統(tǒng)計理論被廣泛運用,統(tǒng)計調查成為獲取信息的重要方法,普查和專項調查是當時最為重要的兩種統(tǒng)計調查方式。
普查最早在清末就被政府運用來推選各地議員人數以及開展全國人口調查,民國時期該方法也被繼續(xù)廣泛使用。專項調查則是針對某一專項內容開展的統(tǒng)計調查,由開展統(tǒng)計的機構制定調查表格、發(fā)放給各地,然后回收,通過分析這些表格,得出結論。民國政府內務部對于土地、警政、選舉、土木、衛(wèi)生、救濟等方面工作就專門制定過30多份表格,然后通過行政方式發(fā)給各級部門,填好后統(tǒng)一回收,并對回收的數據進行分析,從而得出統(tǒng)計結果。民國時期,工商部、農林部、教育部等政府部門也都根據各自需要開展了不同的專項統(tǒng)計調查。統(tǒng)計調查成為各級政府開展工作的重要方式。
因此,許多民國政府部門在編纂年鑒時也采用了開展專項統(tǒng)計調查為年鑒搜集資料。民國實業(yè)部在開展《中國經濟年鑒》編纂過程中,就是通過“令國際貿易局辦理分省調查”,即讓國際貿易局開展專項調查搜集資料;“而令本會作各種統(tǒng)計數字的搜集”,即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開展專項調查收集資料等辦法完成前期資料搜集工作。不僅如此,《中國經濟年鑒》的主編羅敦偉還展望了未來該年鑒統(tǒng)計工作的安排,“完成全國通訊網。……因此本部特令各省實業(yè)建設兩廳,市政府社會局及本部附屬機關,每處指派一辦理統(tǒng)計人員為本年鑒的通訊專員。今后關于搜集資料,當然有許多方便,或許今后也可以對讀者有較大的貢獻。”從中可知,實業(yè)部的年鑒編纂者對年鑒編纂中采用調查統(tǒng)計這一方法高度認可,并努力踐行。
同時,民國中國銀行總管理處在編纂《全國銀行年鑒》時,也廣泛采用調查統(tǒng)計這一方法。一方面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通過與各地的銀行相互配合,通過調查統(tǒng)計獲得了大量資料,“本鑒第二第三第九第十一等章系用印成之調查表格向各銀行直接征求之結果,所發(fā)表格,各銀行均能推誠相助,迅予填還,遇有疑難之處亦承詳為解釋,此為編者所不勝感激者。”另一方面,中國銀行還通過自身設在各地的銀行分支機構自主開展統(tǒng)計調查,“再各地金融機關均非逐年直接調查不可,如派員實地調查,實為經濟及時間所不許,幸本行分支行遍各省,乃利用各地分支行原有之通信網,舉行直接調查”。通過統(tǒng)計調查開展年鑒的編纂,是中國銀行能夠短時間內完成大規(guī)模年鑒編纂的重要方法。
除此之外,大量官方機構、民營出版機構在編纂年鑒時,也都大量使用了調查統(tǒng)計這一工作方法。如民國時期鐵道部在編纂《鐵道年鑒》,財政部在編纂《財政年鑒》均開展了大規(guī)模的統(tǒng)計調查工作。雖然受限于當時統(tǒng)計條件,存在統(tǒng)計方法不夠完善、各類統(tǒng)計調查存在表格設計不夠全面、調查取樣不夠廣泛的問題,但調查統(tǒng)計作為民國時期年鑒編纂廣泛采用的工作方法,讓年鑒擺脫了以往工具書、史書等傳統(tǒng)典籍編纂時過于依賴古籍整理、訓詁等傳統(tǒng)編校方式的局限,不僅提高了年鑒的編纂效率和水平,還將年鑒的編纂推進到一個新的歷史發(fā)展層面。
三、民國統(tǒng)計為年鑒編纂提供資料
民國時期,隨著統(tǒng)計思維在年鑒發(fā)展中地位凸顯,統(tǒng)計方法的普遍運用,大量的、各類型的統(tǒng)計資料紛紛入鑒。不僅統(tǒng)計年鑒收錄了大量統(tǒng)計資料,綜合年鑒也廣泛使用統(tǒng)計資料,統(tǒng)計資料成為民國年鑒的重要內容。民國政府實業(yè)部部長陳公博為《中國經濟年鑒》(1934卷)作序時介紹“中國經濟年鑒出版了,名義上是年鑒,實際上可以說是一部中國經濟全志。而且差不多完全注重統(tǒng)計數字”,主編羅敦偉還對此加以補充,“大半是圖表”。用統(tǒng)計資料來說明問題,配以部分研究文章和評論成為民國大量綜合年鑒內容設置的一種形式。
從內容方面來看,民國時期入鑒的各類統(tǒng)計資料,覆蓋面非常廣,既有大范圍的國勢統(tǒng)計內容,如人口、土地和國民經濟等,也有專項統(tǒng)計,如留學人口調查、各地勞工收入等。如民國北平社會調查部出版的《中國勞動年鑒》就收錄了大量勞動人數、薪資等方面的統(tǒng)計資料,鐵道部編纂出版的《鐵道年鑒》則收錄了大量鐵路里程、路線設計等方面的統(tǒng)計資料。
從來源方面來看,民國時期入鑒的各類統(tǒng)計資料,一部分來自政府部門已經公布的統(tǒng)計成果,如內政部編纂的《內政年鑒》1935卷中有大量內容來自政府統(tǒng)計成果,“本年鑒各篇所用數字及所附之統(tǒng)計,均以內政部統(tǒng)計司之統(tǒng)計結果為主”。《浙江經濟年鑒》1948年卷介紹“三、資料來源 各項資料之搜集,均由主管機關提供”。另外一部分來自各編纂機構為年鑒編纂自發(fā)搜集和統(tǒng)計的成果。如《全國銀行年鑒》1934卷至1937卷采用的大量統(tǒng)計資料就是來自中國銀行自己的統(tǒng)計成果。《全國銀行年鑒》1934卷第六章《銀行統(tǒng)計》介紹中國銀行的工作人員“根據第二章全國銀行總覽內之數字,制成有系統(tǒng)之比較表,凡關于全國銀行之資本,存款,放款,證券,發(fā)行,現(xiàn)金,公積金等,及各銀行之分支行數,從業(yè)人員數,各地銀行之分布數,一一加以統(tǒng)計。”
從內容加工程度來看,民國時期年鑒使用的統(tǒng)計資料既有一次文獻,也有經過反復加工的二次文獻、三次文獻。如《申報年鑒》1933卷收錄的《國際重要統(tǒng)計》,《申報年鑒》1944卷的“便覽”欄目收錄的《中國政府重要職員名錄》《國定紀念日表》等就屬于一次文獻。而《全國銀行年鑒》中的大量圖表則是經過加工的,如《全國銀行年鑒》1935卷就將全國銀行總覽內的數字,制成有系統(tǒng)之比較表,從各銀行的資本、存款、放款、政權、現(xiàn)金、公積金等方面進行詳細比較,“以供研究者一助”。
不過,民國的年鑒編纂者們在收錄統(tǒng)計資料的時候,總體上仍是審慎的,他們很敏感地意識到統(tǒng)計數據在條件局限時的不可靠性。羅敦偉就在實業(yè)部《中國經濟年鑒》1934卷續(xù)編序中介紹,“現(xiàn)階段的中國,如果要統(tǒng)計數字絕對真實可靠,當然是一件太不統(tǒng)一的事”,“如果用官廳公布統(tǒng)計的態(tài)度去編纂,老實說誰也不敢負這個責任,而且也不依樣畫葫蘆地去抄各官署的統(tǒng)計”。因此,對于來自官方的數據,中國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成員們要求“大半經過我們一番審核或者修改”。這種對待數據的嚴謹態(tài)度,使得民國出版的年鑒更為客觀、可靠,并沒有淪為一般性統(tǒng)計資料的匯編。
四、民國時計為年鑒提供組織、人才、法律支持
民國時期,本土年鑒有了較快發(fā)展,無論是數量和品類都遠超以往,成為我國近現(xiàn)代年鑒發(fā)展的一個高峰。這與各類統(tǒng)計組織、人才、法律提供的保障密不可分。
民國時期政府統(tǒng)計機構有了較快發(fā)展。從北洋政府到南京國民政府,1927年統(tǒng)計機構不僅更加完善,還成立了中央各院部會的統(tǒng)計機構,如實業(yè)部、審計部、海軍部等中央部門都成了統(tǒng)計機構,財政部所屬的海關、總稅務司等中央各部直屬機關也成立了統(tǒng)計部門,地方政府的統(tǒng)計機構也逐漸健全。1931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主計處的成立,使得全國統(tǒng)計機構有了最高機關,統(tǒng)計工作的規(guī)劃更加科學,工作的完成也更加高效。統(tǒng)計機構的完善便利了年鑒編纂工作。《申報年鑒》主編張梓生就認為,“年鑒之編纂,在一般調查統(tǒng)計之完備之國家,為事蓋至易易,顧非所論于今日之中國。中國地大物博,又值鼎新革故之秋,百端待理;統(tǒng)計調查之工作,有已臻完備,粲然可觀者,有粗具規(guī)模、未達一間者,有大端缺略、方在從事者,以之編纂某種專門之年鑒,或且綽乎有余”。
民國時期,本土年鑒快速發(fā)展,尤其是官修年鑒大量快速出版,與統(tǒng)計人才的協(xié)助有很大關系。如民國實業(yè)部在組織編纂《中國經濟年鑒》時依靠的工作人員大多是各政府機關的統(tǒng)計人員,這些人員“差不多每一個表、圖,甚至于一個極小的數字,都經過一番審慎的工夫”。同時,各統(tǒng)計學會、調查機構也為各類年鑒編纂提供了大量人才支持。如《申報年鑒》第二卷中的編者“翁文灝、曾世英”就來自北平地質調查所。
為了保障統(tǒng)計工作的完成,南京國民政府制定實施了大量法律,如《統(tǒng)計法》及《統(tǒng)計法實施細則》等。這些法律對于統(tǒng)計年鑒編纂和人員安排都有具體的規(guī)定,如根據統(tǒng)計法規(guī)定,主計處統(tǒng)計局應該按照全國統(tǒng)計總報告的內容,匯編《中華民國統(tǒng)計年鑒》,并呈國民政府核定后發(fā)行,各級地方政府也據統(tǒng)計法編纂各地統(tǒng)計年鑒。這些統(tǒng)計法規(guī)中涉及年鑒的部分,讓年鑒的出版有了相對剛性的約束,同時也從側面顯示了政府機構對于編纂統(tǒng)計年鑒這項工作的重視,這對于民國時期年鑒的推廣和發(fā)展是一種重要保障。
五、一個問題:統(tǒng)計學成為正式學科,年鑒學卻仍未建立的原因
雖然清末民國時期,年鑒受到統(tǒng)計學理論、方法論、內容以及各類具體編纂條件等方面的影響,但是年鑒學并沒有像統(tǒng)計學一樣,在民國時期就成為一門獨立學科,反而至今還在學科建設的路上。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幾個因素。
(一)統(tǒng)計學理論較為完善,年鑒學理論發(fā)展緩慢
年鑒在近代中國發(fā)展的軌跡與現(xiàn)代統(tǒng)計基本一致,都是西方傳入后本土化的新文化。但統(tǒng)計學在傳入中國之前,在西方已經形成體系,無論是理論還是實務,西方統(tǒng)計學都可以供中國統(tǒng)計借鑒。然而年鑒在清末民初被傳入中國時只有圖書編纂實務,并沒有配套傳播國外的年鑒理論。而這與西方國家長期將年鑒視為工具書或者文獻,并沒有形成較為系統(tǒng)的理論體系有關。因此,年鑒在中國本土化的過程中就缺乏現(xiàn)成的、可供借鑒的理論知識。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年鑒學要建立,只能依靠本土理論和實踐的滋養(yǎng)。但遺憾的是,建國后我國年鑒事業(yè)長期停滯,年鑒理論發(fā)展緩慢,至今尚未形成系統(tǒng)的本土年鑒理論體系。缺乏完整的理論基礎,年鑒學的建立也就進展緩慢。
(二)統(tǒng)計學應用廣泛,年鑒宣傳、普及和應用不夠
一個學科,除了豐富的理論能夠推動其建立和發(fā)展外,大量的實踐也可以成為其建立的動力。統(tǒng)計引入中國后,迅速在各個領域被廣泛使用,成為現(xiàn)代學術研究、社會發(fā)展必不可少的理論和方法。而廣泛地使用也使得統(tǒng)計學的成立更為必要。實踐發(fā)展如此重要,甚至在一些情況下,即便基礎理論稍顯薄弱,但如果有豐富的社會實踐及廣闊的市場需求,該學科也能夠順應時代發(fā)展建立起來。比如廣告學,它之所以能夠成為一門獨立學科,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廣告業(yè)的蓬勃發(fā)展。大量廣告的產生和使用,讓廣告的研究十分必要,也讓廣告學的建立具有現(xiàn)實緊迫性。而目前在各地高校備受關注的“輿情學”也是如此,在國外學科體系中并沒有輿情學,但由于國內社會發(fā)展的需要,這門學科在中國的建立成為現(xiàn)實。可以說社會經濟發(fā)展的需要,是促進相關學科建設的重要因素。當前,我國年鑒出版的數量雖然大幅增加,但年鑒的宣傳、普及和應用不夠,民眾對年鑒的認知有限,市場需要不強勁,年鑒的市場發(fā)展無法催生年鑒學。
(三)統(tǒng)計機構、人員、法規(guī)等配套逐步完善,年鑒發(fā)展的助力較少
民國時期,統(tǒng)計機構的完善,統(tǒng)計人員的任用、培養(yǎng),統(tǒng)計法規(guī)的頒布實施,乃至各類統(tǒng)計社會團體的蓬勃發(fā)展,各類統(tǒng)計學術會議的召開,《統(tǒng)計月刊》等各類有影響力的統(tǒng)計期刊的創(chuàng)辦,不僅讓西方的統(tǒng)計理論在中國得到廣泛地運用,影響力不斷增強,還讓西方統(tǒng)計在中國實現(xiàn)了本土化,讓統(tǒng)計真正成為一門可以被中國本土使用的學科。反觀年鑒,雖然在民國時期政府機構也逐漸開始認識到其價值,一些學者也認識到年鑒與方志的一些共通之處,一些出版機構也開始通過各類商業(yè)途徑介紹年鑒的功用,對年鑒進行普及,但是這些舉措總體上力度不大,產生的社會影響并沒有像統(tǒng)計一樣深遠。建國后我國年鑒發(fā)展又長期處于停滯狀態(tài),直到年鑒與方志在機構上的并軌,才讓年鑒的發(fā)展有了相對較為穩(wěn)定的機構保障。同時,雖然2016年12月22日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印發(fā)了《全國年鑒事業(yè)發(fā)展規(guī)劃(2016—2020年)》,對年鑒發(fā)展進行了總體規(guī)劃,但是這些條文缺乏約束性,效果也十分有限。而當前我國年鑒發(fā)展中重編纂輕理論研究,各類學術研究社團少,學術研究氛圍不強等這些都阻礙了年鑒的發(fā)展。因此,從統(tǒng)計學的快速發(fā)展中,年鑒工作者應當積極汲取有價值的經驗,為年鑒學的建立提供機構、人才、法律等方面的保障。
注釋:
1.唐麗娜,楊鎵萁.清末民國時期統(tǒng)計學的傳入與發(fā)展——基于對同時期204 本統(tǒng)計學術圖書的研究[J].統(tǒng)計研究,2021,(3).
2.王德發(fā).中華民國統(tǒng)計史(1912~1949)[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7:149.
3.石瑩麗.民國學界對于歷史統(tǒng)計學的認同與質疑[J].史學月刊,2015,(12).
4.[日]伊東佑轂編纂.世界統(tǒng)計年鑒[M].謝蔭昌譯.奉天學務公所1909年7月出版。該年鑒為謝蔭昌受奉天提學司使盧靖囑托翻譯。該引文為盧靖為《新譯世界統(tǒng)計年鑒》所作序言。
5.申報年鑒社.申報年鑒1932卷[M].上海:申報館特種發(fā)行部,1932:9.
6.李維民主編.中國年鑒史料[M].北京天宇星印刷廠印刷,2003年10月印刷。該部分引文為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政務委員兼新聞局局長董顯光為《中華年鑒》1948卷所作的序言。
7.民國實業(yè)部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1934)[M].北京:商務印書館,1934年7月第2版。此處引文為羅敦偉為該年鑒再版所作的序言“《中國經濟年鑒》再版序”。
8.民國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全國銀行年鑒(1934)[M].上海: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1934年出版,第6頁。該部分引文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為該年鑒所作的《<全國銀行年鑒>編制緣起及經過》一文。
9.民國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全國銀行年鑒(1934)[M].上海: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出版,1934年6月出版,第7頁。該部分引文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為該年鑒所作的
《<全國銀行年鑒>編制緣起及經過》一文。
10.民國實業(yè)部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1934)[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4:9。引文為陳公博為該年鑒所作的序言。
11.民國政府內政部年鑒編纂委員會.內政年鑒(1935)[M].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8。引文為時任國民政府內政部代理部長陶履謙所作的序言。
12.浙江省銀行經濟研究室.浙江經濟年鑒[M].浙江省銀行經濟研究室1948年7月出版發(fā)行,第11頁。
13.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全國銀行年鑒(1934卷)[M].上海: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1934:10.
14.中國銀行總管理處經濟研究室.全國銀行年鑒(1935卷),上海:上海漢文正楷印書局,1935:11.
15.民國實業(yè)部經濟年鑒編纂委員會.中國經濟年鑒(1934)商務印書館,1934年7月第2版,第15頁。此處引文為羅敦偉為該年鑒再版所作的序言“《中國經濟年鑒》再版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