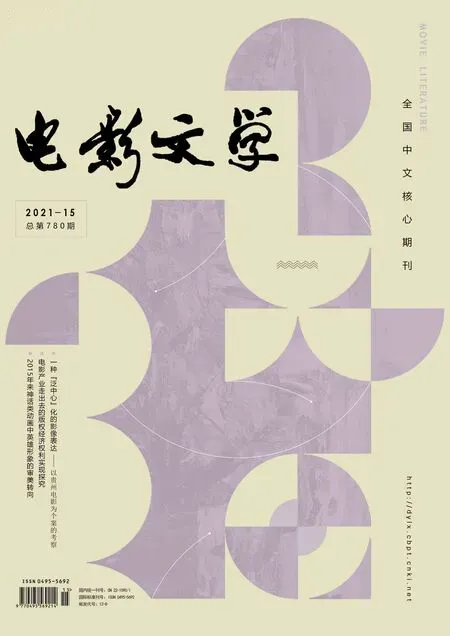少數民族電影信仰書寫的三副面孔
周韻淞 (廣西藝術學院影視與傳媒學院,廣西 南寧 530022)
從“十七年”時期走向新世紀,少數民族電影逐漸在“一體”之下進行著“多元”探索。越來越多的少數民族電影開始反思在現代化進程前,少數民族傳統信仰的生存與發展。這其中有從“他者”(The other)視角進行書寫的非本民族導演,也有從“自我”(Self)視角進行書寫的少數民族本族導演,不同文化背景的導演從不同視角對少數民族傳統信仰審視,并在大銀幕上以截然不同的方式進行著信仰書寫。本文選取了三部由不同文化背景導演制作的、在院線有一定影響力的少數民族電影,考察這些電影中不同的信仰書寫方式,并總結出不同的信仰書寫方式在銀幕上呈現出的不同文化樣貌,進而反思每種“信仰”書寫的不足之處,為少數民族電影信仰書寫的多樣性做出有益思考。
一、電影影像:一種信仰書寫的可能性
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André Bazin)在他的論文《攝影影像的本體論》中曾提出一種木乃伊“情結”(Complexe),他認為如果對造型藝術進行一次精神溯源,那么造型藝術的最初目的是“與時間相抗衡……人為地把人體外形保存下來就意味著從時間的長河中攫住生靈,使其永生”。而攝影機的賦能,讓人類有機會從時間長河中精準截取時間片段并再現在影像上。但對電影來講“形似”的追求是遠遠不夠的。巴贊進而認為偉大的藝術家“他們既能把握現實,又將現實融于藝術形式中,使兩種傾向主次分明”,這為電影藝術的更高追求指出了道路,即讓現實的影像成為藝術想象的材料,從客觀的影像中發掘更有意韻的真實。巴贊的理論闡明了電影影像基于現實,卻能進行“詩意”表達的可能性。而少數民族電影中導演們所想表達的“信仰”正是千百年來少數民族人民對于現實世界“詩意”的想象,電影影像由此擁有了信仰書寫的可能性。但“信仰”在現實中并無實體,電影中信仰的表達勢必是概念的生成和闡釋,是導演運用影像進行思想書寫的過程。所以,少數民族電影信仰書寫的基礎是少數民族自身所能提供的獨特影像言語,這種言語可以概括為以下幾方面:
(一)視覺符號
不同的符號體現著不同民族的文化內涵,一個符號的形成往往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電影影像作為一種能客觀記錄符號的工具,各式符號的直接呈現自然成為少數民族電影信仰書寫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服飾符號,丑丑導演的《阿娜依》《云上太陽》就著力展現了苗族婦女的服飾——窄袖、大領、百褶裙、銀飾等;又如環境符號,在展現草原民族的電影中就時常出現,電影《狼圖騰》中的大草原完美地表現出了“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的文化意象;再如建筑符號,少數民族電影中展現了土家族吊腳樓、蒙古族蒙古包、藏族碉房等。除此之外,少數民族電影的視覺符號還囊括了飲食符號、文字符號等。電影影像對于這些符號的客觀拍攝,記錄下了截然不同的民族生活方式,影像上直觀的差異體現出了少數民族地區不一樣的生活風俗,以及種種風俗后不一樣的文化構建。
(二)民族儀式
在少數民族電影中,民族儀式也是信仰書寫的一部分。在“十七年”時期的少數民族電影往往以“載歌載舞”作為電影結局,這種“載歌載舞”就是民族儀式的體現。但是這樣的影像由于過于強調少數民族人民獨特的歌舞,而忽略了儀式存在的原本含義。在西方文藝理論中,尼采的“酒神精神”、巴赫金的“狂歡理論”等都指出了儀式中蘊含著揮之不去的、潛意識層面的宣泄。所以電影中少數民族的儀式不僅是慶祝,也是他們信仰的體現。“在儀式過程中,少數民族電影通過姿勢、動作、舞蹈、歌唱等表演活動和服飾、頭飾、妝容等物件精心編排構建出一個具有特殊文化意義的儀式場景。”民族儀式成為民族信仰的影像載體,通過對儀式的展現,可以再現信仰的意義。
(三)民族語言
隨著以萬瑪才旦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導演出現,民族語言也成為少數民族電影體現民族信仰的方式之一。一個民族的語言有著不同的韻律韻調,一經翻譯或譯制就會失去了語言本身的獨特性,所以在對民族詩歌、詩詞進行誦讀時,語言的原生性就顯得尤為重要。電影中民族語言的使用在傳播時會形成一定的“文化折扣”(Cultural Discount)現象,但正如羅曼·英伽登(Roman Ingarden)所認為的:“當讀者積極地調動自己的想象以調補作品的不定點和空白,才能使作品不完備的意向性關聯物變成活生生的審美對象。”正是這種語言不理解帶來了與普通生活的間離感,讓信仰在電影中有了顯現空間。
二、少數民族電影信仰書寫的三種模式
少數民族電影創作中,較為常見的信仰書寫模式有三種,分別是“敘事—信仰”“奇觀—信仰”“生活—意象—信仰”。三種信仰書寫模式各有特點,又相輔相成,電影之中往往會混合出現。本文選取三部明顯帶有這三種信仰書寫模式的少數民族電影作為案例進行剖析。
(一)《尋找羅麥》:“敘事—信仰”模式
敘事,是電影的基本功能,也是信仰書寫最直接表達方式。在“敘事—信仰”中,信仰的存在是被直接訴說出來的,電影通過敘事告知觀眾有信仰的存在,卻不直接通過影像展現出來“信仰”具體是何物,從而讓“信仰”成為“缺席的在場”。傳統電影敘事學理論認為,攝影機制造了兩個空間:一個是“親影片的空間,即攝影機取景范圍內的場景”;另一個是“未表現的空間”。“敘事—信仰”中,電影故事存在于親影片的空間,但是想表達的信仰卻存在于未表現的空間,成為影片主人公的“欲望”,推動著主人公不斷尋覓它,從而完成電影故事的講述。
在影片《尋找羅麥》(2018)中,信仰成為存在于未表現空間的“欲望”:正是由于它的存在,羅麥撞死青年之后,認為只有去西藏才能洗滌身上的罪惡;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趙捷才認為羅麥在西藏并沒有死亡,而要去尋找他;正是由于它的存在,趙捷才要將撞死青年的項鏈留在西藏。所有劇情的展開,都是導演關于信仰的設定——去西藏就能得到救贖。正如王超導演在采訪中所說:“西藏是個有靈的地方,什么都有可能發生。在藏傳佛教的宗教意識下,西藏之旅是有靈之旅。趙捷不相信羅麥死了,他的不相信很真誠,人心誠了,在西藏這個地方,不管是幻覺還是夢境,都是有可能性的。”《尋找羅麥》正是王超導演的“有靈之旅”,作為整部電影的掌控者,他將個人對于西藏信仰的崇拜作為整部電影的終極意義,但是他并不知道這種信仰到底從何而來,所以他只能將信仰的表達放在影片之外的“未表現空間”之中,讓主人公羅麥不斷地去尋找。
電影中獨自奔赴西藏的趙捷看到了布達拉宮,聽到了藏歌,看到了辯經,最后還參加了藏戲表演,在藏戲中趙捷終于看到了羅麥的面龐,由此他認為羅麥沒有死亡。在影片的最后,羅麥通過藏戲演員的“附身”完成了“轉世”,成為影片中對于信仰的終極表達,給“尋找羅麥”的故事畫上句號。但是這樣的影像書寫并沒有真正描繪出信仰是什么,相反,這樣的“附身”只是單純地表達出趙捷精神恍惚的狀態。信仰顯然不是電影中羅麥的“看見”,相反,“信仰”的生成應該是在歷史、權力、文化中不斷建構的。電影《尋找羅麥》中的信仰,是導演先驗默認的信仰,是“他者”視角下的信仰訴說,通過“敘事—信仰”這一模式,電影概念性地闡述了一種形而上的信仰觀念,最后卻只能在趙捷精神分裂式的尋覓之旅中表現出來。
(二)《狼圖騰》:“奇觀—信仰”模式
新世紀以來,少數民族電影不斷探尋更廣泛傳播的方式,其中“奇觀化”成為許多少數民族電影創作者較為通行的理念。不少導演借助“奇觀化”影像進行信仰表達,形成了“奇觀—信仰”的書寫模式。在電影《狼圖騰》(Wolf
Tote
,2015)中,導演讓·雅克·阿諾(Jean Jacques Annaud)借助優良的攝影裝備、CG特效以及馴狼等方式,在電影銀幕上打造出了一片“奇觀化”的草原:在這片草原上狼成為最聰明生物,它們會花費好幾個月的時間去圍捕一群黃羊,會運用雪窩去冷藏黃羊的尸體,還會有組織地報復人類……電影中畢利格老人常常將狼與成吉思汗、木華黎做比較,認為這些古代將領的智慧是學習了草原狼捕獵的戰術。導演通過“人化”草原狼的行為邏輯,從而賦予草原狼人性,讓電影中的草原狼呈現出與真實世界中狼的“異質性”,由此草原狼成為電影中的“狼圖騰”。本片除了對于蒙古族“狼”信仰的書寫,還有對“騰格里”——“天”信仰的書寫,在“奇觀—信仰”的書寫模式下,“騰格里”首先是作為一種奇觀呈現,在陳陣與畢利格談起他逃出狼群時,他說:“我逃出狼群后,看到天上有一個東西,好像一張笑臉。”畢利格回答道:“當然,你看見的是騰格里。”“騰格里”仿佛是草原的主人一般,草原上所有生靈的因果都由它起、由它終。“騰格里”這一蒙古語成為電影人物對話中的“奇觀”符號,成為草原上的人們都不自知的服從的符碼,進而讓觀眾產生神圣感,信仰由此開始滲透。誠然,電影天生就有著記錄“奇觀”功能,美國芝加哥大學學者湯姆·岡寧(Tom Gunning)認為對于異國風情的記錄,讓早期電影擁有了獨特的吸引力,由此形成一種“吸引力電影”(The Cinema of Attractions)。“奇觀—信仰”正是透過影像“奇觀”的神秘性,營造出一種信仰氛圍,這本質上是基于現實與影像的二元對立,體現出來的是安德烈·巴贊認為的繪畫作品中的“異質性”。
綜上而言,“奇觀—信仰”本質是靠影像本身進行信仰書寫。電影中的“奇觀化”影像所形成的“陌生感”讓影院觀眾產生了一種“間離效果”,這種“陌生感”讓觀眾面對電影內的少數民族世界時處于一種“無知”狀態,從而生成一種與電影內人物一致的敬畏感,所以說“奇觀—信仰”的書寫模式形成的“信仰”更像是對影像(或影像內容)的敬畏。
(三)《氣球》:“生活—意象—信仰”模式
“敘事—信仰”和“奇觀—信仰”模式都從“他者”視角出發對信仰進行了想象式的書寫。但是何謂“信仰”,“信仰”何為?這一問題并沒有真正解決。隨著以萬瑪才旦為代表的少數民族導演開始拍攝本族電影,出現了從“我者”視角下對少數民族信仰的書寫,電影《氣球》(2020)正是如此。
于少數民族導演而言,信仰不是奇觀,而是生活的一部分。電影《氣球》中,以《敕勒歌》為代表的中國傳統文化里草原的浪漫意象被祛魅:牧羊是藏民們必需的生活,羊兒養得肥壯只是為了賣更好的價錢;尼姑妹妹香曲卓瑪雖然神秘,但是電影中她依舊受世俗情感的困擾;卓嘎面對藏族靈魂轉世的信仰和計劃生育政策兩者間的矛盾,陷入生與不生的問題等。這些現實問題都讓《氣球》中的民族元素去“奇觀化”,成為生活的一部分。導演不再是要展現奇觀,而是要講述生活。
但生活如何書寫信仰?這就要將日常生活意象化,賦予生活以宗教意義,從而對信仰進行書寫。在《氣球》中“氣球”這一意象就貫穿整部電影,電影中氣球的呈現方式有兩種:其一是避孕套做的氣球,這一個氣球代表了現實對信仰的阻力,意義是“不生”;其二是影片結尾的兩個紅氣球,紅色代表了生命的誕生,而影片最后紅氣球飛向天空,和爺爺靈魂轉世形成了呼應,其中一個氣球還沒有飛出就破了,另一個則慢悠悠地飛向了遠方。飛走的紅氣球在一組蒙太奇段落中被每一個人都看見,仿佛這個飛上天的紅氣球是每個人心中隱隱的信仰,飄飄然地在遠處游蕩。在兩種氣球的意象沖突下,是“現代文明下的規則和秩序”與傳統信仰的對抗,這樣的信仰書寫模式在現實生活的場域中展開,不是“缺席的在場”,也不是“奇觀”的影像。
除了“氣球”,萬瑪才旦還喜歡在電影中運用“羊”這一意象符號,在《氣球》中“羊”成為生育的載體。卓嘎用借來的種羊比喻自己的丈夫;卓嘎去醫院檢查時,窗外拴著的小羊暗示了卓嘎被縛的命運;卓嘎懷孕的時候,她做了一個夢,夢見了“咱家這只母羊,產了只羊羔,濕漉漉的”。西藏人之所以注重羊,是因為他們自古以來就有羊崇拜,萬瑪才旦導演將羊符號化,賦予它以信仰意義,從而讓觀眾感受到金巴一家信仰的深沉。
三、少數民族電影信仰書寫的文化意義
信仰書寫是當代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的應有之義。縱觀中國少數民族電影的創作歷程,許多電影都記錄下了少數民族特有的文化傳統,但無論是歌曲舞蹈,還是祭祀儀式,抑或是民族服飾,這些都只是文化的表象。一種文化的形成,不單是物質層面的,還是精神層面的,少數民族文化中現有的所有文化表象,最終都是他們對于生命和自然的思考,并在歷史的更迭中滲透在現實層面,成為我們現在能夠看見的文化符碼。而這種對于天地萬物、生死輪回思考的結果,最終升華為他們獨特的信仰,少數民族電影中信仰書寫的目的不僅在于證明他們存在過,更在于證明他們思考過。
信仰書寫體現了少數民族導演在現代化進程前對傳統民族信仰的反思。少數民族信仰的形成是“少數民族在人與自然物我不分的觀念中,形成的對自然與生存環境獨特的感受模式”。但是隨著現代化的推進,少數民族地區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生活質量得到極大改善,生存問題已經演變為了面對物質生活的極大豐富,傳統信仰何去何從的問題。對少數民族人們而言,信仰是一種生活方式,是在自我約束中保持靈魂的純凈。所以在萬瑪才旦的電影中,信仰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斷受到挑戰,主人公對信仰的掙扎更深刻地闡釋了信仰為何物。在這樣的書寫方式下,導演和觀眾討論的是信仰存在的問題,是信仰在現實世界留下的“痕跡”而非“敘事—信仰”和“奇觀—信仰”的模式下,將信仰看作先驗的、神秘的、能救贖萬物的存在。
信仰書寫有助于少數民族電影“共同體敘事”創新與發展。新時代少數民族電影肩負著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民族團結,保障國家統一的歷史使命,中國電影導演應該主動去探討和闡釋少數民族的信仰內涵,以藝術的提煉,去粗取精,真實、客觀、真誠地對民族信仰進行書寫,以動人的故事、真摯的情感讓少數民族故事成為中國故事,讓更多的觀眾去觀看少數民族電影。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少數民族電影的創作已有歌舞之美、服飾之美、建筑之美、生活之美,而下一步就是要對這些“美”進行升華,進行信仰之美的影像表述,從而與影院觀眾形成情感共鳴。
結 語
近年來,少數民族電影創作熱情越發火熱,創作質量也有明顯提高,但是在院線并沒有取得很好的票房,這是值得引起思考的問題。也許對創作者而言,應該進一步探索少數民族電影吸引觀眾的地方,而不是自覺延續已有的創作傳統。本文所探討的信仰書寫不同于好萊塢電影“真、善、美”的普世價值觀,而是少數民族人民心靈和現實的多重思考,是中華民族對于自然生存思考的痕跡。在電影中正確地理解且書寫出來信仰內涵,有助于更緊密地聯系中華民族的內在聯系,從而打造更緊密的共同體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