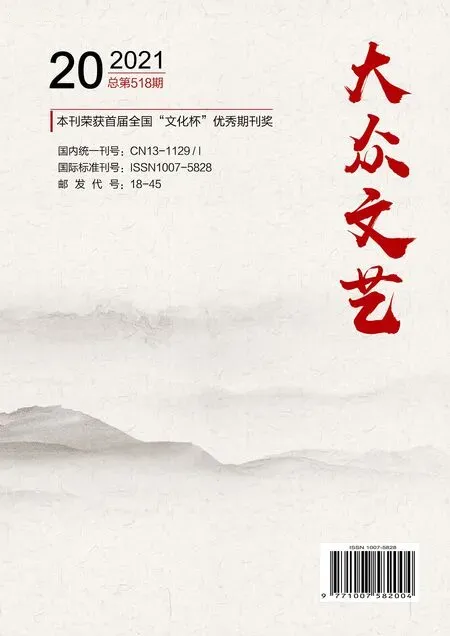論梁實(shí)秋對(duì)五四文學(xué)進(jìn)行批評(píng)的不足之處*
于 惠
(蘇州大學(xué)文正學(xué)院,江蘇蘇州 215000)
梁實(shí)秋受到美國(guó)學(xué)者歐文?白璧德的影響,經(jīng)常在自己的文章中抨擊以盧梭為代表的浪漫主義文藝思想,推崇古典主義文藝觀。梁實(shí)秋還曾以古典主義文藝觀的立場(chǎng)審視五四新文學(xué),寫(xiě)就了《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之浪漫的趨勢(shì)》《“五四”與文藝》等文章。其對(duì)五四新文學(xué)的指摘雖然在某些方面具有合理性,但也存在著諸多不足。
一、對(duì)接受外國(guó)文學(xué)影響的認(rèn)知存在的偏頗
梁實(shí)秋批評(píng)五四文學(xué)不加理性選擇地接受了外國(guó)文學(xué)的影響,認(rèn)為其存在完全否定中國(guó)文學(xué)傳統(tǒng)、變成外國(guó)式文學(xué)、隨意翻譯國(guó)外文學(xué)作品等問(wèn)題,導(dǎo)致其呈現(xiàn)出缺乏理性節(jié)制的浪漫主義混亂。五四文學(xué)確實(shí)受到外國(guó)文學(xué)的影響,但是梁實(shí)秋對(duì)該影響的具體認(rèn)知存在偏頗。
首先,五四新文學(xué)雖然具有反傳統(tǒng)傾向,但并未完全排拒中國(guó)的文學(xué)傳統(tǒng)。《小說(shuō)月報(bào)》就曾在改革宣言中坦言:“中國(guó)舊有文學(xué)不僅在過(guò)去時(shí)代有相當(dāng)之地位而已,即對(duì)于將來(lái)亦有幾分之貢獻(xiàn),此則同人所敢確信者”,積極肯定了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學(xué)的地位及作用。王元化先生談及五四文學(xué)時(shí),認(rèn)為其否定的是“貴族文學(xué)”,但對(duì)包括山歌等在內(nèi)的中國(guó)傳統(tǒng)民間文化是持推崇態(tài)度的。
其次,五四新文學(xué)汲取西洋文學(xué)影響因子的同時(shí)也打上了中國(guó)烙印,因而沒(méi)有變成外國(guó)式文學(xué)。如《孔乙己》《阿Q正傳》等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毫無(wú)疑問(wèn)受到了果戈理等作家的影響,但這些作品寓于形象建構(gòu)中的依然是中國(guó)科舉、禮教等封建制度戕害人性的深層意蘊(yùn)。
再次,梁實(shí)秋認(rèn)為五四時(shí)期翻譯外國(guó)文學(xué)采用無(wú)目的態(tài)度全憑個(gè)人喜好的論斷,可能針對(duì)個(gè)別譯者對(duì)某些作品的翻譯具有適用性,但以此抨擊五四時(shí)期所有的文學(xué)翻譯陷入任性縱情的“浪漫混亂”不免有失偏頗,因?yàn)樵S多的五四文學(xué)翻譯是較有目標(biāo)有標(biāo)準(zhǔn)的,即是較有梁實(shí)秋所推崇的“理性”的。譬如五四期間易卜生的《國(guó)民公敵》《玩偶之家》等劇作被率先翻譯介紹到國(guó)內(nèi),主要是譯者因?yàn)榉捶饨ǖ目剂慷M(jìn)行的理性選擇。文學(xué)研究會(huì)推崇“為人生”的文學(xué)作品,因而基于此標(biāo)準(zhǔn)精心譯介了莫泊桑、安特列夫、高爾基等作家的作品。
二、對(duì)“抒情主義”的批評(píng)存在的偏頗
梁實(shí)秋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之浪漫的趨勢(shì)》中以古典主義文藝觀之立場(chǎng),批評(píng)五四新文學(xué)呈現(xiàn)情感泛濫的浪漫主義特征,認(rèn)為其充斥著缺乏理性節(jié)制的“抒情主義”,從而導(dǎo)致了文體種類混雜、充斥情感及欲望的頹廢主義文學(xué)的產(chǎn)生。若置于五四文學(xué)實(shí)踐中進(jìn)行觀照,上述觀點(diǎn)明顯有失偏頗。
首先,梁實(shí)秋以古典之有色眼光較為偏激地為五四新文學(xué)貼上“抒情主義”的標(biāo)簽,卻忽視了五四文學(xué)作品中的理性思維特征及議論、敘事等藝術(shù)表現(xiàn)特征。就詩(shī)歌而言,五四期間的確有《鳳凰涅槃》等抒發(fā)情感的佳作,但也不乏偏于理性的作品。沈從文評(píng)價(jià)聞一多的詩(shī)集《死水》是“理智的靜觀的”,就在于其中的許多作品在結(jié)構(gòu)安排、情感把握上顯現(xiàn)出了一種理性節(jié)制的美。談及五四時(shí)期的小說(shuō),其的確有《沉淪》為代表的側(cè)重情感表達(dá)的作品,但也不乏理性思考人性、社會(huì)的“為人生”小說(shuō)、“問(wèn)題小說(shuō)”等。另外,從藝術(shù)表現(xiàn)特征層面看,五四文學(xué)作品不僅有“抒情”,還有議論、敘事等。梁實(shí)秋曾經(jīng)將康白情的《草兒》詩(shī)集中的詩(shī)歌分為抒情詩(shī)、敘事詩(shī)。由此我們可以窺見(jiàn)梁實(shí)秋觀點(diǎn)的矛盾性,更可以發(fā)現(xiàn)五四詩(shī)歌不只有抒情的藝術(shù)表現(xiàn)特征。因而梁實(shí)秋對(duì)五四文學(xué)充斥著“抒情主義”的判斷并不是客觀、全面的。
其次,梁實(shí)秋較為狹隘地認(rèn)為“抒情主義”導(dǎo)致的文體種類的混雜,破壞了各種文體之間的界限,卻忽略其豐富五四文學(xué)文體的可能性。梁實(shí)秋基于古典主義文藝觀的立場(chǎng),認(rèn)為不同文學(xué)體裁的界限是分明的,各自具有獨(dú)特鮮明的特征,即詩(shī)歌創(chuàng)作應(yīng)該以抒發(fā)情感為正則,小說(shuō)應(yīng)該側(c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故事情節(jié)的編織等。以此為依據(jù),梁實(shí)秋認(rèn)為五四文學(xué)中彌漫的“抒情主義”使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充斥著不加節(jié)制的情感,模糊了小說(shuō)與詩(shī)歌的界限,并對(duì)五四文體種類的混雜進(jìn)行了批評(píng)。梁實(shí)秋的這種觀點(diǎn)明顯存在局限性,因?yàn)榛谖膶W(xué)體裁發(fā)展的考量,五四時(shí)期出現(xiàn)的抒情性小說(shuō)擴(kuò)展了新小說(shuō)的創(chuàng)作空間。周作人關(guān)于小說(shuō)創(chuàng)作可以抒情的相關(guān)觀點(diǎn),以及《沉淪》等顯現(xiàn)強(qiáng)烈主觀抒情性的小說(shuō)作品的成功創(chuàng)作,就是最好的例證。
再次,梁實(shí)秋抨擊五四時(shí)期的“抒情主義”導(dǎo)致文學(xué)陷入了缺乏道德的“頹廢主義”,卻忽略了這些作品的深層意蘊(yùn)及價(jià)值意義。受古典主義文藝觀的影響,梁實(shí)秋認(rèn)為優(yōu)秀的文學(xué)作品能夠彰顯出情感、欲望受到理性制約的道德性,由此批評(píng)五四文學(xué)放縱情感、欲望的“頹廢主義”。從其《文人有行》等批評(píng)文字可以看出,他所講的“頹廢主義”文學(xué)主要指郁達(dá)夫發(fā)表的《沉淪》《南遷》等“墮落”“不道德”的作品。梁實(shí)秋對(duì)郁達(dá)夫的這些作品的評(píng)價(jià)顯然并不是中肯的,因?yàn)殡m然從表面看這些作品包含著赤裸裸的情欲甚至變態(tài)心理的描寫(xiě),但透過(guò)表層深挖其意蘊(yùn),我們發(fā)現(xiàn)它們并非純粹肉欲的低級(jí)趣味的展示,而是以嚴(yán)肅態(tài)度借助暴露情欲反映社會(huì)、人生,在表達(dá)五四青年個(gè)性解放后內(nèi)心苦悶的同時(shí),對(duì)殘酷現(xiàn)實(shí)、黑暗社會(huì)進(jìn)行了控訴。因而郭沫若、周作人等人才對(duì)這些抒情小說(shuō)給予了高度評(píng)價(jià)。
三、對(duì)抨擊印象主義批評(píng)存在的偏頗
梁實(shí)秋在《現(xiàn)代中國(guó)文學(xué)之浪漫的趨勢(shì)》等文章中,以古典主義文藝觀之視野,認(rèn)為五四時(shí)期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完全根據(jù)的是批評(píng)者的性情、印象,因而抨擊其是極端的浪漫主義并徹底否定這種文學(xué)批評(píng)方法的價(jià)值。梁實(shí)秋對(duì)印象主義批評(píng)的認(rèn)識(shí)及評(píng)價(jià)顯然是有失偏頗的,主要體現(xiàn)在以下三個(gè)方面:
首先,梁實(shí)秋未能注意到印象主義批評(píng)的多元視野。梁實(shí)秋基于古典主義文藝觀的視野,認(rèn)為應(yīng)該以健康倫理化的人性作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唯一的判斷標(biāo)準(zhǔn),從而抨擊了五四時(shí)期缺乏固定標(biāo)準(zhǔn)而進(jìn)行主觀鑒賞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但是梁實(shí)秋囿于古典主義立場(chǎng),指出的缺乏客觀評(píng)判標(biāo)準(zhǔn)等弊端,其實(shí)恰恰顯現(xiàn)出了印象主義批評(píng)的寬廣視野。印象主義批評(píng)的代表人物周作人就認(rèn)為文學(xué)批評(píng)需具有“寬容”視野,沒(méi)有放之四海皆準(zhǔn)的真理性衡量依據(jù),應(yīng)該側(cè)重于文學(xué)批評(píng)的自由個(gè)性,強(qiáng)調(diào)只堅(jiān)持自己的衡量依據(jù)為唯一判斷標(biāo)準(zhǔn)而視其他為異端是文學(xué)批評(píng)視野不“寬容”的表現(xiàn)。正是基于此文藝寬容觀,周作人才力排眾議,為在當(dāng)時(shí)遭到許多人批評(píng)的《蕙的風(fēng)》《沉淪》等作品辯護(hù),有力地保護(hù)了新生力量的成長(zhǎng)。反觀梁實(shí)秋,其堅(jiān)守的古典主義文藝觀使他形成了不“寬容”的文藝批評(píng)視野,因而有時(shí)會(huì)對(duì)文學(xué)作品的價(jià)值難以作出客觀正確的評(píng)價(jià),比如對(duì)郁達(dá)夫的《沉淪》做出了“頹廢主義”的論斷。
其次,梁實(shí)秋忽視了印象主義批評(píng)能夠彌補(bǔ)當(dāng)時(shí)盛行的科學(xué)式批評(píng)的不足。五四時(shí)期的社會(huì)批評(píng)等科學(xué)式批評(píng),因?yàn)槠鹾狭松鐣?huì)改革、思想啟蒙等時(shí)代主潮,而受到當(dāng)時(shí)許多人的推崇。具有理性特征的科學(xué)式批評(píng)雖然能夠?qū)ξ膶W(xué)作品進(jìn)行邏輯性較強(qiáng)的分析、判斷,但卻往往未能立足文學(xué)文本展開(kāi)研究。而印象主義批評(píng)能夠?qū)⑽膶W(xué)本體放在首要位置并使其成為批評(píng)的落腳點(diǎn),通過(guò)直觀感悟從整體上對(duì)文學(xué)文本進(jìn)行審美把握,品味其獨(dú)特的藝術(shù)魅力及審美風(fēng)格,顯然形成了對(duì)科學(xué)式批評(píng)之弊端的有力糾偏。因而,印象主義批評(píng)彌補(bǔ)了科學(xué)式批評(píng)的不足,也豐富了五四文學(xué)批評(píng)的園地,但是梁實(shí)秋卻忽略了此點(diǎn)。
再次,梁實(shí)秋簡(jiǎn)單地將印象主義批評(píng)視為浪漫主義變種的觀點(diǎn),實(shí)質(zhì)上陷入了對(duì)五四文學(xué)思潮的認(rèn)識(shí)狹隘化的境地。梁實(shí)秋以其古典主義文藝觀認(rèn)為文學(xué)批評(píng)的主要方法和文學(xué)的主要類型無(wú)非分為古典的與浪漫的兩種,因而將與古典主義相背離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納入浪漫主義,并視其為浪漫主義的變種。梁實(shí)秋的這種劃分方法,其實(shí)顯現(xiàn)出了其對(duì)西方文學(xué)思潮尤其是五四時(shí)期文學(xué)思潮的狹隘化認(rèn)識(shí)。縱觀西方文學(xué)思潮,主要有古典主義、現(xiàn)實(shí)主義、浪漫主義、現(xiàn)代主義等,梁實(shí)秋提及的“主要”有古典、浪漫兩種文學(xué)思潮顯然是錯(cuò)誤,或者說(shuō)是不全面的。再來(lái)看五四文學(xué)思潮,西方的各種文學(xué)思潮在五四期間如潮水般涌入中國(guó),而且歷來(lái)許多學(xué)者就五四的主導(dǎo)文學(xué)思潮是現(xiàn)實(shí)主義還是浪漫主義等問(wèn)題爭(zhēng)論不休,這些都足以表明五四時(shí)期的文學(xué)思潮是多元的。梁實(shí)秋認(rèn)為五四文學(xué)整體上呈現(xiàn)浪漫主義的傾向,并進(jìn)而簡(jiǎn)單地將印象主義批評(píng)劃為浪漫主義的觀點(diǎn),顯然是有悖于五四文學(xué)實(shí)際情況的。
四、結(jié)語(yǔ)
綜上所述,梁實(shí)秋對(duì)五四文學(xué)的接受外國(guó)文學(xué)的影響、“抒情主義”、印象主義批評(píng)的抨擊,存在著諸多不足。究其原因,梁實(shí)秋對(duì)古典主義文藝思想的偏愛(ài),使其一葉障目,將與強(qiáng)調(diào)主觀情感、個(gè)性自由的浪漫主義有某些相似處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等都納入浪漫主義進(jìn)行批判,認(rèn)為五四文學(xué)彌漫著“抒情主義”、五四時(shí)期的印象主義批評(píng)是極端的浪漫主義等,從而忽視了印象主義批評(píng)在豐富五四文學(xué)批評(píng)及彌補(bǔ)科學(xué)式批評(píng)的不足等方面的作用,也忽視了五四文學(xué)并未全盤(pán)否定中國(guó)文學(xué)傳統(tǒng)、其所認(rèn)為的五四文體種類混雜的意義等。晚年梁實(shí)秋漸漸意識(shí)到對(duì)古典主義的偏執(zhí)限制了其思維,并進(jìn)行了真誠(chéng)“自省”,“我對(duì)于一切事物的衡量難免不有成見(jiàn)……在大體上我一向是被拘囿在理智的范疇之內(nèi)……不過(guò)我近年來(lái)的態(tài)度有一點(diǎn)改變了……有許多事靠了理智恐怕永久也不能了解……藝術(shù)品的格調(diào)原不必統(tǒng)一劃齊,其中可以有各種各樣的格調(diào)”,在“自我檢討”中想必他也意識(shí)到了其對(duì)五四時(shí)期接受外國(guó)文學(xué)影響等方面的批評(píng)是有失偏頗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