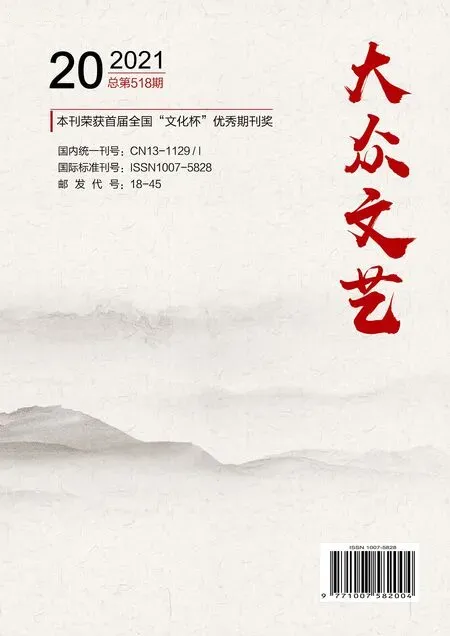“非遺”視域下荊楚民間繡活研究述評
曾婉雲 馮澤民 葉洪光
(武漢紡織大學,湖北武漢 430079)
民間繡活是“以普通布料做繡地,采用刺繡、拼貼、縫制等方法,主要制作日常用品的傳統手工藝術”,這是陳元玉在《“非遺”視野下民間繡活的多維度探究》(2020)一文中首次給出的明確定義。在此之前,以“民間繡活”為題的論文均沒有嚴格定義。依據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項目評選對于“民間繡活”的范圍限定,“荊楚民間繡活”包括荊楚地區入選非遺名錄的所有項目。因此,部分學者將漢繡和黃梅挑花也作為“民間繡活”而論,僅僅是研究視域的不同,不能認作謬誤。
陽新布貼和紅安繡活作為民間繡活被列入2008年的“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另有兩項省級非遺包括2011年公布的第三批項目民間繡活(咸豐縣、宣恩縣土家族苗族繡花鞋墊)和2019年公布的第四批拓展項目民間繡活(大冶刺繡、堂紡疊繡、荊州民間刺繡),共涵蓋了六個子項目。學術研究大多以子項目為研究對象,只有少量論文將“民間繡活”作為整體進行綜合研究。
一、文化內涵研究
馮澤民(2011)探究了荊楚民間挑補繡的共性特征。他將黃梅挑花、陽新布貼和紅安繡活三者結合起來,最早提出“刺繡家族”的概念,認為黃梅挑花是挑繡的代表,陽新布貼是補繡的典型,紅安繡活是以平繡為主的多種繡法相互配合的產物。在此基礎上,王欣(2016)通過比較漢繡、紅安繡活、黃梅挑花和陽新布貼的楚文化同源性,統稱為“荊楚刺繡家族”。“荊楚刺繡家族”生動概括了荊楚地區眾多刺繡項目的文化內涵。
文化內涵研究可從地域環境和人文風俗兩個角度切入。陳元玉(2020)從地域環境的角度解釋了荊楚民間繡活的楚文化淵源,認為湖北陽新、紅安與江西新余三地形成了以楚文化為基礎的吳楚文化積淀區,繡活的地域藝術符號特征鮮明。楚文化的變化發展深刻地映照在荊楚地區的民間繡活上。另外,民間繡活不僅是一項民間流傳的傳統手工藝,還是一種潛移默化的民間文化。馬嬌(2017)從紅安的人文風俗入手,認為紅安人對生命的樸素觀念反映在紅安繡活的圖案紋樣和豐富色彩當中。她從文化角度解讀紅安婦女的創作心理,分析紅安繡活的圖案寓意,只有熟知紅安本土文化才能夠準確把握。
二、藝術特征研究
荊楚民間繡活的藝術特征研究包括造型藝術、色彩搭配和審美語言。探討造型藝術和色彩搭配,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更為生動。胡淑娟(2019)將陽新布貼與延川布貼進行比較,認為陽新布貼的線條稍顯頓挫,其原因在于陽新繡娘的造型未經雕琢,而延川繡娘有成熟的剪紙造型基礎,因此延川布貼畫的線條較流暢。除了有相似之處的研究對象,還可以選取藝術特征截然相反的研究對象進行比較。張其增(2019)將陽新布貼與日本的青森碎布比較,認為陽新布貼的圖案更復雜多樣,青森碎布沒有具體圖案,僅以幾何色塊組合而成,創作隨意度更高;前者色彩更豐富,色彩對比強烈,而后者只有單一藍色調,但層次過渡更豐富。經過比較研究,陽新布貼的藝術特征更加深入人心。
探討審美語言,需要實地考察和多方印證。陳元玉(2013)認為民間繡活選用的素材寓意豐富,直接或間接地反映人們的心理狀態。這一觀點與民間藝術專家們所推崇的“圖必有意,意必吉祥”一說有相通之處。他認為民間繡活的寓意傳達途徑并不限定在圖案的選取上,還可配合相應的物品,比如咸豐、宣恩土家族苗族的繡花鞋和繡花鞋墊往往作為定情信物出現。若沒有親身接觸實物,與手工藝制作人深入交流,難以發掘它們的審美語言。
三、工藝技法研究
專門研究工藝技法的論文較少,部分刺繡項目更無人涉足。紅安繡活的工藝技法十分豐富,光是繡法就有二十余種。王芙蓉在2016年發表的期刊論文《湖北陽新布貼的制作工藝研究》圖文并茂地闡述了陽新布貼的工藝流程,就制作過程中遇到的問題進行分析,并提出解決方案。但是,她的實踐案例與傳統意義上的陽新布貼關系不大,不具代表性。紀陽(2016)和呂妍欣(2016)都從絲繡(或“線繡”)、絨繡和挑繡三大類介紹了紅安繡活的技法,后者比前者費的筆墨更多。紀陽對工藝的研究是概述式,而呂妍欣更注重分析。后者偏向對選材用料和常用工具的介紹,其中對空白鞋墊的制作流程記錄較為詳細,對工具和針法的描寫缺乏系統性。而馬嬌(2017)較為詳盡地記錄了紅安繡活的十五種繡法和五種鎖邊技法,并通過拍照和手繪的方式將步驟圖完整地展示在表格中,內容淺顯易懂,可作為初學者的入門手冊。
四、設計應用研究
荊楚民間繡活的設計應用研究包括案例研究和實踐研究。案例研究包括服裝設計、包裝設計、室內設計以及文創產品設計開發等。葉靜(2016)和陳瑞蓮(2018)都闡述了我國傳統刺繡手工技藝在國內外女裝設計上的應用案例。但是,“我國傳統刺繡手工技藝”與“民間繡活”是前者包含后者的關系,而且我國的刺繡項目十分豐富且風格各異,僅僅因為它們和民間繡活都屬于“傳統刺繡手工技藝”,就被用作應用研究的案例,是否有些牽強?我們不妨轉變思路,往上尋求整個刺繡行業的普遍案例,不如往下深入挖掘自身的優勢和特點,或者橫向拆解成具體元素進行應用研究。比如馬嬌從場合和對象兩個方面來闡釋紅安繡活的應用,曹瓊將陽新布貼拆解成“布貼元素”研究國內外的應用情況。
實踐研究主要與具體產品相結合,研究其設計應用的可行性。比如昌儀琳、龔怡慧、高媛媛和匡睿穎分別從童裝、兒童布藝玩具、文創產品和美術課程教具等方面來探索陽新布貼的設計應用。他們都考慮到了傳統的陽新布貼主要運用于兒童群體的社會根源,積極探索其融入現代生活的路徑,具有借鑒意義。
五、傳承發展研究
文獻調研發現,每個刺繡項目的研究內容有半成以上是以“傳承發展”收尾。說明傳承發展對于荊楚民間繡活的重要性,亦是非遺研究的目的和歸宿。傳承發展研究包含了“品牌化發展”和“生產性保護”和“可持續發展”三個議題。其中,“品牌化發展”和“生產性保護”是所有刺繡項目都需要面對的議題,而“可持續發展”是陽新布貼所特有的。
殷海霞(2012)最早研究荊楚民間繡活的生產性保護策略。她認為陽新布貼需要塑造品牌,實現產業化發展,同時搭建行業交流平臺,拓寬營銷渠道。“品牌化”是包括殷海霞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提出過的傳承發展策略,事實證明,這是實現傳統手工藝長足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產業化”需有度,應該注意平衡經濟利益和社會效益,保存其“優質基因”。陳元玉(2014)概括性地將荊楚民間繡活的“優質基因”歸納為手工制作、工具材料的原真性、制作工序的原生態、圖案的寓意性和產品生活化等五個要素。其中“制作工序的原生態”注定了荊楚民間繡活的“產業化”不像其他產業那樣擴展得越大越好,需要以保護為首要原則,有限度地產業化,建設良好的傳承發展環境。因此,學者在探討產業化發展的同時,應該強調產業化是一把雙刃劍,過度的產業化反而會損傷傳統手工藝的“優質基因”。
依據陽新布貼在廢舊材料再利用方面的特性,引申出“可持續發展”的概念,適應時代發展的需要。趙靚(2013)認為綠色環保的設計理念與陽新布貼“物盡其用”的傳統觀念不謀而合,初步提出陽新布貼也可以構建可持續發展模式。而郭可濰(2021)專門探討了陽新布貼與可持續性相結合的問題。她立足于自身的研究實踐分析了非遺傳承可持續性的促進機制,證明了陽新布貼實現可持續傳承的可行性,具有現實意義。但是文中存在可持續發展模式套用的痕跡,也是可持續相關議題普遍存在的問題。
六、結論
通過對荊楚民間繡活六個研究方向的梳理發現:文化內涵和藝術特征的研究尚有進一步挖掘的余地;工藝技法研究雖然珠玉在前,但是缺乏系統化闡述;設計應用研究存在案例研究牽強附會的問題,轉變思路即可找到出路;傳承發展研究應當客觀分析“產業化”對刺繡項目的利弊,妥善使用這把“雙刃劍”;非遺項目陽新布貼的可持續傳承研究需要避免模式套用,進一步立足于個體特征來講可持續傳承。梳理荊楚民間繡活研究的現狀和問題,可為后期研究提供參考,對今后荊楚民間繡活的相關研究具有積極意義。